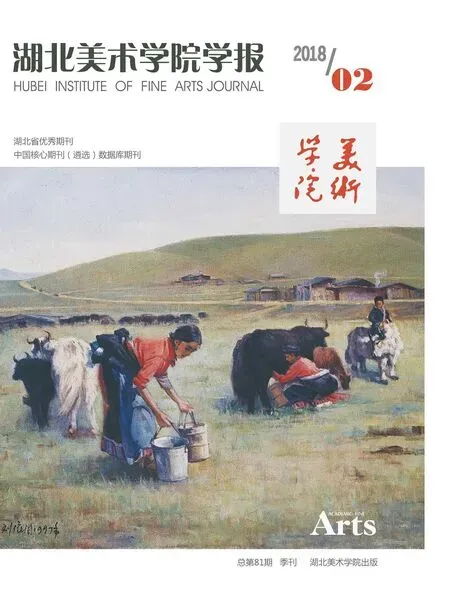个体价值与文化身份
——女性艺术家李青萍解读
韦俏勋
一、引言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中,李青萍是少有的从民国一路走来,毕生坚持艺术创作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对于一个几经沉浮、身负荣誉与污名的艺术家而言,对于一个心头烙满时代的创伤,情感的缺失、在时代浪潮中欲展现自身而不得的女性而言,绘画成为帮助李青萍承受痛苦、宣泄对生命的热爱和愤恨的依仗,这使得她比以其他女性艺术家走得更远,使得她的经验渗出语言之外,使得艺术成为表现她自身更有力的字句。
女性和艺术家作为李青萍身上两个最重要的身份特征,成为理解其艺术的全新视野:她的艺术生涯是否因其女性身份而蒙受打击或得到优待?她的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出独特的声音,并将女性这一群体的独特经历灌注于画面中?她又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女性”与“艺术家”这两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相互排斥的身份的?
二、艺术才华的隐与显
女性身份对于李青萍而言是个含义特别丰富的主题:入行和早期的成功发端于社会对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肯定,但女性与艺术明星的相互交缠导致其艺术生涯的阻断,也消解了身上的锐气,转化为对于艺术世界的持续探索。
40年代以前,李青萍的艺术进路似乎没有因其性别而蒙受损失。顺利进入上海新华艺专学习、海外教学中顺利举办画展并出版画集、回国后多次举办画展声名大振、被日本文艺界誉为“中国画坛第一娇娜”。她的作品得到较高地位的艺术家的指点和认同,使其才情得以在更大、更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涌现。徐悲鸿成为李青萍早期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指路人,来自名家的评价和赏识进一步提升李青萍的知名度。
然而,40年代以后多次身陷囹圄的经历证明,明星与女性身份相互绾结,使她的艺术行为遭到严重质疑。1946年9月,李青萍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并以“汉奸嫌疑”起诉。审讯的提问意味深长[1]:“这几年中来来去去,是否与人相共?又在此兵荒马乱中怎样生活?”“有人检举,你曾拜储民谊为干爹?”“否则(指不拜干爹)不容易跑来跑去。”问讯大多集中在对女画家经济独立和自由方面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女性成就的双重道德评价:在接受男女平等观念的同时,社会仍以家庭价值的视线作为女性终身成就的标准,因此这样一个衣着时髦、社交频繁的女性的成功或许得益于不为人知的暧昧隐私。可见,新旧交替的社会地位和男权主导的政治秩序相互加持,本能地排斥女性超越男性艺术成就的可能性。
和女性艺术家多湮没于家庭俗务中的趋势不同,李青萍终身未嫁且笔耕不辍,时代造成的厄运赋予她对于精神世界的持续关注,获得异乎寻常的表现力。创作于1984年的《我的天地》,深邃混沌的背景上空同时存在两个月亮,似乎在暗示画家当时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孑然一身、渺小无依,偏安于自己的小世界中也许更为安全。1952年后,李青萍先后因拒绝参加“镇反”被遣反、因“重大特务嫌疑”被拘捕,从此展开了二十余年靠捡破烂和卖水为生的生活。她通过从垃圾堆捡来的广告颜料在废旧杂志上持续作画,如所作《戏剧人物》,用当时常见的红色颜料在杂志封面作画足见她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在李青萍的艺术生涯中,女性身份似乎并非始终发生作用。但她遭受的种种苦难都在说明,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对女性发展和行为的怀疑,造成了其艺术发展的转折。因此,女性这一身份先是隐性的存在,而后变成一个包袱,最后也成了台阶。
三、女性特质的可见与不可见
回到艺术实践本身,李青萍的作品中是否流露出女性的特质?她本人对女性身份有何认识,又作何反应?一批数量可观的画作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她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向往,成为对于两性关系的隐晦表达。与此同时,日记随笔中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解释了其作品中试图淡化女性标签的另一种努力。
1.可见:婚姻与家庭的两性隐喻
40年代及之后的牢狱之灾和政治因袭,使李青萍疏离于感情生活,终身未嫁没有孩子的经历使她陷入情感身份的僵局,并始终对这种身份和关系好奇不已,情感的缺失使她尝试通过艺术去理解和表达爱的具体形态。以下将分为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两部分进行论述。
在李青萍的作品中,身体被抽象成流动的存在,脱离了具象的束缚,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紧密依靠、互相慰藉和平等的关系。《二人情》以自由的笔触、强烈的色彩和极具冲击力的构图呈现出男女情感中相互依恋密不可分的状态,由黄、绿、红的形、线、点组成的背景与中央充满动态感的红、绿线条和谐并置,似相互缠绕的两股火焰,其中人脸依稀可辨。画面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效果,画家对于爱、自由、依恋的情绪穿行其中。同类作品还有《伴侣》《拥吻》等。婚姻是爱情在更高的原则下的锤炼和巩固,对此李青萍有着自己的思考。《婚礼》是一场盛大婚礼的记录,画面中女子的修养和姿态毫不逊色于身旁男子,画家对女子服饰和姿态相对细致的描摹,不仅透露出对于美满婚姻的艳羡,也可视为平等自由等女性意识的表征。另一幅《婚礼》将艺术家的认知和观念表现得更为明显,色彩成为渲染画面情绪的重要手段。下方大红色涂抹,几笔若有若无的黑色刮蹭似是人形,目光向上,墨绿色平涂与下方构成平衡感,一松一弛形成动静张力——喜庆与压力并存,和谐与未知接踵而至。更有意味的是,这种色彩和构图间的内在冲突在画家的“留白”中得到了缓解和释放,中部不作色直接透出木板的原色使画面更为透气,使画家的情绪铺写表现出一种节奏性。
“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以继后世也,固君子重之”(《礼记·昏义》),两性结合不仅是当下个体生命的事,还勾连着延续未来子胤的人伦内涵。这种内涵影响着李青萍,孩子成为她母性表达的土壤和诱因,呈现出她作为女性,期待家和事兴、子孙环绕的传统的一面。《天伦》中深色背景之上成人围绕构筑出的堡垒,为孩子开辟出安全自由的成长环境,选取明度更为柔和的红色,犹如温床凸显画家的柔软,寥寥几笔勾画的白色人形杂陈其间,使整个画面热闹且充满希望。同类作品还有《儿孙绕膝》,围绕母与子主题进行的创作将画家对亲子关系的理解表达得更为彻底。
李青萍在艺术中构筑了自己两性身份、家庭身份的种种可能,折射出对爱情和亲情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型的画作表现的是画家对宜室宜家、生育的希望,而非她作为个体的自我价值,体现出李青萍思想中根植于心的传统家庭观念。
2.不可见:消解身份的另一种努力
李青萍的日记随笔和部分作品中,透露她的男女平等观念甚至淡化女性身份的倾向。
她在日记中写道“对国家有贡献,至少不做社会的寄生虫,要做女中典型的先行者,男女都是社会的建设者[2]。”相信男女平等,进入社会接受教育,有职业、经济独立,李青萍像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寻求成功的机会,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代替以往家庭价值的实现作为终身成就的标准,这可能是我们在她的有些画作中几乎不能通过作品辨认其女性身份的原因。40年代齐白石先生评价“青萍画”时说:“李青萍小姐画无女儿气。”30年劫难使李青萍的绘画转向一种“粗糙”的表现手法,从她对色彩的把控和运用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超越女性细腻、柔软的一面:其一,她能在很小的画幅中表现出很大的气势,如《相逢在南洋》,扁长笔触上下延伸拉大画面的纵向视觉空间,符号化的人形因为不同的设色和姿态生动感人,在红、绿、黄的碰撞之中,李青萍留下了空间,增加了画面的节奏感,从而增大了作品的张力。其二,李青萍通过深浅、刮擦、涂抹等方式,能用简单的色彩或同一颜色构成层次丰富的画面,《朝圣者》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条件所限,画家仅有黑白二色和极少的红色油彩,却能在一块做鞋帮的布料上描绘出一群行走在阴阳两界的人,表现出对生的渴望以及自由的向往。
3.可见与不可见:女性群体的记忆与超越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吴静在李青萍艺术展研讨会上说道:“李青萍所走过的路是20世纪很多女性所经历的共同道路,民国解放的整体构架就是从维新、辛亥、五四一路下来,西方的平等观念逐渐进入了民国女性的事业,她们既被唤醒,又在自身的泥沼当中挣扎得更加痛苦,所以矛盾在她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李青萍坚持下来了,因为她对生活和艺术形式的选择是非常果决的,一生把艺术奉为生命,在那个时期的女性艺术家甚至是所有画家当中都是不多见的。”[3]
作为为数不多的从民国一路走来的女性艺术家,李青萍是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延续。民国时期第一代女艺术家(如潘玉良、蔡威廉)注重人物表情、心绪和精神气息的捕捉与勾勒,“为现代女性美术提供了一种表达图式”[4]。此后,涌现出关紫兰、丘堤、郁风等一批女画家,以不同于唯美、细腻的表现性、精神性和极具辨识性的个性化画风驰骋画坛,却也都因为家庭或时代的原因最终退出艺术舞台。50至70年代对女艺术家,甚至新时代女性这个群体而言,都是一个曲折迂回,自我怀疑的时代,包括文学界的张爱玲在内,女性文艺从业者的女性身份遭到了最大程度的质疑,也造成了大批艺术家艺术生涯的断裂,或是寻求更为安全的表达方式。高度一统化体制下的小心翼翼、不得自由对80年代“文艺解放”后的创作也造成了影响,导致李青萍画面中始终笼罩的忧伤压抑气质。
与此同时,“女性表达开始进入自觉自为的新阶段”[5],“跟着感觉走”的李青萍更是如此,线条、用色、笔触日渐老练大胆。这在90年代的作品中更为明显,她笔下的人物和《自画像》,通过色块的组合,形成纷繁厚实的色调效果,强调色彩作为一种表现语言的作用,暗示着她属于30年代奠基的现代艺术根基,呈现出与同样活跃于八九十年代的年轻艺术家(如喻红、陈淑霞等)不同的发展路径。
此外,苦难——这一贯穿李青萍一生的主题,成为她的独特性所在:正是因为经历并跨越了绝大多数女性艺术家从未受到的挫折,她的艺术表现出超越性别的强烈的情绪感和表现力。她的画面中灰调子、深蓝、紫、棕等颜色经常出现,常常伴随着一个踽踽独行或茕茕孑立的人形,犹如李青萍的人生写照。劫后重生的李青萍,长期压抑的创作欲望被释放,仿佛打开了抒情的闸口,她把与苦难交往的被动和主动都体现在画面上,代表作品有《超脱》《天问》《祈祷》等。以《舞者》系列为例,消除人物的个体特征,黄色笔触简单勾勒的更像是游荡在混沌中的灵魂,看似随意的构图实则置入了复杂的心理内容:人物围绕无所依,或振臂或颔首,构成了李青萍自身经历中的不同感受——时代苦难中艺术阉割的郁结、义愤与沉默。对生活发自肺腑的热爱和焦虑,使画面有了气象和血色。
可见,时代认同与否定、自我认同和坚持的复杂纠缠,显示出李青萍艺术的一种特殊形态:早年在时代潮流中习得平等意识,凭借丰富的表现力淡化女性的标签;被人遗忘之后又被人记起,仍然在千人一面的时代大潮中保持自我的身影,但顾影自怜、向往家庭婚姻的心境通过画面不时流露。同时,李青萍超越政治形态和自身性别局限的艺术坚持,使李青萍的艺术表达即使在个人被摒弃的时代也固执地进行超越性别的艺术探索。
四、结语
女性和艺术家两种身份在李青萍身上到底有怎样的联系?
首先,女性身份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对艺术生涯的阻力上。从李青萍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历中,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成功对女性审慎的离间,或者那种女性艺术家的成功,最终无可避免地陷入男性权威所带来的质疑的事实。虽然李青萍早年的艺术生涯看似一帆风顺,但如今人们重新记起和研究其早期艺术的论据,总离不开她与男性艺术家交往的经历和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性艺术家的介入,对于女性艺术家的脱颖而出,以及作品的保存和流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诚然,李青萍作品中的女性阴柔内倾特质,和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主题会不时流露,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两性关系的俯首称臣。李青萍自身的追求,彰显在笔触的处理和立足现实与想象对色彩的洞若观火,集体陷落下固执己见的追求、更体现在她将艺术家身份贯穿始终的坚持中。因此,女性身份在李青萍艺术中的可见与不可见,反映出李青萍独自叩门探索艺术中的困惑,和对困惑的反复咀嚼,这让她的艺术和价值在美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当囊括性别因素作为一种艺术分析范畴时,我们难以回避女性身份与李青萍经历之间的暗合,以及作品泄露出的对此身份的接受和反思,和她从中不断确认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文化身份的努力。以上论据没有哪个能单独充分论证女性身份对其艺术的重要影响,或断言李青萍是一位具有突出女性意识的艺术家,但它们加在一起的粘结与疏离就足以提示,不能忽略女性身份的影响力;同时也提示着,通过性别因素考察艺术进路,成为探索李青萍艺术中一条具有启发性的路径。
[1]尚辉. 青萍残影—李青萍艺术展言谈会会谈纪要[M]//黄德泽. 冷月下的求索:李青萍画评.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56.
[2]李青萍. 青萍日记九[M]//林阳. 李青萍画集.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244.
[3]尚辉. “青萍残影——李青萍捐赠作品展”学术研讨会[J]. 美术文献,2015,(09):94.
[4]姚玳玫. 画谁?画什么——从自画像看民国时期女性西画的图式确立[J]. 美术观察,2011,(03):104.
[5]姚玳玫. 自我画像——一条贯穿共和国60年女性美术的叙述脉络[J]. 美术,2011,(0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