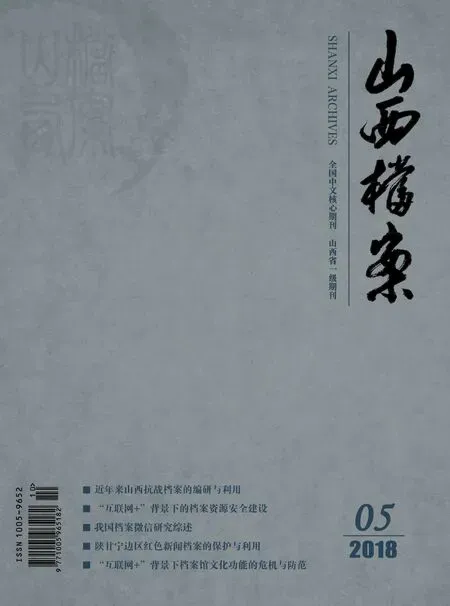汾河中游地区庙会经济功能的变迁
庙会举办的定期化和进一步繁荣,有赖于一定的商品经济条件,即民众利用难得的机会添置家用,解决生产和日常生活所需。于是,庙会逐渐具有了特定的经济功能。在以传统农耕文明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体的前提下,庙会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进行有限度的商品贸易和规范生产秩序。在市场经济时代,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庙会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丰富民众生活和刺激消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庙会,已经起到充实当地经济结构的作用。
一、传统农耕社会庙会进行商品贸易和规范生产秩序的功能
汾河中游是山西庙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地方史料显示,太原﹑清徐﹑太谷﹑文水﹑交城﹑平遥﹑介休﹑灵石等地的民众,每年从正月开始,可以成群结伴“逛”的庙会几乎隔三差五就有一个。以文水县和太谷县为例,文水县在光绪年间有82个庙会,太谷县在民国时期有57个庙会。一些重要的集镇甚至一年有多个庙会。庙会主要分布在每年的正月到十月。届时,城乡人们扶老携幼,上香祈愿﹑还愿,看戏游玩,走亲访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变迁,在休闲娱乐之外的商品贸易的功能得到了体现,赶集添买家庭日用成为庙会期间的主要景象之一。
(一)商品贸易的功能
汾河中游的城乡社会,参加庙会被称为“赶庙”或“赶会”。这类称呼也是到庙会市场买卖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小镇更是如此。不少县志中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祁县,三月二十八日,“县西北五里中岳庙会,货物杂集,远近游人争相贸易。四月八日,祁城紫红各有汤王庙会,如中岳云”[1]。因此,乡镇庙会多且密集。庙会期间,民众从四面八方齐集庙会,购买日常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太谷县,“阳春会上十分热闹,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坛不可胜数”[2]。沙河村会庙会日期是正月二十一日,“村民于里庙祀神演剧,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3]。庙会调剂民众日常所需的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汾河中游庙会的商品贸易情况直接影响到会期的长短。庙会的市场辐射范围大,会期就长;辐射范围小,会期就短。长者可以持续一个多月,单短者可能只有一日,如太谷沙河村正月的庙会就有大﹑小之别。
清代至民国,汾河中游地区民众趁着庙会拖儿带女置办生产生活日用品的现象广泛存在。究其原因,主要与境内市镇网络不发达有密切关系,这与江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南属于我国各级市场体系比较完备的地区。江南庙会比较突出的是娱乐功能。与之相比,汾河中游的庙会,商业贸易的功能则体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有商业街的存在,只有靠近城镇或交通相对发达的居民对于庙会的依赖才相对低一些。这些地方的人们,赶会的时候凑热闹的成分多于交易的成分,庙会的娱乐功能要强于商品贸易的功能。
(二)规范生产秩序的功能
汾河中游部分区域相对发达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使庙会具有规范生产秩序的重要功能,即庙会期间祭祀各类神灵的过程中,也体现着对农田灌溉水资源进行分配的权利。晋祠周围村庄持续性的庙会是典型代表。
在祭祀的过程中,对水资源具有支配地位的村庄具有特殊的位置,而其中具有支配权力的核心人物就是 “渠甲”——渠长和水甲。渠长和水甲的职责是规范管辖区域内用水秩序,具有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之权。晋祠周围村庄的渠甲人员总数151名。每当庙会举办之时,渠甲就是庙会盛大祭祀活动的主持者。这种公众场合的特殊角色既具有广而告之的作用——宣告其权威性,又使他们具有了神圣的职责——必须公平分配水资源。为了保证渠甲的权威性和公平性,产生渠甲时就要求“充应渠甲者为善良,不愆不忘”。渠甲一旦产生,报县府存案后,就成为农业生产中分配水利资源的合法指挥者。
二、市场经济时代庙会市场交易与消费的功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时代,各地庙会的举办恢复正常,历史上已经停办的庙会得到恢复和扩充。一年四季,庙会遍布城乡社会。1985年的文水县古庙会,从农历正月开始,月月有庙会,全年共有153个。
(一)市场交易的功能
各个庙会不仅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而且在赶庙逛市中完成主要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的购买,庙会的市场交易功能得到加强。太谷县和清徐县的东怀远村﹑西怀远村在每年的娘娘庙会上,商铺和摊点林立,各路商家﹑摊贩大约有上百户,交易的商品种类齐全,虽然它们大多是中下层消费者需要的中低档生产生活用品,商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但结实﹑耐用﹑价格便宜,能够满足村民生活生产需要。这里既有卖铁锹﹑锄头﹑镰刀等工具的摊位,也有卖菜刀﹑砂锅﹑塑料盒等生活用品的摊位,还有卖玉米籽﹑豆籽﹑瓜籽等种子的摊位。更多的摊点则直接定位为买卖儿童消费品,如贴画﹑四驱车﹑玩具手枪﹑遥控车﹑遥控飞机﹑拼图﹑魔方﹑跳跳床﹑台球和各样儿童图书等。现代便利的交通使十里八乡的人们纷纷赶庙会﹑凑热闹,东瞅瞅,西看看,挑选适合自己的各种商品。各地庙会的商品交易总额成倍增长。
进入21世纪,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交通越来越便捷,市场经济的活力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体现。城乡民众尤其是乡村居民通过进城购物满足家庭所需的愿望很容易实现,加上农民进城或外出务工机会增加,通过庙会解决家用的问题变得不再如过去那么迫切和必要了,庙会市场交易的功能正在不断弱化。
(二)消费功能
在庙会市场交易功能弱化的同时,庙会的消费功能却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人们逛庙会期间的文化娱乐消费和走亲访友﹑迎宾待客等方面。
汾河中游地区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方面主要是传统戏剧表演。这项活动是庙会主办方集资进行的公益性质的大众文化消费项目。庙会期间能不能请得起戏班子直接折射出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太原北郊区的横渠,2015年农历七月传统庙会期间,所辖范围内驻有的各类企业和个人纷纷出资,共18.5万元,请到的戏班子连续演出十余场。但有些地方却因为集体经济困难出现有庙有集而无戏的情况,如2015年太原南郊晋祠附近的花塔村和清徐县徐沟的丰润村,即是如此。
三、新常态下庙会充实经济结构的功能
近年来,山西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亮点。数据显示,继2014年保持23.5%的较高增速外,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省旅游总收入达到460亿元,又比上年同期增长18.6%,远远高于GDP增速。其中的节日旅游已经成为城乡社会生活的新常态。处于汾河中游的晋中市,更是在全国率先实行一周4.5天工作﹑2.5天休息的安排,鼓励城市居民利用节假日﹑休息日走出家门,融入各种类型的城乡文化旅游活动中。这说明,国家倡导的大众旅游新时代已经来临。
就全国旅游市场来说,民俗文化旅游正在焕发生机,乡村旅游也在持续升温。庙会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既是得到传承的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贴近城乡生活﹑具有多重功能的传统项目。如果地方政府借助人们的故乡情怀,努力引进新的发展思路,庙会便会成为各地市县经济结构的有效补充,即实现庙会丰富人们生活﹑增加地方旅游收入的双重功能。
汾河中游的部分庙会,已经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中体现出重要性。卦山﹑绵山﹑晋祠﹑傅山文化园﹑双塔﹑动物园等庙会是突出的代表。这些庙会已经基本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以“逛”城乡庙会为突出内容的旅游经济结构类型,实现了以传统节日旅游经济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新常态。同时,通过节日庙会介绍﹑宣传了山西的悠久历史文化,庙会旅游成为当地政府向内向外宣传的靓丽名片。
“十三五”期间,山西把发展文化旅游列在非煤产业之首。数量庞大的城乡庙会正是城乡旅游中的一个个宝藏。尤其是卦山﹑绵山﹑晋祠等具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庙会,应该成为大众旅游时代的一个重要领域,需要挖掘潜力,加强辐射力,由地方政府进行文化整合,打响文化招牌,招商引资,围绕核心文化元素发力,实现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庙会在文化产业化中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总之,庙会是汾河中游历史上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地域特色文化。在历史上曾经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不同的经济功能。今天,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乡民俗旅游已成新常态,庙会文化应该在新时代占据特定的位置,不仅要体现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功能,还要在充实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地方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