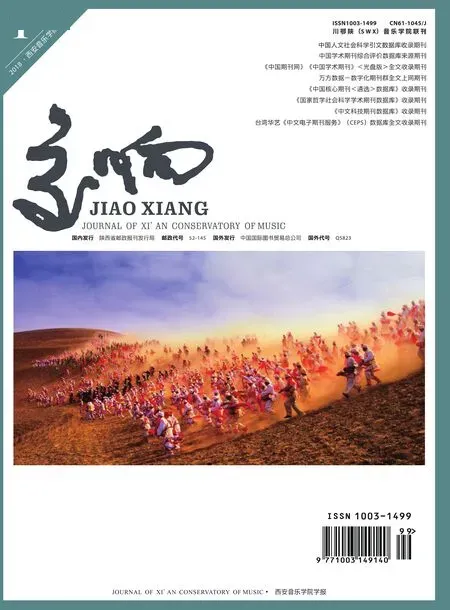论儒家文化与筝乐情趣的交融
●贾阳果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一、儒家文化精神与古筝艺术情趣中的交融
“‘文化’一词,在中国传统中本是一个动词,最早在《易经》中表述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的是人文精神的化育生成功能。”[1]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精神对古筝艺术情趣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古筝艺术题材、艺术审美和古筝艺术所体现的民俗意识中都影响至深,其崇尚正道气节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贵和观念和乐观知足与重视礼俗的观念在古筝艺术情趣中都留有抹不去的痕迹,足以呈现出儒家文化精神与古筝艺术情趣的交融与审美。
(一)崇尚道义气节与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
儒家文化提倡注重人格操守,崇尚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在儒家看来,强调人的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人要为国家、集体、家庭整体着想,而不是为己私欲谋福利,人要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重义轻利观。孟子曾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生,亦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理想产生冲突,要选择后者,要舍生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种志士精神在孟子那里就变成了“我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正是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高贵品格。这种高贵品格荀子称之为“德操”,“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有了这种操守,就能“素其位而行”,“人不知而不愠”,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和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有了刚毅自强,就能“中天下而立”,有着铁肩担道义的气概,有着敢于抗拒外侵、坚守气节、精忠报国的社会历史使命感。
筝曲《临安遗恨》是作曲家何占豪于1992年创作的协奏曲,乐曲取材于传统乐曲《满江红》的旋律素材,以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为创作基点。整首乐曲表现了民族英雄岳飞被奸臣所害,无法精忠报国,在狱中痛苦、无奈、愤慨等多种复杂的悲愤和无奈心情。快速的节奏,激烈的旋律刻画出岳飞铁骨铮铮、保家卫国的英勇杀敌形象和壮观的激战场面,缓慢的节奏和哀怨忧伤之调,又勾勒出侠骨的岳飞也有柔情的一面,亲情、友情、国情油然而生。乐曲最后在转调和相同的主题旋律下结束,似乎缅怀岳飞《满江红》“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胸怀和赞扬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历史责任感,感受其“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淡泊,以及抒发其“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英勇报国之大怀。乐曲选取以精忠报国的岳飞为创作题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儒家文化崇尚浩然气节的精神在古筝艺术中的再现、交融和延展。不仅再现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而且这种精神激发我们参与创造美好的中华文明,使之生生不息,永不停止。
(二)贵和持中、宽容平和的精神
有人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史其实是儒道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两种文化的发展主线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各自保持着清晰的发展痕迹,但是还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着。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人文艺术方面,许多儒者如王羲之、李白、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张可久、汤显祖、曹雪芹、吴承恩、八大山人、郑板桥等等人文名家身上都注有儒道两种文化精神,其作品既具有儒家文化精神的风范,又流露出道家文化精神的神韵,可谓是兼儒融道之作。诗、词、元曲、小说、书法等是如此,古筝艺术情趣也是如此,体现逸情之趣的筝曲有着儒家贵和、平和之格调,也可以说是儒家贵和、宽容平和精神在逸情筝曲中是表露无遗的。
《论语》曰:“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从中可知,“和”的本义是指歌唱的相互应合。所以《说文》曰:“和,相应也”,“由此引申为不同事物之间彼此相互交错而又相济相成而达成的平衡、和谐的关系。”[3](P3)儒家有着贵“和”的精神,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君子无所争”[4](《论语·八佾》),讲求中和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和”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也是天地万物最好的存在状态,只有“和”,万物才能携生育代,只有“和”,音乐的情感才能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审美标准,只有“和”,个人修养才能“温而厉”、“恭而安”,只有“和”,才能享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述而》)天人交融的浪漫美景。
儒家贵“和”的思想,体现在儒家的宽容之态和精神之中。《荀子·非相》:“接人用枻,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荀子·非相》)《荀子·不苟》:“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绌以畏事人。”(《荀子·不苟》)儒家的宽和、宽容之态度是一种兼容万物之气度,也是彰显人之德性,“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宽容是君子德性象征,有宽容的情怀和意识,可以得众拥护,“宽则得众”(《论语·阳货》),“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荀子·非相》)也可以成就天下大事。宽容既是心态,又是精神人格的体现,“儒家的宽容精神,与孔子的自由精神实为一体……此乃孔子精神涵容度量之大与高。孔子‘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正是一种廓然虚旷的心灵境界,同于佛家与庄子“空”的智慧与“无”的智慧。”[4](P100)
被喻为“仁智之器”、“众乐之师”的古筝也受到儒家贵和、宽容的文化精神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古筝逸情之美的格调上。从古筝艺术形式上来看,表现逸情之趣的筝曲,如《出水莲》、《梅花三弄》、《暗香》等旋律大都庄重典雅,不失儒家尚雅之风;音韵和而有致,端详和谐,不失儒家尽美之格;节奏繁简适度,中节沉稳,不失儒家平和之韵;速度不温不火,缓急适中,不失儒家中和之调。从古筝艺术内容上来说,一些逸情筝曲也彰显出了儒家“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的宽容品格和美好品德。以莲花、梅花、兰花、竹作为意象的逸情筝曲,既是一种隐的象征,与世无争,悄然生息,不起风云,又有着一种高贵品格之涵义。莲花、梅花、兰花、竹都是君子象征,体现着君子的宽容之德与“和”之品格,高贵、纯洁和与世无争的精神中蕴藏着巨大的宽容品格。以君子之花命名的筝曲如《梅花三弄》、《莲花谣》、《暗香》等透露着儒家平和宽容的文化精神,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意蕴上,既可以尽善,又可以尽美也。
(三)乐观知足、重视礼俗的观念
两千多年来,儒家精神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影响并渗透着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并形成了固定的情感意识和礼俗观念,其中儒家文化中的乐观知足精神和重视礼俗的观念对古筝艺术乐情之趣的审美也有着一定的渗透和交融作用。
乐观知足精神在儒家文化中不难发现,《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就表明儒家的生活态度是乐观的,知足的,孔子评价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瓤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既是个乐观主义者,又是个生活知足者。孔子也是这样的大圣人,即使简陋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还自我解嘲“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还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种乐观的态度可以忘忧、忘贫、忘老,达到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中。中国有句俗语叫“知足常乐”,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这里的寡欲就是知足,《申鉴·杂言下》也是这么说的“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申鉴·杂言下》)元代诗人赵孟頫也讲,“君子贵知足,知足万虑轻。”(《元诗选·丙集》)洪自诚也说“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明]洪自诚:《菜根谭》)等等,这些格言都说明了儒家注重中庸并保持淡泊的人生态度和知足的乐趣心态,体会到无尽的快乐和情趣。
儒家乐观精神和寡欲知足的态度也渗透到古筝艺术的乐情之趣中。体现古筝乐情之趣的乐曲一般是反映民间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题材。这些民风题材的筝曲都体现着辛勤劳作的中国人民,保持着知足和乐观的精神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为整日的辛苦劳作而愁眉不展,不为简朴的生活而耿耿于怀,而是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怀着一颗知足的心,播种着大地的希望。《春耕谣》、《春耕时节》都是以春耕题材为创作意趣,体现着劳动者自劳自乐的情趣,还有体现出收获丰收成果的乐曲。《赶集路上》“乐曲形象地描绘了山村农民们喜获丰收后高高兴兴赶集的情景,抒发了农民们对美丽秋色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5](P91)。还有《金色的秋天》、《丰收锣鼓》等筝曲都洋溢着劳动者丰收知足的快乐心态。此外筝曲《幸福渠水到俺村》、《幸福渠》明朗轻快的旋律,也刻画出了农村人幸福知足的心理。儒家文化这种乐观知足的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劳动者在农事上的知足心态,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习俗方面。如东北地区的人们在喜庆的日子通过载歌载舞的秧歌和敲锣打鼓的活动来庆祝美好的节日,筝曲《关东秧歌》和《东北风》正好描绘出人们载歌载舞的快乐心境,体现着一份乐观和知足感。又如各族人民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或唱歌、或跳舞、或泼水等来庆祝自己美好的生活和知足幸福心情,《草原晨曲》、《侗族舞曲》、《芙蓉春早》、《欢欣的节奏》、《闽南春歌》、《泼水》、《欢乐的苗寨》、《金色的延边》、《瑶族舞曲》、《彝族舞曲》、《迎春舞曲》等这些表现异族生活风情的筝曲,其旋律和内容都在表达一种情愫,那就是乐情,乐情之中彰显出儒家乐观知足的文化精神和快乐心境。
概括地说,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图形。三元组是知识图谱的通用表示方式,基本形式主要有:实体1-关系-实体2,实体-属性-属性值。例如: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地理位置-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知识图谱已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搜索、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内容分发等领域。
儒家重视礼俗的观念在古筝乐情之趣中也有所反映。儒家的礼俗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其所注重的孝敬父母、谦虚谨慎、富有同情心、彬彬有礼、温良恭让的文化精神,都注入了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一种固定的、特有的心理模式,这是礼,而俗呢?“习俗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而礼则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由统治者加以取舍、定形并推广”[6](P79),如儒家礼俗文化中婚俗文化一直保持至今,人们还是按照先人的婚俗文化进行婚俗活动,只不过是形式变化了,而内容依然是儒家礼俗文化的精髓所在。“婚礼意味着除了孝敬父母之外,还将负起养儿育女的职责”[6](P80)。《抬花轿》和《婚礼场面》两首筝曲承袭了民间音乐的精华神韵,还把儒家礼俗文化精神演绎其中,体现民俗生活中的儒家礼俗文化精神是无处不在的。
二、古筝艺术情趣对儒家文化精神的阐释和传承
审视古筝艺术情趣,从中可以折射出对儒家以情为美的阐释,透露着儒家的创新精神和传承了筝乐情趣寓教于乐的功能。
(一)古筝艺术情趣对儒家以情为美的阐释
古筝艺术情趣中悲情、逸情和乐情之美折射出了儒家音乐的情感美论。对于“情”,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就有“四情”、“六情”和“七情”之说。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认为四情是天性也,荀子的“六情”之说,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礼记·礼运》也认为人之情是自然之美,“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不管是“四情”、“六情”、“七情”也好,都是人的自然之情,就如孟子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一样,是人性的客观存在,不可去除的。但是儒家的“情”要同“礼”统一起来,“情”要达到一种德善之美,充满着内容之美,因此在音乐中的情要流露着“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的情,音乐情感上要体现出一定的内容之美。
古筝艺术的悲情之美,在内容方面都流露出儒家重视音乐情感的内容之美。在古筝音乐的“悲情”之中,可以歌颂爱情之悲美,《秦桑曲》、《骊宫怨》、《云裳诉》、《孔雀东南飞》、《陌上桑》、《西楚霸王》等筝曲都在抒发着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坚贞的情意;也可以颂扬大情的悲壮之美,《临安遗恨》中岳飞爱国报国的壮美之情,《苏武思乡》中苏武忠守气节之美,《汨罗江幻想曲》中屈原爱国之情,《草原四姐妹》中的亲情之美,哀伤之情的《叹颜回》等筝曲都在抒发着一种能震撼人心的情,这种“情”,积淀了儒家“虽悲观仍愤激,虽无所希冀仍奋力前行”[7](P46)的悲美之情。
古筝艺术的逸情之美,不管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有着儒家所提倡的尽善尽美之意。体现逸情的筝曲在主题精神上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如《梅花三弄》、《出水莲》、《暗香》、《高山流水》等曲中的意境如同儒家弟子追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述而》)美的境界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形式方面,端庄柔和的旋律,不温不火的中庸速度,不繁不简的音符,演绎着逸情筝曲中所透露出儒家重视“中节”的文化精神。
古筝艺术情趣中的乐情,一方面反映了儒家认为七情中“乐”情是人之常情之一,肯定了情感艺术中乐情之美;另一方面古筝艺术的乐情之趣彰显出了儒家礼乐安邦、天下顺焉的政治主张。乐情之趣的筝曲内容大都是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乐曲,百姓快乐幸福,说明天下安定昌盛,符合了儒家通过音乐现象看社会本质的论断。
(二)古筝乐曲体现出儒家提倡的创新精神
每一种事物都是在时间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古筝艺术情趣也不例外,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创新精神。
儒家文化彰显出创新精神,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说明孔子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者,《雍也》云:“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对于周礼,孔子认为齐国能够变化一下,便可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如果再变化下,就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孔子也关注人品行的发展变化,“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担心学生不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徙”字突出了变化和发展之义。《子罕》说:“子在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说明孔子在匆匆流水中感受到事物生生不息及人应该不断进取的道理。《易传》中也有儒家创新的论见,《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下》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系辞下》)这里说的是“变易”之义,体现创造之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系辞上》)“开物成务”是经过“通”和“变”的方式来实行的,但是还要通过人主动创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其创新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封》)这正是对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创新精神的赞扬和肯定。
古筝艺术情趣的创新既彰显出古筝创作者有着儒家的创新精神,又体现在古筝创作曲上。创作者的精神和思维决定着创作者的成果,古筝创作者要想创作出异于传统乐曲,就应该有变通思维,《丰卦》彖辞云:“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丰卦》)认为人应该也有尚变思维,才能符合天地盈虚大道,具备创新思维的古筝创作者做到了,他们创作的筝曲就是他们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产物。
古筝创作曲是相对传统乐曲而言的,是古筝艺术的一种创新,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多样化的人工调式定弦。人工调式就是作曲家自己设计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调式音阶,使用一些新的调式色彩音,使筝曲整体的调式色彩音趋向多样化和丰富性,如王建民的《幻想曲》,采用四个八度连续定弦法,此定弦法,含有同主音大小调所交替进行的变幻色彩,为多彩的旋律音调提供了创作素材。又如王建民的《莲花谣》,采用“人工模式化音组定弦,即按一定的音程比例关系以固定规律进行成组的连锁上行……而音组之间的交替衔接同时也会有各种调式调性产生的可能。因此,这种定弦给乐曲在调式调性的发展空间上提供了很大的余地。”[8](P3)二是古筝演奏技巧的创新。古筝演奏技巧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演奏手法上,如使用快速指序技法,可以演奏传统技法所无法胜任的七声音阶和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拓宽了古筝在旋律与音型方面的弹奏范围,使古筝由色彩乐器向旋律乐器行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8](P3)又如使用特殊的演奏技巧,譬如《长相思》,用左手食指随意在左边无音高的弦上刮动,《幻想曲》、《箜篌引》、《西域随想》、《黄陵随想》等乐曲中的左手分别在琴盖、琴板、琴弦等不同位置上拍击,使古筝演奏效果模仿了打击乐器的音响效果,从而丰富了古筝的艺术表现力,也使观众在视觉和听觉上焕然一新。三是古筝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传统筝曲的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情特征,创作筝曲在此基础上,拓宽了创作风格,表现不同少数民族风格特征,如西域风格的《西域随想》,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幻想曲》,维吾尔族风貌的《木卡姆散序与舞曲》,西藏风格的《谐》,湖南花鼓风韵的《湘舞》,戏曲格调的《戏韵》和《打虎上山》,神秘风格的《山魅》等筝曲创作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诠释着创作者与乐曲所流露出儒家的创新精神。
(三)古筝艺术情趣传承儒家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
古筝音乐是寓教于乐的艺术,其抒情达意的属性和一些富有文化内涵的乐曲是人们疏导情性的工具,也是完善人格修养的重要手段,在此同时,古筝音乐又是娱乐心情的绝佳载体。古筝艺术情趣体现了儒家的寓教于乐之功能,在寓教中培养美好人格,汲取着人文历史知识,在审美中愉悦情愫,愉悦身心。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孔子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主要认为音乐才是一个人最终完善人格的标志,也是一个人最终完成所学之道的标志,更是培养高尚品德的手段,因此儒家认为音乐具有寓教美育、通伦理之功能。《乐记》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著,主张“以善主真”,“以善主美”,重视“乐者,通伦理也”,多处说到“乐者,所以象德也”,“乐者,德之华也”,“观其舞,知其德”等之句,旨在表明音乐是培养美德的途径,也是德性优劣的体现。荀子也有此观点,他在《乐论》中曰:“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音乐可以打动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可以培养、熏陶人的情感,从而发挥重要的教化作用。教化作用是音乐寓教功能的体现,《吕氏春秋·音初》也云:“风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而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知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吕氏春秋·音初》)汉代董仲舒也认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汉书·董仲舒传》)可见,儒家孜孜以求地主张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
古筝音乐实践和传承着儒家文化寓教的主张。体现悲情之趣的筝曲,都是有着重要文化内涵的乐曲,一方面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和人格精神,如《苏武思乡》中苏武的为人,其坚毅、坚守气节的人格品德和不畏艰难险阻、吃苦耐劳的精神会感染着人性,使人性也散发出苏武般的人格魅力,再如《临安遗恨》中所流露出岳飞精忠报国、爱国、卫国的铁肩道义气魄,无不让人折服;又如闪耀着人性的坚强勇敢、血浓水的亲情责任感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富有报国思乡情感内涵的《汨罗江幻想曲》;操守忠贞爱情的《孔雀东南飞》;流露出力拔山兮气盖世、铁骨铮铮的豪迈气概的《西楚霸王》等筝曲都在召唤着人性的闪光点——坚强不屈的人格精神、爱国卫国的高贵品格和奋力搏击的浩然之气。另一方面从筝曲也可以汲取历史文化知识,了解历史文化内涵。古筝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础使人类对其有所研究,其过程就是寓教的过程。一些表现人文历史的筝曲如《苏武思乡》、《林冲夜奔》、《汨罗江幻想曲》、《孔雀东南飞》、《西楚霸王》、《临安遗恨》、《云裳诉》、《长相思》、《崖山哀》、《箜篌引》等筝曲都在向我们描述着不同历史阶段中不同的人文历史,从中汲取着历史文化知识和其精神内涵。
如前文所述及,表现逸情之趣的筝曲,既可以培养儒家中节、儒雅、宽和的情性,又可以渲染着道家追求自然和融入自然之乐,享受怡然自得的逍遥之趣以及贵柔守雌的人格魅力。体现乐情之趣的筝曲,既可以感受浓浓的生活情趣,又激发着人类要有热爱生活之心,并养成热爱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精神的品性。
古筝艺术情趣本身就体现着儒家于乐的审美愉悦功能。孔子素有闻《韶》乐,便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审美效果,说明《韶》的愉悦作用之大。古筝是善于抒情的乐器,心情伤悲之时,挥之一曲,所有的负情绪随着乐曲在指尖下倾泻而出,《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去忧莫若乐。”(《管子·内业》)悲情筝曲可以清扫内心的负面情绪,使之归于平淡;身心俱累时,弹上一曲,全身关注于逸情之趣中,享受乐曲带来的和风细雨,沐浴其中,如遇甘露,轻松无比;乐情之趣的筝曲让心情焕然一新,畅想于欢快的节奏中,穿梭在轻盈的音符里,乐情之心油然而生,趣味连连,融发气神!
[1]杨义.诗魂与民族魂[N].人民日报,2002年 6月 11日.
[2]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3]蔡和萧.儒家“贵和”思想的现代世界意义及其价值[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4]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阎黎雯主编.中国古筝名曲荟萃(下册)[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0.
[6]杨世文.论先秦儒家的礼俗观[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
[7]林同奇.人文寻求录 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赵曼琴.古筝快速指序技法概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