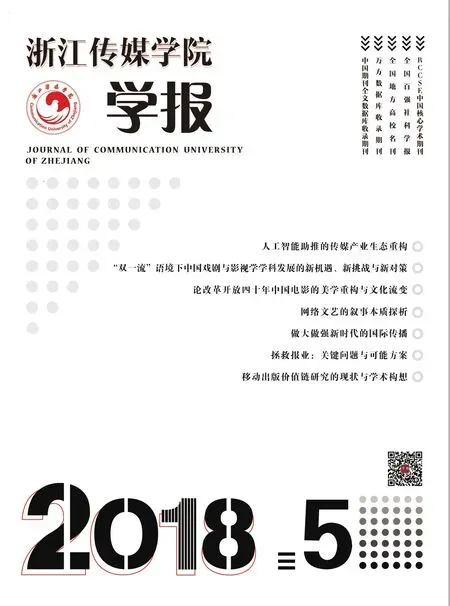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美学重构与文化流变*
陈旭光
四十年惊回首: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艺术轨迹,其美学流变与文化升沉之脉络清晰可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在个体心灵“伤痕”的感伤抒情吟咏中苏醒,在对影像造型的“美”的寻觅中进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探寻,更在产业改革、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受严峻考验而奋进,又在世纪之交的低潮中艰难却坚定地大步前行。改革开放以来,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电影审美风格的变化、导演代际的变迁——从四、五、六代到新生代或“无代”或“新力量”群体,电影观念和文化的交汇碰撞融合都异常剧烈。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电影不断走向复兴和辉煌的四十年,给中国电影留下了一段值得铭记甚至大书特书的历史。
一、四十年中国电影文化形态或格局概貌
不妨说,一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电影发展史,就是一部电影观念变革演进、电影文化不断交汇冲突融合创新的历史。在电影文化的剧烈变革中,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导演队伍、电影生产、市场与管理机制等也发生巨变。而正是在这些几乎全方位的巨变中,我们迎来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我们可以从中国电影文化形态、艺术观念、类型格局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辨析这些变革的来龙去脉及复杂关系,探求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剧烈变革和多元文化并存交融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道路。
笔者曾经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实际上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表现之一是“社会市场化、阶级分层化、意识形态的淡化与分化”,其深层原因则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审美文化的制约,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主宰一切的。”[1]转型的结果,是由原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齐划一的阶级划分——工农商学兵,以及“市民文化、市民意识形态正逐渐地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鼎足而立,三分天下”,[1]变得今天这般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的更为复杂多元化。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笔者也曾经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动,劳动者内部及各阶级内部的分层化和利益多元化趋势明显,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分化出许多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2]
正如论者指出的,“仅从职业来看,工人阶级内部就有如下不同阶层: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产业工人阶层,从事流通、服务活动的商业劳动者阶层,从事精神产品创造和传播的知识分子阶层,从事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管理者阶层,从事企业管理职能的经理者阶层以及因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制等形成的下岗工人阶层等;农民阶级也发生了重大的分化,主要有从事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业的传统农民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乡镇企业的农民工阶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性质)等;而新兴社会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充分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化和群体化趋势的凸显和加剧。”[3]当然,当下的社会阶层状况强调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和谐共处,这使得一种以社会和谐为基础的“共享文化”或“新主流文化”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成为可能。
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史是一部电影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那么,从社会阶层分化和相应社会意识形态复杂化的角度看,这四十年,我们历经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沉浮隐显,也目睹了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传统边缘文化的崛起等等。其中主流文化的整合与强势,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流变,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形态的崛起,青年意识形态的逐渐长大成人,成为最重要、最新异的现象。
从历史、地域(或曰时间、空间)以及电影美学、电影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电影也历经了中国电影传统、主流性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边缘性的“鸳鸯蝴蝶派”市民文艺传统、红色主旋律电影与主流电影文化传统、港台电影文化、好莱坞电影及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的交汇、磨合、紧张、对立或融合,等等。
很大程度上,上述文化之微妙的消长起伏、角力暗斗和变迁沉浮构成为一部中国电影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云变化史。表现于电影艺术与审美,则一定程度上呈现为美学风格的流变、电影导演的代际变迁或“无代”际变迁,以及创作观念、创作态势与类型格局的流变重构。
在当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中国电影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平民、市民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四大潮流格局。准确地说,是形成了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其他多元文化的文化共融局面。
二、四十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简述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经风云起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社会发展历程同步甚至同呼吸。概要而言,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阶段。
(一)1978—1989:起步新时期
此阶段的中国电影历经从“伤痕”“反思”、奋进到落潮的电影美学潮流,折射出一条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从鼎盛到落寞、退潮的心理历程和文化发展线索。
第四代导演是新时期电影开风气之先的创作主体。《小花》以前所未有的优美影像来表现战争,加浅红色滤镜的镜头,英姑在水中中弹倒下时优美的慢镜头表现,一种久违的战争的诗意让人耳目一新也引发某些批评争议。《城南旧事》表达一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韵味,一种如“缓缓的小溪”一样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氛围。《小街》表达了对美好青春的留恋、健康自然的男女之情和人性之美的向往,也表达了对扭曲的非人性现实的批判,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相互理解。《巴山夜雨》以高尚的情怀和诗性化的电影语言,批判社会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寻找蕴藏在人们心底的人性的美好与良善。应和着“电影与戏剧离婚”“丢掉戏剧的拐棍”“电影语言现代化”等美学自觉的表达,第四代导演还开始实践视觉造型美学崛起之电影语言实践。《小花》等电影对战争的诗化的唯美化表现,都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成为第五代电影视觉造型美学的先导。
第五代导演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孩子王》对传统的“吃人”的隐喻,对“文革”时候文化荒芜的反思,不乏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精神。《黄土地》以近乎呆照的镜头,静默无声的大色块造型,创造了稳定凝重而开阔大气的造型形象,也表现出内向性的情感基调和缓慢凝滞的时间感,借此隐喻了传统的深厚凝固冥顽。《霸王别姬》以中国半个世纪多的历史为背景,表现了大历史中人性的复杂。《活着》通过富贵这一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折射了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的变迁以及历史巨变中个体的无力与无奈感。
第六代导演是“自我命名”的一代。他们抛弃宏大的民族、国家、历史主题,在影像世界中传达真实感受到的感性现实。《头发乱了》《周末情人》《北京杂种》等以摇滚乐为对象或结构框架,《苏州河》《冬春的日子》《巫山云雨》《小武》《过年回家》《周末情人》《月蚀》等,则传达了动荡不安、迷离驳杂的生活经验与生存体验,“无父一代”的迷乱、困惑和希冀。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精英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条从寻找、确立自我,到反思民族文化,到一代人的个体精神痛苦的心路历程。
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加入了这个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合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改革的风潮,心灵的巨变。在改革的阵痛与社会的激荡的风云中,就如被称为“杂种电影”(意指兼容多元文化,既有“野合”“弑父”、酒神狂欢等传奇性民间文化,成长仪式、长大成人的成长主题,也有民族抗日的宏大主题),引领中国电影大众化、商业化潮流的《红高粱》里的酒神式“狂欢”所隐喻的那样,中国迎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期。
(二)1990—2002:新世纪之交的转型
在此阶段,以《顽主》《甲方乙方》《大撒把》《有话好好说》等为代表,嬉笑自嘲的“顽主一代”电影和一枝独秀的冯氏喜剧时期代表了新的市民意识形态的崛起。
“冯氏喜剧贺岁片”作为中国电影中较早具有“类型”特征的电影,曾在新世纪前后的电影市场上“一枝独秀”。《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天下无贼》《私人定制》等,以独特的“冯氏幽默”——京味文化、语言幽默、平民形象、市民情绪、世俗化内容等,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现实变迁的一面“镜子”,也折射了一条平民意识形态与消费文化崛起的道路。
期间,《被告山杠爷》《二嫫》《天狗》《安居》《马背上的法庭》等现实题材影片,仍然艰难而顽强地以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表达了对时代变革进程和进程中的个体“人”的关注与思考。《阳光灿烂的日子》则崛起了一股清新的青春文化,开中国青春电影的风气之先。影片超越了对“文革”历史的简单道德价值评判,表现了在已逝的青春记忆中那种飘忽、迷茫、充满不确定性的诗意,堪称青春的抒情诗或呓语,“长大成人”的青春寓言。
(三)2002——新世纪的拓进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类型格局与艺术探索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坚持和转换适应,新生代或网生代导演成为主力,香港、台湾电影人大量内地化,合拍片不断增多,电影文化在蹒跚中走向繁盛。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全面加入电影业,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互动狂欢的格局和突飞猛进的态势。
新世纪的第一份厚礼是以《英雄》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大片。《英雄》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一个“大片时代”,它第一次使电影成为一种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电影工业或文化产业的运作,电影产业观念、电影营销观念等开始深入人心。《英雄》在资本运作和产业经营中初露中国电影工业国际化、产业化的“峥嵘”。从《英雄》开始,大投资、大市场、大营销、大明星、大制作等“大片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在大片崛起的背景下,以《疯狂的石头》为肇端,从《失恋33天》到《人在囧途》《泰囧》《港冏》等各种“囧”电影,小成本影片、喜剧电影及其他类型电影,开始与大片分庭抗礼。中国电影呈现出类型化趋势和格局。
三、迈入电影新时代:当下格局与突出成就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中国电影迎来了全面的繁盛,有几个重要现象或成就值得总结。
(一)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格局形成了一种以“大片”(包括重工业大片、新主流大片、“合家欢”电影等)为排头兵,带动众多中小成本类型电影的“大鱼带小鱼”的格局
除“大片”外,当下中国电影几种主要类型是:喜剧片、青春电影、玄幻电影和犯罪、惊悚、悬疑电影。时下中国电影呈现的类型格局,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说,则是代表主流文化和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观众的意识形态需求的大片与满足各个不同阶层的审美消费和意识形态取向的类型电影之间达成了基本和谐的“生态”关系。
(1)喜剧电影的繁盛与喜剧新美学的拓展
“后新时期”喜剧热潮的涌动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大众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当人们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在僵化的思想禁锢中“解冻”,尤其是在生活逐渐安定小康之后,“娱乐”的狂欢顺理成章成为了一种时代美学风潮和文化消费的重点。就像《顽主》中三T奖T台走秀的狂欢化的仪式性场景所隐喻的那样,一个堪称“娱乐为王”的时代来临了!喜剧片具有世俗化、通俗化、娱乐化取向,但也是颇为靠近现实生活,接地气的。喜剧具有世俗性风格和生活化美学的艺术形态,是可以充满当下世俗生活气息的。
喜剧类型电影中的“公路亚类型”电影如《人在囧途》《泰囧》《心花路放》《后会无期》等,以一个“在路上”的旅行叙事结构,《重返20岁》《夏洛特烦恼》《港囧》《煎饼侠》等则通过“圆梦”情节,讲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梦想,折射社会现实与众生心态。《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等以小人物的意外暴富为戏剧性情节点,人性冲突、良心选择为故事线,人性发现和收获爱情为基本的结局模式,给社会底层提供财富想象、心灵慰藉与道德完善。
从类型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母类型’,喜剧全面与其他类型互相融合或互相渗透,比如与青春爱情片、公路片、刑侦探案片、奇幻电影,等等,以多种形态与观众相遇”。[4]而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形态,当下喜剧电影出现的美学形态是开放的,也是年轻化的。当下中国电影的喜剧美学与新中国以来以国家为本位的崇高美学、英雄话语、宏大叙事,以及讽刺性喜剧美学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笔者曾经描述这种新喜剧美学的主体为:“有着年轻人特有的草根性和娱乐狂欢精神。他们放纵想象力,放纵身体语言,不像冯小刚那样自矜自炫于在丰富的生活阅历基础上对生活的洞察幽默,而是以表情、表演、影像、叙事等的夸张,逃避对个体主体的关注和对现实作精雕细刻、默识体验型的关注。他们奉行娱乐至上,不关心娱乐的社会伦理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姿态的反讽搞笑,成为他们的重要话语手段,他们是以反讽、颠覆、搞笑、娱乐化的方式从边缘借助商业的力量向中心和大众社会突进。”[5]
(2)青春电影的梦幻功能、青春消费与市场价值
当下观影人群趋于年轻化,青春电影受到90后、00后观众的喜欢。青春片讲述关于青春“消费”、成长寓言、情感伤感、幸福梦想、闺蜜友情等话题,表达对事业、爱情、人生等成功及物质富裕的中国“青春梦”,也反映了“消费逻辑”的影响。青春电影在艺术表现上往往影像风格时尚,光影流丽。《同桌的你》《我的少女时代》《匆匆那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北京爱情故事》《乘风破浪》《谁的青春不迷茫》等“小回忆”“小感伤”的“小电影”证明了中国式“青春”的市场价值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匮乏。
《小时代》系列、《万物生长》《致青春》《我的少女时代》《左耳》《我的青春期》《栀子花开》《后来的我们》《遇见你真好》等影片,唯美的服装、年轻的身体、流丽的时尚成为最吸引眼球的元素。而故事本身却了无新意,颇为乏味,这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上的舍本逐末、“视觉至上”。以校园为“纯爱”、追爱的主要场所,表现出某种“纯爱”理想,也透露了导演生活经验的缺乏。
《七月与安生》通过双重自我的人设以及寻找自我的主题表达和开放结局的设置等,在叙事上颇有创新,对女性个体心理也有较细腻深入的开掘和表达,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式青春电影的成熟。《闪光少女》积极主动地试图化解与主流文化的矛盾,二次元造型风格的男女生以民乐对抗西洋乐,打造民族文化认同的梦想。
(3)玄幻魔幻类电影的“虚拟消费”或“想象力消费”
在互联网时代,拟像化、类像化的媒介环境,游戏、网络、动漫、二次元等如空气之于人一般弥散于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和想象空间,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毫无疑问,这一代人对架空历史、超越现实、放纵想象力的虚拟世界有天然的亲近性。于是,一种“梦幻消费”或“想象力消费”的玄幻或魔幻类电影在新世纪崛起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此类电影往往具有形象主体、时空环境和故事情节的假定性、虚构性、玄幻性、梦幻性等特点。
《画皮》系列、《狄仁杰》系列、《捉妖记》《美人鱼》《九层妖塔》《寻龙诀》,以及层出不穷的以“西游”为大IP的电影改编(如《西游伏妖篇》《西游降魔篇》《大圣归来》《女儿国》《悟空传》)等奇幻类电影,多以冒险、探险、探案为主线而进行“玄幻化”打造。《九层妖塔》《寻龙诀》都是冒险压倒奇幻的类型杂糅电影。《捉妖记》系列通过作为“他者”和人类镜像的“妖”而反观自身,表达万物均可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4)警匪、犯罪、侦破类电影的小众化突破
侦破悬疑类电影具有犯罪暴力、悬念惊悚、高智商推理、深层心理表现等魅力,颇受年轻受众欢迎。《白日焰火》在现实题材和心理惊悚类型电影的拓展方面颇为出色。《烈日灼心》是警匪、侦破类型与心理类型的叠加;《心迷宫》颇为接地气,它通过“罗生门”式多线叙事,以一个颇具本土气息和黑色幽默气质的农村悬疑故事,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法制缺失与人性沦丧的现实。《暴雨将至》虽为侦破犯罪类型,但表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心理化叙事,风格化的雨夜造型,具有一定的艺术电影气质。但叙事功力与情节合理性的不足,如《记忆大师》《嫌疑人X的献身》《心理罪》等表现出的游离生活真实、现实感与地气的缺失等现象,仍然是此类电影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5)艺术电影自成一体的坚守和跨界努力
进入新时代,《二十二》《冈仁波齐》《无问西东》《罗曼蒂克消亡史》《驴得水》《我不是药神》等原本小众化的艺术电影,跨越艺术电影与类型电影的鸿沟,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其他艺术电影也在寻找自己的独特道路。《路边野餐》《长江图》《我的诗篇》等与文学(诗歌)形成一种富有意味的“互文”关系,既通过影像、叙事表达诗情营造诗意,更以诗歌承担叙事和表意功能,有些直接朗诵或入画的诗歌,坚实,富于哲思,有质地,丰富、强化了电影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十二公民》《驴得水》则与戏剧形成某种“互文”关系。《一个勺子》《不成问题的问题》《八月》《二十二》《嘉年华》《我不是药神》等,聚焦主流视域之外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质询社会真相,悬拟公平正义,别有一种艺术的良知与人性的勇气,凸显了导演的现实关怀力度。黑色幽默喜剧电影《驴得水》改编自戏剧,表达人性反思与国民性批判及知识分子反省的主题。《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叠合黑帮片类型的艺术电影,以华丽精致的色调与抒情性的音乐氛围,以及重组时空的复杂的叙事游戏,表达了一种浓丽香艳格调的“民国想象”。《嘉年华》以悲悯冷静的女性情怀,以及丰富的隐喻性意象,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清醒冷静的批判,并不煽情却具有发人深省且预言现实的力量。
新世纪艺术电影的坚守和变革,表现出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它为商业电影和主流电影提供了艺术借鉴和养分,对于电影主流观众艺术趣味的养成和合理的电影生态营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香港、台湾电影人北上,大量合作合拍电影,成为推动中国电影辉煌和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
港台与内地(大陆)合拍在真正意义上的突飞猛进应该以2003年CEPA协议生效为开端。首先在大投资类“高概念”电影大片上成绩显著。这也是合拍片对中国电影在电影大片观念上和操作上的直接实践。大片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合拍”作为一次文化融合的实践功不可没。
大投资大片的登堂入室从2002年《英雄》开始,实际上大片实验在《天地英雄》《七剑》等合拍片中已小试牛刀。《英雄》虽是张伟平的新画面为主要出品方,但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甄子丹等香港明星的联袂出演,江志强等香港影人出任出品人与制片人等,使得这部影片成为香港与内地合拍的里程碑式作品。此后,《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夜宴》《赤壁》《战国》《关云长》《鸿门宴传奇》等,进一步加大了古装历史题材大片的合拍。
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大片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及《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体现了合拍片的最新、最高成就,也体现了香港电影文化近乎完美的“内地化”或“新主流化”[6]。新主流电影大片合拍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异特质:跨国题材、异域风光、民族情结、军事械斗、动作武打,国家文化形象展示等。文化上多元共融,类型上也兼容并包,既有动作武打类型的现代化,也有好莱坞超级英雄类型电影的明显影响。而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再到《建军大业》,则呈现了中国主流电影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色文化主题类电影通过商业化运营、市场化包装表现宏大题材、国家文化形象的一条“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步步升级的道路轨迹。《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大量引入港台明星,《建军大业》则让曾导演过《无间道》的刘伟强执导,这无疑表明香港电影文化和内地电影文化深度融合的“蜜月期”的来临。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合作拍片越来越渐入佳境,昭示了主流电影文化的新走向,昭示了文化开放,更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
(三)新时代“新力量导演”成为生力军和主体力量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发布,这是国家第一次把电影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掀起了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高峰。新主流电影大片占据票房的半壁江山。这是一场以主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交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新力量”导演在国家的推介下隆重登场。
新力量导演在观念上最大的优势是一种“电影工业美学”观念:“秉承电影产业观念,类型生产原则,游走于电影工业生产的体制之内,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体制性与作者性等关系,追求电影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7]他们不像第五代导演以启蒙者的姿态述说精英话语的“话语欲望”,也不用体验第六代导演在工业与艺术之间无处安身的迷惘。他们在票房和口碑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得益于他们游走于电影工业化生产体制内并能处理好与个人风格表达之间的关系。
于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工业美学”*参见笔者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的系列论文:《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8期全文转载);《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电影工业美学原则与创作实现》,《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电影工业美学再阐释:现实、学理与可能拓展的空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原则——正在他们身上实践生成,并贯穿于其电影生产的全产业链。新力量导演实践的电影工业美学也诞生了一种新美学:“电影工业美学是工业和美学的一个折中,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①
电影工业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资源或者文化定位就是把电影主要定位为一种大众文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历程中,港台影视剧的进入与持续影响,美国电影的巨大市场和影响力,是中国电影大众化的外部因素。创作上,“顽主”系列电影、冯氏贺岁片,以《英雄》为肇端的武侠电影大片,各种商业化类型电影等的相继出现,都引领了一个中国电影的大众化潮流。既然把电影定位为大众文化和大众艺术,电影工业美学必然注重普适性的价值观传达,持守一种大众化而非精英化、小众化的新美学,尊重受众、市场、票房,“受众为王”,尤其是尊重青年受众,理解青年文化,甚至试图成为青年文化的代言人。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重构与文化的创新及融合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因其广泛的受众审美需求、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而在四十年中国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总结而言,四十年的电影文化在如下几个文化建设意向上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并继续进行积极的建构。
(一)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精神实施积极的“现代化转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电影对传统文化的影像转化是传统文化继续在中华文化发展中承传繁荣的重要实践。
新世纪的古装武侠电影对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即影像化转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疏远现实、营造诗意意境、满载文化符号的艺术表达和文化重构,呈现出东方美学意味。如《英雄》通过色彩与造型的写意营造的飘逸、空灵的意境美学,是写意性、表现性美学的影像再现和符号化表现。
《夜宴》中的竹林杀戮段落,也颇具乐舞神韵。白衣少年与深绿的竹子、黑衣杀手构成鲜明的色差,杀手的凌厉迅疾与白衣少年的无所畏惧引颈而死也构成一静一动的张力,再配之以动感鲜明、节奏明快的音乐,使得整个杀戮场景充满动感和韵律。《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则以对色彩与画面造型的强调,营造出一种繁复奇丽、浓墨重彩的视觉景观,形成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十面埋伏》中的牡丹坊,富有唐文化韵味,整齐的乐器、夸张的异域风格舞蹈,呈现了唐文化的丰富多元的大国文化特征。《妖猫传》作为一部东方奇幻大片,其视觉风格和特效制作广泛借鉴了文人画、敦煌壁画等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风格,营造出中国式的华丽堂皇、错彩镂金的诗意画面。
一些艺术电影也以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像化转化独树一帜。《刺客聂隐娘》画面细腻有质感,意境深远高古,对话精简,意味清新隽永,常用远景镜头,几乎不用特写,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这是一种文人化了的书卷气很浓、很中国化的文人情怀、历史伦理观和诗意雅兴。《不成问题的问题》,通过淡雅的黑白影调,缓慢的表演、对话,复现的场景等,“刻意”营造出一种东方美学或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蕴。《长江图》《路边野餐》对佛教文化的理解与隐喻化、诗意化表现也别有人生况味和哲理意蕴。
在逐渐兴起大热的玄幻、魔幻电影如《画皮1、2》《狄仁杰》系列、《捉妖记》、西游题材等电影中,原来一直居于边缘地位、地下状态的传统亚文化、次文化,也加入到文化繁荣的大合唱之中。这些电影以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要素构造出一种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在自然人与作为自己的“他者”异类的原始情感关系中询唤真诚的人性、美好的爱情,使大众对鬼魅进行审美的想象。如曾经创下票房记录的《捉妖记》,也是亚文化转向和现代融合的产物,传达了万物平等、人妖和谐相处的普适性自然观。
(二)中国电影完成了香港电影文化的“内地化”或“新主流化”,形成了独特的合拍片新美学
在香港电影人北上合作拍片的过程中,香港影人经多年实践而成就的电影理念与电影美学,那一套独特的“合拍片美学”,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中国电影的风貌。“香港电影的加入,也直接促成中国内地影业的成长,深化内地影业的市场化。从融资、制片、故事、制作到营销,几乎所有的大片都不乏香港的身份印记,处处可见香港演员、技术人员和创作人员对每部破票房纪录大片和对每年成长的电影数目所做出的贡献。”[8]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与内地影人的合作过程中,香港影人独具的电影商业理念、工业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职业精神、市场意识、平民意识、娱乐精神等,都使中国电影人获益匪浅。成为主流的合拍电影更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成就的重要有机组成。
(三)中国电影宽容并接纳了青年“边缘”文化和某种“青年新美学”,使之完成主流化或亚主流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80后、90后、00后,年轻一代在电影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笔者曾经认为,“在中国电影(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的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电影的‘成年人气息’过于浓重,‘青年文化性’积弱。上半世纪的内忧外患、颠沛流离,下半世纪的政治紧张和意识形态重压,都是种种原因之一。《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春之歌》等影片虽以青年人、青年心理、青年问题等为题材和观照点,具有一定程度的青春性,但相对来说,意识形态的浸淫或者往其它类型影片的倾斜,使得这些影片多了一份明朗的理想主义色彩,少了一份青春感伤、青春忧郁的私密性和真诚性。其青春叙述热情洋溢,个人成长史从属于国家的生成史,凸现为了至高无上的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主题。因而很自然的将个体叙述消融到国家、历史的大叙述之中,形成了共性大于个性的艺术特征。在此类电影话语中,个人成长的成年仪式与革命胜利的宏大话语完全缝合在一起,或者说,个人的成长是为了印证国家和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不容置疑性。”[5]
但新世纪以来,这种“国家化”“主流化”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青年文化的崛起已不容忽视。就观众主体而言,年轻人、“小镇青年”占据着电影市场的主体;就电影美学与文化而言,青年文化性特征是生活化、世俗性、娱乐化的。作为网生代,他们热衷游戏、虚拟世界,政治意识不强,但颇具商业市场意识、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从导演角度着眼,第六代及更年轻的网生代导演已经开始考虑社会、票房、受众、口碑等问题,其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毫无疑问,青年亚文化迟早都会与主流文化融合或者演变为主流文化。第六代导演曾经打造偏于小圈子、个体精英知识分子的青年文化。进入新世纪,与电影观众的年轻化相应,以《失恋33天》《全城热恋》《全球热恋》《爱》《致青春》《小时代》系列、《前任》系列等青春爱情轻喜剧为代表,掀起了一股青春浪潮,《闪光少女》《十万个冷笑话》等则走得更远,以二次元、无厘头、动漫游戏等,全力打造青年文化。虽然仍未能得到成人社会的认可,但青年文化继续顽强“在路上”。
五、结语:走向新时代
在笔者看来,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决定行动。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观念不断革新的历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发展最大的问题也是观念问题,是解决电影是什么的问题,也是一些长期对立矛盾的电影观念的融合甚至是折中妥协的问题。例如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或工业性的二元对立,长期以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上世纪80年代关于“娱乐片”的争论就是一个明证。原本学术意义上的争鸣因为种种原因也因为过于先行的观念未能有现实土壤的依托而匆匆终结,使得一场初见效果的娱乐片思潮(《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等)也无疾而终,张华勋等导演带着遗憾、委屈而退场。
笔者承认电影是艺术和工业的矛盾体,要以综合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来进行务实求实的电影工作。这是四十年中国电影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至少就笔者个人而言,在观念转换上的最大收获和确立。
鉴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发展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必须建立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观念。既要认可电影的娱乐性、工业性、商业性,但在中国的独特语境下又不能走极端。如果说要求中国的导演做好所谓“体制内的作者”的话,我们应该把“体制”理解为——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影生产体制、管理机制、运作模式等,还应该包括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中国式的真善美要求,中国式的伦理标准,以及“本土化”“接地气”,反映或折射现实,尊重中国伦理本位等标准或要求。
新近崛起的“新力量”导演是一个新的有自己特点的群体。从某种角度讲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新成果。这个“新”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的命名。“这不仅是中国电影新生的力量,也是中国电影创新的力量”(张宏森语)。他们在前辈经过四十年中国电影的实践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电影观念,代表了与时俱进的先进生产力。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文化的多元、包容、“妥协”、折中、务实,尊重观众、热爱电影。他们遵循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具备商业、媒介文化背景下的产业观念,服膺“制片人”中心制,做“体制内的作者”,秉承并实践标准化生产的类型电影观念并学会与制片人及创作团队进行有效合作。在适应体制并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展现自己的才华,创作经得住观众审视、市场检验的电影作品。这种创作精神正符合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经过而立进入不惑的沉稳、踏实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态。
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回归“新常态”。票房结束连续高速增值而回落。粉丝电影不灵、IP热潮退去,观影群体选择更趋理性。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电影界应该建构一种兼顾电影的技术/艺术、工业/美学、技/道特质的“工业美学”原则,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电影新时代。在这种“新常态”下,中国电影人更加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