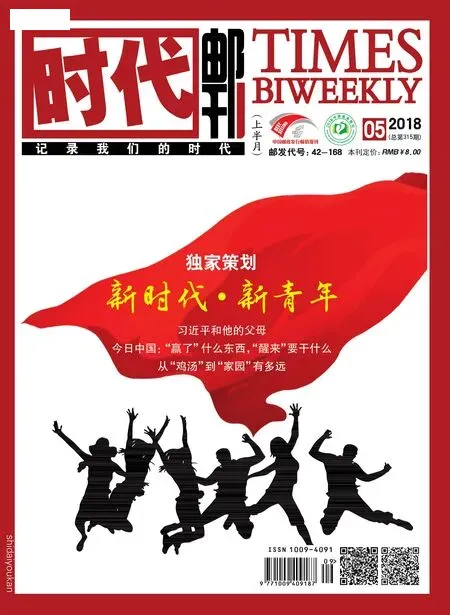麦香
麦香是阳光的味道,麦香是大地的味道,麦香是母亲父亲的味道,麦香扑面而来……
一只布谷鸟从麦浪尖上一掠而过,留下几声短促而简洁的鸣叫:“莫黄莫割,莫黄莫割……”它的叫声唯美而悠远,连着农人的心。
印象里,母亲喜欢掐几支快要成熟的麦子,放在手心里搓掉外壳,再放在嘴边用力吹,这时手心仅剩下晶莹透亮的绿色麦粒儿,然后放进我的嘴里,那股麦粒灌浆时溢出的青郁香气在口腔内回旋,那味儿像槐花里掺进了蜜,像玫瑰里拌入了糖。母亲的动作那样娴熟,那样虔诚,那种对土地的感情,是我所不能体会的。
麦子要熟了,每年要熟一次,仿佛麦子和农人们约好,它一步一步辛苦跋山涉水走来,要人们在这个时节来接待它。
麦收时,夜色的余晕还未散尽,全家老小就走进大麦田。每人三四行,低着头,弯着腰,左手向外侧一搂,镰刀在麦秸的根部用力一拉,“嚓嚓”两声,麦子便整齐地躺下。远处树上的百灵鸟不时叫两声,那样清脆。那些年,我们要一连割上好几天,从天色泛出微光,直至暮霭升起鸟倦归巢。
割累了时,我喜欢躺在麦地里。麦子很柔软,饱满馥郁的麦香让人沉醉,身边生长着碧嫩的野草。我躺在柔软的麦地里好久不想站起来。一个人一生遇到多少人不知道,但总有几个人能记住;一个人一生邂逅多少味道,记不清,但这麦香,在生命里总也无法抹去。
记忆中的家乡,树是那样粗,天是那样蓝,云是那样白。麦收前夕,父亲和哥哥在村东边的梨树地头碾压麦场,用沉沉的石磙碾压,一遍复一遍,直至把地面碾压得结实如石,在阳光下泛出耀眼的光亮,麦场才算告一段落。
风一来,父亲便坐不住了,走到麦堆前,迎着风,把混有麦皮的麦粒儿高高扬起,这时,麦粒儿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饱满的麦粒落下来,麦皮随风落向了稍远的地方。累了,父亲会蹲在麦堆前歇一会儿,抓一把金灿灿的麦子放在鼻子前深深地吸上一口,那表情是陶醉的。一个能被麦香陶醉的人,他的幸福是简单的,也是悠远的。
麦收时节,父亲常常在麦场上要忙到深夜,月亮挂在树梢头,那清辉如水洒在父亲的背上,洒在麦场上,洒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