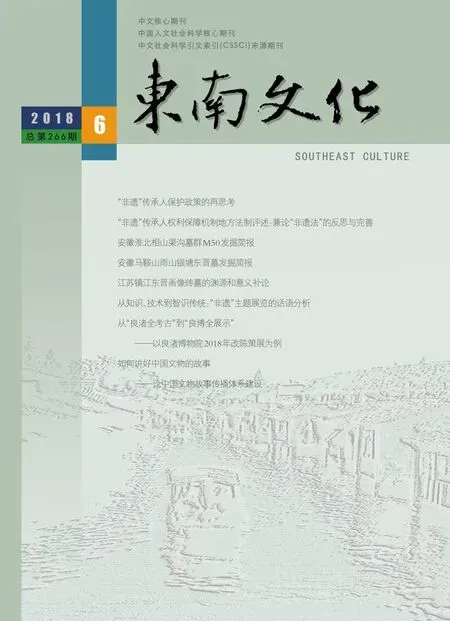“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的再思考
吕 静 薄小钧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以树立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这一制度不仅疏于为大多数传承人提供真正利于精进技艺的社会环境,也忽视了非遗的多样性特点,与当今国际社会新理念的普通传承人、群体传承人和传承社区的保护意识尚有距离。政府和社会需要提升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应关注更多的普通传承人;还应引入企业和社会力量,促进民间自发的传承机制的运作;要加强非遗产权的法规保护及产权意识的培养,推动全社会民众与传承人共同保护优秀非遗的良性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当中选拔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予以精神褒奖和经济资助,是我国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一项长期的政策。迄今为止,已有四批1986个非遗项目、1836位传承人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不过,目前这种精英式的个体保护政策,果真是保证可持续性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良性政策吗?少数个体传承人真的能够承担起拯救那些岌岌可危的非遗的重任吗?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有了制度性保障和实际措施。但是,随着国内外对非遗认识的逐步深化,特别是相关学者越来越关注非遗持有者的群体性和社区性特征,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停留于只重视个体传承人的法律政策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二、国内外非遗传承人政策溯源与现状
对于个体传承人的重视是由日本的“人间国宝”政策所开创。1950年以奈良法隆寺金堂及壁画、京都鹿苑寺金阁被火烧毁为导火线,日本开始认识到在现代工业、商业和消费风潮的挤压下,日本的文化遗产已经危机四伏。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出台,该法在1968年的第二次修订中,提出了对作为“人间国宝”的传统手工艺的杰出匠师加以保护的新概念。所谓“人间国宝”,即被日本政府认定为表演或工艺技术领域里的“身怀绝技者”,他们拥有绝世技能,能够传承某项重要文化财。“人间国宝”每年得到政府一定额度的补助金,用于培养后继者以及开展传承活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非遗保护政策,首先认识到了身怀绝技者的重要性,并以官方立法的形式予以保护;在提高民间手艺人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唤醒了整个社会对于非遗传承的重视。
“人间国宝”制度出台后迅速为国际社会借鉴和吸收。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泰、法、捷克、菲律宾等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人间国宝”制度。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效仿日、韩的“人间国宝”模式,建立类似的机制。
事实上,中国对工艺技术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也有选拔制度。1979年原国家轻工业部受国务院委托组织评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到2005年,已有5届、共评选出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4年中国加入国际非遗保护组织并成为委员国后,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原国家文化部正式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列入法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是:(1)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各级政府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传播活动予以支持,包括提供场所、经费资助等。各省市陆续认定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近九千名。同日本、韩国等一样,法律还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将被取消资格。
三、现行传承人保护政策之不足
在现行非遗保护政策中,对非遗传承主体的保护主要集中于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保护政策虽然颇有成效,但也显现出不少问题。
(一)传承人“代表”责任之重
代表性传承人一旦被选拔出来,政府、社会和民众对大师精湛的传统技艺和创造力给予肯定和尊崇的同时,也寄托了对他们担当传承非遗文化重任之殷殷期待。于是,代表性传承人既要继续精研技艺、建业创新,身负文化传承之重任,又要对非遗技艺之外的社会性宣传、教育,甚至地方经济的增益发挥作用,他们承受着来自本业和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
首先,从现行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律法规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以下职责和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遗调查;参与非遗公益性宣传。不过,现行法规给予他们在传承事业上钻研、磨练技艺的时间、空间的保障,特别是在传承人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的保护方面严重缺失。对非遗传承主体的保护,就是要对“身怀绝技”者技艺的保持和精进,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提供充足的时间、空间、人力和经费的保障。实际情况中,有些传承人沦为政府管理部门应付专项检查的工具,用来充当部门政绩的门面,甚至成为支持地区经济的摇钱树。比如,浙江景宁畲族“三月三”的对山歌、吃乌饭、祭祖先节俗,成为当地政府举办“畲族风情旅游节”招徕游客的节目,“三月三”本土民俗被当地官员和庞大的游客队伍扰恼[1];广东番禺的“飘色”民俗,因地方行政力量的介入,“飘色师父周旋在其中,时而忘记自己是传统的携带者的身份,去迎合政治力量的需要”[2]。各种强加在传承人身上宣传、示范的义务过重,牵扯了过多本应专注于本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代表性传承人的压力之一。
其次,代表性传承人一旦被政府认定身份,全社会把拯救该非遗项目的期望聚于其身,对代表性传承人来说,责任的压力往往超过了荣誉感。寥寥数个传承人要将延续传统手艺的责任和义务一肩挑起,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显而易见。有时候传承人的压力不但来自于他们“需要做什么”,更来自于他们“做不到什么”。像四川羌寨的“释比”(祭司)肖永庆,作为当地非遗“羌年”的代表性传承人,他至多也只能熟记熟唱羌族的史诗,而无力让“羌年”这样的地区性非遗再兴辉煌[3]。
现行非遗保护政策中,以集中“火力”的方式支持个别精英式传承人的保护模式,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目前政府和社会对手艺人、传承人高龄存世的担忧,就是现行政策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各级政府倾力保护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人在艺在,人去则艺失。管理部门心存侥幸地把“赌注”压在个别代表性传承人身上,那么必然会对他们的老去离世而惶惶不安。将传承非遗的重任仅仅系于代表者一身,忽略和放弃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众多普通的民间传承人,一方面挫伤了民间传承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实质性地损害了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二)非遗多元性认识之缺
目前,在以国家—省—市—县四等级科层制为基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机制中,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级别高下分明,待遇层次有别,与民间的普通传承人拉开了距离。这种精英式传承人保护制度并不适用所有的非遗项目。
首先,在民俗类非遗项目中,各种地区性的节庆、庙会、歌会、集市起源并扎根于固定的社区,基于民众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而产生,与该地域每一个人都有血肉联系,构成了这一社区的群体记忆。节庆的创造者、实践者是广大的基层民众,他们以及他们的活态性实践活动才应该是非遗政策中的保护对象。以“羌年”节庆习俗为例:羌族新年是农历十月初一,延续三到十天。新年里村民敬神祭祀、上山还愿,聚集一起吃团圆饭、喝咂酒、跳莎朗;村寨的祭司“释比”主持各家上山还愿仪式,唱诵史诗。肖永庆、王治升作为祭司“释比”,被评定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4],他们能传唱大量羌人史诗,精熟各种祭仪程序。但从本质上说,“羌年”里的各种祭祀和节庆活动,主角是村寨里的每一位男女老幼,离开了羌寨村民的参与,“释比”连同其所精熟的祭祀仪式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其说“释比”是被重点保护的代表性传承人,毋宁说整个村寨以及每个村寨成员都是“羌年”这一非遗项目生死存亡之所系。
其次,在很多歌舞表演类的非遗项目中,表演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合作的关系。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多声部情歌”,至少由两组男女共同完成,“团体中的每个人在演唱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很难判断哪个更重要”[5]。一旦将他们割裂开来保护,只能是“1+1=0”的效果。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中的经济性资助政策出台后,最直接的矛盾来自于利益之争[6]。原本团队成员平均分配的演出补助金,因为被代表性传承人一人占有,导致表演团体出现裂痕。
非遗产生于悠长多彩的人类生活过程,非遗形式万象、种类繁多,极具复杂性、多样性。非遗不仅存在于手工技艺、表演、礼仪,更覆盖民众生活、生产、娱乐和休闲的全部领域。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科学、谨慎地定义: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此,树立一两位精英传承人,并没有体现群体创造的特质。可见,不考虑非遗项目本身的特性,忽视传承群体的组成形式,一概以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加以认定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中的一大阻碍。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和学界把无形文化遗产分作两类,即无形文化财(技能和工艺类)、无形民俗文化财(民众的生活形式与习惯),制定了分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如后文所记的三种资格认定等措施,值得借鉴。
(三)政府主导评选之弊
目前非遗传承人的选定以各级政府机关为主导,导致了在一些手工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评审中,技艺水平的专业性评判不够专业。例如,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天津“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一种仍以家庭作坊形式为主制作生产的传统年画。杨家埠的四家著名画店都是百年老店,互相竞争,水平和质量彼此不相上下。2007年杨洛书被认定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后,四家画店的关系开始紧张,凭着国家级传承人的名号,杨洛书的“同顺德”成为当地销量最好的画店。同一行当、同样作品、同样流派的年画工艺传承,杨氏一定超越其他三家的专业性理由不够服人,因此同行艺人“对杨洛书的成名之路表现出了各种羡慕、嫉妒与不服气”[8]。同样,广东省级非遗项目“吴川泥塑”的很多民间艺人对高氏入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心存不满,认为手艺超过他的大有人在,偏偏他被评定为代表性传承人,还独享省级津贴。于是,泥塑师傅集体拒绝媒体和学者的采访调查,以示抗议[9]。张连沛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户撒刀锻制技艺”传承人,也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户撒地区唯一一位仍会打制“七彩刀”的手艺人,但因各种原因,未被评上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连沛倍感不平和失落,挂锤歇业不再打刀[10]。
目前,非遗传承人的评定标准、评定程序都是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统一制定和执行,完全由行政主导,忽视了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排除了一大批掌握丰富知识和高超技能的民间艺人”[11],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各种质疑声四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担当专业性超强的评定专门技艺高低的评判者,是否合理?即便在评审中聘请了专业人员介入,但对专家选定的过程,本身就属一个高度专业范畴的工作;而且,由政府来评判行业人员的技艺高低,这种方式也超出了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范围。
重视个别代表性传承人、实行“精英”化行政管理的保护思路,在非遗保护刚刚起步的阶段,效果卓然。但时至今日,这种行事简单化、表面化、笼统化和绩效化的积弊已然凸显。通过行政把控式的手段来选拔少数精英式代表性传承人,倾斜资源、打造模范,试图通过提升一人来影响一大片,意愿可嘉,但成果有限。在今日深化和完善非遗保护政策的大背景下,超越过去那种单一的、有局限性的行政干预政策,建立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细化的保护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四、传承人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一)传承主体的多样性认知
对传承主体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随着社会对非遗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内外相关前沿理论和田野调查的进一步发展,非遗传承人的内涵正在逐步扩展:非遗传承人不只是手工技艺、口头文学、表演艺术和民间知识类的“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扩展到礼俗仪式、岁时节令、社祭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群体传承;除了重点保护精英式传承人,人数更多的普通传承人同样值得关注与呵护。因为非遗根植于民间土壤,是地区民众群体共同创造的人类文化结晶。优秀的非遗绵延至今,依靠的是各类传承主体的薪火相传;扎根于社会基层的众多普通传承人,是精英式传承人的孕育母体。在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中,对普通传承人和群体传承人等传承主体的保护,同样不能缺位。
有些非遗项目,其工艺技术中的个人色彩不够明显,且拥有这一技能者人数众多、技艺水平难胜高低。如果套用四等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层体系来评判非遗项目保持者的重要程度,可能无法评选出“身怀绝技”者,或者会遗漏重要的非遗技艺。中国北方的麻纸制造技艺就是一例,当地人用废旧麻绳、麻布、麻鞋底为原料,经切麻、洗料、碾料、洗料、打槽、抄纸等工序制造麻纸。这种技艺分布于黄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麻纸亦是我国代表性的传统造纸[12],却很难选出代表性的传承人。
日本政府和学界对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主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将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分作三种不同形式加以认定:其一是个别认定——他们是高度体现或取得重要无形文化财(艺能和工艺技术)技能的个人。比如琉球古典音乐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岛袋正雄作为杰出的演奏家被认定为该音乐的保持者,即“人间国宝”;漆艺雕金的保持者中川卫,被认定为工艺技术领域的“人间国宝”。其二是综合认定——由二人或以上形成一体的情况作综合认定,像歌舞伎、能乐、组踊等。其三是团体认定——有些工艺技术中个人色彩和风格比较淡薄,“身怀绝技”并不明显而该技能的保持者人数众多,在此情况下,对所有保持者的团体给予团体认定[13],比如柿右卫门制陶技术保存会、小鹿田烧技术保存会、久留米絣(染织)协会。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非遗内涵的丰富性和非遗形式的多样性特点,分门别类、细化非遗保持者的资格,是具有针对性、更具科学性的有效保护政策。
(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事业
政府应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将非遗传承与保护的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纳入保护事业,既可以让非遗保护获得专业性科学性支撑,又可以缓解政府财力资源、人力资源匮乏的窘境。
1.利用专业性的民间组织
在传统手工业、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很多行业存在过历史悠久、组织成熟、运行合理的行会组织。行会在业内人员的专业指导、整合协调,规范手工业和商业运作,以及防止业内恶性竞争、维护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4],其自治的性质、在行业内自我完善净化的特点、权威性的评判,得到业内成员的认可。另外,在非遗的活动中,民间还有各种自发组织的协会。这些行会和协会对业内的活动以及工匠、艺人的专长特点了如指掌。前文提及在评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龃龉,传承人之间互相诋毁等现象,反映了工匠艺人们对政府的非专业性评判及评选活动忽略行会组织所产生的抵触和不满。如浙江省丽水鼓词协会会长对传承人评定办法提出意见:“代表性传承人的推选过程根本没有我们协会的参与,最后被认定的传承人年纪很大了,没有得到我们同行的一致认可。”[15]
这类行会和协会比政府部门更了解本行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承现状,更清楚匠师的技艺和地位,对各种民间的生产与民间活动有更专业的治理协调能力。这些专业性民间组织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长年积聚的行业威信更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像日本著名的文乐协会、能乐协会和歌舞伎保存会,接受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在本行业的保护和振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因此,我国政府也应该认识到行会、协会的特点和优势,诸如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审、非遗传承与保护方面,让它们的运作重新“活起来”,承担起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这是今后非遗传承和保护事业中应该加强的方向。
2.吸纳企业和社会赞助
非遗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中确保资金投入,是取得非遗保护事业成功的保障。要认识到大多数非遗项目很难实施生产性保护和生产性自救,因此,要维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甚至自身的生存,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对于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资助,我国已制定有法律法规。根据2012年出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年可以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2万元补助[16],专款用于开展传习活动。各级地方也有相应细则,比如北京市规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获补助2万元;上海市规定70岁以上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经申请每人每年得到近6000元津贴补助;江苏省以“生活补贴、立项资助、以奖代补”方式,对高龄和无固定经济来源的传承人发放生活补贴。但是,这些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全部依靠政府国库资源的支持力度毕竟有限。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非遗保护方面,也没有采取全部依靠国库财源的做法。像法、英、德、意、日等国家,大致拿出国民经济总预算的0.01%~1%,投入到支持非遗以及传承人的经济资助中。目前,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经济资助情况是僧多粥少,不足以支撑体量庞大的非遗保护事业。因此,引入社会资源,共同承担非遗保护职责,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美国,采取了引入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政策,鼓励和吸引私人企业和地方的支持;在日本,政府支持企业和财团设立基金会,投入非遗保护。众所周知,日本的民间社会对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民众和企业不断增强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和社会在逐步形成的慈善捐赠等意识中,正在寻求更多机会回馈社会,政府可以借此引导企业的捐赠进入到急需资金的非遗保护事业。笔者建议,在政府主导下设立非遗保护的基金会,聚集的资金可以资助非遗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可以资助传承人精研技艺、培养后继者,亦可以资助表演的活动场地、演出的成本等。
(三)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制度
我国应尽快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制度,既保护非遗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人权,也保障传承人享有发展自己所持有非遗的文化权利。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提供了有利于保护和支持非遗的重要借鉴。如意大利威尼斯制定了民间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享受无限期保护的法规,若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民间文化,不仅要获得文化部门的许可,还要缴纳使用费,而政府对收取的使用费以基金的形式进行管理。
笔者建议,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可以借鉴保护音乐人原创音乐、作家原创文学作品那样,对任何以营利和消费为目的,使用非遗工艺技术、图像造型、音乐舞蹈的企业、个人收取版权费,然后将钱款以经济资助的形式返还给该项非遗的持有者、传承人。这不仅可以成为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和维持自身生活的良好资金来源,同时也是对传承人应有的尊重和肯定,促进社会对于非遗保护的认知度和责任感。
五、余论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是政府、社会、学界及民众的共同事业,其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通过立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体现国家意志,为非遗的传承保驾护航。而且,除了政策层面,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非遗的保护工作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获得保障。政府在今后对非遗保护的主导作用不应削弱,而更要加强,因为今日众多的非遗项目早已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社会基础,丧失了自然发展的经济环境。国家权威的介入,为游离于当今社会、脆弱不堪的非遗以及非遗传承人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生存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非遗保护的主导,应体现在政策指导和法规建设的层面,而非介入包括传承人专业技能的认定等非遗工作的具体事务;政府应该充分调动社会的综合力量,将之投入到漫长、艰辛的非遗保护事业中去。
[1]金叶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重构现象——以泰顺畲族三月三为例》,《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李晓:《番禺飘色传承人的调查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3]陈安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传承人述论》,《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任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政府参与》,《民族学刊》2011年第2期;王田:《羌年——从村寨走向舞台的节日》,《世界遗产》2015年第12期;同[3]。
[5]田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6]同[5]。关于非遗保护中的利益之争,学者讨论不少,另参见高蕾:《大南直村布朗族蜂桶鼓舞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文化遗产》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座谈会会议纪要》,《文化遗产》2011年第2期;邓薇:《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8]荣树云:《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9]陈冬梅:《吴川泥塑传承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谢黎蕾:《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1]陈兴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2]张学津:《北方地区传统手工造纸工艺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3]〔日〕文化庁長官官房政策課:《2006年〈我が国の文化行政 平成18年度〉》,第47页。
[14]彭泽益:《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5]刘秀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6]2016年起,补助金额从原先每年的1万元提升到了2万元。
南京博物院举办“纸质文物修复用材料”研讨会暨学术沙龙
2018年11月4日,由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纸质文物修复用材料”研讨会暨学术沙龙在南京博物院举行。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主持会议,全国多家博物馆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围绕“纸质文物修复用材料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修复用纸、胶粘剂、绫绢等主要修复材料的质量评价”“修复材料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文博单位作为使用单位对接修复材料生产、加工企业,以提高修复材料的适用性”以及“目前情况下修复材料的选用或对现有修复材料的再加工”等五个议题展开讨论。在后续的提问环节中,年轻一代的文保人就“日本的纸张图谱的具体内容”“修复过程中应如何记录纸样”等问题分别向相关专家请教,并得到专家们的积极回应。
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国内纸质文物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东南文化》编辑部)
——围棋
——勉冲·罗布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