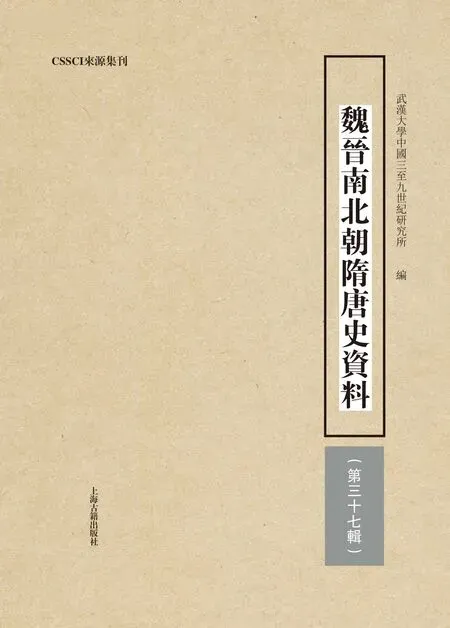漢晉之間吴蜀的督將與都督制
雷家驥
一、 前 言
學界討論魏晉都督制之文甚多,而論述其起源及早期發展則極少。筆者昔曾撰就《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下文簡稱“前拙文一”)一文詳論其源起及早期發展,略謂魏晉都督制源於先秦以來的監軍制,兩漢時則有督軍制並興,性質皆屬於君主派臨軍中的擁節使者,是將軍領兵制所衍生的軍隊監督制度,至東漢寖假有取代將軍以爲統帥之勢,亦即漸由軍隊監督系統轉變爲統率指揮系統,並且從統率指揮系統復分化出作戰系統與軍區系統兩種體制;至於降至漢末始出現、包含“都督”在内的諸督將,則僅是野戰軍戰時編制的基層軍官罷了。就發展至漢末而論,則監軍使權位重於督軍使,均屬於軍隊的監督指揮層級,督將則僅爲職低位微的鬥將而已,此與魏晉擁節都督爲上,擁節監次之,擁節督又次之的常制大不相同。其間變化的趨勢,實以北方軍系董卓、袁紹、曹操等集團的發展爲其主流。
爲此,筆者遂從當時“都督”一職,懷疑劉備所謂向孫權“求都督荆州”之事是否有確,因而另撰就《劉備“求都督荆州”與“借荆州數郡”析論》(下文簡稱“前拙文二”)一文,大意略謂州郡都督實屬軍區系統,當時蓋爲中級軍職,頗以太守、中郎將等官爲之,權位低於大將重臣所任之軍區督,以故位爲左將軍領荆州牧的劉備,不至於向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的孫權求取此職。考劉備所求,蓋爲“董督荆州”——以荆州牧身份索求統督荆州全般事務——之職。
本文乃是此二文之姊妹篇,目的爲探究孫、劉兩集團的都督制如何緣起?爲何在作戰系統之外,軍區系統又産生要塞督與軍區督之别,而與袁、曹軍制不同?要塞督與軍區督兩者關係如何,孫吴軍區督後來爲何及如何漸漸統屬於軍區都督,是否模仿了曹軍制度?而蜀漢則爲何不如此發展,以致使都督制的發展主流在曹魏而不在吴、蜀?
本文論述孫、劉集團此制的發展下限止於吴、蜀亡國,與前拙文一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此二集團在漢末發展時間短促,非如此斷限不足以觀其變化,更不足以論其特色;至於研究此制的權威嚴耕望先生,於其大著《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已暢論魏晉都督制矣,[注]嚴先生名著《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列爲其所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臺北: 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B,民國79.5三版。但對二國此制則較少著墨,蜀漢尤少,且内中尚有可值商榷或補充之處,而小尾孟夫之《六朝都督制研究》對二國的論述更是付之闕如。[注]小尾孟夫: 《六朝都督制研究》,廣島市: 溪水社,2001年。加上漢末至魏初之間文獻不足,尤以蜀漢爲然,致使陳壽批評蜀“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云云,[注]詳《三國志·後主傳》卷三十三,第902頁。本文所引正史,俱據臺北: 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是則蜀漢不僅闕遺於漢末至魏初時段,即使其建國以後亦然。爲求探索二國此制的特色以及解答爲何發展主流在曹魏而不在吴、蜀等問題,儘管研究起來相當吃力而瑣碎,致使本文不免多所考辯,乃至有冗贅之嫌,但亦不得已也。
只是與都督制有關的一些特殊軍隊建制或軍兵種,如督(都督)中外軍事、羽林督、繞帳督、解煩督、營下督、帳下督等,以及一些較常見的戰時軍兵種編制分科,如水軍督、騎督、糧督等,因與本文主旨相關性不大,格於篇幅,也就請容略過不論了。
二、 赤壁之戰前後孫軍督將的肇始與變化
督將原非兩漢軍隊之常制官職,東漢末卻成爲作戰系統的戰時野戰編制,而最早出現於董卓西涼軍系的軍中。
漢中平六年(189)靈帝崩,政亂,董卓率軍入京廢少帝而立獻帝。翌年(獻帝初平元年,190)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號稱義師,推袁紹爲盟主,於是董卓挾獻帝西遷長安。初平二年二月,長沙太守孫堅率軍數萬人進戰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注]《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卷四十六,第1096頁。蓋是“都督”一職之始見;不過,董軍是役之主帥並非華雄,“都督華雄”僅爲其軍胡軫部的戰鬥將校而已。實際上,是役董軍之主帥爲胡軫,史載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吕布爲騎督”,又謂“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云。[注]前引句見《後漢書·董卓列傳》注所引《九州春秋》,卷七十二,第2328頁;後句見《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引《英雄記》,卷四十六,第1096頁。按: 《英雄記》謂胡軫爲“大督護”,當時無此職,蓋誤,前拙文一已辯之。此爲孫吴軍制史上最早遭遇有都督編制的軍隊。
此役董軍胡軫部的野戰編制爲“大督—都督(督將)—戰兵”,而作爲主帥的大督——其實大督也是督將——既然位階爲二千石之太守,則其下的都督位階更低,固理所當然。稍後叛殺董卓而逃至關東、兵力僅有數千人的平東將軍吕布,麾下置有一支號稱攻無不破的“陷陣營”,編制兵力僅七百餘,號爲千人,由“都督”高順所指揮。[注]吕布軍之“都督高順營”及“陷陣營”,“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見載於《三國志·吕布傳》注引《英雄記》,卷七,第223—224及227頁;《後漢書·吕布列傳》注引《英雄記》同而略簡,見卷七十五,第2450頁。由此可知,董卓軍系的都督,領兵約千人,位任在將軍、太守之下,蓋可無疑。相對於此,作爲討卓群雄的諸軍,兵力稍壯亦頗編置督將諸職,顯示此軍隊戰時新編制已漸漸普及。如孫策、孫權兄弟崛起相繼領兵,所部即有都督乃至大都督之編制,是否起源於孫堅模仿董軍則不詳。
孫堅戰死於進擊荆州劉表之時,所部由其子孫策所領,發展至五六千人,遂轉戰而據有揚州的江東四郡,至獻帝建安三年(198)被曹操表爲討逆將軍,封爲吴侯。五年,策欲乘曹、袁相拒於官渡而襲許昌迎漢帝,尋爲刺客所殺。此時,孫軍已見置有督將,如史謂“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鋭,乃以(陳)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注]見《三國志·陳武傳》,卷五十五,第1289頁。又謂“策表(徐)琨領丹楊太守,會吴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注]據《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吴景是孫策之舅,曾任袁術的督軍中郎將,策後以景爲丹楊太守;徐琨則是孫權妻舅,事見《三國志·吴主權徐夫人傳》(卷五十,第1197頁)。是則孫氏的兩舅皆曾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即是其例。至於直以“都督”爲稱的督將亦已見置,如《三國志·吕範傳》謂範將私客百人歸策,因屢立功,策“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吴,遷都督”。裴注引《江表傳》曰:[注]見《三國志·吕範傳》並注,卷五十六,第1309—1310頁。按: 孫策於建安四年征黄祖,《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引《吴録》載其表,謂“臣討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吕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等同時俱進”云云(卷四十六,第1108頁),顯示吕範此前已遷都督,領兵爲孫策的部將,而此時之“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應是孫策私署之官。
策從容獨與範棋,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更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按: 孫軍此時的兵力遠不及袁紹、曹操,麾下衆將校領兵多少由統帥配置,故配都督吕範“兵二千,騎五十匹”殆已不少,即如任中郎將或校尉之周瑜等人,所配兵力亦不過如此罷了。[注]建安三年孫策授瑜建威中郎將,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程普爲吴郡都尉前已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韓當蓋爲校尉,亦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可見孫策常配手下大將以此兵力而已。三將各見《三國志》其本傳,不贅引。既然吕範先領宛陵令,則孫軍早期的都督,職級應大抵與縣令相當,是以孫策謂吕範領都督是“屈小職”也。
揆諸史實,孫堅當年職位爲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孫策此時則爲討逆將軍、領會稽太守,父子均以雜號將軍領州郡,故麾下僅置有尚未位至將軍的中郎將、校尉等官,而其戰時編制的都督更只是位約縣令之小職,與董卓軍系的都督相當。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吕範原本爲文官的宛陵令,故孫策稱之爲士大夫,遷都督後領兵二千、騎五十匹若已算是“大衆”,但其都督則仍僅屬軍中統率系統的小職,故須穿軍服至討逆將軍、領會稽太守孫策的衙門閤下報到啓事。太守領兵本是漢制,以故太守有郡將之稱,吕範以都督軍職衙參太守,接受軍令,顯示太守孫策的地方行政系統與軍隊統率系統仍分開而置,即使降至建安五年孫權嗣位,曹操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之後,軍中已置有大都督之職,如史載“初,孫權殺吴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權弟)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注]此事《資治通鑑》繫於建安九年。其後媯覽、戴員因兵變而殺孫翊,爲孫翊夫人所平,見《三國志·吕範傳》並注引《吴歷》,卷五十一,第1214—1215頁。然而大都督之權位仍低於太守,與魏晉之制大不同。
降至建安五年官渡之戰前,袁紹集團的軍制已有頗大改變。時任“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紹,集結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曹操,其戰時野戰編制是將監軍沮授所統部隊分爲三都督,而分命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由是言之,三都督之每一都督所統兵力理應不少,以故乃有曹操襲擊袁軍後勤重地烏巢,殲滅其都督淳于瓊以及所督督將、騎督萬餘人之舉,[注]見《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五年十月條並注引《曹瞞傳》,卷一,第21頁。可見此時袁軍之戰時野戰體制爲“都督―督將―戰兵”。都督權位已大爲提高,近乎是戰役級的主帥職,與孫權、劉表兩軍遲至赤壁之戰的建安十三年,都督一職仍爲縣令級戰鬥單位督將甚爲不同。
孫氏父子三人之死對頭——荆州刺史劉表所屬的江夏太守黄祖,軍中亦編置都督,而兩軍作戰均編有水軍都督或督,[注]按: 祖部之“都督蘇飛”(見《三國志·甘寧傳》注引《吴書》,卷五十五,第1292及1293頁)似爲步軍都督;而同書《吕蒙傳》謂蒙“從征黄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卷五十四,第1273頁),顯示荆州軍亦編有水軍都督。其實孫堅、孫策、孫權三父子均曾先後出征劉表,而常爲黄祖部沮敗於長江夏口、沙羨間之水域,故孫軍當亦編有水軍。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孫權先攻破黄祖“舟兵”,滅祖(《三國志·吴主權傳》建安十三年條,卷四十七,第1118頁),然後始有進與曹軍交戰之事;及至曹操敗後,同年底雙方復交戰於合肥,此役即確見孫軍編有水軍之樓船督,如《三國志·董襲傳》載建安十三年“曹公出濡須,(偏將軍董)襲從(孫)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卷五十五,第1290頁)是也。因此孫權、劉表之揚、荆兩軍皆以水戰見長,但水戰的編制是否與步軍同,是否仿自董軍編制已不可考。
在與作戰系統之野戰督及都督出現於戰時編制約同時,袁、曹二軍亦已出現軍區督及都督的建制。官渡之戰前,袁紹之“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即是軍區督的顯例,而曹操任命尚書程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則是軍區都督之例,至於命侍中、守司隸校尉鍾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則更是軍區主帥擁節的濫觴。蓋因群雄不論如何任命其屬爲野戰或軍區督將,性質皆是私署而非朝命,僅因曹操已挾天子而令諸侯,是以能够或方便假朝命而爲之也。據此諸例,可見建安初期主持軍區者已稱督或都督,但除了鍾繇之外皆未擁節,而且軍區督的權位殆重於軍區都督,拙前文一蓋已析論之,於此不再贅。
孫軍此前雖已置有隸於太守而以保衛該郡爲任務的都督與大都督,但迄至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發生前,猶未見有軍區都督之建置,而孫氏父子亦始終未以揚州都督或會稽都督爲稱,或許與當時孫氏僅據有揚州江東四郡之地,[注]據《續漢書·郡國四》所載,東漢揚州刺史部有九江、廬江、丹陽、會稽、吴郡、豫章六郡。按: 九江郡、廬江郡在江西,爲袁術之地盤,故術使孫策轉戰江東四郡。孫策定四郡後,“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吴景爲丹楊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爲吴郡太守”(見《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故名爲五郡,而實佔原江東四郡之地也。幅員褊小,而内部又僅有山越服叛的問題,未至成爲群雄地盤争奪戰目標等因素有關。不過亦於此期間,“督”之作爲作戰系統指揮職,已漸漸出現及推廣於孫軍編制之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出濡須,孫權命偏將軍董襲督五樓船駐濡須口,[注]同注①。即爲一例。董襲之督水軍駐濡須口,殆即爲孫軍之野戰督轉爲要塞督的濫殤。
按: 孫策死前孫軍戰時可能已有督軍、督將之實而無其名,如建安四年孫策征黄祖,曾上表謂“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吕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等同時俱進”云云,[注]參《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卷四十六,第1104頁。顯示此役孫策親任統帥,群雄親任統帥例不名督,是以周瑜等人均應是其分道督軍,故皆以太守中郎將等官職從之,只是諸將官職應皆是孫策所假,[注]諸將皆以“行”爲名,即非漢廷所正拜,至於江夏、桂陽、零陵三郡均屬荆州,時爲劉表屬郡,孫軍連荆州邊鄙也仍未佔領,以故其爲虚任遥領可想而知矣。以故未采“督”爲編制之名而已。及至孫權統事,勢力漸壯,乃漸出現督軍、督將之名實。例如《三國志·周瑜傳》云:
(建安三年,孫)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吴,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宫亭。……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
按: 麻、保二屯蓋屬荆州之地,十一年之役周瑜所督的孫瑜是領衆萬餘人、時任綏遠將軍、領丹楊太守的孫權從弟;[注]孫瑜是孫堅季弟孫静之子,詳見《三國志·孫静傳·瑜附傳》,卷五十一,第1206頁。此外孫軍中尚見有“督張異”“督陳勤”等督將之名,[注]見《三國志·淩統傳》,卷五十五,第1296頁。顯示此役之周瑜已是主持攻戰的督軍主帥,故編有衆多戰鬥督將,與董卓軍系的編制頗爲類似,只是周瑜尚未稱爲“大督”而已。及至建安十三年春孫權再攻江夏,而周瑜則爲“前部大督”,蓋因孫權自己督軍於後,故此之“前部大督”實是前鋒大督之意,即前敵總指揮也。只是無論如何,周瑜由孫策初時之戰鬥督將,至孫權時已升遷爲可以主持戰役的督軍,甚至采董軍之制而直稱大督,下轄若干戰鬥督將,則已爲不争之事實矣。此於赤壁之戰的作戰序列,可能看得較爲清楚。
赤壁之戰發生於建安十三年的下半年,即接着孫權再攻江夏之後而發生。原因是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操因之得其水軍,遂統有水、步兵而欲順流下江東。孫軍將士聞之皆恐,多勸孫權迎降,惟周瑜與魯肅執拒之議,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就此戰役的性質而言,是孫、劉兩集團聯合作戰;作戰序列則是周瑜、程普與劉備三頭馬車,各督所部水、步諸軍協同作戰,其上並無統一指揮之總司令,而參戰諸將亦均未見以“督”爲稱者,至於擔任贊軍校尉的魯肅則殆是吴軍參謀長,或兼孫、劉兩軍的聯合參謀。
劉備之事容詳下文,此處先述孫軍。《三國志·吴主權傳》扼要載云:
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按: 周瑜戰前原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本軍有兵二千人、騎五十匹;而普傳則謂普爲蕩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本軍亦有兵二千、騎五十匹,兩人可謂勢均力敵。赤壁之戰是大戰,影響深遠,然孫權卻分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勉强編成作戰序列,其上曾無統一指揮之部署,事後孫瑜之弟孫皎追述此事,謂幾敗國事云云。《三國志·孫静傳·皎附傳》云:
後吕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説權曰:“若至尊以征虜(孫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注]孫皎亦爲孫静之子,《皎附傳》謂其“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故在孫軍已算是大軍統帥。他督夏口時,“輕財能施,善於交結……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因此孫皎應是富有軍旅經驗者,所言應不虚。參《三國志》卷五十一《孫静傳》,第1206—1208頁。
也就是説,赤壁之戰時孫權將衆督將分爲左、右兩部,其上各置督軍,職稱爲左督、右督,因此導致左督、右督彼此不服,統一指揮上頗有問題,而幾敗國事。如此之部署,或許與孫權自己督軍“續發”於後有關。[注]按《周瑜傳》載謂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議者咸謂不如迎之;周瑜卻謂禽操宜在今日,“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孫權)破之”。注引《江表傳》則詳謂周瑜曰:“……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魯肅)、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見卷五十四,第1261—1262頁。後來孫軍欲襲取荆州關羽之時,孫權雖將左督、右督改稱爲左大督、右大督,其實恐怕仍會犯同樣的錯誤,所以吕蒙才提出“目前之戒”,促使孫權改變作戰序列爲大督與後繼——相當於前部大督與後部大督,以便前敵統一指揮,而終定荆州。
由此可知,孫軍雖然早已有過都督、大都督、督、大督之編制,但是降至建安二十四年(219)襲取荆州之時,作戰系統各級軍官尚未完成正名以及嚴上下之分,當時之“督”既可以作爲戰役主帥之職稱,也可以作爲戰鬥將校之職稱,視用兵情況而定,運用靈活;至於此前“大都督”之職稱,既非用以名戰役的主帥,而“都督”則更僅是營級編制的戰鬥指揮而已。例如遲至建安十八年十月曹操征孫權時,《三國志·武帝紀》載其都督仍爲營級的指揮官云: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
大抵上,孫氏三父子之戰略發展,是先取揚州江東之地,然後逆江而上覬覦荆州,然而卻屢爲江夏太守黄祖所敗。在戰争發展期間,孫權已漸明顯視戰事需要而任命野戰的戰役級或戰鬥級督將,如前引周瑜、程普、吕蒙、孫皎皆爲戰役級督軍主帥之例;至於公孫陽,則恐怕僅是戰鬥級督將,可能是濡須督麾下的江西營都督罷了,位階與早先變化不大,仍一如吕布軍中高順之爲陷陣營都督。
或許從《三國志·甘寧傳》所載寧從孫權攻皖,爲前部督率領所部都督突擊偷襲曹軍之事,了解孫軍此時的野戰編制更爲清楚:
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熟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
此事與前述諸例,可以窺見孫軍作戰時視情況編成升城、前部、後部、左部、右部等督,而都督——領兵戰鬥的督將——則隸屬於督之下。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降至赤壁之戰後,孫軍的野戰體制,除了最高統帥(孫權)外就是“督―都督―戰兵”,上下節級的分别已漸漸清楚,而類似於董卓軍系的編制。
除此之外,據前拙文二所述,知此時孫權以“全據長江”作爲國家戰略,並已漸有“夾江防禦”的軍事戰略構想;然而此前因尚未破敗劉表、黄祖而佔領荆州,故未遑依此構想而落實部署。及至赤壁之戰後,復因所佔領的荆州南郡之地已借與劉備,在劉備管治之下亦不能落實部署,以故“全據長江”的戰略態勢未能形成,“夾江防禦”之軍事戰略也不能遂行,只能於長江北岸先擇點作試驗。
所謂擇點作試驗,是指“夾江防禦”戰略下的建置軍區(州郡)都督——此時期嚴格説應是要塞督——制度試驗。軍區都督制是實施區域防禦戰略的軍事體制,但孫權此時僅有揚州所屬數郡之地,幅員不大,故無建置州郡都督之必要。揆諸戰史,赤壁之戰時曹軍從荆州南下,赤壁之戰後因與劉備對峙於襄陽—江陵一綫,故此後曹軍南下遂頗改從揚州江西之壽春—合肥一綫以攻吴。曹操數次由此綫欲順着合肥以南之濡須水進入長江,遂使濡須口成爲建安時期孫、曹兩軍必争之地,於是被孫權選爲戰略要塞建設重地,且是最早置督的要塞之一。
按: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剛結束,曹操退走,曹仁奉令留守江陵,隔江與周瑜相對,此時續發的孫權,卻迫不及待地率衆圍攻合肥,嗣因戰不利而曹軍援至,乃撤退。前謂建安十三年曹操出濡須,孫權命偏將軍董襲督五樓船駐於濡須口,此即應是孫軍於長江北岸最早部署要塞駐軍督之濫觴。稍後孫權借荆州南郡地予劉備,於是荆州攻防之事遂交給劉備,而自己則以經營長江下游揚州之西、東兩岸地爲主,秣陵建治及濡須建塢,即成於此階段。《三國志·吴主權傳》載云:
(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内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亦即曹操用移民手段,將揚州江西的廬江、九江等郡靠近江岸之地空置,用作戰略廢地,蓋因此階段孫權對曹操頗采戰略攻勢之故也。廬江、九江二郡近江之地既成戰略廢地,故孫軍勢需於江北已佔之地擇點建設要塞基地,以支援戰略攻防之用。由於此故,孫權早期在江北所置的某地督,如濡須督等,因旁無郡縣兵民可轄,因此率多爲要塞督。
關於此戰略構想的施行,孫權曾與諸將討論,最後決定采納偏將軍吕蒙的建議。《吕蒙傳》稱其“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云云,此即正式建設要塞基地之先例。至於《吴録》則載謂:
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吕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注]見《三國志·吕蒙傳》注,卷五十四,第275頁。
此爲選擇於濡須立塢之主因,而其戰略構想已將攻防兼備考慮在内,爲後來孫吴沿揚、荆二州長江南、北兩岸實施“夾江防禦”戰略張本。《三國志·朱桓傳》敍黄武元年(222),吴王孫權與曹魏決裂,魏軍大舉攻吴,而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濡須督朱桓勉勵所部,謂“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足見濡須立塢之重要與險要。
朱桓曾以蕩寇校尉“督領諸將”討平丹楊、鄱陽山賊,稍遷裨將軍,後代周泰爲濡須督,而《三國志·周泰傳》載泰原以别部司馬領兵,數從權征戰,曾陷陣救權,遂以戰功補爲濡須口對岸的春穀長。本傳續載:
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
假如謂縣令級的春穀長周泰,自赤壁之戰後的建安十八年正式首任濡須督,至二十四年改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而後始由裨將軍朱桓代之,恐怕不符史實。因爲此期間曾出任濡須督者,起碼尚有蔣欽、吕蒙二將。
《蔣欽傳》謂建安二十年欽以討越中郎將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逍遥)津北,欽力戰有功,遷蕩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右護軍”;《吕蒙傳》亦謂從“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扞衞。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是則孫權稱王以前,先後出任濡須督者爲春穀長周泰、蕩寇將軍蔣欽以及廬江太守吕蒙,最後才是裨將軍朱桓。[注]逍遥津之役發生於建安二十年,明見《三國志·甘寧傳》,卷五十五,第1294—1295頁,《賀齊傳》亦然,但蔣欽還都時間不詳;至於《吴主權傳》將中分荆州及征合肥二役統繫於十九年,殆誤,或許曹軍於十九年來征,二十年遂發生逍遥津之役。《吕蒙傳》所謂“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應在二十一年;魯肅卒於二十二年,故蒙是年移屯陸口,尋拜漢昌太守。
總之,濡須塢爲孫權早期建立的戰略要塞,作爲要塞之督,是隨時在據點遂行要塞保衛戰的指揮官,而與統轄數郡乃至一州之地、執行區域防禦之軍區督有所不同。要塞督既帶有相當濃厚的戰將性質,故初期位階僅爲縣令、中郎將等級,且多不領郡縣,稍後始遷至偏裨將軍或雜號將軍等級。因此,建安十八年曹軍於濡須口攻破孫權之江西營,恐怕是屯駐於濡須塢外而受濡須督指揮之别營,至於所獲之都督公孫陽,則應是此營的指揮官,此編制與孫軍當時新形成之“督―都督―戰兵”野戰體制正相符合。
無論如何,孫策死前攻佔揚州原有之江東四郡,再將之分爲五,自以討逆將軍領會稽太守,而以吴景爲丹楊太守,孫賁爲豫章太守,朱治爲吴郡太守;並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是故建安五年孫權統事後,曹操雖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但轄區仍僅有此五郡,至多再包有赤壁之戰前夕從黄祖手中奪來的荆州江夏郡部分地區而已,所轄尚不及原揚州刺史部之大。即使降至赤壁之戰後的建安十四、五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備自領荆州牧時,孫權實際所轄幅員仍無太大改變,所領徐州牧不過只是遥領虚銜罷了,是以始終不需建立州郡都督的軍區體制,甚至連要塞督也未落實施行。若是,則以左將軍領荆州牧的劉備,向並未施行軍區都督制之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孫權“求都督荆州”,乃是絶不可能的情事,應是“求董督荆州”——即求加重總督荆州事務的全權——之訛誤,前拙文二已詳究之,於此不再贅説。
三、 荆州三役所見孫、劉兩軍督軍督將之演變
孫、劉、曹皆靠私募部曲起家,漸次依上述方式發展壯大,史傳所述已多,前拙文一既已析論述曹軍的發展,兹不復贅。此處僅欲以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後孫軍與劉軍的演變情況概略窺察此兩集團之都督制發展,而由孫吴方面始。
孫、劉本爲同盟,且結有婚姻,但是基於集團利益,天下並無永久的盟友甚至親戚。爲了生存與發展的利益,此下孫、劉兩軍曾發生過三次荆州之役:
第一次爲建安二十年(215)孫權以戰争方式向劉備索還荆州之役;
第二次爲建安二十四年(219)孫權襲取荆州之役;
第三次爲魏文帝黄初三年(漢昭烈帝章武二年,222)漢帝劉備報荆復仇之役。
兹依次序析述之如下。
前拙文二曾詳析孫權集團的國策與開國戰略魯肅早已代籌,即“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剿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周瑜死前且已着手整備軍隊,企圖實踐西攻巴蜀以及北伐襄陽之既定戰略。及至魯肅卒,吕蒙代領其職務與軍隊,密陳計策,建議“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史謂“權尤以此言爲當”云。孫權之所以贊同此策,蓋因其早已有必争荆州的構想,戰略目標極爲清楚明確之故。至於劉備的國家目標與開國戰略,則稍晚至諸葛亮始爲之代籌,此即二人在隆中所對的構想:
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争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吴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將孫、劉的國家目標與開國戰略兩相比較,則孫權之目標是欲創建帝業,故先求保守江東,再求西進發展,是以必争荆州以成“全據長江,形勢益張”之勢;而劉備則是欲興復漢室,因此必須優先北伐,故俟天下有變則從荆、益發動鉗形攻勢以滅曹。劉備構想既然如此,以故僅能對孫權采取守勢,並且因刻意結好,使自己缺乏適當的警惕與防範,是以對孫喪失了戰略上的行動自由權。據此可知孫權何以采取戰略主動且雖收回荆州三郡猶不滿足之原因矣。
第一次孫、劉荆州之役,概略如《三國志·吴主權傳》所載:
是歲(建安十九年)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吴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吕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前拙文二已述赤壁之戰前,雙方是否曾有戰後分地協議已不可知,而劉備則於戰後實有借得荆州地——僅南郡一郡——之事實,並將此郡析置爲南郡、襄陽郡與宜都郡三郡,故仍勉强可算爲向權借得荆州數郡之地。[注]胡三省於《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條注“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時,謂“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又云:“荆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似有意指射劉備貪得無厭。按: 荆江南岸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之地,本就是劉軍南徇所得,談不上由“周瑜分”之,故胡注不可信。至於江、漢間四郡,於赤壁戰後分爲曹、孫所佔,劉備又焉能欲兼得之 因此之故,所謂“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也者,蓋指分油口——後稱公安之地。其後劉備所欲借之荆州地,則指時正掌握在孫軍手中的南郡、江夏、長沙等地。事實上孫權僅借予南郡之地而已,其江夏、長沙部分則仍保留不借。由於劉“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是位於南郡江南之一小塊地區,且當時是貧瘠沼澤之區帶,是以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作爲借地之藉口耳;如果是分給長沙等四郡之地,則尚安能謂所給地少耶?裴松之於《上三國志注表》謂壽書“失在于略,時有所脱漏”,是則其所載借地之事即可作爲顯例,致使胡三省爲之誤注。筆者前拙文二即爲此而作詳辯,於此不再贅。因此,孫權“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則起碼應指此三郡而言。然而觀上述劉備推託之詞,不僅只是虚辭而已,且大似有曾答應孫權,若能借予南郡地,則將來地盤擴張之後,將連江南諸郡也一并割與孫權之意。其情若屬實,即是意謂劉備以江南諸郡爲餌,誘使孫權答應借江北之南郡地也,所以孫權對劉備之失信才會大怒,竟怒至決意破盟興兵。
爲此之故,當孫權判斷劉備託辭而虚與委蛇後,遂決然逕自任命接近其地盤的南三郡——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及至諸長吏被劉備授權之“董督荆州事”關羽驅逐後,乃決定敗盟開戰,毅然遣吕蒙督軍取此三郡,另遣原駐陸口的魯肅率部向西移防巴丘以禦關羽,自己則進駐陸口以爲諸軍的總指揮。由於孫權發起此戰時,是令原駐於陸口的魯肅進駐湘水、洞庭匯入長江口之要塞巴丘——也就是周瑜當年身死之地,而自己則進駐魯肅原駐地,兩軍分爲吕蒙部之掩護及支援,所以吕蒙乃能迅速取得三郡。相對的,劉備始終似未真切了解孫權的國家戰略,而又急於整治新佔領地益州,是以此戰未戰即已喪失先機。及至劉備親自率軍回援,進駐公安,卻未順江而下進攻巴丘,直指陸口;反而是抽調原被魯肅牽制之關羽,率部南下洞庭湖南部的益陽,欲與吕蒙争鋒以救三郡,是則劉備至此仍無意與孫權大決可以知矣,故謂軍事行動自由權盡失。由於魯肅、吕蒙兩軍之戰場態勢是外綫作戰,益陽地形亦不利於關羽,以故益陽會戰並未發生,而關羽軍則被魯肅、吕蒙成功堵截於益陽附近的關羽瀨,雙方呈現膠着對峙狀態,[注]《三國志·甘寧傳》載寧“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鋭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見卷五十五,第1294頁。按: 益陽縣上流是指湘水支流資水流經縣西北之地。會劉備得知曹操進軍漢中,懼失益州,以故遣使求和,此戰遂以中分荆州結束。
綜觀此戰過程,孫、劉均是親自督陣,而前綫兵力各約三萬人。據孫軍前綫諸將各本傳考察,彼等皆以不帶“督”銜的太守或雜號將軍指揮作戰。不過,劉軍董督荆州事的蕩寇將軍、襄陽太守關羽所部,此時恐怕已編有野戰都督之職(詳下),而主攻的孫軍吕蒙部主帥吕蒙,則是以偏將軍領尋陽令的官職督軍,另一别道主帥昭信中郎將吕岱亦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注]吕岱事見《三國志·吕岱傳》,卷六十,第1384頁。以阻拒掩護爲任務之魯肅,此時仍爲横江將軍、漢昌太守。兩軍主將編階如此,蓋與孫、劉二人此時也仍只是州牧、將軍之位階有關。且又由於此役既以和解分地的方式結束,以故雙方均未於鄰接地區,派駐以“督”統領隨時敵對作戰的駐軍。
第二次荆州之役發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趁關羽北攻曹仁於襄陽之時,派遣吕蒙等襲取荆州。
此役發生的關鍵因素,筆者以爲與孫權欲徹底完成其國家戰略有密切關係。因爲孫、劉雖中分荆州,大抵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但掌握於劉備手中的南郡(及其分置的宜都、襄陽郡),地緣戰略最重要,且位居吴屬長沙、江夏二郡之上游,對二郡下游的揚州威脅亦大,且使孫權“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的戰略目標不能達成,以故孫權非要取得不可,只是考慮時機上的問題而已。或許没有太在意孫權戰略構想的劉備,保有南郡實懷璧其罪,是其不智之舉,然而卻又不得不保有,否則其北伐的戰略構想即無以實踐。因此,荆州南郡之擁有與否,對劉備而言是兩難之勢,對孫權而言則是志在必得,厥爲此戰之關鍵因素,可以無疑。
戰前孫皎已以都護、征虜將軍、江夏太守的身份代程普督夏口,吕蒙則以左護軍、虎威將軍、漢昌太守代魯肅督陸口,孫權原本的作戰序列是仿赤壁之戰,欲令孫皎與吕蒙爲左、右部大督,領兵西攻,尋因吕蒙意見,遂改以吕蒙爲“大督”,孫皎爲後繼,前文已述。是役,孫軍因采取奇襲戰術,以故爲了鬆懈關羽之警惕戒備,吕蒙先稱疾回建業,密請以孫權的帳下右部督陸遜自代,權遂召遜爲偏將軍、右部督代蒙至陸口。陸遜既至,修書與關羽申其謙下自託之意,令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然後具啓形狀,陳羽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注]吕蒙、孫皎、陸遜當時官職各見《三國志》本傳,欺敵奇襲則分詳蒙、遜二傳,不贅。按: 此處謂孫皎任江夏太守,是因其代原江夏太守程普之缺也。尋擒斬關羽等。《三國志·吴主權傳》略載戰況云: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閏月,權征羽,先遣吕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别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十二月,(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荆州。
此役之所以能迅速以完勝結束,就戰略言,與孫權戰前充分秘密部署準備,君臣一心有關;而與關羽當時全力專注北伐,鬆弛對孫軍警戒,且留部異心不齊亦有關。就戰術言,關羽主力集中於前綫北伐,而在孫軍奇襲之下,留後大本營公安先降,導致行政中心江陵必不能保,故孫軍之作戰可謂選擇非常正確。
嚴格而言,關羽之北伐不能謂完全違反既定國家戰略,只是劉備尚未部署妥當,而關羽即擅自北伐而已。蓋建安二十三年秋曹操西征劉備,另命征南將軍曹仁討關羽,屯樊城,以故劉備集團此時的作戰態勢是兩綫被攻而非鉗形北伐。及至翌年三月曹操軍臨漢中,於陽平與劉備相拒,而南陽間則因苦繇役,郡治所在之宛城守將侯音等與吏民共反,連和關羽,使關羽認爲有機可乘,遂率都督趙累等擅自冒險出兵。由於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迅速屠宛斬音,於是關、曹兩軍乃正面交鋒。會霖雨十餘日,沔水暴溢,曹軍立義將軍龐悳部爲水所困,乃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今日,我死日也!”奮戰不降,爲羽所擒殺。[注]詳《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二十四兩年諸月條,及同書《龐悳傳》,卷十八,第546頁。並且,假節鉞率軍來援的左將軍于禁,此時也因沔水暴溢之故,七軍皆没,而降於關羽。[注]詳《三國志·于禁傳》,卷十一,第524頁。
筆者之所以如此冗贅,蓋爲指陳劉、曹、孫三支軍隊的戰時編制。可以説,三支軍隊發展至此,基本上仍皆是漢制的將軍領兵制,但已有些變化,即將軍之下置有督將,而劉軍之督將更直稱爲“都督”,位於太守之下,應是劉備地盤擴張、兵力壯大後沿襲董卓以來的新編制,且可能在第一次荆州之役時期已施行。至於孫軍編制中,吕蒙、孫皎皆以將軍督軍,在作戰序列上,吕蒙更直任爲“大督”,孫皎爲繼督,其實俱爲大督。孫軍很早即編有以大都督、都督爲稱的野戰督將,而此戰既置大督爲總帥,則其下亦必援例編有諸督以遂行作戰,陸遜之爲右部督應即爲其一例。置大督以爲戰役總帥,不必最高統帥事事親征之例既開,故第三次荆州之役時吴軍遂置有“大都督”的編制——自此將“大都督”取代“大督”以爲戰役總帥也,於是孫吴之都督制乃開始漸有眉目。
第二次荆州之役結束於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翌年(220)正月魏王曹操薨,子丕嗣位,同年十月丕受漢禪,改元黄初。又翌年——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四月,漢中王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章武元年七月,漢帝劉備親征孫權,遂發生第三次荆州之役,不過兵敗而退,孫、劉互争荆州經年,至此乃止。
先主劉備出兵之前,已被曹操生前表爲假節、驃騎將軍、領荆州牧、南昌侯的孫權,遣使向魏帝曹丕卑辭稱臣。魏侍中劉曄建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强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强其衆而疑敵人耳。……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矣。”[注]劉曄之言見《資治通鑑》魏黄初二年八月條,卷六十九,第2192頁。按: 《三國志·劉曄傳》無載此言;又,劉備若已起兵,則魏斷無不知之理,何以劉曄所謂“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竟是推測之辭,而《資治通鑑》則繫之於八月?事有可疑,待考。不過,所謂孫權“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則殆爲實情。曹丕不納,遂受權降,遣使策命權爲吴王,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注]策文見《三國志·吴主傳》黄初二年十一月條,卷四十七,第1122—1123頁。按: 當時曹丕已踐祚稱帝。使權能專心抗備。翌年——黄初三年(222),孫權在擊敗漢軍之後,復與魏破裂。魏文帝興兵致討,吴與漢復交,建元黄武。
《三國志·陸遜傳》扼載吴與蜀漢第三次荆州之役概況云:
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注]《三國志·吴主權傳》作“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見卷四十七,第1122—1123頁。按: 竊疑此處第一個“督”字乃是“大都督”的省文,而又省卻“假節”二字。蓋“大都督”與“都督”爲孫軍作戰系統的戰時編制,説已見前。由於孫軍先前有“大督”之名,故此處孫權以軍區都督——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吴王——之身份,任命陸遜爲作戰系統戰時編制之假節、大都督。州都督任命其屬下爲戰時野戰軍主帥之大都督,驟看似不合體制,其實正合魏晉定制前初起之漢末制度也;而孫權已册吴王,故陸遜所假之節,應即爲吴王之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注]馮習或謂是護軍,如《三國志·潘璋傳》載“劉備出夷陵……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卷五十五,第1300頁。按: 護軍多有本官,如第二次荆州之役吕蒙以左護軍、虎威將軍領漢昌太守,或許馮習是以某將軍充護軍,故史傳多稱其爲將軍。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别督,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
(遜)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由於孫權已被封爲吴王,以故此次征伐用兵的作戰編序遂以假節、大都督爲統帥,朱然等督則殆爲其下之督軍,是以火攻時諸軍同時俱攻;至於漢帝劉備雖自親征,但其軍捨船就步,非順長江而下,故江南陸路主力亦編置大督、别督諸職,與吴軍名異而實同,江北别動則命黄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注]《三國志·黄權傳》明確謂權“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未謂是江北諸軍大督,尋因江南軍敗退,江北軍亦因道路隔絶而不得還,以故黄權率所部降於魏,見卷四十三,第1044頁。其實也就是“别督”之一,所部即是爲防範魏軍側翼來襲的掩護部隊。若史書所記可信,則此戰即應是三國初始,敵對雙方戰役編制有征伐大都督之始見,只是漢軍此役首次編有“大督”,而未如吴軍般直稱“大都督”罷了。先前孫軍襲荆是以吕蒙爲“大督”,孫皎爲繼督,劉備蓋仿於此歟?然而溯其源,兩軍實皆沿承靈、獻之際董軍的野戰編制也。
又按: 黄武元年即魏黄初三年、漢章武二年,此時魏文帝曹丕已建立作爲大帥級的軍區(州)都督制,但吴、蜀尚未實行。不過,東漢後期督軍制原就從監軍性質而兼向統帥性質傾斜發展,因此督軍作爲征伐軍統帥的性質愈後愈明顯,只是將征伐“都督”提升至大帥級職稱,是以曹操於建安二十二年任命夏侯惇爲始,而職稱提升爲“大都督”,則是以孫權爲先。或許因吴王權當時已是魏臣,以故承用魏此甫行的新制而變化之,也因此“大都督”的職稱亦可視爲魏制的職稱。至於漢帝劉備,則因其國號仍爲漢,以故仍沿用漢之舊制歟?再者,孫軍在第二次荆州之役前已有將護軍充作主帥的傾向,故大將頗加護軍、都護諸職,劉備此役亦以護軍馮習爲大督,[注]據《三國志·潘璋傳》,謂“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云(卷五十五,第1300頁),可能馮習是以某將軍、護軍充任戰時的大督。恐怕也是沿承漢末以來護軍督軍化之趨勢,而兼采吴軍之體制也。
不僅此也,東漢督軍制的功能主要在監軍指戰與監督駐軍,而在陸遜假節爲大都督以前,吴軍戰時各級指揮官編有大督、督以及其下的都督諸等級,亦有左、右、前、後部督等作戰序列之分,戰鬥職能分化頗細。例如前引《甘寧傳》,謂寧拜西陵太守時云:
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魏太守)朱光。計功,吕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
是則皖城之戰,孫權親征,甘寧所任升城督在作戰序列是攻城指揮官,其部下之都督則爲攻城的分隊隊長。戰後論功之所以以吕蒙爲最而寧次之,是因甘寧之任升城督實爲前敵總指揮吕蒙所薦。[注]《三國志·吕蒙傳》:“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卷五十四,第1276頁。因此,此役的作戰序列應爲: 統帥(行車騎將軍孫權)―督(前敵總指揮左護軍、虎威將軍吕蒙)―升城督(攻城部隊指揮、西陵太守甘寧)―都督(攻城分隊指揮)―兵(攻城戰士),其節制層級甚爲明確。
至於此戰之前,《吕蒙傳》載蒙曾以偏將軍領尋陽令,後督濡須駐軍云:
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第一次荆州之役)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右部督)淩統以死扞衞。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
濡須口是孫權戰略東綫之江北要塞,吕蒙勸權夾水口立塢以爲平時之備,所以其後張遼等來攻時,孫權遂以蒙爲濡須督——濡須要塞指揮官,其下之作戰序列則尚有右部督、蕩寇中郎將、領沛相甘淩等。[注]《吕蒙傳》見同上注1275及1277頁。甘寧本官見《三國志·甘寧傳》,卷五十五,第1296頁。
由以上二例及《三國志》與《晉書》其他吴將諸傳事迹所載,知孫權稱帝前即於長江南北兩岸相當於村級、鄉級或縣級要塞——如公安、樂鄉、夏口等地皆因地居衝要而建城,當時實未置縣[注]參《水經注疏·江水三》楊守敬疏,卷三十五,第2874頁。——逐漸派置駐軍,指揮官則是以該要塞命名之督,用以實施“夾江防禦”的軍事戰略。這些要塞督督兵於要塞,彼此之間構成互相支援的防禦綫,有事則發兵相繼,此即吴軍所謂的“江渚諸督”。江渚諸督的設置用於防禦而非用於進攻,曾經引起濡須督鍾離牧的遺憾;[注]“江渚諸督”用於防禦而非用於進攻,鍾離牧由公安督遷濡須督,即曾以此引以爲憾。詳參《三國志·鍾離牧傳》並裴注所引之《會稽典録》,卷六十,第1393頁。而吴末名將巴丘都督陸凱則曾欲進諫,直謂“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云,更可概見江渚諸要塞的兵將,其平時與戰時之任務實僅止於此。[注]參《三國志·陸凱傳》,卷六十一,第1407頁。當然,這些要塞督並非一時之間同時並置,而是隨着孫權的開疆拓土而陸續設置者,且因其彼此之間具有互相支援的戰略關係,以故其後有些要塞督遂可能由督要塞漸漸擴大爲督軍區,如前述的陸凱由巴丘督升爲巴丘都督即是其例。此中最明顯之例並非陸凱,而是在第三次荆州之役後,陸遜由征伐野戰軍大都督統兵留駐西陵,漸由西陵督實際成爲孫吴最重要的大督區主帥——西陵都督,逼使蜀漢也不得不於永安要塞置督,漸成巴東都督。
孫權要塞督設置的時間以及督區的擴大多不可考,其指揮官之職名頗常見於史傳者,厥有濡須督、夏口督、虎林督、沔中督、西陵督、巴丘督、武昌督、蒲圻督、京下督、都下督、廣州督、徐陵督、江陵督、蕪湖督、無難督、牛渚督、柴桑督、武昌督、樂鄉督、公安督、中夏督等。及至吴朝建立以後,都督地位漸提高至在督之上,以故有些較重要或督區擴大後的指揮官職稱也改稱爲都督,此即已是郡級的擁節軍區都督矣,如夏口督孫壹奔降於魏後,魏帝稱其爲“吴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羡侯孫壹”,[注]見《三國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紀》甘露二年六月乙巳詔,卷四,第140頁。只是較常見於史傳者蓋爲西陵都督、樂鄉都督等軍區都督罷了。這些要塞督之漸變爲擁節軍區大督或都督,應是孫吴仿效魏晉施行常都督制而漸變的結果,但運用起來似乎更爲靈活而得心應手。
關於要塞督與軍區都督之演變及分際既明,則都督制研究權威嚴耕望先生所論吴都督區或許有些矛盾誤會之處,[注]嚴先生所論請參前揭書第27—34頁,此處非必要不再贅引頁碼。於此僅提供鄙見以概略説明之。
按: 孫軍野戰諸督在孫權猶是行車騎將軍、徐州牧時代,率多以都尉、校尉或中郎將充之。孫氏父子對所部采行世襲領兵制,故這些軍官父子兄弟繼襲之間,率多督原部留駐原地,並漸加“督”名。隨着勢力壯大,要塞漸多,孫權遂逐漸以雜號將軍充任要塞督。及至原爲野戰基層軍官之“都督”,名位發展至將軍級别,漸居“督”之上,遂建立起仿傚魏晉體制之軍(野戰軍)都督制以及常(州郡軍區)都督制,使“都督”提升爲征伐戰役大帥或軍區防禦大員之職稱。此種變化發展,與孫軍最高統帥孫權由行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大將軍,以至接受封王及獨立稱帝的身份改變有關。
例如,第二次荆州之役後,行車騎將軍孫權襲殺關羽而還,拜平南將軍吕範爲“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注]見《三國志·吕範傳》,卷五十六,第1310頁。及至孫權被册封爲使持節大將軍督交州領荆州牧事吴王後,綏南將軍領南郡太守宣城侯諸葛瑾則於“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注]瑾傳見《三國志》,卷五十二,第1233頁。降至孫權稱帝後,拜假節左護軍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步騭“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注]騭傳見《三國志》,卷五十二,第1237頁。按: 陸遜在第三次荆州之役大勝劉備之後,加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治所蓋在西陵,鎮守三峽以防蜀漢。及至黄龍元年吴王權稱帝,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直至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猶詔“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詳見《三國志》卷五十八本傳。據此,姑不論步騭“代陸遜撫二境”所指確爲何地,要之陸遜鎮守西陵,有“都督西陵”之實而卻無其名,是以嚴先生謂“西陵都督始於陸遜,但遜傳不云督”(前揭書,第29頁)。鄙意名實之間或許尚值斟酌,蓋孫吴當時尚未以“都督”作爲軍區統帥之職稱也。此三例,由吕範之督扶州以下至海而未擁節,至諸葛瑾之假節督公安,以至步騭之假節都督西陵,均可證諸人的官爵隨着孫權身份的改變而水漲船高,由無節督變爲擁節督以至變爲擁節都督的制度性發展。孫吴此常都督制發展雖晚於魏晉,但其受魏晉制度的影響則無可置疑。
四、 吴祚建後之由要塞督發展至軍區都督
孫權在赤壁之戰後、第一次荆州之役前,即是行車騎將軍時期,已開始於要塞設置督將,如前述濡須口之部署即爲明例。在第二次荆州之役襲取荆州後,領地大拓,但由於“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的戰略目標尚未完全達成,而戰略情勢卻已從主動變爲被動——即需北防曹操、西拒劉備之態勢變化,以故孫權遂逐漸於緣邊置督,並日益推廣之,甚至於其上設置大督或都督以爲統御。
荆州西部地區是孫吴北防曹操、西拒劉備最吃重的區域。兹從此地區開始,順長江東下,折南至交廣,略論其戰略情勢以及置督或置大督以及都督的情況,以概見孫吴此制的發展演變。
據《吕蒙傳》,偏將軍領尋陽令吕蒙於魯肅死後,奉令“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當時魯肅、吕蒙均未以督爲名,而是以太守統領政軍。及至吕蒙獻計襲取荆州後,拜南郡太守,尋卒,由朱然繼其領軍之任。《三國志·朱然傳》載云:
朱然……本姓施氏……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别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虎威將軍吕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黄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
黄龍元年(吴大帝權稱帝元年,229),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吴大帝,234),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赤烏十二年卒。……子績嗣。……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是知朱然雖以將軍假節鎮江陵,但猶無江陵督或都督之類名義,而卻有督將之實。其督所部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劉備,正是當時假節大都督陸遜所督五萬人的戰時督將之一,蓋由軍區督將轉爲野戰督將,率江陵所部編入陸遜之作戰序列也。直至十三年後的嘉禾三年,孫權已稱帝,並與蜀漢恢復盟好,漢、吴相約分道大舉攻魏,而朱然與全琮猶且分任吴軍之前敵左,右督,戰時編制仍與赤壁之戰時相當,可見孫吴都督制的發展相當遲緩,落後於魏。又,依世襲領兵制的慣例看,朱然之子朱績既襲業爲樂鄉督,則朱然死前似應是以左大司馬右軍師充任此督,情況頗似當年陸遜之在西陵而鎮荆州也,故嚴耕望先生謂“江陵實無督”,朱然之所謂鎮江陵,其實是“以樂鄉在江陵對江不遠,屯樂鄉,即以鎮江陵也”。[注]樂鄉於兩漢尚未從荆州崛起,據《水經注疏·江水三》,樂鄉在江陵長江南岸,屬孱陵縣之一城,城爲陸抗所築;然楊守敬疏則謂朱績時已有,抗蓋改築耳,去江陵五十里。見卷三十五,第2872—2873頁。另外宜注意的是,諸葛瑾之子融襲任爲公安督、步騭之子協襲任爲西陵督後,孫權特命朱然總爲大督,嚴先生認爲是謂朱然“除督江陵外,又兼總西陵公安兩督也。大督即都督之謂”。[注]參嚴著前揭書,第28—29頁。
筆者按: 江陵實有督,只是明確見載之時間均在吴末,[注]如《三國志·陸遜傳·子抗附傳》載抗爲樂鄉都督,“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卷五十八,第1355頁);又吴亡之年——天紀四年(280),晉攻吴,杜預“斬江陵督伍延”(《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卷四十八,第1174頁;《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二月條作“杜預克江陵,斬吴江陵都督”),皆是其例。而自周瑜以降、朱然以前歷任南郡太守或在江陵領兵者,則的確未見以督爲名。江陵原爲南郡之治,吴改爲荆州治,南郡則移治公安,要之江陵始終爲荆州之都會,曹操當年即以江陵有軍實而精騎追擊劉備,降至吴時,江陵仍以城固兵足見稱。《三國志·陸遜傳·子抗附傳》曾載西陵督步闡叛亂,樂鄉都督陸抗往征之事,概可窺見江陵以及其附近要塞之戰略形勢與部署:
鳳皇元年(吴主皓,272),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彦、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
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車。抗聞,使咸亟破之。……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
由此可見,作爲長江上游大都會之江陵,地勢平衍,水陸俱利,四通八達,具有極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因此必須建設得城固兵足。由於荆(江陵)、襄(襄陽)之間有荆襄大道直接貫通,其側另有一條輔道;而由襄陽下沔水南至揚口(即中夏口),[注]《水經注》載揚口在江陵東南二十里豫章口東,爲夏水之首,見卷三十,第2866頁。西折入揚水,亦有水道至江陵,以故在水陸交通俱利的情況下,[注]關於江陵的水路交通,請詳嚴耕望先生之《荆襄驛道與大堤豔曲》,《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第1039—1078頁。形勢對禦敵防守反而不利,當日赤壁之戰時劉備入夏水西折江陵,迫使曹仁棄守即取此道。於是,孫吴遂於襲取荆州之後,在江陵周圍要塞之地陸續置督,如其西的西陵(黄武元年改夷陵爲西陵),其南的樂鄉、公安,其東的中夏口,皆爲拱衛江陵之戰略要塞,因此皆先後置督,[注]嚴耕望先生前揭書歷數孫吴督區,而遺中夏督未提,蓋此地置督恐爲較晚之事。例如陸抗病死於鳳皇三年,其子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景以尚公主而拜偏將軍、中夏督,後皆爲晉軍所殺(《三國志·陸遜傳》,卷五十八,第1360頁);《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録》亦載翻子忠爲宜都太守,“晉征吴,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卷五十七,第1327頁),顯示中夏督應是很晚才置之督。以利江陵之戰略防禦。由此反思當年赤壁新勝,孫權接受魯肅之勸,借江陵等地給劉備,恐怕即與自忖防禦體系尚未建立,故借地予備以“多操之敵”,免得獨承曹軍壓力的考慮有關。而鳳皇元年此役,陸抗不怕羊祜之主力南下來攻,並大言即使攻下江陵也“必不能守”,即因江陵防禦體系已建設完成之故。
此理既明,於此再據此役觀察樂鄉都督陸抗的指揮部署,以證諸督之關係。
筆者以爲,孫吴緣邊國防綫由西陵順長江東流,出海折經東南諸郡南延至交、廣,所置諸督中厥以西陵督承受戰争之壓力最重,蓋因此地區是孫吴最直接北防曹魏、西拒蜀漢而兩面受敵之唯一戰略要地。爲此,難怪孫權奪取荆州之後,遂即任用陸遜爲荆州牧而卻駐節西陵,無都督西陵之名而卻有其實,甚至後來西陵督有時升格爲西陵都督,乃至西陵都督與樂鄉都督並置。由於西陵有此極重要的戰略地位,對江陵正面及側翼防禦——正面對魏、側翼對漢——尤爲重要,故當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引致晉軍分從正面及側翼來攻時,遂令江陵之安全出現重大缺口,致使陸抗寧捨江陵而親自督軍西征,以奪還江陵之側翼要塞,阻止已抵近西陵的晉軍繼續挺進,鞏固江陵的防衛。[注]此役之後九年,吴亡。就戰事而言,主因厥在建平、西陵側翼之失守,晉巴蜀水軍順流而下,與荆州都督杜預指揮的晉軍夾擊江陵而輕易取之,然後再順流而下攻抵吴京。其後隋軍攻陳亦是如此,可謂歷史之重演,亦可見西陵戰略地位的重要。筆者對此兩役曾作分析比較,請詳拙著《隋史十二講》(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之第四講,及《隋平陳之戰析論——周隋府兵改革成效的一個觀察》,《中國中古史研究》11,2011年。在陸抗率領樂鄉大營主力西征前,已敕令江陵督張咸破堰放水固守江陵城,另令近在油口的公安督孫遵巡弋南岸兼接防樂鄉,防禦羊祜,以爲戰略預備隊。由此可知,自三峽以東,宜都(治西陵)、南郡、武陵以至長沙的洞庭湖以西長江一綫,在孫權時已開始陸續於戰略要地——西陵、江陵、樂鄉、公安、中夏、巴丘等地置督,雖或有督名,或無督名,但基本上多爲要塞督,只負責督當地駐軍,[注]如樂鄉與公安地隔油水,二地均屬江陵長江對岸孱陵縣之地,只是樂鄉更近江陵,僅一江之隔而已。是則一縣兩地並爲軍事要塞,俱無戰略縱深可言,故應只是督當地駐軍而已。使此地區呈現點狀防禦態勢;然而至遲降至吴大帝權後期,已任命樂鄉督朱然爲大督,兼總西陵、公安二督,遂使荆州西部地區之軍事出現統一指揮,沿江由點與綫構成長條型的防禦區——即後來都督區性質之軍區,而由大督兼督督區内的諸要塞督。於是,“夾江防禦”的軍事戰略乃得以實行。
據此以觀,“大督—督—都督—戰兵”之原孫軍野戰編制,本與軍區制無關,此時由野戰制移用於軍區制的變革之際,嚴先生謂此軍區大督實質相當於魏晉的軍區都督可,但謂其“即都督之謂”則頗爲不妥。蓋縱使然子朱績繼襲爲樂鄉督,且至“永安(景帝休,258—264)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注]引文原標點爲“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按: 孫吴軍制頗常加將軍以都護、護軍、左護軍、右護軍、左軍師、右軍師等銜,績父朱然先任車騎將軍、右護軍,後任左大司馬、右軍師即可爲例,故筆者凡於此等處皆改正其標點。績事迹附見其父朱然傳,引文見卷五十六,第1309頁。亦僅表示朱績之樂鄉督督區擴大而已,甚至似有大督之實而竟無其名,而景帝更未假之以都督之稱。其後孫吴仿行魏晉常都督制,此督區之主帥始擁有“都督”之名,而以陸抗正式出任樂鄉都督,[注]《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載鳳皇元年八月征西陵督步闡時,正式稱陸抗爲樂鄉都督,見卷四十八,第1169頁。但已接近吴之末期矣。陸抗原爲征北將軍·柴桑督,《三國志·陸遜傳·子抗附傳》載云:
永安二年(景帝休,259),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晧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吴主皓,270),大司馬施(朱績復本姓施氏)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按: 陸抗遷爲西陵都督,都督區“自關羽至白帝”,嚴先生釋“關羽”爲位於洞庭湖南方益陽縣之關羽瀨,故謂陸抗的西陵都督區與其後來擔任的樂鄉都督區全同,惟治所有遷徙耳。不僅如此,此都督區亦勢必與時任實際樂鄉大督朱績的督區——自巴丘上迄西陵——重疊。若史文無誤,則荆州西部此時殆或西陵都督與樂鄉大督二都督並置,只是二都督區究竟如何劃分,史文所述恐有問題;[注]嚴説請參嚴先生前揭書,第27—28頁。按: 吴分宜都郡置建平郡,治白帝東之巫縣,信陵爲江水過巫縣進入西陵峽的要塞,屬建平郡,故謂西陵都督區與樂鄉都督區實際全同。又,下文述吴亡之役時,西陵與樂鄉即分置有二都督。吴亡於天紀四年(280,晉咸寧六年),距朱、陸二人任都督約二十年而已,故荆州西部此時一度實行二都督並置,殆亦不能謂全無可能。若史文有誤,則陸抗應僅是西陵督,隸屬於樂鄉(大)督朱績,故西陵屬於樂鄉(大)督區之督統範圍,所謂“督自巴丘上迄西陵”是也,[注]筆者以爲,陸抗的西陵都督區與朱績的樂鄉大督區應無可能同時重疊存在,故陳壽所書必有一誤。觀陸抗僅爲鎮軍將軍,而朱績已拜上大將軍、都護,則陸抗恐怕當時只是“拜鎮軍將軍,督西陵”,何況實爲大督的朱績亦僅稱“督自巴丘上迄西陵”而已。亦即是説,陸抗先爲西陵督,隸屬於實爲大督的樂鄉督朱績,及至朱績卒後,陸抗乃晉拜爲樂鄉都督,“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接管朱績所遺的大督區,而移治於樂鄉。真相是否如此,或待更多證據出現始能確定。何況白帝爲蜀漢之重鎮,焉可能被吴劃入西陵都督區耶!真相如何,殆待進一步確考。
不過無論如何,從第二次荆州之役襲得荆州後,孫權的戰略形勢是北防曹魏、西拒蜀漢,以故必須以江陵爲荆州西綫的戰略中心,於舊南郡、武陵、長沙三郡之長江流域廣置要塞督。要塞督之間互不統屬,兵力亦大小不一,是以孫權晚期遂於諸要塞督之上設置大督,俾使軍令能統一指揮,而形成(軍區)大督區—(要塞)督區的區域防禦體系,與野戰系統之大督—督體制相呼應,最後仿行魏晉常都督制,於吴朝後期漸漸形成都督區—督區的制度。雖然如此,孫吴其他督區的發展,與此戰略吃重區之發展並不完全一致。
吴朝末期荆州西部之要塞督,有時也沿用東漢以來制度稱爲監,如《晉書·世祖武帝紀》太康元年載是年晉軍伐吴之概況云:
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楊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吴江陵都督伍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即公安)。
所謂“夷道樂鄉城”,恐應標點爲“夷道、樂鄉城”,因爲吴之樂鄉不在宜都郡之夷道縣,而在江陵對岸南郡之孱陵縣。江陵、樂鄉夾長江段水深江闊,江中有許多沙洲,大者可戍兵,《水經注疏》已備言之。因此,此都督區不論以江陵或樂鄉爲名,治所之所以常設於樂鄉,大概是與其地居於州治江陵以及郡治公安之間,宜治水軍,地緣戰略重要有關。由上述戰役可知,吴西陵都督下有西陵監,夷道有夷道監,而二地在行政上均隸屬於宜都郡,是故二監應皆是戰時要塞督之加重,以隸屬於因戰争需要而升格之西陵都督。事實上,據《資治通鑑》是月條所載,晉巴蜀水軍是先擊破吴丹楊監盛紀所部,然後順流次第攻克西陵,殺西陵都督留憲、西陵監鄭廣;再克夷道,殺夷道監陸晏,直逼樂鄉;樂鄉都督孫歆與戰,大敗而還,於心理不穩之際俾杜預乘機輕兵偷襲,失手被擒。保衛江陵主力之樂鄉既失,於是杜預遂能揮軍直破江陵,斬殺江陵督(或作江陵都督)伍延。
本戰,《資治通鑑》謂“斬獲吴都督、監軍十四”云云,[注]詳《資治通鑑》是年月條,卷八十一,第2561—2562頁。又前揭拙著《隋史十二講》之第四講對本戰已有詳析,於此不贅。可見此戰區於吴末設置都督區以及要塞督或要塞監之多,而都督與要塞監、要塞督之間的運用靈活,爲曹魏、蜀漢二軍所鮮見,故是孫吴軍區制之明顯特色。
前謂孫吴緣邊國防綫由西陵順長江東流,出海折經東南諸郡南延至交廣,所在要地多置督,只是以西陵督承受壓力最重,是孫吴直接北防曹魏、西拒蜀漢之唯一戰略要地。其他各地諸督以及大督——當時多未以“大督”或“都督”爲稱,嚴耕望先生前揭書已率多有所論考,故此處僅據其説,欲對其未論及或頗有問題之處略作補充,俾使對孫吴都督制發展施行之情況,了解得較爲完整而已。
按: 荆州西部都督區不論其主帥稱西陵都督或樂鄉都督,對吴而言皆爲大軍區,轄境不論是“自關羽至白帝”抑或是“自巴丘上迄西陵”,皆指東至洞庭湖之長江流段。在此流段中,關羽瀨(吴時屬衡陽郡益陽縣)並未置督,而巴丘則爲湘水與洞庭湖入接長江的要塞,吴建有邸閣城,[注]見《水經注疏·江水三》及熊會貞疏,卷三十五,第2882頁。以故置有巴丘督,且一度升格爲巴丘都督。巴丘督或都督僅見於《三國志·陸凱傳》:
陸凱……丞相遜族子也。……五鳳二年(吴主亮,255),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累遷蕩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寶鼎元年(266),遷左丞相。
巴丘督以偏將軍充任,故應是要塞督;但巴丘都督以假節的鎮西大將軍領荆州牧充任,則必已是大督,只是是否統轄全武昌右部則不詳。要之吴大帝崩才三年即見有巴丘督,則此督或可能爲大帝所置。巴丘督之東,順流需經陸口、夏口始能至武昌,而陸口是當年魯肅屯駐之地,此時則旁置蒲圻督;夏口是程普屯駐之地,此時置有夏口督。其間另有沔中督,殆置於夏口逆入沔水之某段流域,殆是針對魏江夏郡敵軍並掩護夏口而置。[注]詳參《三國志·宗室傳·孫静子奂附傳》裴注所引《江表傳》,卷五十一,第1208頁。夏口督與沔中督至遲置於孫權稱帝之時,[注]《三國志·宗室傳·孫賁子鄰附傳》載鄰累“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249)卒”(卷五十一,第1210頁)。按: 赤烏爲吴大帝孫權年號,故孫鄰死於大帝晚年,而此處之“夏口沔中督”應作“夏口、沔中督”,二督之置應不會晚於是年。則蒲圻督應亦爲孫權所置。觀陸凱以偏將軍轉督武昌右部,則此三督此時應不隸屬於武昌右部督也。
武昌原爲江夏郡之鄂縣。建安二十四年第二次荆州之役進行時,孫權進駐公安。黄初二年(221)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有來攻之意,孫權遂自公安移駐於鄂,改名武昌,並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同年七月漢帝劉備親征權,第三次荆州之役爆發;十一月,魏文帝策權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封吴王,遂以爲都。及至黄武八年(229) 四月吴王權稱帝,改元黄龍,九月遷都建業,乃徵坐鎮西陵之陸遜入輔太子登,並掌武昌留事。直至末主孫皓之甘露元年(265)九月,從西陵督步闡之建議而由建業再度徙都武昌;然於翌年寶鼎元年(266)十二月又還都建業,而以衞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此期間,先是陸遜以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治在西陵而坐鎮江陵,是孫吴最早有實無名的西陵都督。及至孫權稱帝,拜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徵遜輔太子,並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直至赤烏七年(244)代顧雍爲丞相,猶詔“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據陸遜入輔武昌之年,吴大帝另命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步騭“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應指宜都郡與南郡二境。步騭在西陵二十年而卒,由其子步闡繼業爲西陵督之例觀察,則原領荆州牧的實際西陵都督陸遜,不啻仍以荆州牧調兼有實無名之武昌都督,所謂“董督軍國”是也。
陸遜卒於赤烏八年(245)二月,吴大帝乃遷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注]見《三國志·諸葛恪傳》,卷六十四,第1433頁。但似僅代遜荆州牧之事,至於武昌地區軍事的部署則有所變化。《三國志·吕岱傳》云:
嘉禾三年(234),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潘濬卒,岱代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
按: 濬傳謂其爲太常,“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赤烏二年(239)卒,是則此年或稍後,蒲圻正式置督,而以領兵屯駐之鎮南將軍吕岱爲首任蒲圻督。在赤烏八年(245)陸遜卒後,大帝分武昌地區軍事爲左、右兩部,吕岱既“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則吴大帝時的蒲圻督應隸屬於武昌右部督,並一度由督改監,而由吕岱之子吕凱爲蒲圻監。易言之,吴大帝時期西陵都督應東督至巴丘督,再往東即歸屬武昌右部督統屬。是則武昌右部督此時雖不名大督或都督,但督區則與西陵都督區相若,殆至大帝崩後始有變化。及至吴亡之時,尚書虞昺被任命爲“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注]虞昺爲虞翻之子,其事見《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録》,卷五十七,第1327頁。以阻擋來伐晉軍,蓋亦武昌右部督之任也。
任武昌左部督者,可述之事概鮮,而有范慎差可紀。《三國志·吴主五子·孫登傳》謂黄龍元年孫權稱帝,立登爲皇太子,而范慎等皆爲其賓客,東宫號爲多士時,注引《吴録》云:
慎……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晧移都,甚憚之……以爲太尉。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爲之隕涕。鳳凰三年卒。
按: 《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繫慎死年於鳳皇二年(273),而於建衡三年(271)載“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是則范慎之武昌督實即武昌左部督的省稱,而慎任此職約四十年,難怪自恨久爲將。
不過,孫吴後期也頗似有意僅設武昌督或武昌都督一職,如魯肅之子魯淑,“永安(景帝休,258—264)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269—271)中,假節,遷夏口督”;[注]《三國志·魯肅傳》,卷五十四,第1273頁。前述宗室孫鄰之子孫述,曾“爲武昌督,平荆州事”。[注]《三國志·宗室傳·孫賁子鄰附傳》注引《吴歷》,卷五十一,第1210頁。孫述不詳何時出任,魯淑則應任於范慎擔任武昌左部督之時,故殆爲武昌右部督之省稱。或許建衡二年夏口督宗室孫秀投奔於晉,[注]孫秀爲孫泰之子、孫匡之孫,官爲前將軍、夏口督。史謂秀以公室至親,握兵在外,吴主晧意不能平。建衡二年,晧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詳見《三國志·宗室傳·孫匡秀附傳》,卷五十一,第1213頁。情勢緊急,是以就近調武昌右部督魯淑爲夏口督,是則此時武昌右部督都區已縮小,故夏口督不隸屬於武昌右部督歟?及至建衡三年初吴主皓圖謀大舉攻晉,當此之時,適值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陶璜大破交阯,光復九真、日南等地,故“徵璜爲武昌都督”。蓋此時右部督魯淑已遷夏口督,左部督范慎已拜爲太尉,是以徵璜還師,合左、右兩部而爲武昌都督一部,另圖大用歟?只因“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交州,而另任孫述爲武昌督——此似非左部或右部的省稱,並特加“平荆州事”一名,以代陶璜未赴之任耶?[注]請詳《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建衡三年條(卷四十八,第1168頁)及《晉書·陶璜傳》(卷五十七,第1558頁),此不贅引。按: 孫述雖是宗室子弟,但位望及戰功遜於陶璜,此可能爲任之以武昌督而非都督的原因。
武昌左部督東面轄地不知至何,但與武昌同屬荆州的江夏郡,而位於此郡最東之柴桑督,則似亦爲其統屬。柴桑位於長江南岸,夾江對岸介於武昌、柴桑之間的半州督,隸屬於揚州蘄春郡尋陽縣,似也應統屬於武昌左部督。但是,半州駐有屯兵蓋甚早,甘寧、潘璋皆曾以偏裨將軍屯駐於此;而孫權之子孫慮,於孫權稱帝之黄龍三年(231),亦曾以假節、鎮軍大將軍、開府治半州,而詔書稱謂“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内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云云,似有任其爲方面大督之勢。[注]孫慮治半州的時間見《三國志·薛綜傳》(卷五十三,第1253頁),詔書見《三國志·吴主五子·孫慮傳》注引《吴書》(卷五十九,第1367頁),而慮本傳則載其卒於嘉禾元年。又,嚴先生前揭書謂半州在尋陽縣。至於張昭之侄張奮,則於昭卒於嘉禾五年(236)以前爲領兵將軍,因“連有功效,至半州都督”。[注]詳《三國志·張昭傳》,卷五十二,第1224頁。其文若無訛,則張奮殆是繼孫慮而督半州者,且爲孫吴首見而直以“都督”爲名之大督。此時陸遜未死,武昌尚未分爲左、右部督,是則當孫慮治半州時,與陸遜掌武昌一般,兩者俱是大督區,而亦均爲有實無名之都督也。由此時以至張奮之繼爲都督,陸遜似乎不大可能統轄之,即使武昌已分爲左、右部督,而左部督恐亦不能兼統之,除非半州都督降格爲半州督。可惜張奮後任之情況史料闕如,以故武昌左部督之督區至何,長江之揚州西部段置督情況如何,均已難明。只是因《三國志·賀齊傳》載建安二十一年,齊與陸遜討平長江下游鄱陽、丹楊一帶民變,而“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乃知皖以西約位於長江鄱陽湖段之吉陽督,極可能隸屬於左部督。[注]吉陽在何不詳,嚴先生前揭書疑在今安徽東流北三十里處,暫從之。因半州都督後來極可能降格爲半州督,是以判斷其可能隸屬於武昌左部督。也就是説,武昌左部督督區可能包括揚州蘄春郡之半州督,以及揚州廬江郡之吉陽督。若還合武昌左、右兩部督區看,則陸遜當日所掌有實無名的武昌都督,可謂與其先前所掌亦是有實無名的西陵都督區幅員相若。
賀齊以安東將軍督扶州以上至皖,可算是孫權爲行車騎將軍時最早設置的軍區大督;及至第二次荆州之役後,孫權另任吕範以建威將軍督扶州以下至海,此則是與陸遜在上游鎮西陵之同時,在下游出現的有實無名大督。按《三國志·吕範傳》載云:
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
揚州丹陽郡爲孫氏根據地所在,以故長江此流段必須加强防禦,以免實行西進政策時被北軍或山越乘虚傾覆。因此,以扶州爲中心所分置之上、下督區,對建業安全可謂極爲重要,是以亦最早設置實質大督區於此。嚴先生前揭書謂扶州“必在建業濡須口間殆可斷言,或者即洞口牛渚上下歟”?按: 牛渚即采石,漢以來即爲江防要塞,故吴亡前牛渚督曾升格爲牛渚都督,[注]吴有牛渚都督何植,見天紀三年八月條,《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卷四,第1172頁。蓋欲加强防禦以確保建業安全也。姑以此塞爲中心觀察,則所謂“扶州以上至皖”也者,蓋從牛渚督逆溯長江,西經蕪湖督、濡須督、虎林督、皖口督諸要塞而止,再上已屬吉陽督地。易方向看,長江東出武昌左部督督區之吉陽督,與經皖口、虎林、濡須、蕪湖諸督而至牛渚督,剛好相接無縫。由此再連接“督扶州以下至海”,即是從牛渚督順流,經京下督、徐陵督而至海也。京下督殆在吴京建業之西長江、淮水(今秦淮河)交界處;徐陵爲京口所在,位於今江蘇丹徒縣西長江邊,《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條胡注,謂“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是也。[注]見《資治通鑑》該年月條,卷六十六,第2101頁。兩塞歷來皆爲保衛建業(今南京市)安全的重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謂樂鄉(或西陵)都督區是在夾江防禦戰略下部署的上游軍區,則武昌督區可算是中游,而以扶州爲中心之督區即爲下游。假如以江陵、武昌、扶州爲三中心之督區,的確曾督領其附近之各要塞督,而所督範圍與數目亦穩定,則後二者雖無都督之名,治所也不確知,但仍與前一都督區般,均各由兩個核心點——上游督區分爲西陵與樂鄉,中游直以武昌分爲左、右,下游亦直以扶州分爲上、下——構成,以此由點而綫形成夾江綫狀態勢的防禦。
長江由西陵東至海口夾江防禦綫既明,出海之後折經東南諸郡,於第二次荆州之役後,沿海先於屏障建業南面之吴郡設置吴郡都督,再南則置三郡督以督會稽、臨海、建安三郡,呈面狀防禦態勢。蓋吴郡都督與三郡督所防者,厥以最令孫吴頭痛的山越爲主,防海賊之重要性不大,並且由於討伐山越的任務常由中央派兵,而非由此二督督所部執行,以故此二督的事迹也較少見載,於此不贅。
經三郡督督區折西沿海而行,即至廣州(都)督區以及交州都督區。嚴先生只述廣州督,而認爲“都督廣州軍事”及“都督交州軍事”皆是晉制名號而不可信爲吴制,復對吴末交、廣二州用兵時的軍制似乎也頗有誤會,故稍冗述之。
交廣發展概略,據《晉書·地理下》交、廣二州條所載,其地於秦末曾爲趙他所據,漢武帝平之,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又置交阯部刺史以督之。其後郡數屢有調整,至順帝時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建安八年(203),張津爲交阯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請立州,乃將交阯刺史改爲交州牧,並拜張津爲之,尋移治番禺(今廣州市)。孫權乘亂佔有交部,吴王權黄武五年(226),割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爲交州。值亂,廣州復還并交部。直至永安七年(景帝休,264)孫皓即位,復以先前諸郡立爲廣州。此時期二州相當落後,至晉時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編户二萬五千六百,廣州統郡十,縣六十八,編户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人衆多無城郭,絶大部分人口均是不被編户賦役的南方民族種落。
在此情況下,交廣首次較大規模的民變,發生於蜀亡之歲的吴景帝孫休永安六年(263),當時交阯太守貪暴,百姓苦役,故郡吏吕興殺太守等,以郡内附於魏。魏南中監軍霍弋遣軍來援,“破吴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吴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陶)璜爲蒼梧太守”反攻,大破晉軍,遂復交阯。吴因用璜爲交州刺史。後來九真郡功曹李祚復保郡附魏,璜往拔之,“晧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可見此役吴軍仍依陸遜以來往例以“大都督”指戰,而亦仍漢制置監軍使者以監督之。[注]事詳《晉書·陶璜傳》(卷五十七,第1558—1560頁),但該傳將事件發生時間繫於“孫晧時”,蓋誤。《三國志·三嗣主·孫休傳》將事件發生原因繫於永安五年,過程繫於六年,《資治通鑑》據之,是也。陶璜曾戰敗,監軍責之,璜答以“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即謂己無充分的戰役指揮權之故。虞汜之職名,依漢征伐軍之例稱爲“監軍使者”(見其父虞翻傳,《三國志》卷五十七,第1327頁),監軍只是三國時之省稱。吴軍野戰大都督、都督與軍區大督、都督不同,前文已言之,是則戰後陶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蓋是吴末已開始采用魏晉軍區都督之制也,與前文提及虞翻之子、虞汜之弟虞昺,在吴末爲“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之例頗同。嚴先生引用此事例,謂“曰大都督,曰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皆都督也”,然因前名屬野戰編制,後銜爲軍區建制,故嚴説恐怕不甚準確。
至於交廣較大規模的兵變,則發生於吴末主孫皓之時,距國亡僅差一年,而已見有“廣州督”,甚至“都督廣州軍事”之職的設置了。《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載云:
(天紀)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别。晧時又科實廣州户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吴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八月,以……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于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晧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
而《晉書·滕脩傳》則載云:
孫晧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晧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吴,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晧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
按: 漢末討伐董卓時,群雄皆是各自募兵以爲己之部曲,吴制父兄死則所部由子弟相繼統領,兵將人身依附尤爲密切。當年陶璜等指揮吴軍反攻魏軍時,殉陣的“前部督脩則”就是新任桂林太守脩允之父,[注]詳見《三國志·三嗣主·孫皓傳》建衡三年正月條注引《華陽國志》,卷四十八,第1168頁。而其所部亦應已由脩允所繼領,故郭馬等以“累世舊軍,不樂離别”而反叛也。廣州督虞授僅此一見,其職銜與其他要塞督一般無異,與陶璜之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故軍中位望未必很高;但桂林郡是廣州屬郡,太守脩允死後其遺部處置未必與廣州督無關,故廣州督處分廣州屬郡新死郡將的遺部,而欲將之分配給他將他部,並不是難以想像之事。此關係或許由前文提到的濡須督,與駐於濡須口之江西營都督關係作觀察,始可能獲得某些印證——即要塞督可指揮其直屬以及附近之諸營督將也。因此,郭馬等督將的兵變,之所以首先攻殺廣州督,胥與此關係極爲密切。
至於郭馬兵變後不自號“廣州督”,蓋與此督的名號不高,難與來討的“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滕脩相比之故。而其所以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則顯然是一不做二不休,不僅要權位高過滕脩,甚至連老長官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陶璜的名位也想搶過來,以象徵交、廣二州在軍事上的統一指揮。筆者之所以如此言,是本於東漢以來已形成的慣例——督軍(或監軍)系與行政(刺史或太守)系分别而置——始作如此之言。出身“累世舊軍”的郭馬,可能一下子尚未想到突破此慣例,見兵變前吴置廣州督虞授,又有南海太守劉略、廣州刺史徐旗,所以也就習慣性地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用此作爲叛軍統帥之號,實行親自領軍而不理政,而另以同夥殷興作爲廣州刺史、吴述作爲南海太守,蓋遵從慣例而爲也。
據上推論可知,吴末之廣州督,可能是孫吴最後設置甚至是唯一一任之督。此督可能只負責督廣州管内諸軍事,因此也就是以廣州地區作爲督區範圍,督區較要塞督乃至長江流域諸大(都)督區爲大,或可與三郡督督區相比,但其軍事上的重要性則難與長江流域諸大(都)督區相匹。因爲此督與吴郡都督、三郡督一般,殆皆是用以應付内亂爲主,而非爲了抵禦外患也。
總而言之,孫吴建祚前已陸續設置要塞督,建祚後督區規劃漸擴大,出現以大督區或都督區轄領區内諸要塞督之制,此時孫吴已有官員虚領州名之事例,但大督或都督則仍未以州爲名;及至都督交州與都督廣州之銜出現,始明顯采用魏晉現行的常都督制,但已是時至孫吴之末期矣。
五、 劉備建國前後都督制的發展
孫吴都督制之淵源與發展概如上述,而劉備則於稱帝不久即因戰敗而亡,自後事無巨細皆專於諸葛亮。諸葛亮切志北伐,忽於細微,故被陳壽批評謂“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因此,有關蜀漢之督與都督記載,尤需多所考述,以故雖僅論其概況,然仍不能免於贅論。
按: 劉備初起時人微言輕,實力薄弱,《三國志·先主傳》云:
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黄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黄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别部司馬……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袁紹攻公孫瓚……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又史謂“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關)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别部司馬,分統部曲”。[注]見《三國志·關羽傳》,卷三十六,第939頁。别部司馬於漢朝軍隊部曲制中秩比千石,地位低於校尉。劉備集團重要人物初起時官位不過如此,蓋因其兵力薄弱之故,因此劉備常依違於群雄之間,並曾投靠曹操。其後曹操以備爲豫州牧,且於建安四年復表備爲左將軍,關羽、張飛則先後被授以偏將軍、中郎將之官,但備軍兵力仍然薄弱。尋而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操遣備“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注]見《三國志·先主傳》,卷三十二,第874頁。按: 術死於建安四年六月。是則劉備也曾督領曹軍,有督軍經驗。
由於兵力薄弱,即使降至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前,劉備在新野稍已穩定,兵力頗有整補,但仍僅約有兵萬人而已,因此早期劉備集團未見置有督軍督將之制。直至赤壁之戰後,劉備“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聲勢漸壯大,拙前文二已詳論之,以故在據有荆州大部分地盤後,兵力得到更大的補充,遂開始設置作爲野戰軍戰鬥單位指揮官、地位在太守之下的“都督”職,雖名爲“都督”,實則是野戰督將也,如同當年董軍與孫軍一般。是以在第二、三次荆州之役時,史書載劉備集團的關羽、張飛、孟達等太守、將軍麾下,皆已置有此野戰都督職。[注]關羽麾下有都督趙累等,已見前文。張飛任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麾下有營都督,見《三國志·張飛傳》,卷三十六,第944頁。至於《三國志·郤正傳》載其父“揖爲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見卷四十二,第1304頁。按: 宜都太守孟達以將軍領兵屯於上庸,不進兵救關羽,致羽敗亡,乃於漢獻帝延康元年(亦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黄初元年,220)七月率部曲降於嗣魏王曹丕。不過,隨着領地的擴大,劉備集團亦開始置有軍區督、軍區都督以及要塞督。大抵劉備西攻益州前委關羽以“董督荆州事”,故關羽實爲劉備最先以及唯一曾置的實職州級軍區督,説已見前;至於郡級軍區督則以向朗、軍區都督則以鄧方、要塞督則以馬超爲最早。至於略晚任爲漢中督的魏延,史載建安二十四年劉備攻佔漢中,被群下推爲漢中王,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荆州”云云,[注]見《三國志·先主傳》,卷三十二,第887頁。似謂劉備對魏延委以方面重任,故授延以“漢中都督”之職,筆者按諸情實以爲不盡然,蓋陳壽殆有所訛誤,請容下詳。
考劉備於建安十九年圍攻成都,馬超來奔,備授以“平西將軍、督臨沮”。[注]見《三國志》本傳,卷三十六,第946頁。臨沮縣屬南郡,蓋爲今湖北當陽縣西北沮水西岸之要塞,馬超督此,蓋因翌年曹操親征漢中張魯而降之,而孫權亦攻荆州以中分其地,因此乃命馬超督此要塞以分曹、孫臨壓之勢以及協防荆州歟。大概劉備既已命令諸葛亮率宜都太守張飛等西入援助攻蜀,故另命向“朗督秭歸、夷道、巫、夷陵四縣軍民事”,代張飛督治宜都郡。[注]本傳謂“先主定江南”,使朗督此四縣軍民事,時間則不詳。按: 張飛既任宜都太守,即使軍、民分治也不應由朗督其郡之民事,故此事應在飛入蜀之後。詳《三國志·向朗傳》,卷四十一,第1010頁。是則向朗實爲劉備最早任命之郡級軍區督,只是當時猶未以“督宜都”爲名耳。嗣後蜀平,劉備改調向朗爲巴西太守,導至宜都軍務乏人主持,又值曹、孫來攻,以故臨時調遣大將馬超前往駐防臨沮;然而當關羽兵敗被斬於臨沮時,卻未見馬超有所作爲,難道漢中王劉備改命馬超爲左將軍後,亦已將之調走,協防荆州的責任已由繼張飛之後正任宜都太守的孟達,將兵屯駐於上庸(今湖北竹溪縣東南臨堵水處)所代替?[注]孟達不知何時正任爲宜都太守,要之劉備命其北攻房陵,屯駐於上庸。其後因不受關羽的軍令,致羽兵敗被殺,而率衆降於曹魏。事見於《三國志·劉封傳》,卷四十,第991頁。史有闕文,其詳難知,要之馬超實爲劉備集團首見的要塞督。
當此之時,劉軍中已普置位在太守之下的作戰系統營都督職,但也開始置有郡級的軍區督。建安十九年劉備平蜀後,將犍爲屬國都尉升格爲朱提郡,乃將原任都尉鄧方升爲朱提太守,並選其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此即是其郡級軍區都督之首例,而資歷名位略低於郡級軍區督,正與漢末以來作戰系統之野戰督高於野戰都督的慣例相符。至於魏延之鎮守漢中則與此頗有不同,而非被授以“漢中都督”之較低軍職。按: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攻取漢中,被群下推爲漢中王後,欲自公安遷都成都,故在撤軍前任命魏延鎮漢中。據《三國志·魏延傳》所載:
魏延……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
據此,則知魏延實以劉備從龍舊部,又數有戰功,以故爲備賞識,遷爲牙門將軍——應是位在翊軍將軍趙雲之下的劉備親軍將領。此處傳文之所謂“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也者,蓋謂提拔魏延以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之官,而授權其“督漢中”以坐鎮於漢川也。然因其並未授節,故位望次於張飛當時之假節右將軍巴西太守,是以鎮漢川的重任,當時衆論以爲必在張飛。但是,卻因其“督漢中”的確是獨當一面之職權,是以若從職權而論,則魏延不僅與張飛相當,抑且亦與董督荆州事關羽之假節鉞前將軍襄陽太守,以及督臨沮馬超之假節左將軍相當,職權殆重於僅爲光棍將軍之後將軍黄忠以及稍後一度短暫“督江州(今重慶市)”的翊軍將軍趙雲,[注]趙雲原爲牙門將軍,劉備定成都後遷爲翊軍將軍,蓋皆是居中領兵翊衛天子及中央的將軍。其後劉備親征孫權,不聽趙雲“不應置魏,先與吴戰“的諫阻,遂‘留雲督江州’”;及至劉備敗還秭歸,“雲進兵至永安”,遂再無其督江州的記載。詳參《三國志·趙雲傳》並注所引《雲别傳》,卷三十六,第949頁。按: 觀此,知劉備可能不喜趙雲的勸諫,故不欲讓其隨軍參戰,而留之於江州督軍,以領戰略預備隊或護衛大軍補給綫也。及至劉備敗還秭歸時,趙雲東進至永安,蓋爲上前阻拒陸遜之追擊。劉備尋而崩殂,而趙雲亦當已隨丞相諸葛亮護送靈柩西還成都,是以其督江州爲時甚短,且是屬於戰時之野戰編制而非軍區建制。又,同卷載黄忠死於劉備稱王後的翌年。所以劉備謂“今委卿以重任”也。是則此時劉備概依獻帝初時之先例,逕以延爲軍區督,而非軍區都督。
劉軍較早見於史傳之軍區督、要塞督,蓋即上述的關羽、向朗與馬超,其次爲魏延,而皆依例未以“董督”或“督”入銜,至於鄧方則不詳。大抵從劉備取荆攻蜀、稱漢中王以至稱帝敗亡,有關督將的記載可謂稀少。此期間,另有一軍區都督吴壹亦見於史傳。吴壹爲劉備妻兄,劉備稱帝之章武元年(221)以護軍、討逆將軍爲“關中都督”(見後),殆爲虚號遥領而已,因爲蜀漢從未統治過關中也。這些督將或以董督、督、都督見稱,或逕以將軍爲號,尚無統一的規劃,要之在軍區,則“董督”之權位資望高於“督”,“督”高於“都督”,殆與孫權此時以將校領兵,開始廣泛推行要塞督之制,以及剛開始施行軍區督制度的情況頗爲類似。可見陳壽之誤,實誤於用西晉定制以視此時之劉軍也,於是乃將“督漢中”視同“都督漢中”。筆者前拙文二竊論陳壽記載劉備向孫權“求都督荆州”之説不可盡信,由此益得佐證。
此種情況需至劉備死後一段時間,諸葛亮南征北伐之軍興,督將的記載始稍多見,甚至見有依魏、吴將前綫軍區督直接轉爲征伐野戰督之例。如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注]《三國志·魏延傳》,卷四十,第1002頁。即是以漢中督轉爲諸葛亮北伐軍的前部督之例。戰時以督軍、監軍甚至性質相近的護軍統兵督戰,是東漢以來漸成的慣例,劉備早先征吴,作戰序列是以將軍(或稱護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爲别督,即爲其顯例。此征伐體制殆不同於曹魏,而卻與孫權於赤壁之戰後的體制約略相當。蜀漢軍隊保守此制,直至亡國猶然。
爲加深對蜀漢此體制運作的了解,於此先欲略舉一二先主死後不久而史料較爲明確的事例,以作下文論述諸葛亮主政以後此軍制的論證基礎。
按《三國志·馬忠傳》載云:
建興元年(魏文帝黄初四年,吴王權黄武二年,223),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八年,召爲丞相參軍……明年,亮出祁山……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冑,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吴,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是則馬忠先以丞相府幕僚,督將軍張嶷等軍討汶山羌有功,因而稍後在南夷豪帥劉胄反時,丞相亮徵庲降都督張翼還,而以忠代之。及至忠建立戰功,乃加其監軍、奮威將軍,故忠遂以此官職——監軍、奮威將軍、庲降都督——全權統一指揮此地區,也就是以中央派遣軍指揮官兼爲庲降軍區都督,全權統率指揮此地區的所有部隊也。因此,馬忠遂將原都督的駐地,由牂牁郡平夷縣(今貴州畢節市)南移至味縣(今雲南曲靖縣),用以加强鎮撫。下文引及之鄧芝,以揚武將軍行中監軍督左部,前將軍董和以中監軍督漢中,中郎李豐爲江州都督督軍,職名均與馬忠類似,皆是其例。鄧芝之職應屬作戰時的野戰軍系統,董和當屬平時軍區系統之軍區督,而李豐則殆兼二系統而任之,略如馬忠之以中央派遣軍指揮官兼爲軍區都督也(詳下)。蓋蜀漢僅有一州之地,此時除了中央野戰軍於戰時編有督將之外,又於平時分置若干軍區督軍,而其軍職又分有監軍、督軍、護軍等名號以加之,用以加强軍控,俾丞相諸葛亮安内攘外之志能切實貫徹也。
六、 蜀漢國家戰略的改變以及軍區、要塞督
荆州喪失後,諸葛亮與先主當日於隆中對話時所規劃的荆、益鉗型北伐戰略構想,遂不可能完全施行。諸葛亮爲了貫切實踐北伐興漢的國策,當務之急是與吴復盟,用以減輕東面壓力及争取援助;其次是鎮撫南中,取獲軍資,以爲穩定後方而支援北伐之用;再後即是全力貫徹北伐。這也就是諸葛亮既定的東守南撫北伐中支援之國家戰略,下文略依次考論蜀漢此軍事部署。
蜀漢東守之險塞重鎮爲永安。
此地位當長江三峽西入巴蜀之險要,也是先主兵敗喪身之處。永安在東漢名爲魚復縣,隸屬巴郡,漢末將巴郡析置巴東、巴西之三巴後,魚復遂隸屬於巴東郡,嗣因劉先主進軍征吴及兵敗撤退皆停駐於此,建有永安宫,故改名永安,爲巴東郡治,以故永安都督也有巴東都督之名,是蜀拒吴之東部最前綫要塞重地。據《華陽國志·巴志》所載,李嚴爲首任永安都督:
巴東郡,先主入益州,改爲江關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北井六縣爲固陵郡。……章武元年……聽復爲巴東,南郡輔匡爲太守。……先主征吴,於夷道還,薨斯郡,以尚書令李嚴爲都督,造設圍戍。嚴還江州,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爲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將軍南陽宗預爲都督。預還,内領軍襄陽羅獻(憲之誤)爲代。蜀平,獻仍其任,拜淩江將軍,領武陵太守。[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先主死時“以尚書令李嚴爲都督”,《三國志》無載,而《華陽國志》則僅此一見。按: 軍區都督權位較低,但當時李嚴的權位僅次於丞相諸葛亮,應不至於任爲此職。揆諸史傳,此地軍區督或都督僅四見。其一是留駐永安、名位常亞於趙雲之護軍陳到,於後主即位之延熙初,曾以征西將軍官至永安都督。[注]陳到《三國志》無傳,事見陳壽注楊戲所著的《季漢輔臣贊》陳叔至條,《三國志·楊戲傳》,卷四十五,第1082頁。下文引及此贊皆依此傳所録,不再贅注出處卷頁。其次是後將軍宗預,《宗預傳》謂預於延熙十年(247)以屯騎校尉出使孫權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内侯。景耀元年(258),以疾徵還成都”。[注]見《三國志·宗預傳》,卷四十一,第1076頁。其三是與干政宦官黄皓朋比的右大將軍都督巴東閻宇,時已至蜀亡前夕。其四是原爲巴東都督閻宇的“副貳”、上引文誤作羅獻的羅憲。史謂“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憲聞成都已敗,猶自堅守;吴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亦固守巴東,令吴兵不得過,後降於魏。晉公司馬昭“即委前任,拜憲淩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吴,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注]閻宇與羅憲之事,均附見於《三國志·霍峻傳》注所引之《襄陽記》,卷四十,第1008頁。憲於《晉書》有傳,謂黄“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又謂吴兵退後,“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云。見卷五十七,第1552頁。是則永安雖是行宫重地,三峽要塞,但李嚴已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衆護軍皆統屬於己——包括護軍陳到,且既不領巴東太守,故當無又領永安都督之必要,《華陽國志》蓋誤也。
此軍區地位如此重要,鄰近有强敵吴之西陵督陸遜在旁虎視眈眈,又值國喪,故留中護軍李嚴於此總統諸護軍,蓋勢所必要也。陳到既是名亞趙雲之名將,任期最久的宗預則是爲孫權敬佩的外交家,二人將軍本官不低,任之固宜,或許因宗預的位階資望較高,以故任爲永安督而非都督。至於右大將軍閻宇,資歷不詳,恐怕原來位望也不高,只因朋比於黄皓,而黄皓當時正排斥執政的督中外軍、大將軍姜維,以故外放以爲己援耶?因此當魏軍來攻、國家將亡之時,故被抽調率領主力入衛也。位望最低的羅憲,僅是閻宇的副都督,代宇留守永安而已,但國亡時表現得最出色。觀此軍區常以都督爲名,蓋是因吴蜀復盟後,雙方無虞,所以遂以都督作爲軍區主帥的職稱。
自永安逆長江西下即至另一險要江州(今重慶市)。此即諸葛亮規劃内作爲中支援的重鎮。
江州爲巴郡郡治,附近水道險峽處置有關,《水經注》已述之。此地向西扼控至成都、向東扼控至永安之長江水道,是故有“東關”之稱。當年趙雲隨諸葛亮入蜀援備即於此地分道並進,會師於成都,終平巴蜀;其後劉備征吴駐於永安時亦留雲督江州,以爲戰略預備。江州不僅可以支援永安都督區以及作爲成都的屏障,兼且向北可經由宕渠水(今渠江)再轉陸運通漢中督區,支援大軍北伐,故其地緣戰略之重要可知,以故諸葛亮出征,此地即爲大軍的留後重地。
中都護李嚴原駐永安監護内外諸軍,大抵因巴東已無虞,諸葛亮又即將北伐,因此於後主建興四年(226)將之移駐江州,其後官職似曾有加領“江州督”之職,故《三國志·費詩傳》末附載云:“王沖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注]見該傳末,卷四十一,第1017頁。然而李嚴之曾爲“江州督”,《三國志》僅此一見。因其移駐調職,以至其子李豐之繼任爲“江州都督督軍”,事關政局的穩定以及北伐的成敗,故於此頗欲略作詳贅。
據《三國志·李嚴傳》記載,李嚴爲劉璋成都令,建安十八年被署爲護軍,奉命拒劉備於緜竹;但卻率衆降於備,遂被拜爲裨將軍——偏裨將軍實爲最低級的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復因平亂有功,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先主病危,徵拜尚書令,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該傳載李嚴父子其後的事迹云: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宫,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即章武三年,223),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禄勛。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説“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乃廢平爲民。
據此可知,李嚴在諸葛亮首次北伐以前,是以假節中都護輔漢將軍尚書令光禄勛副丞相諸葛亮共同輔政,[注]《三國志·先主傳》章武三年二月條載謂“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卷三十二,第891頁。而未見任爲江州督。按: 當時蜀漢全國政軍大全實操之於丞相亮,故李嚴之以中都護“統内外軍事”也者,[注]《後主傳》與《三國志·李嚴傳》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卷四十,第1000頁),皆僅稱嚴爲都護,殆爲省稱。蓋指以中央都護——相當於中央總護軍——之職監護留駐永安的内、外諸軍。因爲先主崩後,諸葛亮需奉梓宫先還成都並輔立後主,而其敗戰禁軍(内軍)以及征伐諸軍(外軍)大部分仍留永安警備駐防故也。護軍之置主要是爲了監護軍隊,故此時李嚴蓋以都護之職盡護此殘餘留駐的中外諸軍;不過爲了使李嚴更名正言順的監護留駐禁軍,因此後主繼位後,尋即加嚴以宫殿守衛部隊長官——光禄勛(即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之官。由此年以至建興四年,李嚴遂皆在永安監護内、外軍事,直至因諸葛亮計畫北伐,需進駐漢中,乃轉嚴爲前將軍,使知留後事,而將其移屯江州;[注]《三國志·後主傳》載建興“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卷三十三,第894頁。另留其中一護軍陳到駐永安,仍皆統屬於嚴。如此部署,表示永安先前野戰諸軍轉爲地區防禦駐軍後,可能每軍皆各置護軍,四年以後仍監護於駐節江州之中都護李嚴也,如下文引及《季漢輔臣贊》中之護軍輔匡,殆即其例。
根據前引《華陽國志·巴志》所載,李嚴既在巴東“造設圍戍”,則此時永安附近要地殆皆部署有駐軍,而且諸軍皆編置有護軍,以故先主死前以李嚴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而留鎮永安,蓋爲因應其死後國喪時期的特殊部署也。也因此故,所以李嚴轉爲前將軍、知留後事,移屯江州後,仍以中護軍統領駐永安的護軍陳到,而附近諸軍之護軍也仍皆統屬於嚴。如果李嚴的確於此時擔任過江州督,則是其同時兼任此督區部隊的主帥也,是則在其北調漢中後,諸葛亮用其子李豐以中郎之低位繼爲“江州都督督軍”——蓋即江州軍區都督兼區内北伐野戰預備隊督軍,[注]戰時部署,常是主力在前作戰,後方則保留一支預備部隊以隨時上前支援,此即預備隊。乃爲刻意的部署矣,然而嚴傳及《後主傳》皆失載其事。
揆諸史傳,江州軍區的主帥最早應是費觀。費觀於《三國志》無傳,楊戲於後主延熙四年(241)所著之《季漢輔臣贊》贊及之,而陳壽爲之注疏云:
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
費觀之資歷在先主死前僅爲裨將軍,後來遷爲巴(西?)郡太守、江州都督,先主死後諸葛亮尋即封其爲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蓋爲加强其位望也。彼既是個性矜高而又好榮利的李嚴舊僚,爲人又善於交際,是故才能與副相李嚴通狎如時輩,或許其封侯拜將亦與嚴有關。因爲同文贊及的孫德,初爲劉備的書佐,累至京縣的縣長成都令,始能於“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楊(揚)威將軍”。[注]參《季漢輔臣贊》,卷四十五,第1088頁。至於更後的鄧芝,亦爲孫權敬佩的外交家,先累官太守、尚書、將軍,然後始如李嚴般以重官——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陽武亭侯——爲“督江州”。[注]參《三國志·鄧芝傳》,卷四十五,第1071—1072頁。江州軍區主帥僅見此五例,其中之孫德與鄧芝出任“江州督”時官職都不算低,李嚴更是僅次於諸葛亮的副相;然而費觀與李豐出任“江州都督”時,官職何以偏低?或許由此戰事無虞的内地督軍五例,可以略窺蜀漢軍區制的演變,曾經有過軍區督高於軍區都督,而其中有領郡者有不領郡者,需因人、時、地而制宜此一不明朗的發展過程;至於出任邊境接臨大敵的軍區,如巴東、漢中二區,則是因前綫要緊之地,以故始規劃常由重將名臣出任歟。
審建興元年以前費觀爲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孫德任江州督,是則李嚴之任江州督,蓋應是在其移駐江州後之事,换言之李嚴於建興四年移駐江州至八年赴漢中之前,殆應是以中都護、尚書令而兼爲江州督也,只是史失其載而已。
跨有荆、益,乘時北伐,興復漢室,爲諸葛亮與劉備昔日已定之國策,故《後出師表》開章明義即言此事,所謂“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是也。國弱而不采攻勢國防,迎之者勢將是偏安待斃之局,是以諸葛亮於表中向後主力陳此國家戰略之重要,明確指出敵强我弱,“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注]《後出師表》所陳此義,可詳參《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之《漢晉春秋》,卷三十五,第923—924頁。又,此表或疑非亮所撰,但不確,觀其内容甚合亮的身份地位以及當時情實,故采之。因此厲兵講武,屢次北伐。然而兵戎之事,除了考驗統帥的領導統御以及指戰藝術外,尚講究將領人才與夫後勤補給的部署,缺一不可。《後出師表》上於建興六年首次出師北伐之時,當時趙雲等將仍在,然而此役之後雲等七十餘將校陸續死去,下文所列建興九年北伐大軍諸將姓名,即知將材已漸凋零,由是北伐之勢更急,以故乃有一再用兵之舉。
建興九年之役應是北伐的第四役,而首役之所以不利而退還漢中,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因後勤糧運不繼,一是因馬謖街亭戰敗。諸葛亮吸收教訓,此役除了部署諸將更完整外(詳下);尤其特命中護軍、驃騎將軍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主持後勤,而表其子李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權位僅次於亮,先前將李嚴移防,殆是欲委任李嚴屯駐江州,作爲北伐軍的後勤基地以及戰略預備隊指揮官,兼向東支援永安前綫以防吴也。[注]蜀漢在先主死後雖已與吴復盟,但對吴仍抱有戒心。史載宗預早先任丞相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吴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吴,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云,由此可見一斑。李嚴率兵赴漢中之後,亮特别拔李豐爲江州都督督軍,蓋欲在後勤指揮官已移駐漢中的情況下,留其子代爲戰略預備隊指揮官,表示欲與其“父子戮力以奬漢室”,並示無猜而安撫嚴也(見下)。及至出師,諸葛亮再命李嚴以中都護署丞相府事,則是兼委李嚴在漢中掌理國内留守事務之大任。而其結果,竟是因李嚴督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呼亮來還,怠誤軍機,致使糧盡軍退之事再度發生,而北伐遂無功而還。
按: 諸葛亮當初既調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而其留後人選,則居然提拔光禄勛——李嚴原任此官——屬官、秩僅六百石的中郎李豐爲之,使主力出征時,兩父子俱在國内掌握政軍,故可謂故意而又刻意,安撫至極矣。李豐出任“江州都督督軍”之職,與當日劉備攻吴,留趙雲以翊軍將軍“督江州”之例略同,實是非常時期督要塞而兼掌留後的重要督軍之職,只是趙雲當時屬於作戰系統臨時編制之野戰督,而李豐此時則屬於軍區系統之建制軍區都督罷了。此銜與十年前曹丕篡漢之際,曹魏諸大將在緊急狀態下署理“行都督督軍、某州刺史”的任命非常相似,拙前文一已論之,二者蓋有相因相仍之關係也。揆諸史傳,諸葛亮之所以作此人事安排,據其事後所寫之《與平子豐教》中,謂實因“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注]《諸葛亮與平子豐教》可詳前揭《三國志·李嚴傳》裴注,卷四十,第1000頁。隱然暗示李嚴與諸葛亮之間頗有心病,以故亮欲開誠布公以感動之,[注]據諸葛亮議處李嚴後上表批評李平(即李嚴)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説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可見此正副輔臣間的關係與心結。引文卷頁同於上注。遂任其子以如此重責,俾使能互相無猜而戮力共奬漢室也。
無論如何,由諸葛亮從國喪以至第四次北伐期間對李嚴父子所作之軍職安排,則戰後對嚴怠誤軍機而予以撤職重懲,的確是開誠布公之舉,蓋諸葛亮在首役雖有捷勝,但也因街亭之敗而自貶三等也。[注]建興六年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竟使魏明帝爲之西鎮長安;然街亭之戰,亮諸軍前督馬謖違其節度,大爲張郃所破,遂拔還漢中,戮謖以謝衆。事後上疏自責,“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後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見《三國志·諸葛亮傳》,卷三十五,第922頁。至此,諸葛亮與諸將議定李嚴之罪時,彼等會署之銜遂可得而一窺蜀漢此時的軍制。諸將署銜如下:
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吴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吴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注]詳參《李嚴傳》注所録諸葛亮之《上尚書公文》,卷四十,第1000頁。
據此,會銜諸將之排名,基本上是依戰時軍職名號的次序——如行中軍師、前軍師、督前部、督後部、督左部行中監軍、行前監軍、行中護軍、行前護軍、行護軍、行中典軍等,並兼參平時將軍軍號的高下而排列。由於更高級之中都護驃騎將軍署丞相府事李嚴是被議處之人,其下之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等亦可能受到波及,故皆無可能參與此會,即使典留後預備事的江州都督督軍李豐,也未會銜於其中。因此會銜諸將,恐怕皆是實際參與此次征行而又參加此次會議的北伐將領,而且未是其全部,是以左右前後之序列並不齊備,有些更是以暫“行”的名義署銜。據此會銜以推,此次北伐軍實際編爲前、後、左、右、中五部,大約每部各依次編置軍師、督軍、監軍、護軍、典軍等戰時五職,只是有些未與會者可能未署銜而已。復次,除了少數人在諸葛亮死後掌權爲名臣——如鄧芝、費禕、姜維——之外,僅有由漢中督調任前軍師的魏延、由關中都督入序的吴壹算是開國以來的宿將,[注]二人有宿將之稱,見《三國志·馬良傳》,卷三十九,第984頁。其餘大多數人名迹均不及此數人,甚至是名不見經傳,是則可知蜀漢人才之凋零矣。
戰時徵調軍區主帥進入作戰序列,固爲魏、吴也有的部署,但戰時編制分有前部督、後部督、左部督、右部督、中部督乃至升城督及其他别督等職,孫吴軍隊此前已是如此,而曹魏則史料欠詳。不過,諸軍整齊地各置軍師、督軍、監軍、護軍、典軍等五職,魏吴似無此例,蓋是蜀漢之特色;而其中之行中軍師、督左部行中監軍、行中護軍、行中典軍,則恐怕俱是直隸統帥丞相亮所督的中軍本部屬職,以故未見督中部之名。[注]按: 《三國志·向朗傳·兄子寵附》載“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衞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卷四十一,第1011頁)是則蜀漢曾有中部督的編制,是典掌後主宿衞兵之督將,應未參與此次戰役,而留衛後主也。由於如此,根據前面筆者諸分析,推論此時假如督軍在蜀漢已變成一軍之作戰主帥職,則監軍當是一軍之作戰監督職,而護軍則是一軍之安全維護職,大體尚可了解,然而軍師、典軍卻尚需略予補充始能説明。
按: 軍師、軍師祭酒、軍師將軍等職在兩漢之間已見,有時並置,軍師地位高於將軍以及軍師祭酒、軍師將軍,[注]如《後漢書·鄧禹列傳》載重建漢號前,鄧禹以“前將軍持節……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卷十六,第601頁),顯示戰時編制中,軍師地位應高於將軍及軍師將軍。但平時皆甚少用以除拜。自漢末戰亂以來,群雄始多置,如盧植於靈、獻之際爲袁紹軍師。[注]盧植抗議董卓廢立,恐爲其所害而逃離長安,後被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見《後漢書·盧植列傳》,卷六十四,第2119頁。荀攸於建安元年爲曹操軍師,因屢獻計建功,故曹操於建安七年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爲亭侯。其後轉中軍師,爲魏國尚書令。[注]詳《三國志·荀攸傳》,卷十,第324頁。曹操且於建安三年正月初置軍師祭酒,[注]見《三國志·武帝紀》,卷一,第15頁。其後遂廣置,而有前、後、左、右、中之分,如建安十八年五月,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操三讓,《魏書》載其事云:
於是中軍師陸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勛……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涣、王朗、張承、任藩、杜襲……等勸進。[注]此之《魏書》應是王沉《魏書》,文見《三國志·武帝紀》該年月條裴注,卷一,第39頁。又,引文之標點爲筆者所改點。
據是以知,降至建安中,曹操集團的軍師殆已有中、前、後、左、右之分,皆其重臣爲之,序在將軍之前,地位甚高;[注]如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即遷爲三公是也。見《三國志·武帝紀》,卷一,第49頁。復有軍師祭酒,序在亭侯、關内侯之前,蓋是諸祭酒之長。此諸職殆皆文職,多不帶軍號,故應是參預謀議之職,而有佐臣之稱。此爲曹操集團之特色。至於本部之外,曹操於戰時他軍亦置有軍師之職,如楊俊由“南陽太守……徙爲征南軍師”是也,只是有否帶軍號則不詳。[注]見《三國志·楊俊傳》,卷二十三,第663頁。可見其設置此職之繁。孫權雖偶置軍師,但多不見載,蓋亦爲謀議之職。[注]如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事務一已委之。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昭復爲權長史,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可見吴軍師之地位。見《三國志·張昭傳》,卷五十二,第1219頁。吴軍師爲獻計謀議之職,《三國志·吴範傳》所載範事可爲助證,見卷六十三,第1423頁。
至於劉備,《諸葛亮傳》載劉備於赤壁之戰時即“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税,以充軍實。……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云。是則軍師中郎將、軍師將軍此二職不僅以獻計謀議爲主,且有執掌留守、後勤之權,而亦不帶軍號,略如蕭何當年之助劉邦也。因此,親待亞於諸葛亮的龐統,死前曾與諸葛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後隨劉備西征益州,參預謀議。[注]詳《三國志·龐統傳》,卷三十七,第954頁。由於諸葛亮之軍師將軍職權如此重要,以故實際地位居於關、張諸將軍之前;[注]《先主傳》載建安二十四年秋,羣下上劉備爲漢中王之表,見諸葛亮已序於關、張諸將軍之前。《三國志》,卷三十二,第884頁。至於益州平後,麋竺之所以能以“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也者,蓋是因其曾於危難時資助劉備軍資,並進妹於備爲夫人故也,但劉備亦僅止於“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如此而已。[注]詳《三國志·麋竺傳》,卷九十九,第368頁。在蜀漢建祚後也有軍師閒置之例,如劉琰在後主立後,班位每亞李嚴,“爲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注]見《三國志·劉琰傳》,卷四十,第1001頁。由此可見劉備與曹、孫初置此職時異同之處。然而大抵上軍師在軍之地位仍甚高,觀諸葛亮於北伐軍序列中,文武官皆可帶軍師銜而排於最前列,且皆帶軍號,即可知之,此實爲蜀漢的特色,蓋用以表示在其國策指導之下文武合一切志北伐歟。
典軍之名,始見於靈帝崩前之置西園八校尉,而曹操即是其中的典軍校尉。其後曹軍亦曾置此職,如夏侯淵在官渡之戰時,以潁川太守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拜典軍校尉。[注]詳《三國志·夏侯淵傳》,卷九,第270頁。此例可見典軍校尉序位在督軍校尉之前。不過,曹軍之典軍校尉似爲領兵實職,任之者見載極少,更未見直名典軍者。孫權亦然,孫權稱帝前後均未見其有典軍或典軍校尉之置,直至孫皓亡國前始見有左典軍一名,[注]見《三國志·三嗣主·孫晧傳》,卷四十八,第1162頁。而其詳則不得而知。劉軍除此會銜外亦極少見典軍之職,今所見兩例,一是《三國志·王平傳》,載“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吴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另一是《三國志·董和傳》裴注,介述諸葛亮主簿胡濟云:“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是則蜀漢之諸典軍,皆以將軍帶之而有領兵之權,序位在軍師、督軍、監軍、護軍之後,或許諸典軍所領,是天子或統帥大營之親衛諸軍。[注]二人分見《三國志·王平傳》(卷四十三,第1050頁)及《三國志·董和傳》裴注(卷三十九,第980頁)。按: 王平原爲劉備牙門將,建興六年首次北伐時隸屬於諸葛亮愛將馬謖部,謖戰敗而平部獨完,特爲亮所重,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胡濟原爲諸葛亮主簿,二人皆與亮密近,且似皆領亮之親衛軍。由於密近,是以外調時多爲最重要之漢中督,其例頗同於原爲劉備牙門將軍之魏延,特被劉備不次提拔爲漢中督也。
總而言之,諸葛亮主政蜀漢時期,由於頻繁北伐,於平時常制之外,戰時軍中殆普置前、後、左、右、中五部野戰軍,每部各編或多置軍師、督軍、監軍、護軍、典軍等五種戰時參與謀議或監督軍旅之職,且皆由其中之督將所兼帶。類似的職銜仍頗散見於諸葛亮死後,並且也頗用以作爲軍區正副主帥之職稱,恐怕這種軍制,即爲蜀漢軍隊所特有,而與魏、吴軍制有所異同之重大特色所在。然因史文有闕,不敢遽斷。
蜀漢征伐作戰體制如此,並不意謂軍區體制亦盡是如此。例如《季漢輔臣贊》贊先主穆皇后之兄吴壹時,陳壽注曰:“先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但於《三國志·後主傳》建興十二年(234)八月條則謂“以左將軍吴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注]《季漢輔臣贊》及陳注,見《三國志·楊戲傳》,卷四十五,第1083頁;《後主傳》見同書卷三十三,第897頁。已去護軍之職。於此不禁要問,蜀漢由“都督”轉爲“督”,由“關中”换成“漢中”,究竟有何意義,是升抑或降?按: 漢末袁紹、曹操之軍區制中,都督一州或都督某地區,於建安中、前期是中級軍職,後期則已是高級軍職;魏文帝曹丕於篡漢之際,逕改“行都督督軍”爲軍區“都督”,遂使此名號正式成爲方面大員之職稱,前拙文一已詳論之矣。章武元年是劉備始元,正當魏文帝改“行都督督軍”爲軍區都督之時,故劉備不可能如此快就仿效之,且劉備又從未統治過關中,是以蜀漢之“關中”性質應屬於虚置或僑置,吴壹是第一位此類型的遥領州郡軍區都督。因此,吴壹由關中都督改爲漢中督,而此時期蜀漢之軍區督重於軍區都督,是則吴壹的軍職是由虚遷實、以重易輕也,況且本官已遷爲重號將軍而加假節耶,故應是升官。鑑於蜀漢僅有益州一州之地,以故不效法當時魏文帝之置大帥級州都督,但亦因益境遼闊,復需保持王朝之體制,以故置有郡級都督,應可想而知也。可見劉備即尊前後,一塞或一郡之軍區都督,除了李豐等少數人之外,本官多爲中、高級之官,位階均不太低;若從其始終僅有益州一地的實情看,則其軍區督及都督,與郡相當而或過之,可算是蜀漢之地方方面大員矣,以故頗常不領郡,而由副都督兼之。副都督不是正式職稱,任之者蓋以監軍、護軍、典軍或參軍等職稱爲名,然爲數不多,固仍爲蜀漢軍制之特色也。嚴耕望先生據蜀漢督區僅一郡或數郡,謂“此與魏制大異”,但吴制大抵上所督亦與蜀漢頗同,只有副都督之特色與魏、吴皆異。
蜀漢之重要軍區,依次爲漢中、永安、江州以及庲降,可算是其四大軍區。永安、江州述已見前,於此兹再述執行南撫戰略的庲降,以證上言之不虚。
庲降地當益州南部的雲貴高原,漢以來有“南中”之稱,民族種落衆多而社會政治情況複雜,故庲降都督之置,以鎮撫諸族爲主要任務。劉備置此都督蓋在取得益州之後,首任都督爲鄧方(字孔山),前已述之,其人見於《季漢輔臣贊》之贊鄧孔山條,陳壽爲之注曰:“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是則庲降都督初置,即以太守帶雜號將軍爲之,並由於鄧方以朱提太守首任此職,故初治厥在朱提郡郡治之南昌縣(今貴州鎮雄縣),隨着軍事需要而東遷至與荆、交二州接近的平夷縣,再向南深入滇池東北而駐於味縣也。陳壽謂鄧方卒於章武二年恐不確,其實蓋卒於章武元年,繼任者爲李恢。《三國志·李恢傳》載云:
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吴,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
是則劉備稱帝之前,此軍區都督即已由州郡長官或帶軍號以任之,甚至可能使持節,本官地位不致太低,約與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魏延相當,只是不稱“庲降督”而已。繼鄧方出任庲降都督的李恢,曾爲劉備領益州牧時之重要屬僚,以故任之爲庲降都督並使持節領交州剌史,只因交州當時屬吴,故亦應是僑置或虚置,但形式上不失爲方面大員。
李恢卒後,由張翼繼任。《三國志·張翼傳》載云: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十一年)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是則因張翼本官僅爲綏南中郎將,以故位階略低。張翼被馬忠替代後,前引《三國志·馬忠傳》載其於建興十一年(233)遂平劉冑之亂,故加忠監軍、奮威將軍,蓋戰後委馬忠以監軍奮威將軍庲降都督之官職——即中央派遣軍指揮官兼爲庲降軍區都督——全權統一指揮此都督區内的所有部隊也,因而遂將都督駐地由平夷縣南移至味縣,居於南中之中,處於民夷之間,用以加强鎮撫之事。馬忠卒於延熙十二年(249),可謂久任其職矣,而繼之者殆爲張表。
張表是蜀郡名士,無傳,附見於卷四十五《三國志·楊戲傳》,僅略謂“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没”。《華陽國志·南中志》謂忠卒後,“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爲楊羲(戲)爲參軍副貳之”。[注]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南中志》,第247頁。楊戲即是《季漢輔臣贊》的作者,與張表友,本傳謂其出身州府僚屬,後“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任期不詳。
楊戲於景耀四年(261)卒,卒後兩年蜀亡,此期間之繼任庲降都督不詳,但知霍弋在蜀亡之際也擔任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霍弋附見於卷四十一其父霍峻之傳,而《三國志·霍峻傳》云: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静。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即蜀亡之炎興元年,263),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於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是則霍弋先任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與前任楊戲同;其後又轉護軍,統事如前,即以護軍爲庲降屯副貳都督,或是逕以護軍代爲實際之都督?其後因永昌郡夷獠之亂,故領永昌太守率軍討平之,然後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應指南中諸郡——諸軍事。按: 以副都督兼領駐地太守是蜀漢軍制之特色,以故霍弋應是以監軍爲職稱的副都督代行都督事也。至於蜀亡之歲進號安南將軍,最後降於魏而仍前任,始終未見升任爲庲降都督,而庲降都督亦不知是誰,其情況與事迹蓋同於巴東副貳都督羅憲之堅守永安。
霍弋降前之官職既拜監軍、安南將軍、庲降屯副貳都督、領建寧太守,故其降後所“仍前任”應即是此官職。然而同傳注引《漢晉春秋》記其堅守後降之事稍詳,卻謂“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云,而《三國志·陳留王奂紀》咸熙元年(264)七月辛未詔,則稱霍弋爲“南中都督護軍”。不過,《資治通鑑》於魏元帝(即陳留王奂)咸熙元年三月條所載又異於此,謂“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得(後主劉)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云。[注]參《資治通鑑》是年月條,卷七十八,第2485頁。按: 胡三省注謂“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巂已降魏也”。據此,除非“都督南中”之“都督”作動詞用,否則霍弋於國亡前蓋已正任南中都督,而司馬昭將之降爲南中都督護軍或南中都尉,但仍委以本任,事權不變。何者爲是?
筆者以爲,假如時無新任之庲降都督,則霍弋以監軍、安南將軍、庲降屯副貳都督、領建寧太守指揮南中諸郡軍事實爲可能,蓋如先前馬忠以監軍、奮威將軍、庲降都督全權統一指揮其都督區内的所有部隊,只是霍弋職稱是以副都督掛監軍銜,而馬忠則以正都督掛監軍銜罷了,然皆高於楊戲之掛參軍銜。正因霍弋以此職稱“還統南郡事”,以故始能“率六郡將守上表”投降。因此,降魏後謂司馬昭拜之爲南中都督,其事則相當可疑,其原因有二:
一是軍區都督權位高於軍區監。考堅守永安而後降的巴東副貳都督羅憲,司馬昭將其軍職略降爲巴東監軍,則霍弋由監軍、庲降屯副貳都督降爲南中都督護軍誠爲可能之事,蓋降敍乃是處置降臣常見之例。何況“都督護軍”乃至“都督督軍”之職曹操已先行之(詳拙文一),而蜀漢亦已有李豐爲“江州都督督軍”的先例。由此可知,陳留王奂之詔書似更符合實情,而司馬昭“拜南中都督”蓋是省文或誤;至於《資治通鑑》先言“霍弋都督南中”,後謂“降爲南中都尉”,則皆應爲誤,尤其都尉位階偏低,故降爲南中都尉固是劇降也,想當時招降納叛、收拾人心之際,司馬昭將不至於如是。
二是蜀無南中都督之職。“南中”自漢以來皆是地理名詞,未作地方行政區劃之用;“庲降”亦是地名,在南中,但確切方位不詳。[注]裴松之采訪蜀人,謂“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云云,見《三國志·李恢傳》注,卷四十三,第1046頁。又,《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南中志》任乃强注謂非地名,而是“招徠降附者之義”,蓋是猜測之詞,未睹實據,見該書第231頁之注釋2。蜀在南中所置唯一都督雖治所屢徙,但一直以庲降爲名。是則霍弋降魏若拜爲南中都督,即使有也是軍事倥傯之間所權置,而非定職,故霍弋之後,僅見晉武帝司馬炎於交州刺史陶璜卒後,一度用吾彦“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以平亂而已,[注]陶璜原爲吴之末代交州刺史,正文前面已述之;吴亡降晉,武帝詔復其本職,未聞曾爲南中都督。璜在南三十年,及其卒後,九真兵賊作亂,逐其太守,吾彦悉討平之。是則吾彦蓋因用兵,故武帝臨時兼授其以南中都督之職也。二人於《晉書》有傳,於此不贅。又,晉武帝是將都督定制之人,南中都督於魏、晉之際僅此兩見,蓋未爲定制也。其後再未見南中都督霍弋或吾彦之職名,而《晉書·地理下》交州條亦僅謂“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遥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罷了。[注]見《晉書·地理下》交州條,卷十五,第465頁。甚至吴亡前夕,交州交阯郡吏民叛吴附晉,晉武帝以馬融爲太守。融病卒,史載遥領交州之“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等,自蜀出交阯,破吴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云。[注]事見《晉書·陶璜列傳》,卷五十七,第1558頁。由此觀之,霍弋入晉後,殆可能初爲“南中都督護軍”,稍遷“南中監軍”,所管治之南中軍區,於魏、晉之間未限於監護益州南部七郡而已,應亦兼及交州,故若其由蜀漢監軍、安南將軍、庲降屯副貳都督、領建寧太守的官職拜爲晉南中都督,蓋是升職而非降也,當時蓋爲不可能之事,是故以陳留王奂詔書所敍的職名較爲正式準確。
要之,蜀漢庲降都督區爲四大軍區之一,都督區爲南中七郡,幾佔半個益州,遠較漢中、永安及江州三督爲廣,但因其職以鎮撫内部的南中種落爲主,並未臨接大敵,是以其建制始終爲軍區都督而非軍區督,主帥本官也略低於漢中等三督。情況略如吴末的交、廣二都督。
至於與北伐關係最爲密切的漢中督區,雖前面已略有論述,但於此仍欲稍作補充。
漢中郡之北雖有秦嶺連綿横亘,但爲蜀漢北伐以及防禦的主要軍道所在,而且於諸葛亮北伐取得武都、陰平二郡之前,[注]據亮傳,亮敗於街亭而退還漢中後之翌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於是詔策亮復爲丞相。其位置孤凸於巴蜀之北,使其三面受敵,而被曹軍一再進兵於此,以故形勢危峻,地緣戰略極爲重要。因此,劉備爲漢中王,遷治成都,遂思得重將以鎮漢川,乃拔魏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俾其帶郡以統督政軍,委以重任。魏延自後亦一再由漢中軍區督轉爲北伐野戰督,故曾於建興九年北伐之役一度短暫由李嚴代督漢中。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由漢中郡之褒斜道北伐,卒於渭濱五丈原後,魏延尋因兵變被平,後主乃以外戚左將軍吴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不久王平因平魏延之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吴壹駐漢中,又領漢中太守,至十五年遂代壹督漢中。至於胡濟於亮卒後爲中典軍,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此皆前已述之。胡濟始任時間不詳,殆至蜀亡仍在任。漢中督僅見此五例,任之者皆蜀漢重臣親將,而未見以“漢中都督”爲稱者,蓋此區乃最重要之軍區也。
析論至此,因嚴耕望先生並未對蜀漢之要塞督有所考論,故此處除了早期督臨沮的馬超之外,仍欲對餘者略作論説,以見其全。
按: 劉璋之時早已在益州之北置有白水軍督之要塞職,劉備且曾督此軍,[注]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召劉備入蜀助攻漢中張魯並拒曹軍,乃推備行大司馬,又令督白水軍。其後鬧翻,劉璋遂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劉備。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事見《三國志·先主傳》,卷三十二,第881—882頁。及至劉備佔有益州之後此督似已取消。蓋劉備既已取得漢中而置督,則白水諸地漸已成爲後方内地,尤以諸葛亮取得武都、陰平二郡後爲然,自後益州内地遂不再見有要塞督之設置。亮卒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内政軍事基本上仍能克遵亮規,對主攻的姜維亦有所抑制,故也未嘗有所虧喪;但當此時,魏之權臣司馬氏卻已易守爲攻,以故蜀漢開始見有要塞督之置,如張翼之於武都郡督建威、廖化於陰平郡督廣武等是也。[注]張翼於延熙元年以後假節督建威,廖化督廣武則時間不詳,俱各見《三國志》卷四十五之本傳。按: 《華陽國志·劉後主志》謂景耀二年六月,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本傳未載此事,恐爲廖化之訛,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劉後主志》,第417頁。其後至延熙十六年(253)費禕死後,與禕共録尚書事的衞將軍姜維遂獨掌大權,尋又加督中外軍事,遷爲大將軍,以故北伐尤急而事功卻不彰,甚至曾因大敗而自貶。鑑於魏軍南征的形迹漸顯,國内主守的聲音漸出,因此姜維開始調整戰略戰術,《三國志·姜維傳》載其事云:
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虚。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衞、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此諸地確切位置多不詳,要之在采守勢戰略之下,幾乎棄守秦嶺諸軍道,將重心退至漢壽(約在劍閣東南之嘉陵江東岸)、樂城(約在漢中成固附近之漢水南岸)、漢城(也在漢中)等要塞,分命漢中督、監軍、護軍等將守之,而諸將其實多爲要塞督或要塞監。至於三塞之北,則亦命將校於要地栅營以駐兵,此即所謂諸“圍”也,概與李嚴當年在巴東“造設圍戍”相當。諸圍的指揮官有的也稱爲督,如建威督、西安圍督即是其例。[注]西安圍督王嗣官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見《三國志·楊戲傳》注所引《益部耆舊雜記》,卷四十五,第1091頁。據《三國志·鍾會傳》記載魏軍東路主力來攻時的情況云:“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由此即可知此重點防禦之敵進我守、敵退我攻戰術,勢將徹底失敗,難怪北軍能輕易突破漢中、陰平之軍道,壓逼蜀漢主力集結退守於劍閣。
總之,先主稱帝之前戰略以攻取佔領爲主,故極少設置要塞督。諸葛亮以北伐爲務,使敵國應接不暇,也無廣置要塞督之必要。蜀末易攻勢國防爲守勢國防,故需於北邊險要之地設置要塞督,並頗以將軍、太守爲之,職稱或稱爲督,或監或護,名號指揮均不詳,終不能收救亡圖存之效。由此諸例可見,蜀漢末年之要塞督,殆與赤壁之戰後孫吴初行此制時的要塞督職權性質差不多,但數量則遠少於吴,蓋蜀有山嶺之險,而無夾江防禦形勢之故也。有險而仍失守,諸葛亮當年所謂“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誠非“事後孔明”之言。
七、 結 論
就作戰系統而言,兩漢的監軍、督軍原是監督軍隊之使職,至漢末已變成指揮官之職,而新出現的諸督將,包括世所熟知的“都督”,皆爲作戰部隊職低位微的野戰鬥將。從傳世的史料看,董卓軍隊首先出現“大督—督將(都督)—戰兵”的戰時編制,隨着戰事之延續,此制漸發展成熟,曹操更順此衍生出軍區性質的督軍制度,而“督”的權位資望高於“都督”。
孫堅是最早與編有督將制度之董軍交戰者之一,但兵力不大,縱使其二子繼續發展,至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地盤仍僅限於佔有揚州刺史部的江東四郡而已,故軍中除了編有位於將軍、太守之下的野戰大都督及都督之外,自無設置軍區督之需要。發展尤晚的劉備更是如此。自赤壁之戰後,隨着在長江下游與曹操、長江上游與劉備的戰争發展,孫權已漸視戰事需要而任命野戰的戰役級及戰鬥級督將,如以大軍主帥爲大督或左、右督,下編升城、前部、後部、左部、右部等督,上下節級、分工野戰的分别已漸清楚,規模頗具,似視曹軍編制更爲靈活。
不過,赤壁戰前,孫權已有西進荆益以徐圖天下的國家戰略構想,並據此而策劃出“夾江防禦”的軍事戰略,因此在戰後隨着地盤與兵力的擴充,遂亦開始施行野戰與軍區督將分爲二系的制度。其野戰體制已由董軍當年的“大督—督將—戰兵”發展成爲“大都督—督將—戰兵”的體制,與曹軍的發展情況概略相當。至於軍區體制,則主要是爲遂行“夾江防禦”的戰略而陸續編置要塞督,即派遣將校領兵屯駐於長江南北兩岸諸要塞,以備防禦之需;而此階段大破劉軍的大都督陸遜,更於戰後留督西陵,後來漸變爲荆州西部統轄附近諸要塞督的軍區都督。也就是説,孫軍軍區系統之“軍區(都)督—要塞督—駐兵”,而軍區(都)督位階高於要塞督的體制,已開始出現,只是較曹魏稍晚。其與曹魏比較不同的是,因曹操已挾天子而令諸侯,且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故曹軍不論是野戰或軍區主帥,皆頗擁節爲之,也極少設置要塞督;相對的,孫軍主帥多爲私署,因無朝命,以故皆無擁節的任遇,陸遜於第三次荆州之役所以爲假節大都督,蓋是因爲孫權已向魏文帝稱臣而被封爲吴王,故其所假之節應是吴王之節。
孫權在赤壁之戰後、第一次荆州之役前,即是任爲車騎將軍時期,已開始於要塞設置督將,其於濡須口設置濡須督殆是部署要塞督之始。在第二、三次荆州之役取得荆州後,領地大拓,雖因猶未取得巴蜀,“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的戰略目標尚未完全達成,但戰略情勢卻已從主動變爲被動——即需北防曹操、西拒劉備之態勢變化。因此,孫權遂沿着長江逐漸緣綫置督,日益推廣,甚至於其上設置大督或都督以爲要塞督的統一指揮官。要塞督初由縣令、中郎將等級之將校出任,且多不領郡縣,降至建祚後則率多以將軍爲之,大督或都督更常以輔臣重將擔任,地位大爲提高,只因初時尚僅有揚、荆二州而已,所以並無州都督的建制,州都督要至吴末始於交、廣二州出現。
孫軍沿江所置的要塞督,有時也沿用東漢以來慣例置監,就是所謂的“江渚諸督”,爲孫吴軍制之特色所在;其上所置之大督或都督,則隨着孫權由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大將軍,以至接受封王及獨立稱帝的身份改變而改變,漸漸穩定發展爲擁節軍區督或都督,成爲方面大員,以故孫吴都督制的發展晚於魏晉,且應是模仿魏晉常都督制的結果。
孫吴江渚諸督衆多,頗常見於史傳者,由長江自西而東,約略計有西陵督、江陵督、樂鄉督、公安督、巴丘督、中夏督、沔中督、夏口督、武昌督、蒲圻督、柴桑督、虎林督、濡須督、蕪湖督、無難督、牛渚督、都下督、京下督、徐陵督等等。其後晉軍攻至荆州,《資治通鑑》載謂“斬獲吴都督、監軍十四”云云,可見僅一荆州戰區,於吴末設置都督區以及要塞督或要塞監之多,而軍區都督與要塞監、要塞督之間的運用靈活,概爲曹魏、蜀漢所鮮見,故也是孫吴軍區制度的明顯特色。
大抵而言,樂鄉(或西陵)都督區是在夾江防禦戰略下部署的上游軍區,武昌督區可算是中游,而以扶州爲中心之督區則爲下游。假如以江陵、武昌、扶州爲三個中心,則後二者雖無都督之名,治所也不確知,但仍與前一都督區般,均各由兩個核心點——上游都督區分爲西陵與樂鄉,中游直以武昌分爲左、右,下游亦直以扶州分爲上、下——所構成,以此由點而綫、首尾相連,形成夾江長條型的防禦態勢。及至長江出海之後,折經東南諸郡以至交廣,於第二次荆州之役後,則置有吴郡都督、三郡督以及廣州(都)督區與交州都督區。前二都督區主要用於屏衛吴都以及鎮撫山越,後二都督區則用以鎮撫蠻獠,因此督區範圍較大,但重要性則難與長江流域諸大(都)督區相匹。因爲此四都督之置,皆是用以應付内亂,而非爲了抵禦外患也。
總而言之,孫吴建祚前已陸續設置要塞督,建祚後督區規劃漸擴大,出現以大督區或都督區轄領區内諸要塞督之制。此時孫吴已有官員遥領或虚領州名之事例,但大督或都督則仍未以州爲名;及至都督交州與都督廣州之銜出現,始明顯采用魏晉當時現行的常(州)都督制,但已是時至孫吴之末矣。
至於劉備,由於兵力薄弱以及毫無地盤可言,以故初期發展尤慢於吴,需降至第三次荆州之役時,劉備始效法孫軍以“大督―督―戰兵”作爲野戰體制。更由於從劉備以後,蜀漢大軍征行,常由宰輔親爲元帥,因此雖亦編置督將,而上述體制卻不明顯,發展始終不甚成熟。基本上,可能因爲其國號仍然爲漢,故不致大改漢制,而猶沿用兩漢的將軍領兵制,但已略有一些變化,如第二次荆州之役時,關羽所部即已置有位於將軍、太守之下的野戰都督,自是孟達、張飛等部亦置之。雖然可以説劉備模仿董卓、孫權之野戰體制,但是此職低位微的野戰都督仍屬漢末新制,以故猶可視爲承用漢制也。及至諸葛亮主政,由於頻繁北伐,遂於戰時將北伐軍編成多個作戰序列,如置前、後、左、右、中五部序列,而每部或各編置軍師、督軍、監軍、護軍、典軍等五種參與謀議或監督軍旅之職,且皆由其中之督將所兼帶。這種軍制雖然仍是根據漢末軍制而變化,但是整編得如此整齊,則卻是蜀漢軍制與魏、吴軍制不盡相同的重大特色所在。
隨着領土的擴大,劉備死前亦已開始部署爲數不多的軍區督、軍區都督以及要塞督。大抵劉備西攻益州前委關羽以“董督荆州事”,故關羽實爲劉備最先以及唯一曾置的實職州級軍區督。至於郡級軍區督則以向朗、軍區都督則以鄧方、要塞督則以馬超爲最早。稍後魏延之督漢中亦爲軍區督而非軍區都督,而吴壹之爲“關中都督”則是遥領而已。這些督將或以董督、督、都督見稱,或逕以將軍督軍爲稱,尚無統一的規劃。要之在軍區系統,則“董督”之權力甚大,而位望高於“督”,“督”又高於“都督”,自劉備死前已然,至亡國時猶然,基本上仍是漢末之制也,此亦與蜀漢始終僅有一州之地,領土於三國最小的實情有關。
先主劉備死後由丞相諸葛亮專政,爲了貫切實踐北伐興漢的國策,其當務之急是與吴復盟,用以減輕東面壓力及争取援助;其次是鎮撫南中,以獲取軍資,穩定後方而支援北伐;再後即是全力貫徹北伐。這也就是諸葛亮力主的攻勢國防戰略構想。在此戰略構想之下,諸葛亮的既定規劃是東守、南撫、北伐、中支援,因而蜀漢遂置有永安、庲降、漢中以及江州四個地位約爲郡級的督區,可以算是其四大軍區。也因在此攻勢戰略之下,國内並無設置要塞督的必要,以故要降至亡國前爲防禦魏軍來伐始再設置。
此四大軍區之中,漢中地緣戰略最爲重要,因此主帥一直稱爲督;庲降之主帥則一直稱爲都督,蓋因其位居後方,以鎮撫民族種落爲主,故督區最大而戰略地位卻不如其他督區,情況頗類似於孫吴的交、廣二都督也。至於永安、江州兩督區,其主帥或稱督或稱都督,人選似乎因人因時而制宜,並無較爲剛性的規劃。
軍區督及都督可算是蜀漢之方面大員,但不必定領郡,而頗常以副都督兼領之。副貳都督不是正式的職稱,有時以監軍、護軍或參軍等職稱爲名,故亦得視同軍區監,實爲蜀漢軍制之另一特色。
至於蜀漢之要塞督,在諸葛亮上述既定戰略之下,國内已無設置之必要。及至後期魏軍南征的形迹漸顯,國内主張守勢國防的聲音漸出,因此督中外軍的大將軍姜維乃開始調整戰略戰術,部署點狀的圍戍,此即當時的要塞督,如建威督、西安圍督即是其較著者,用以施行重點防禦之敵進我守、敵退我攻戰術;縱使蜀漢塞督的職權性質與吴差不多,但數量則遠少於吴,遂造成其後魏軍輕易突破漢中、陰平之軍道,壓逼蜀軍主力全綫退守劍閣,以致戰力雖仍可觀而卻終於亡國。諸葛亮力主北伐時所説“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之語,誠值得再予檢討重視,豈能因陳壽一句“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而忽略歟。
總之,就都督制的發展而言,孫吴雖較蜀漢發展爲早而且完備,但均不及曹魏之早而完善。此外,爲因應戰亂的長期化,魏晉都督制發展時間最久且有規模,孫吴較有變化而最終回采魏晉制,蜀漢則較爲保守漢制,此均是其特色所在,難怪此制發展的主流在魏而不在吴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