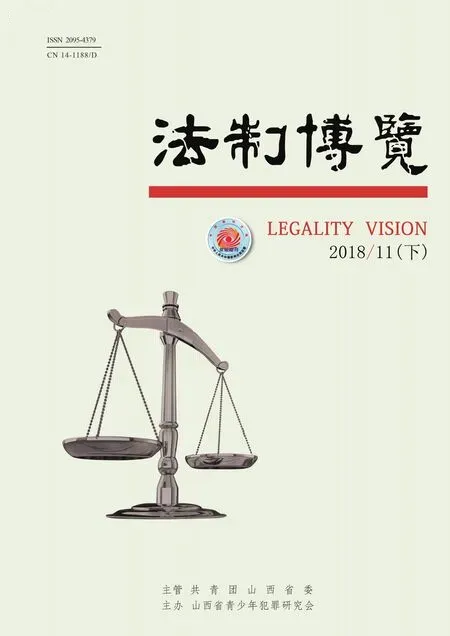浅谈扒窃型盗窃罪当前司法认定的现状
张 静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天津 30017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扒窃型盗窃案件也日益增多,导致人们的社会安全感降低,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共安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一种特殊型盗窃加以入罪,将扒窃规定为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盗窃罪的定罪模式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很大程度的降低了扒窃入罪的要求,不再有盗窃的次数和数额的限制,但这样就使司法实践中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很多具有争议性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甚至各个机关内部对扒窃行为认定意见不一,出现了各地甚至同地扒窃案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一、扒窃型盗窃罪的内涵
2013年4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根据解释规定,可以从目的性、场所性、人身性三个主要特性来把握扒窃的内涵,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国家之所以动用刑法来惩治扒窃行为,一方面在于扒窃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更重要的是该行为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该行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且紧贴他人身体,严重影响了他人的人身安全,被发现极易转化为抢夺、抢劫等暴力型犯罪,扒窃行为侵犯的不仅仅是传统盗窃罪的财产权,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的人身权和公共安全。
二、当前司法实践中扒窃型盗窃罪认定的现状
有这样两个真实的案例,某城一男子扒窃数额8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重庆一男子扒窃数额1.5元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同样是扒窃,扒窃数额少的反而受到的刑罚较重,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对扒窃构成要素以及相关法律内容界定不清,造成了这种混乱的局面。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扒窃数额的限制、扒窃场所的认定、扒窃行为对象的“随身携带性”以及扒窃行为的既未遂标准等几方面。
(一)扒窃数额的认定。扒窃入罪是否需要数额的限制,学界也是众口不一。有的认为盗窃罪是财产型犯罪,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形式,理应有数额的限制;有的认为扒窃相对于盗窃的普通形式而言,其危害性要远大于盗窃行为本身,因此只要有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不需要有数额的要求。纵观全国各地的扒窃案件,扒窃数额少至1元钱几十元,多则达到典型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由于理论认识的不统一,从而导致各地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地区扒窃案件的入罪标准有很大差异。现实中的案例,很多被害人随之被盗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与现金放在一起的身份证件、票据、银行卡等等,有些票据、证件相对于盗窃者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大多都被随意丢弃,找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相对于被害人而言,却比现金更有价值,这些物品的灭失,给被害人带来巨大损失。笔者认为,数额不是扒窃行为是否定罪着重考虑的因素,扒窃对象具有随机性,扒窃所得数额仅仅是行为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应着重考虑扒窃者的主观恶性。即使扒窃数额仅有1元钱,也要充分考虑扒窃者年龄、是否系累犯、职业犯、团伙作案,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在人流密集场所、早晚高峰期等客观情况,不能因为数额小,而不追究扒窃者的刑事责任。
(二)扒窃场所的认定。司法解释规定扒窃的行为地点界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顾名思义,公共场所具有流动性、人员的不特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刑法》中,对于公共场所的定义也是采用列举式的定义,即“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这种定义不能穷尽所有的公共场所,就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困惑:以上列举的都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非典型的场所,比如医院的门诊大厅、学校、政府的政务大厅是否也是公共场所。扒窃因其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从而使立法者将其从普通盗窃中分离出来单独入罪,但是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往往难以被人认识,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扒窃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因此非公共场所的贴身窃取财物的行为不能评价为扒窃。
(三)随身携带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对随身携带的界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随时支配可能说,也称近身说,认为随身携带是指他人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的财物,包括在飞机、火车、地铁上窃取他人置于货架上、床底下的财物,扒窃的财物不限于体积微小的财物,置于火车架上体积较大的财物盗走的行为也属于扒窃;另一种观点是物理接触说,也称贴身说,只有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财物,包括口袋内或随身的包中财物才能认定为随身携带,扒窃该类财物时具有了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害人系货车司机,凌晨在一家24小时快餐店桌子上趴着睡着了,被害人称睡着前手里拿着手机,嫌疑人李某趁被害人睡熟之机把被害人手机盗走,经鉴定,被盗手机价值1200元人民币,店内的监控无法看到手机被盗过程,也无法确定李某是在桌子上盗走的手机还是在被害人手里盗走的手机。如果根据近身说的理论,无论嫌疑人李某在桌子上还是在被害人手里盗走的手机,都构成扒窃,不需要考虑盗窃数额大小;如果根据贴身说,李某若在被害人手里窃的手机,认定扒窃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如果嫌疑人李某是在被害人睡觉的桌子上窃的手机,因为手机已经脱离被害人的身体,不宜评价为扒窃,同时被盗手机的价值因为达不到盗窃罪入罪的标准,不构成犯罪,只能进行行政处罚。由于法律认识上的分歧,从而导致本案截然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本案应采用近身说,嫌疑人李某的行为构成扒窃,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扒窃行为的既、未遂标准。对扒窃案件能否够构成犯罪未遂,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比较主流且争论最为激烈的应属“失控说”与“控制说”。“失控说”是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失去控制的为既遂;“控制说”是以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实际控制的为既遂。实践中,经常出现财物尚未完全离开被害人身体,或者刚刚离开被害人身体就被发现的情形,按照“失控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既遂,但如果运用“控制说”,行为人的行为就不宜认定为既遂。既未遂认定标准的不统一,直接导致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差别,出现同案不同判,甚至罪与非罪截然不同的结果,影响公平正义的实现。笔者认为扒窃型盗窃罪应当遵守刑法总则的规定,存在犯罪既遂、犯罪未遂和中止形态,扒窃应当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了扒窃行为,使被害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支配权,亦或扒窃行为人实际取得了财物的控制权,就构成犯罪既遂。
因为立法技术、社会思想的发展以及学术的进步等多方面的原因,立法者通过的法律条文可能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缺陷,需要通过后续的司法解释等方式完善。司法认定的困境源于扒窃行为入刑的立法缺陷和司法适用标准的不统一。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提供相关权威的指导性案例,给各地法院提供权威性的审判量刑的参考,来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