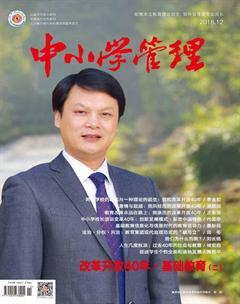这40年,如你所愿
孙金鑫
编者是以作者的作品为喉舌的,我们原本不计划就“改革开放40周年”的选题再多说些什么。但在收到褚宏启老师发来的《人生几度秋凉:过去40年的社会与教育》一文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浮上心头,陡然间唤起了我的许多记忆,不由得重新审视过往与当下。
我犹记得,1976年的一天,还是小儿的我,拽着姑姑长长的辫梢,跟几百名男女老少一起,默默地来到大操场集合。天色黑沉沉的,人们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痛哭声高高低低、此起彼伏,我小小的心里,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大人们回忆说,当时是发自内心的悲痛与惶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后可怎么办呢?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引方向的伟人走了,自己的前途在哪里?老百姓的前途在哪里?国家的前途在哪里?
我犹记得,后来我上小学,每学期学费大概是两元钱,而有的人家连这两元钱都拿不出。那时候的小学,主要开语文数学两科。初一时,学校终于开了英语课,但英语老师的英语是她半年前现进修的,她自己也常常搞不清楚怎么发音。我是第72个到班里报到的学生,班里同学太多了,以至于到现在我也不确切知道自己的初中同学都有谁。
我犹记得,我们是最后一届不用交学费的大学生,国家奖学金用饭票的形式发下来,每月66块,女生用不完还可以“救济”男生。我们毕业时,国家还包分配,还有用人单位来学校选人要人。毕业后我到学校教书,那时学校还有校办工厂,老师的福利往往与校长的“经营”能力相关。那时新东方、学而思等机构大概还没有创立,孩子们周日时还会三五成群满街疯跑。
......
40余年过去,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们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2.70亿在校学生,建成了全世界体量最大的教育,儿童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到“上好学”,迎来了政策改进和实践推进的双重曙光。
我们的中小学校,正是在这变局中不断成长—
颜值高了—学校从千校一面到各美其美,开始办出各自特色。“铃和小鸟,还有我,大家不同,大家都好。”底气足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已经连续6年超4%,校长们不必再为了办学经费而去四处“求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再也不会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了。根基牢固了—国家开始建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学校开始为学生提供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品质提升了—教师从研究教转变为研究学,各地各种教育教学方式的探索层出不穷。“良师”更多了—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更高层次人才也开始进入基础教育系统。管理更人性化了—从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学校管理越来越有本土味道,越来越回归教育本真。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有兴替得失中,最重要的“兴”和“得”,是让我们终于发现了自己。我们找到了方向,不再困惑于国家和民族该向哪里去;找回了文化自信,从对中外文化的重读中找到立身立国之本;激发了生命潜能,相信通过努力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新世界”,中国教育走过了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推进的发展过程。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干部教师心智的唤醒和解放,让人们扔掉了思想的拐棍,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认识到自我的力量,不再依赖,不再抱怨,不再被动等待“上面”和“英雄”的意志,开始沐风栉雨,独立前行。
所以我们更希望对这40年有一个深情的回望,做一个理性的研判。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最合适的人来讲述最合适的领域。他们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特别熟悉中小学管理实践;既有高度凝练概括的能力,更有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们将文章的写作当作一次与历史和未来的对话,极其严肃、极度认真地对待此事。裴娣娜老教授,一次次给编辑打电话,谈方向,谈结构,谈内容,逐字逐句地修改核实。桑新民老先生,一次次与老友们核对文章中的每一个人物和细节。李金初老校长,重新翻阅几十年来的资料......
他们越是如此用心,我们越是不敢有丝毫怠慢。
我们希望,能借助这次回望,看到中国学校管理的伟大与肤浅,明白我们的光荣与失败,让理性、民主、科学、人文的光芒,永远映照我们的目光与脚步。未来几十年,我们遇到的矛盾将更为尖锐,城乡差异、区域差距、价值重建、择校升学、师资重组、学生减负、家校互动、阶层固化等等问题将更加错综复杂,教育领域可能会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点。但我们为孩子们终身发展奠基的初心不能变,教育追求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担当不会变。
阳明先生说:“你未看此花時,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教育领域改革开放40年的花,无论我们看与不看,都在那里芳华绽放。我们期待的是,能以此告慰当年那些苦闷彷徨的人们,告慰当下这些迎风奔跑的人们:这40年,这盛世,终会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