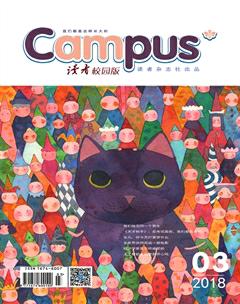我就是那个画画最好的姑娘
绒绒
我从小最怕和别人比。
无非是比谁穿的衣服好看,谁的零花钱多,谁家亲戚又从一个很远、远到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寄来了礼物……
小时候,我家的生活不宽裕,又没有一个住得这样“远”的亲戚,所以我总是那个在一旁羡慕其他人的、性格有些孤僻的小女孩。
有时候我挺讨厌这样的自己——既对这种无聊的攀比感到不屑,又暗自难过于自己着实没有一项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去和其他人比。
后来我终于发现自己有一项别人都比不上的技能——画画。小时候我也没上过什么特长班,就是在美术课上跟着老师一笔一笔地学出来的。
后来,美术老师看我在画画上颇有些天赋,就让我帮他做一些事情。比如,学校的公告栏需要经常换板报,下午放学以后,老师就带着我把原来的板报擦掉,用各种颜色的粉笔画一版更加多彩、漂亮的板报出来;再比如,学校里举办一些小型的美术比赛,老师会让我过去帮忙画画海报。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只会躲在角落里羡慕别人的小女孩了。每次画完学校的板报,同学们第二天一早看到跃然于黑板上的画面,就会像他们曾经讨论衣服、零花钱和礼物一样,围到我身边,追问我是如何画得这么好看的。
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也许是因为好胜,所以每次的美术课,我一分一秒也不敢放松,每一笔线条仿佛都在我的脑袋里构思了半个世纪。放学以后,我会买彩色画笔和绘画本画画;绘画本画完了,就偷偷趴在窗台上,用画笔把窗台涂得五颜六色。
因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应该有一样拿得出手、逢人便可炫耀的特长吧。
后来一次机缘,美术老师帮我报名参加了全市中小学生美术大赛。
我还记得我的参赛作品是一幅画鹰的国画。为了画好这只鹰,我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每天放学以后,我就一个人跑到画室,一遍又一遍地画。
美术老师对我说,画一只鹰,最重要的是画好鹰的眼睛。于是我跑遍了小镇的书店,问店员:“有没有关于鹰的图画书?”“有没有更多关于鹰的图画书?”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认识了世界上所有的鹰——它们的品种、它们的羽毛和它们的眼睛。
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可是做了足足两个月的准备啊!
等待结果的日子是煎熬的。教室与画室隔着一个操场,到了快出比赛结果的那几天,每次课间休息的10分钟,我都第一个冲出教室,飞快地跑过操场去对面的画室问老师:“我得獎了吗?”
我得奖了吗?
我没有得奖。
当时对我最大的打击在于——我刚刚获得的能与其他人“攀比”的资本,瞬间被剥夺了。
这着实令我难过了一阵子。相较于“我为什么没有得奖”,更令我无法释怀的,也许是“为什么我明明那么努力,却还是比不过别人”。
后来,老师发现我去画室的次数少了,画板报也不积极了,分明变回了曾经那个躲在角落里、性格有些孤僻的小女孩。
他得知缘由后,叫我去画室。我一进画室,吃了一惊。
老师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我看见那些我曾经画过的鹰,一张一张地铺在画室的地板上,像是等待我检阅一般。
老师让我先看第一张,然后跳过中间的无数张,直接看最后一张,问我有什么区别。
区别显而易见——与最后一张画里有些睿智与凶猛的鹰相比,第一张画里的鹰简直像一只刚刚出生、丑陋又可怜的小鸡。
我终于明白了“比较”的意义。我们是应该“比”,但不是和其他人看上去的华丽与优越比,而是与曾经那个幼稚与彷徨、脆弱与迷茫的自己比。
我再回过头看自己曾经画过的鹰,原来真的每一滴墨、每一张纸都没有浪费;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原来真的每一步都算数。
每一分努力和徘徊时的焦灼,都是为了邂逅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我们也终将如愿以偿。
这件事情过了很多年,我仍然记得当年我画的那只鹰的眼睛——犀利而有光,透着倔强和不服输的神情。
我也终于愿意挺起胸膛告诉自己和其他人:“对,我就是那个画画最好的姑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