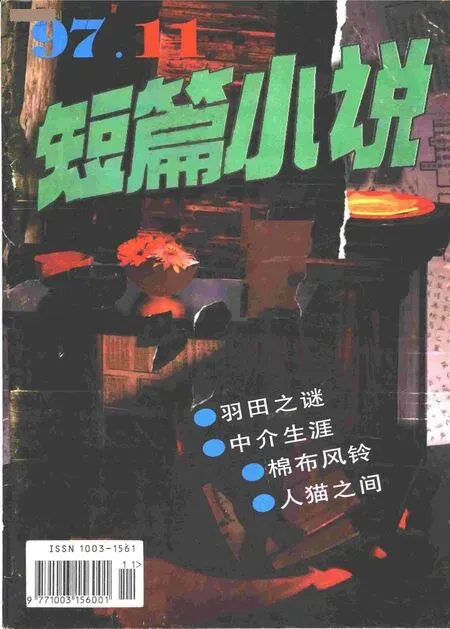往事
◎彭兴凯

批斗会
金柱家出事的那天晚上明月皎洁,我同村里的伙伴们照例聚在大队部院门前的空场上玩。记不清夜色已经有多深,我的耳朵猛丁让人揪往了,不用看我就知道是父亲。父亲是大队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到大队部公干。公干完了,就会锁上院门回家睡觉。发现我和伙伴们聚在那里玩,他轻则一声怒吼,重则会揪住耳朵牵着我回家。根本没什么辙儿,我只好一面哎哟哎哟地叫着疼,一面乖乖地跟着他回家睡觉。
那天晚上也是如此。
但是那天晚上我刚刚进入沉沉的梦乡,却被一阵狗叫和砰砰的打门声惊醒了。不单是我醒来了,父亲和母亲,还有大姐二姐也都醒来了。大家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黑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两个姐姐甚至吓得发起了抖,嗦嗦的,似是筛糠。还是父亲镇定些,从床上欠起身子,冲着外面开了腔,谁,半夜三更的,砸什么门啊?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悲怆的哭声,说,宋书记啊,塌天了啊!你可得给俺做主啊!说着,那人竟嗷嗷地哭起来,哭声高扬、嘹亮,如同驴鸣。
父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冲着外面说,你是谁?到底出了什么事?
门外的哭声顿了顿,继续哭咧咧地说,宋书记啊,俺是刘文生啊。俺老婆她不要脸,和人家胡搞,让俺堵了门子捉了奸啊!
父亲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嘴里轻轻嘀咕了一声,又骂了句什么,有些不情愿地叹口气,然后开始穿衣服。将衣服穿好,开了门,跟着刘文生走了。
刘文生家虽然住在我们村,但他并不是我们村里的社员。他在县城供销社站门头,是个吃皇粮的工作人。黄昏,我们在村口玩的时候,经常见到那条通向村外的小路上,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地朝村子驶来。那人来到村头跳下车,推着车子进村巷。便是从城里回家的刘文生。
听着父亲与刘文生的脚步声远去,我却没有了睡觉的意思。我知道刘文生是金柱的父亲。金柱不但是我的小伙伴,还是我们孩子中的头儿,也是我最宾服的人。他瘦瘦的,似一只猴子,最是能爬树,再高的树都能爬上去。春天和夏天,鸟儿做窝的时候,我最喜欢同他一起去掏鸟窝。掏了鸟蛋和鸟雏,我们就架起一堆火烧了吃。我最宾服他的地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能上树,还因为他是我们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有一次我们和邻村的孩子起了战争,两村的孩子在河滩上狭路相逢,我们是六七个人,他们却是十来个人,而且年龄都比我们大。双方还没有交手,我们就吓得打起哆嗦,直朝后面缩。金柱却一点恐惧也没有,一个人挺着胸脯迎上前,小虎羔子似的冲向敌阵。邻村的孩子竟然胆怯了,最后被他打得溃不成军,一个个逃之夭夭。
金柱爹半夜里哭嚎着来找父亲,我知道他家里出的事情非同小可。究竟产生怎样的后果,是我非常关心的。我决定起床去看看。主意打定,我就穿衣下床,拔脚朝门外走去。
夜已经很深了,那轮圆月早偏向远方,村巷里显得很黑暗。不过,借着淡淡的星光,还是能让我看清路径。很快便来到金柱家。
金柱家当然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地方。他家的院子里有一颗石榴树,石榴熟了的时候,那玛瑙似的石榴粒儿总是牵着我馋馋的目光。进了金柱家的院门,院子里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都站在那棵石榴树底下,抬着眼睛向屋内张望,嘴里小声嘀咕着什么。屋里,金柱爹刘文生还在哭嚎,还不时地摔砸着家里的器物。随着器物碎裂的声音,就听到他们家的孩子发出的宏亮的哭声。我企图挤进人群钻到屋里,更近距离地看个究竟。可是我刚一动作,就让民兵连长梁有全拦住了。我只好和那些看热闹的村里人一样,站在院子里,拼命踮起脚,朝屋里探着脑袋。我想看看金柱在干什么,眼下是什么情形。那一片宏亮的哭声里,是不是有他的声音。刚踮起脚,就听到父亲威严的声音传过来,文生,你先别闹好不好?
刘文生哭着说,宋书记啊,俺没脸活了啊!俺万万没想到,老婆她这么不要脸啊。
父亲说,捉奸要捉双的,你说,那个人是谁?
刘文生说,还有谁?就是李大力那个王八羔子啊!
父亲一怔,提高了嗓门说,李大力?他人呢?
刘文生又哭嚎起来,说,这个王八蛋早就跑了啊!
父亲半天没有吭声。屋里传来的还是刘文生的哭嚎声,当然还有他们家孩子的哭声。一家人哭嚎着,就见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对民兵连长梁有全发布了命令。
父亲说,马上通知村里的基干民兵,立刻把李大力抓回来!
是!民兵连长梁有全打了个立正,去通知基干民兵去了。
见梁有全出了门,父亲又进了屋,对刘文生道,情况我都知道了,怎么处理他们,你有什么要求?
刘文生的话冲口而出,我要村里开他们的批斗会!
父亲一怔说,开批斗会?你不怕这事传扬得人人都知道啊?
刘文生又呜呜地哭了起来,说,书记啊,出了这种事,还能瞒住谁啊?
父亲点起一支烟吸着,沉吟了半天说,文生,你就别哭了,先睡觉吧,等抓住了李大力再说批斗会的事。父亲不等刘文生有什么反应,就从屋里走了出来,抬眼看到院子里站了许多人,他的眉头就皱紧了,将眼一瞪吼道,看什么看?都回家睡觉去!
父亲人高马大,又是大队书记,村里没人不怕他。听他这一吼,呼啦啦一下子就都散去了。我怕父亲看见我,又要揪耳朵,早抢在他前边溜回了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钻进被窝打起了呼噜。当然,那是我故意的。
记不清是何时睡去的,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新崭崭的一天了。
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全村人就都知道了夜里发生的事情。吃过早饭我走在村巷里,就看到好多人在碾台边、巷道口,或者井台上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特别是那些女人们,更是一个个振奋无比、兴致勃勃。她们一边在那里叽喳着,一边在脸上制造出丰富而又多彩的表情。我没有凑过去听她们聊什么,我快步穿过村巷,来到大队部,看梁有全指挥的基干民兵是否将李大力抓到。
李大力是位光棍汉,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李大力是个大个子,足足有一米八,长脸,直鼻,下巴与腮上全是黑黑的胡子。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几百斤重的挑子担在肩上连口气都不喘。他在村里的林业队干活,看管村外那片树林子。我们去树林子里掏鸟蛋或者拾柴的时候,就会看见他背着杆土枪在林子里走,遇到兔子斑鸠什么的,他就会将枪从肩上取下来瞄准射击,砰的一声响,就有野物毙命在他枪口下。他除了打猎外,还喜欢去河里捉鱼。夏季里河中发了大水,从下游水库中呛上来许多鱼,村里人就都纷纷下河去捕捉。别人捕鱼都是用网捞,他不,他用炸药炸。制造一个小小的炸药包,点着,朝水里一丢,随着嗵的一声大响,就有白花花的鱼漂在河面上。我和金柱他们就喜欢跟着他跑,猎到鸟或者鱼什么的,他也不吝啬,总是分给我们些,让我们烧了尝鲜。那时候,在村里的大人中,除了当着书记的父亲,我就宾服他。
我一直不明白李大力为什么会打光棍,他有爹有娘,家景也不错,而且还身高力强的,可是,他就是没有说上媳妇。而村里比他条件差许多的,比如拐子李财,独眼龙宋树根,还有地主羔子马家良,都说上了媳妇,孩子也都一大群了,唯独他光棍一条。有一次,我甚至还就此问题问过母亲。只是,母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现在,他和金柱娘通奸事发,今后怕是永远说不上媳妇了。
大队部院门外的空场上,已经聚起不少村里人。他们的目的同我一样,也是来看热闹的,其中就有几个与我一个年龄段的伙伴们。只是里面没有了金柱。我并没有加入其中与他们嬉戏,我进了大队部的大院门,朝父亲的办公室探头探脑,看父亲如何处理这件事。父亲早饭都没有吃便来到大队部,正端坐在那把只有他才有资格坐的椅子上指挥着民兵抓捕李大力,脸上表情严肃。父亲对站在面前的民兵连长梁有全说,一定要把住各个路口,绝不能让他跑了!
是!梁有全回答。
父亲又说,派人到山沟里搜一搜,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
是!梁有全又是一声回答。
父亲接着说,还有村里的地瓜窖子、萝卜窨子什么的,也不能放过。
是!梁有全给父亲打一个标准的敬礼,急忙带人而去。
父亲的判断果然没有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民兵终于将李大力捉住了。而且正如父亲所料,他果然藏在村外的地瓜窖子里。
我看见李大力的时候,他是被两个民兵押着从村外走来的。他戴着一顶三页瓦的棉帽子,一只帽耳向下耷拉着,一只帽耳则似鸟的翅膀支楞着。可能是藏身地瓜窖子的原因,他的身上全是土,连黑黑的络腮胡子上也沾满土渣。他面无表情地被两个民兵押着,低着头走路,一直进了大队部。我和村里人急忙围过去看,但是,大队部的大门却让父亲指挥着民兵给关死了。大家站在门外探头探脑地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看见,终于觉得无趣,只好四散了回家。
走在回家的巷子里时,我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哇哇地响了,父亲在喇叭里下通知,要求社员们晚上到大队部开批斗会。
村里开社员大会,地点就在大队部。村子不大,五六百口人,大队部的院子刚好能容下。那几年村里经常召开批斗会,批走资派的,批地富反坏右的,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还有小偷小摸什么的。往时开批斗会,大都是男社员参加,女社员除了年轻姑娘外,家庭妇女一般是可以不来的。这天晚上的批斗会却出现了例外,父亲并没有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可是,村里几乎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其中就包括那些家庭妇女们。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大队部的院子都容纳不下了。最后,不得不迫使我们这些小孩子攀到了墙头上,或者院子里的树杈上。
我爬到了大队部院子里的一棵榆树上。幸好那棵榆树在院子的中心部位,骑在树杈上,可以居高临下,将会台看得清清楚楚。
攀到榆树上后,我倒是没有先急于朝会台上看,我拿了眼睛在别的树杈上寻找,想看看金柱来没来。可惜,我的目光所及,都是那些与我同龄、或者稍大些稍小些的孩子们。他们同我一样,每人占领一个树杈,猫似地骑在那里,却单单没有金柱的影子。我知道,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他家,金柱应该早来了,他最是能爬树,这棵榆树的最高处一定是非他莫属的。
没有看到他,我自然有些怏怏的。
社员们到得前所未有的齐,会就开得早,天刚擦黑,父亲就宣布会议开始。就见奸夫李大力和淫妇金柱娘给押到会台上来。
会台并不是特地搭起的会台,在大队部院子的中间位置,放一张办公桌,桌子前面留有三米见方的空场,就算是会台了。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就端坐着我父亲。一盏汽灯悬在头顶,将会台照得亮如白昼,也将父亲脸上的威严清楚地照了出来。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开会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退色的军大衣,戴一顶同样退色的棉军帽。他这么一身军衣打扮,显得特别威武,也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感到特别自豪。
桌子前边的空场上,就站着李大力与金柱娘。
金柱娘是个四十五六岁的胖女人,脸白白的,有少许几个麻坑,黑黑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在后面挽一个大大的髻。在没有事发前,她是村里的头面人物,经常见她甩着大屁股走来走去。前几年,一度她还成了村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她能站在会台上将“老三篇”倒背如流,甚至,她还跑到公社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当着全公社的社员们背诵过,很是风光。这天的晚上,她同样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同样挽着一个大髻,也没有见她哭,她站在那里,只是扬着下巴看天上的星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而站在她旁边的李大力相对来说就消沉些,头埋得低低的,大冬天的似乎有汗从脸上淌下来。
说是批斗会,也不似平常的批半会,社员们要一个个地发言,还要让被批斗者低头弯腰什么的。对李大力与金柱娘的批斗,主要是由父亲以村书记的身分对两人进行审问。那情形,类似于现在的公审。
李大力,你说,你和王凤花多长时间了?父亲用严厉的声音开始审问。
王凤花就是金柱娘的大名。
李大力表现得很配合,问什么就老实地答什么。
李大力说,六年拐弯了。
你们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李大力张嘴要回答,父亲却阻止了他。父亲转脸望向金柱娘,说,王凤花,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王凤花却没有将我父亲放在眼里,她站在那里,只是翻了翻眼皮,什么也没有说。
民兵连长梁有全就适时地跳了起来,大声地配合我父亲道,王凤花,宋书记问你话,你没听到?说,你和李大力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凤花终于开口了,连想也没想就说,俺忘了。
忘了?父亲一瞪眼要发作,但是马上他又忍住了,转脸望向李大力,道,李大力,你说,什么时候?
李大力想了想道,是那年腊月里。那天我去她家玩,把烟袋忘在她家里了。晚上又去拿,正巧刘文生没回来,俺们就那个了。
会场上出现短暂的沉默。父亲似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这时,还是民兵连长梁有全很配合地站了起来,振臂高呼道,打倒流氓分子李大力!
所有的人立刻随着高呼,打倒流氓分子李大力!
民兵连长又高呼,打倒破鞋王凤花!
所有的人也跟着高呼,打倒破鞋王凤花!
如此一呼口号,会场上的气氛就热烈了许多,也让父亲的思维恢复到正常。父亲又开始审问下去,说,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在一起鬼混?
李大力说,晚上。
你们就不怕让刘文生发现?
都是刘文生不在家的时候。
若是刘文生回来了怎么办?
李大力说,刘文生回家了,王凤花就给我留下暗号。
什么暗号?
李大力还要回答,会场中不知是谁喊,让王凤花回答!
父亲十分顺应民意,对王凤花说,王凤花,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王凤花翻翻眼皮,还是那句话,俺忘了。
忘了?你分明是负堣顽抗!民兵连长梁有全说。
俺就是忘了!王凤花竟然不吃他这一套,硬生生地回了一嘴。
打倒破鞋王凤花!民兵连长梁有全恼了,又喊起了口号。
口号喊罢,还是父亲选择了妥协,对李大力说,李大力,你说,你们都用什么暗号?
李大力在看了王凤花一眼后,擦了一下汗,开了腔,刘文生若是回家,她就在门口的猫道里放一块小石头。我来时一摸,摸到了石头,就不能进家了。
会场上不知谁开了腔,那,昨晚咋让刘文生捉奸了呢?
李大力喏喏了几下,没有答上来,低下脑袋不吭声了。
说!民兵连长梁有全又喊起来。
说!社员们跟着也喊起来。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刘文生来了。他分开众人,从会场外挤进来,站在了会台上。他是个小个子,瘦瘦的,矮矮的,同李大力站在一起,简直就似大人与小孩。显然,父亲召开的批斗会给他做了主,撑了腰,他非但没有再哭嚎,脸上还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他先是狠狠瞪了王凤花一眼,又狠狠瞪了李大力一眼,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大家,有些得意地说,他们让我捉了奸,这都是天意啊!那天,我回家走到半路上,车链子突然断了,我只好推着车子走,回来时就到了半夜,他们就让我堵在屋里去了。
会场上不知谁又开了腔,王凤花,你说,你为什么要跟李大力胡搞?
接着有人响应,对,你说,为什么与李大力胡搞?
王凤花还是翻着眼皮不回答。李大力呢,不待大家来问他,忙忙地回答了。
李大力说,她可怜俺是个光棍汉哩!
说,你们的第一次,是谁先主动的?不知谁又喊起来。
父亲这时却摆了摆手,让大家不要再问了。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天,皱了皱眉头道,天也不早了,说的也不少了,明天还要整修大寨田呢,会就散了吧。
批斗会开得如此之快,这还是第一次,大家都怔在了那里。但是,父亲的话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大家在怔了一下后,还是怏怏地四散回家了。
众孩子们自然更不情愿一场热闹这么快就过去了,骑着树杈,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才慢慢地溜下来。因为天还早,我们没有急于回家,就仍是聚在大队部外面的空场上玩。但是,我们却破天荒地没有玩平时最热衷于玩的那些游戏,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开起了批斗会。在批斗会上,我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喜子自告奋勇扮演李大力,余财则主动要求扮演民兵连长梁有全,只是由谁来扮演王凤花,却一时没有人请缨。后来,还是在我提议下,用捉阄的办法得以解决。
夜虽然不很晚,但是非常寒冷,不知何时天阴了,还起了风,西北风嗖嗖地刮过来,吹得我们的骨头疼。然而,寒冷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热情,我们的批斗会开始了。
李大力,你说,你和王凤花多长时间了?我学着父亲,用严厉的声音开始审问。
喜子扮演的李大力说,六年拐弯了。
说,你和李大力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二牛扮演的王凤花开了腔,俺忘了。
忘了?我学着父亲,一皱眉头正要发作,突然从黑暗里冲出一个人,向我猛地撞了过来。我冷不防就被撞倒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我一面揉着摔痛的腿,一面借着月光去看。这一看我怔住了,撞我的人竟然是金柱。他正拿发红了的眼睛凶凶地瞪着我,腮上似乎还挂着闪闪的泪珠。他比我大两岁,个子也比我高半头,自然是打不过他的,我吓得一哆嗦,慌忙跳起来,逃也似的回家去了。
绝 户
住在西院里的喜子从墙头上露出脑袋,冲着我家的院子喵喵地学猫叫。喜子一学猫叫,我就知道是在唤我。我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煎饼从屋里蹦出来,冲着喜子说,你叫什么叫,俺正吃饭呢。
喜子用手团成个小喇叭,将声音压低说,俺哥说山里的杏子都黄啦。
我的眼睛猛的一亮说,真的?
喜子说,骗你是小狗!
我的眼睛再一亮,立刻将手一挥说,走,咱们弄杏吃去!
喜子双手撑着墙头,一耸身子上了墙,又蹭的一下跳到我家的院子里。我们勾肩搭背就朝院外走。到了院门外,我和喜子做了个分工,分头去喊村里的其他伙伴们。我到了村东头,他到了村西头,眨巴眼的当儿,七八个小伙伴就在村巷里的碾道旁聚齐,然后一路大呼小叫地出了村。
村是个小山村,出了村是条小河,过了小河是片树林子。过了树林子就是一架很大的山。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山里。对我们来说,山里是个无比美妙的地方,因为那儿有鸟蛋可以掏,有蚂蚱蝈蝈可以逮,更有许多野果可以采食。那时候物资匮乏,没有多少瓜果供我们食用,野果就成了最高级的奢侈,比如托盘、车梨、毛桃,等等。我们最乐意吃的,当然就是那黄橙橙的杏子了。只是杏子不同于野果,可以随便去山里采摘。杏子是有主儿的,它们的采摘权和食用权,是属于它们的主人的。我们要尝到它们的美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一次贼,偷。
做贼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事。做个大贼,有可能进局子;做个小贼,有可能被人打骂。可是,那杏子太诱人了、太甜蜜了,太想将它们送入口中,满足我们馋涎欲滴的口腹之欲了。为了得到它们,唯有铤而走险了。
我们过了那条清清浅浅的小河。
我们穿过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子。
我们走进绵绵亘亘的山中。
我们进了一道深深的山沟。在山沟里,我们猫了腰,将脚步迈得轻轻,还要在沟中的树丛中、乱石间躲躲闪闪地走,渐渐地就到了沟的尽头。到了沟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山村,村里只住着三户人家。三户人家全姓冯,是亲亲的三兄弟。三户人家的房子周围全部栽满了树,夏天,枝枝杈杈全绿了,就将三户人家的房子遮掩在里面,远远地你若不仔细去看,根本不知道还住着人家。那些将房子遮挡住的树,就有许多果树,有梨,有枣,有桃,有山楂,有柿子,当然,还有杏。其中的一棵杏树还是麦黄杏,杏的个头有鸡蛋那么大,圆圆的,上面有红红的小斑点。麦子黄梢的时候,杏子就熟透了,沉甸甸、黄灿灿,咬一口在嘴里,腮帮上就会挂满蜜汁儿,浓浓的,能将人甜死!
我们的目标,就是那棵麦黄杏。
我们将脑袋抬起来,那上面的杏子果然是熟了,映着天上的太阳,果然是灿灿的黄。我们再次猫了腰,慢慢接近那棵杏树,终于来到了那树下。我们弯下腰,摸起地上的石块儿,奋力地向那杏树投掷过去。哗,如同天上下起雹子,只见无数颗杏子雹点儿似的哗哗地落了下来,一颗一颗,在地上、在草丛中乱滚乱蹦。我们跳将起来,猛扑上前,以极为迅捷的速度捡拾起来。
尽管我们是猫了腰的,踮了脚的,悄悄悄的,可是,还是让人发现了。
发现我们的,是冯家的四妮子,她的任务就是专门看守这棵杏树的。她从院子里蹦出来,立刻就大声呼喊起来。一边呼喊着,一面向我们追过来。刚到手的杏子还没有下肚,当然不能拱手交出,大家吓傻了眼,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我沉着冷静,一声令下,喊,快跑,快跑啊!大家这才撒了脚丫子。我们是顺着山沟爬上来的,要逃脱,就要朝山沟里逃,如此一来,我们就逃得有点屁滚尿流。不知翻了多少个跟头,不知打了多少个滚儿,才从那坡岗上进了沟。
进了沟,我们原以为安全了,刚刚吁出一口气,哪料到冯四妮子并没有罢休,追得越来越近了,手里还抄着一根木棍子。这一下,我们就更害怕了,抱着脑袋继续逃。逃啊逃,终于就逃出了山沟。逃出了山沟,应该算是安全了,回头一看,果真不见冯四妮子的影子了,我们大喜,才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正要从容地享用那些杏子,冯四妮子竟然鬼神一般抄到我们的前面,冷不丁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蹦出来,堵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全傻了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了辙儿。正要乖乖地将杏子交出来,还是我这个孩子王有了主意。我将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了转,突然对伙伴们说,快脱裤子呀,让冯四妮子看咱们的鸡鸡呀。
伙伴们立刻心领神会,眨眼的当儿,就都将裤子脱了下来,一个个冲冯四妮子翘起了屁股。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冯四妮子冷丁站下,脸红红地勾下了脑袋,接着捂着脸,抽答着跑走了。
望着她渐渐跑远,我们才知道已经转危为安。
那一天,吃着蜜似的杏子,我们是唱着凯歌回家的。
虽是唱着凯歌回家的,我还是有些忐忑与不安。毕竟,我们的偷盗行为让冯四妮子发现了,还当着她的面脱下了裤子,向一个女孩子露出不该露出的部位。这应该是一个十分恶劣的事件,她如果将此事件告诉她的爹,那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了,我这个头儿就更逃脱不了干系。父亲喜欢揪我的耳朵,那是我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我犯了错误,父亲大人就不仅仅是让我耳朵吃苦的事情了,究竟如何惩治我,我都想象不出来,我只知道父亲会将牙咬紧了,凶凶地对我说,老子揍死你!老子不揍得你学祙子叫,算我不是你的爹!
我一直不知道祙子也会叫,更不知道祙子叫是什么样的声音,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一定是十分恐怖和难听的。
我怕极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敢出家门。不但连家门也不敢出,还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支着耳朵,听我家那只大黑狗叫。
那只大黑狗如果叫,就是家里有人来了。
那只大黑狗如果凶凶地叫,就是家里有陌生人来了。
那只大黑狗如果凶凶地、疯了般地叫,就是冯四妮子的爹冯秋山来了。
冯秋山是个打狗子。他在每年入冬的时候,就在怀里揣上一条勒狗绳,走村串庄去买狗,然后将狗杀掉制作成狗肉肴,盛在两只瓦盆里,挑到公社驻地去出售。那时候是不准许个人随便做小生意的,即便是到了冬闲,也要组织起来搞大会战。冯秋山就经常跑到我们家,找我父亲求情,批准他去打狗挣些活泛钱。冯秋山来了也不空着手,总是将狗肉肴包在一枚干瘪瘪的荷叶里,给我父亲尝鲜。不知是父亲受了他的贿赂,还是同情他一大家子,穷得实在揭不开锅,总是无声地默许。冯秋山打狗,就同狗们结下了仇口,他不管到哪里,只要同狗相遇,狗们就疯狂地咬、没命地咬。一只狗咬,两只狗咬,三只狗咬,一会儿,全村的狗就咬成了一片,比起世界大战还凶嚣。
我家的大黑狗突然叫起来,而且是疯狂地、凶凶地叫起来。
这是我们去偷杏子的第三天。
过了三天,我见姓冯的并没有什么动静,原以为太平无事了,正喜滋滋地准备喊上喜子他们再到山里走一遭,可是,我的腿还没有迈出门槛儿,狗就没命地咬起来。我的心立时就提到了嗓子眼。我踮了脚,探出脑袋朝门外一看,我的那个天啊,果然有人走进我家的院子来,来人果然是冯四妮子的爹冯秋山。是夏天,冯秋山自然不会带什么狗肉肴来贿赂我父亲,可是,他的手里并没有空着,我拿眼一看,竟然是冯四妮子。冯四妮子穿着一件破烂烂的小红褂子,扎着一对弯弯的豆角辫儿,低着眉、顺着眼,一只小手牵在他爹的大手里。看见冯四妮子的一瞬间,我的腿就打起软儿来,心怦怦地差点跳出嗓子眼。我知道,人家这是找上门儿来算账了。想起父亲凶凶的样子,想起挨揍时我要发出祙子的叫声,我差点儿尿了裤子。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逃走。可是,已经晚了,冯秋山那架山一样的身板儿,已将我牢牢地堵在了屋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一闪身子跑到了里间。
父亲是在家的,吃过早饭后,正歪在床沿上看报纸。我躲到里间的门后面,一面吓得打哆嗦,一面侧着耳朵听。我打算好了,如果父亲闯进来揍我,我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也不出来。半天过去了,父亲并没有闯进来,冯秋山也没有告我的状。我支着耳朵听,听了老半天,终于还是听明白,他来找我父亲,是要把冯四妮子送给民兵连长梁有全。他自己做不了主,让我父亲给批准。
父亲说,这是好事啊,梁有全的媳妇不生孩子呢!
冯秋山说,那,村里能同意?
父亲说,既然是好事,村里怎么能不同意呢?
冯秋山说,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父亲说,只要你这个当爹的舍得,定就定了呗。
冯秋山说,好。
冯秋山说过好之后,就站起来,手里牵着冯四妮子走了。
爷俩儿走远了,我才知道太平无事了。肚子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胆子就又大起来。我从门后闪出来,悄悄地溜出屋,追着那爷俩儿去了梁有全家。
民兵连长梁有全三十多岁了,娶来媳妇差不多有十来个年头,可是就是不生孩子,这事在我们村是人人知道的事情。梁有全当过兵,人高马大的一个汉子,又在村里当民兵连长,是父亲最为器重的左膀右臂,算是头面人物,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在村里人面前便很是抬不起脑袋,经常听他唉声叹气。收工回家,就喜欢喝闷酒,喝过酒之后,就喜欢打老婆。他老婆杨丽娟眉清目秀的,还有一副圆崩崩的大屁股,能将报纸上的文章念得哗哗的,因为不生孩子,经常挨男人揍。梁有全打她,她从不反抗,只是抱着脑袋哭,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她家距我家不是很近,隔着好几幢院子,但是每次挨揍的时候,她的哭声却能传到我家里来。母亲听了就很为她抱不平,就跑过去安慰她。如果梁有全在场,母亲就狠狠地骂他。杨丽娟听了,竟反过来劝我母亲,说,大嫂,就让他打吧,谁让俺不生孩子呢?
母亲说,不生孩子就该挨打啊?她说,俺对不起人家啊!让人家绝后了啊!母亲劝了几回,杨丽娟都是这么个态度,母亲也就懒得去管了。
除了梁有全外,我们村里还有一个男人喜欢打老婆,就是冯秋山。
冯秋山打老婆,也是因为子嗣的事。他老婆并非不生育,而且还挺能生,嫁给冯秋山不到十年,就一气儿给他生了七个孩子。只是七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儿子,全是些丫头片子。在村里,只要没有儿子,同样是绝户,冯秋山的老婆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冯秋山是个打狗子,他打老婆时就采用对付狗的手段,用勒狗绳将老婆吊起来,用树条子拼命地抽,抽一下,还要骂一句。他老婆就没命地哭。如果是顺风,哭声甚至能从山里传到村里。如果恰巧梁有全也在打老婆,两个女人的哭声就会交织在一起,抑扬顿挫、遥相呼应。

同病相怜,梁有全同冯秋山竟然成了好朋友。冯秋山来我家,除了送给我父亲一包狗肉外,还总是带着另一包,那是送给梁有全的。每次送给梁有全狗肉时,冯秋山总要留下来,同梁有全喝上一气酒。两人就着狗肉肴,总是将酒喝得醉醉歪歪。有时一面喝着酒,想着没有子嗣的事,还要相抱着脑袋大哭上一场。
我追着冯秋山的屁股来到梁有全家时,梁有全正在家里打老婆,他将老婆按定在院子里,手里抄了只鞋子,正在猛打,打得杨丽娟的屁股啪啪响,看见有人进了门,他才将举起的鞋子定格在半空中。
梁有全说,秋山哥,你怎么来了?
冯秋山说,给你送闺女来了啊?
送闺女?梁有全鼓着眼珠子不明白。
冯秋山说,你忘了?那天喝酒时我说的什么?
梁有全眨着眼睛想了想,才猛丁想起来,他望望冯秋山手里牵着的冯四妮子,又望望冯秋山,急忙将老婆从地上扶起,咧嘴笑着说,嘿,丽娟,咱们也有孩子了呢!秋山哥真将他闺女送给咱了呢!
杨丽娟开始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站起来,看看梁有全,又看看冯秋山,再看看冯四妮子,忽然就乐了起来,划着泪痕的脸上又流下了泪。
冯四妮子就做了梁有全与杨丽娟的女儿。
冯四妮子来到梁有全家,杨丽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代销铺,给冯四妮子裁了件花褂子,接着牵着她的手,把她送到了小学校,让她上了学。冯四妮子原来有大名,叫冯四兰,上了学之后,就将名字给改叫梁小兰。但是我们既不叫她冯四兰,也不叫她梁小兰,我们叫她冯四妮子梁小兰。
冯四妮子梁小兰同我一般大,就和我读了同一个年级,而且,还和她桌挨着桌儿坐。想起那天去偷杏时冲着她脱裤子的事,我对她充满了戒备与怯意,生怕她将此事给老师说。那样,事情就糟糕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生担心的情况,才将心放进了肚子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冯四妮子梁小兰非但没有找老师告状,有这么一天她来上学时,还突然将我拦在校门口,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杏子递过来。
给,她说。
我怔住了,不相信她会以德报怨。
见我不接,她又说,拿着呀,俺家的杏可甜呢!
我还是没有接,我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怕可能是一个骗局。
她瞟了我一眼,说,怎么,不要?不要我可给别人了。她说着转身要走。
杏子的甜蜜是太诱人了,如此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呢?我不管是不是骗局了,伸出手,极端没出息地接了过来。
杏子如糖似蜜地吃在肚子里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有点自鸣得意了。
更让我得意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竟然经常性地吃到她带给我的山果,除了杏之外,还有桃子、李子、山楂什么的。
在学校读书,我们是一个年级,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和她也经常在一起玩,拾柴、摸鱼什么的。她的红衣服在我们这些小子中,总是那么扎人的眼睛。我甚至有些喜欢起冯四妮子梁小兰来。
自从梁有全有了女儿后,就不再打老婆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杨丽娟更是换了一个人,再也不埋头走路了,再也不低声下气了,非但不,还经常听到她脆脆的笑声飞起来。他们家和冯秋山家的来往就更加密切。我去找冯四妮子梁小兰玩时,经常见冯秋山坐在梁有全家,咣咣地碰着杯子喝地瓜烧,杨丽娟则在一边笑笑地给两人热菜倒酒,嘴里一口一个秋山哥,叫得亲亲的、甜甜的。
冯四妮子梁小兰到梁有全家时是夏天,转眼间夏天就过去了。又转眼间,秋天就来了。再一转眼,冬天就来了。冬天来了的时候,冯秋山又干起了打狗的营生,天天见他带着勒狗绳走街串巷,惹得一村狗狂咬;村里的其他人,则又集中起来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山岗上红旗招展、炮声隆隆、人喊马嘶。就是在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时候,梁有全出事了,他让塌方倒下的石头砸死了。
梁有全死了,杨丽娟就成了寡妇。那时候,村里是有几个寡妇的,但大都是年老的寡妇,都六七十、七八十了。杨丽娟还不足四十岁。不足四十岁就守了寡,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村里软心肠的女人们都为她抹泪与叹息,都思谋着为她寻出路。
第一个为杨丽娟改嫁操心的,就是我母亲。她找到杨丽娟,一面纳着鞋底儿,一面说,兰子她娘,你还年轻,总不能这么一辈子啊?改嫁吧。
杨丽娟却摇头。
母亲说,你可得想开啊,现在是新社会,寡妇改嫁是正常的事啊。
杨丽娟还是直摇头。
母亲知道杨丽娟性子犟,劝了一阵子,见没有松口的可能,叹着气走了。杨丽娟也就一直过着守寡的日子。好在有冯四妮子梁小兰陪伴,寡妇的日子倒也不怎么寂寞。转眼,一年就过去了。再一转眼,两年就过去了。时间过了差不多有三年,寡妇杨丽娟竟然怀上了孩子。等村里人知道情况时,她的肚子已经高高地鼓了起来。寡妇突然怀上了孩子,在村里自然又生出一场波浪来。有一段时间,村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嘀嘀咕咕、交头接耳的,就是议论这件事。嘀咕了一阵子,大家得出的结论有两条,一是梁有全与杨丽娟之所以没有孩子,原来压根就不是杨丽娟的事;第二条,便是杨丽娟并没有守住寡,不知跟哪个野男人搞上了。接下来,这个野男人是谁,便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关注归关注,野男人是谁却一直是个谜。
谜还没有解开,杨丽娟就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下面带把儿的男孩。其后,杨丽娟就同养女冯四妮子梁小兰,以及亲生儿子过起来。走在村巷里的时候,经常见她开着怀,露出白生生的两只大奶子给孩子喂奶,脸上现出的表情都是慈爱而又骄傲的内容。很快,她的儿子就到了七岁。到了七岁,该是上学的时候了。这一年,过了暑假,学校里要招新生时,杨丽娟就领着小儿子来登记报名。
老师吴加刚说,叫啥名?
杨丽娟说,冯志强。
吴加刚一怔说,他父亲不是叫梁有全吗,怎么叫冯志强呢?
杨丽娟说,俺就给他起名叫冯志强。
柿子树
槐花是突然之间开放的,一嘟噜一嘟噜,一串儿一串儿,绵绵密密,挂满了枝枝杈杈,雪也似的白。花儿释放出的浓香,弥散得满街满巷都是,吸一口在腔内,能让人飘飘忽忽、熏熏欲醉。太阳也挺不错,高高地悬挂在头顶上,将明艳而又灿灿的光普照而下,把所有的物事照得炫亮。我置身在艳阳与浓香中,站在村头的小坡岗上,伸了脖子,在朝远处张望。不单我在朝远处张望,村里还有许多人都跑过来,伸着脖子朝远处张望。而且陆陆续续的,还有更多的人从家中、从村巷里走出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眨眼间,村口上就聚起一大片人。大家一面张望着,一面在那里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脸上都带着有事的表情。
我们张望的地方,就村子对面的那架山。
那是一架很大的山,东西走向,高高低低,龙似的从远处逶迤而来,又龙似的伸向远方。在山的腹部,还有许多分支与分叉,似是龙身上生出的爪,横一道,竖一道。爪与爪之间,就形成许多的沟与豁。在这些山梁沟壑中,却有一座与别的山不接壤的独立山包,看上去很是另类。那山包圆圆的、高高地矗立在那里,似是女人硕大无朋的乳房。我们管这座山包叫奶子崮。
前些年,我们经常去奶子崮。因为奶子崮上有一棵杮子树,那杮子树很大、很高,老枝杈丫、如龙似虬,一到秋天,树上的杮子就熟透了,一枚一枚,似是挂满了小红灯笼。我们就攀到树上,揪杮子吃。熟透了的杮子是比蜜还甜的,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大快朵颐。杮子没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到这里来,因为那崮的岩壁上有许多老鸹在那里做窝,我们借着岩壁的缝隙攀爬上去,总能掏到它们的卵蛋或者小雏。可是后来我们就不敢去那儿了,因了那儿成了一块凶地。
那是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那天晚上村里有电影,一村人都聚集在村头的空场上看电影。电影刚看了一半,不知谁抬了一下头,发现黑夜中的奶子崮上亮起了许多灯明。那灯亮亮晃晃、明明暗暗,久久地不见消失。过去的奶子崮在晚上是从来没有灯明的,这些灯明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什么人要在夜晚去崮上呢?村里人感到了强烈的好奇。不过,尽管好奇,并没有谁跑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毕竟是黑漆漆的晚上,而且还有电影要看。因此,直到第二天天明,村里人才知道了答案。原来那奶子崮上的杮子树上吊死了两个人。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是与我们村相邻的村子的,虽然已经各有各的家室了,却勾搭在一起了,最终让人捉奸在床。事发之后,两人就选择了殉情,跑到奶子崮上来,双双吊死在那棵杮子树上了。等村里人发现他们时,两具尸体已经腐败得不成样子。本来,双方的家人是要将他们抬回村子,各自埋在各自家里的坟地的,见实在没有办法向崮下搬运了,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埋在了那崮上。那崮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土,全是石头,连坑也无法挖下去,大家就收集些石块儿,将他们堆在了石块下。
崮上发生了如此的凶事,又有两座石块儿堆起来的坟冢戳在那儿,村里就没有人再敢到崮上来。大人不敢来,小孩子们就更是不敢近前半步了。别说去那崮的顶部了,就是附近的小山小岗,我们都不敢再去了。
现在一村人都跑到村头上,站在那里望奶子崮,是因为奶子崮上又出事情了。今日一大早就有人传来消息,说那棵杮子树上又有人吊死在那里。而且,这次吊死的,是我们村里刘喜才家的三女儿冬梅。
冬梅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她还有一个外号叫三妖精。
刘喜才家就在我们家西边住,中间隔着喜子家。刘喜才家是村最穷的一户,他老婆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儿子,三个是女子。刘冬梅是老小,在女子中排行第三。刘喜才一家十口人,只有他一个壮劳力,日子过得如何凄怆也就可想而知。晚上捉迷藏的时候,我经常溜到他家里去躲藏,有时还趴在窗子上朝他家屋里看。冬天,天气冷寒,他家的人穿不起暖和的棉衣,就缩在炕头上,盖着一床烂被子用相互的身体取暖。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似是一窝猪崽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最穷困的人家,却出了位闭月羞花的美人儿,便是三妖精。
三妖精还不仅仅美丽,她还有一副别人不具备的好嗓门,最是爱唱歌,只要嗓门一亮,就好似画眉鸟悦耳的啁啾。那时候村村都有宣传队,一过了秋,打罢了场,就要聚拢起来排演节目,三妖精的美丽和好嗓门,让她想不成为宣传队的主角都难。更兼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平时喜欢唱两口,知才爱才,自然就将她吸收到宣传队来了。不但吸收到宣传队来了,还派她去镇上进修了半年,顶替随军的春红当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又是村里最雅致轻闲的美差,自此之后,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村巷里,大家见到的她,就都是美丽而又迷人的仙女了。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的美丽,又努力地要向更极致的方向发挥:穿的衣服虽然破旧,但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本来就缎子似的黑亮黑亮,又总梳得齐齐整整;走起路来时,再有意扭摆起柳条小腰和圆鼓鼓的屁股,那韵味儿就有了,那风情就出来了,就有了勾魂摄魄的魅力。
三妖精不管走到哪里,身上都牵着男人馋馋的目光。
三妖精刘冬梅在村里美丽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到了十四五岁的年纪,并且由小学升到了初中。
村里是没有初中班的,要想继续读书,就得到公社驻地去。和我一般大的伙伴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辍学,到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公社驻地上了初中。其实,我的学习一点也不好,尤其是算术,更是狗屁不通,每次考试总是得个大鸭蛋。去公社驻地上初中,我一万个不愿意。父亲却非让我继续上学不可,不仅让我读完初中,还要让我读完高中。无可奈何,我只好苦着脸子去了学校。好在,那时候经常搞运动,学校三天两日就要停课闹革命,我去学校的时间少,留在村里的时间多,也就有机会仍然同伙伴们在一起。
已经成为半大小子了,我们当然不能老是玩耍了,得帮着大人干些事情了。那时候,最适宜我们干的事情就是拾柴禾。春天,我们扛着镢头去山里刨草根;夏天,我们就抄着鎌刀去山坡割青草,秋天到来的时候,则背着一个大花笼筐,去树林子里搂树叶。那片树林子十分大,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边。当然,名义上是去搂树叶,更多的是在树林子里玩。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已经不满足于玩攻山头、捉迷藏之类的游戏了,我们开始玩更高级些的游戏,比如打扑克、下棋什么的。除了打扑克下棋,我们还开始了在性方面的涉猎与探索。伙伴里面只有我上了初中,就比他们多掌握了些这方面的信息,我就似个使者,将信息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他们。比方公社公共厕所里那些关于性的打油诗,还有男女阴具与阳具的涂鸦,都是由我吸收过来,又传播给大家的。有一次,甚至在我的提议下,大家来了次集体手淫。
那天落叶飘飘,六七个半大孩子躲在树丛中,排成一溜儿,都将裤子脱到脚踝处,挺直各自的阳物。我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只是,正当我们做着那种动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响,有人朝这边走过来。拿眼一看,是三妖精。她背着个小药箱,是去林子那边的小山村里巡诊的。我们一惊,忙提上裤子逃走了。尽管是逃走了,心还在怦怦地跳,我怕刚才的事情让三妖精看到。如果让她看到了,那可就惨了。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心里喜欢她。
我暗暗喜欢三妖精,伙伴们暗暗喜欢哪个女孩子,我并不知道。于是,有这么一天,我们再次来树林子拾柴禾时,我便发出了一个提议,让大家用都坦白坦白,看看各自喜欢哪个女孩子。
众伙伴们平时就对我言听计从,齐说,好。
我说,那,咱们谁先说?
众伙伴们却不好意思起来,你推我,我推你,又把眼来望我,齐让我先说。
我自然不想将自己的秘密先告诉大家,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咱们找块石板,喜欢谁就写上谁的名字,然后再同时亮出来看,怎么样?
我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齐说,行。
树林子里有许多薄薄的石板,再找一块硬些的小石子儿在石板上划,很容易地就能将字写出来。一会儿,大家就将各自喜欢的人名写在了石板上。接着,再将各自手里的石板集中起来,一齐翻转,亮给大家看。这一亮,所有的人都怔住了,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写得竟然是同一个名字:三妖精!
哎呀呀,都喜欢三妖精啊?我们全叫了起来,又全大笑了起来。
随后的日子里,都暗暗喜欢三妖精这件事,就成为我们之间公开的秘密。只是,秘密公开之后,我们却无一例外地都对三妖精疏远起来。过去,村里的卫生所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一进卫生室,我们就喜欢不停地抽鼻子。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在闻来苏水的味儿,其实不然,我们是想从来苏水的味儿中,捕捉三妖精的气息。三妖精喜欢打扮,总是弄得香喷喷的,人走到哪里,就将香味带到哪里,那香味儿闻到鼻子里,会让你有一种迷醉的感觉。自从大家都喜欢她的秘密公开化后,我们都矜持起来,发现谁朝卫生室跑,就会遭到嘲笑和揭发。
我们便浅尝辄止、裹足不前了。
可是,现在,让我们喜欢的姑娘竟然上了吊,死了。这是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想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站在村头的空场上,我发现伙伴们也全来了,大家同我一样,也站在那里引着脖子朝那崮上望。我们相互交换一下眼神,都不知说什么好,都在心里暗暗地难过和惋惜。
奶子崮上有好些人影在晃动,那是父亲指挥着村里人为三妖精收尸。眼神好的,甚至能看见收尸的人是怎么将三妖精从树上放下来的,又是怎么将她从崮上抬下来的。只是最终,三妖精和邻村吊死的那对男女一样,并没有被抬回村子里来,正儿八经地举办一次葬仪,而是在崮下面的一个小坡岗上,随便挖了个坑儿埋在了里面。
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死了,在我们村还是史无前例的。她为什么要上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也是村里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事发的当天,我们就知道了原委:三妖精怀上了孩子,都七八个月大了。三妖精还是个姑娘,还没有嫁人,甚至连婆家也没有找,突然怀上了孩子,自然是不许可的事情,是无法向大家交待的。正是因为不许可,无法交待,她才选择了自杀。村里人自然也知道,一个姑娘怀上了孩子,并不是姑娘一个人的事情,促成这件事情的,应该还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一定得是位男人。那么,那个与三妖精怀上孩子的男人是谁呢?
很块,大家便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是小学教师吴加刚。
吴加刚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高中毕业后,他本来可以去当兵的,因为家里的成份问题而搁浅。无可奈何,他就当了小学教师。吴家刚不仅有文化,还会写毛笔字,村里每次搞运动,是要张贴标语的,这些标语就都出自他之手。当然,除此之外,过年时家家贴的对联,婚嫁时的喜联,也全出自他的手。他不仅会写毛笔字,还会唱,有一副亮亮的好嗓门。村里宣传队的男一号,就由他来担当,并且和三妖精成了搭档关系。唱《红灯记》,吴加刚扮李玉和,三妖精扮李铁梅;唱《智取威虎山》,吴加刚扮杨子荣,三妖精就扮小常宝,再加之他人长得相貌堂堂,两人在一起,很有那么点珠联璧合的味道。而吴加刚因为成份不太好,说了个媳妇丑丑的,有三妖精这么一朵花在身边摇曳生姿,他如果不采摘,就只能是傻子了。
三妖精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种,肯定无疑。
村里人的猜测没有错,事情马上就得到了证实。
刚刚将三妖精的尸身入土,刘喜才就闯进我家来。
当时父亲正喝着小酒,将酒瓶子咂得吱吱响,刘喜才的闯入让他不由一怔道,喜才,你怎么来了?
刘喜才抱着脑袋哇哇大哭道,书记啊,你可得为俺做主啊,俺好好的一个闺女,不能就白白地死了啊!
父亲怔了一下说,她是自己吊死的,你让我做什么主啊?
刘喜才哭着说,可是,她是怀了孩子才死的啊?一个黄花大闺女,咋就怀了孩子呢?你得给俺找出那个家伙啊!
父亲又怔了怔,说,我又不是公安,怎么给你找啊?
刘喜才更大声地哭着说,还用找吗?就是吴加刚那个王八羔子啊!
父亲还是怔了怔,说,喜才,你可不能乱说啊,要有证据啊!
刘喜才就又大哭起来,说,全庄人都说是他,还有假啊?
父亲说,都说是他也得有证据呢。
刘喜才就不讲话了,瞪着眼睛盯我父亲,忽然脸一拉道,俺知道你向着吴加刚,俺找公安局告状去!说着,站起来转身就走。
父亲丢下手里的酒瓶子想追他,刘喜才早刮风似的出了院门,不见人影了。父亲冷丁一下站定在那里,慢慢地又跌坐在凳子上,眉头拧起一个大疙瘩。我和母亲都知道,父亲每当将眉头拧成大疙瘩,就是遇到难事了。父亲遇到难事的时候还会发脾气,看见谁不顺眼就会甩耳光子。我和母亲都有些怕,不敢拿正眼去看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忽然听得门外一阵脚步响,门开了,又见一个人一头闯进来。大家还没有认出来者是谁,那人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我忙拿眼去细看,是小学校的老师吴加刚。吴加刚跪在那里,就给父亲叩起了头,嘴里说,书记啊,求求你救救我啊。
父亲先是皱眉头,接着说,吴加刚,看来那事还真是你作下的了?
吴加刚说,书记啊,是我对不起刘冬梅啊。
父亲盯着吴加刚,冷冷地说,你作下了,那就承担责任吧!
吴加刚突然哭起来,说,可是,我进去了,我一家咋办啊?孩子小,老人老……
父亲还是冷冷地说,知道今日,当时干什么去了?
吴加刚哭着说,书记啊,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啊,是她主动的啊!那天晚上,我们排完了节目,她突然说肚子疼,就倒在我怀里了啊……
父亲的眉头就皱了起来,突然提高了嗓门怒怒地道,吴加刚,别说了!你们俩没一个好东西,给咱们村丢人现眼!
吴加刚抬起眼望望父亲,见父亲冷着个脸子严肃得像尊神,他便跪行着向前,抱住了父亲的腿,哭着说,书记啊,你可要救救我啊。
父亲盯着吴加刚,闭着嘴没有吭声。过了半天,他才将吴加刚推开,口气和缓了下来道,你和三妖精的事,别人看见过吗?
吴加刚说,没有。
你们的事,村里没任何人知道?
吴加刚说,都是胡猜,没任何人知道。
父亲还是拿眼盯着吴加刚,沉吟了半天之后说,没人知道,那就好。我告诉你,只要你咬住口,死也不承认,这事就好办了。
吴加刚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冲着父亲点了点头,爬起来,走了。走到门口,又返转了回来,扑通一声跪下,再次给父亲叩了个头。
三妖精的爹果然告到了公安局,村里就来了一辆三轮电驴子。电驴子在大队部院门外停下,从上面下来三个公安员。三个公安员来到大队部,先是知会了我父亲,接着就挨门串户地开始了走访与调查。最后,命人将吴加刚带进了办公室。那一天,大队部院门外热闹起来,大家聚集在那里,一面七嘴八舌地嘀咕着,一面冲着院子张望,看公安员怎么把吴加刚铐走。但是,三个公安员一连审了吴加刚三天,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来。
吴加刚逃过一劫,刘喜才也没了辙儿,渐渐地,也就将这事忘下了。
不过,吴加刚还是得到了惩罚。惩罚他的,就是我们。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我们悄悄地翻进他家的墙院,将一只臭哄哄的死猫吊在了他家的门鼻子上。第二天,姓吴的开门去学校上课,一见那死猫,差点将魂儿吓掉了。
我在公社读完了初中,又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不久,在父亲的周旋下,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省城,成了位吃皇粮的城里人。不过,每逢过春节,我还是要回老家来过的。每次回老家,只要一到村头,一望见那片熟悉的房舍,我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就是三妖精刘冬梅。我就不由自主地站下来,举起眼睛朝奶子崮望。苍茫的天底下,就会看到那座山崮高高地挺立在那里,那棵柿子树也还在,甚至还能看到上面的几只老鸹,正在那里发出呱呱的叫声。但是,有这么一年,我在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却不见了那棵柿子树,崮顶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团白云在那里飘。我很是奇怪,带着疑问回到家中,从母亲那里我才知道,那杮子树是父亲临离任的时候,派人用斧子给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