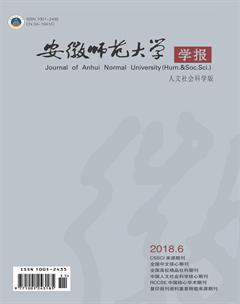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基于“毁绿种菜”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卢义桦 陈绍军
摘要: “毁绿种菜”现象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毁绿种菜”的始兴、“除菜还绿”的反复、“走访劝说”的尝试和“开心农场”的建立等四个阶段;对其治理可以分为“堵”“疏”以及“疏堵结合”等三个阶段,并呈现出由“硬治理”到“软治理”再到“复合共治”的实践逻辑;治理的内在机制是为情感提供实践空间,使土地情感在社区空间中得以表达。社区治理应当纳入情感和空间的维度,并以空间营造的方式实现情感的再生产,最终实现社区的善治。
关键词: 毁绿种菜;软治理;硬治理;复合共治;情感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6014109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 is quite common nationwide, and it is always a major problem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will have a systematical study o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cess, practical logic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 by taking a case study of L community in N city of J Provinc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henomenon of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rising of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 the repetition of “uprooting vegetable and planting green plants”, the practice of “interview and persua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appy Farm”;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f “blocking”, “dredging” and “combination of dredging and blockage”, and present the practical logic from “hard governance” to the “soft governance” to the “composit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space for emotion, to make sure land emotion could be expressed in the community spac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should incorporate the dimensions of emotion and space and exert their function, and make emotion reproduction to realiz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in the way of space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
Key words: growing vegetable by destroying green belt;soft governance;hard governance;composite governance;emotional governance
近年來,“毁绿种菜”(又被称为“占地种菜”“圈地种菜”)现象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屡禁不止,并成为很多社区久治不愈的顽疾。伴随着“毁绿种菜”现象的愈演愈烈,国内各类媒体对此的报道不断涌现,层出不穷。绝大多数的报道认为“毁绿种菜”是一种不文明现象,应当禁止。报道内容主要是各地方如何整治“毁绿种菜”现象的实践经验。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报道认为应当换种思维看待“毁绿种菜”,比如通过开辟“开心农场”、鼓励“阳台种菜”或引导居民以其他方式来进行种菜等。不断见诸报端的“毁绿种菜”现象已然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治理议题,属于社区治理微观层面的“末梢治理”。虽然在社区治理工作中对于“毁绿种菜”的整治是一件小事,但往往是这些看起来无关痛痒但却像“牛皮糖”一样的事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社区治理成本,使得社区治理出现“碎片化”,不利于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换言之,正是诸如“毁绿种菜”等众多“小问题”构成了社区治理的诸多面相,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治理这些“小问题”便是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拷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那么社区到底该如何治理“毁绿种菜”呢?“毁绿种菜”可以被根治吗?“毁绿种菜”的治理对于当前社区治理有何启示?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对于治理“毁绿种菜”的研究,可以为其他相似类型的社区“微治理”提供治理经验。
目前学界关于“毁绿种菜”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毁绿种菜”发生及延续机制[1]、“毁绿种菜”与邻里矛盾[2]、英国“配额地”制度对“毁绿种菜”的启示[3-4]、“毁绿种菜”的原因与对策[5]等。显然,学界对于社区应当如何整治“毁绿种菜”仍未能在经验和理论层面进行详尽的探讨。笔者在J省N市L社区进行有关社区建设及社区治理方面的调研时,发现该社区之前发生过“毁绿种菜”现象,社区治理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后来专门开辟了一块“开心农场”供社区居民种菜,使得“毁绿种菜”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这引起笔者的关注与思考。本文遵循既有关于“毁绿种菜”的研究脉络,从实践社会学视角出发,对L社区“毁绿种菜”的治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对L社区治理“毁绿种菜”的过程进行全景式呈现;其次,阐释从“毁绿种菜”到“开心农场”这一过程中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再次,从土地情感和空间再造两个方面阐释“毁绿种菜”治理的内在机制;最后,基于上述讨论探究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以J省N市L社区为研究个案,经验资料来源于2017年8月笔者对L社区的田野调查。L社区位于J省N市城郊,于2012年由3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是一个拆迁安置社区,社区总面积7.3平方公里,人口2800多人,其中劳动力人口约占60%。笔者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L社区“毁绿种菜”的社区治理展开调研,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一、从“毁绿种菜”到“开心农场”:一场社区“种菜运动”
L社区“毁绿种菜”现象及治理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毁绿种菜”现象在L社区开始出现并渐渐兴起;其次,社区反复多次开展“除菜还绿”运动;再次,社区通过上门劝说等非正式制度手段治理“毁绿种菜”现象;最后,伴随着“开心农场”的建立,L社区“毁绿种菜”现象最终走向终结。
(一)“毁绿种菜”的始兴
L社区于2012年6月建成后,社区居住开始陆续入住。“毁绿种菜”现象也从此时开始出现。一些老年人发现社区有空地后,便开始利用这些地块开始种菜,主要种植的是一些平时食用的蔬菜。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开始“毁绿种菜”。从楼前楼后的绿化带到社区四周的边角地,几乎都被社区居民开垦为一个个“家庭菜园”。从刚开始的极少数社区居民开始零星种菜到形成大范围的“毁绿种菜”,用时不到2个月的时间。当时,只要走进社区就能看到绿化带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在社区内“毁绿种菜”的居民以老年人和妇女为主,他们普遍拥有农业种植的经验和习惯。在这一阶段中,“毁绿种菜”现象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呈现出发生快、扩散强的特征。
(二)“除菜还绿”的反复
伴随着“毁绿种菜”现象的愈演愈烈,加之有社区居民的不断举报,社区居委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了“毁绿种菜”的专项整治工作。2012年11月初,由L社区居委会联合T街道办、物业管理公司联合采取强制性措施清除社区绿化带及边缘空地上的蔬菜和其他农作物,并及时为绿化带复绿,基本消除了“毁绿种菜”现象。同时,L社区加强了巡查力度,并张贴了相关宣传标语,又正逢秋末冬初天气寒冷,不适宜蔬菜生长,所以并没有再次出现“毁绿种菜”现象。然而,随着天气转暖,“毁绿种菜”现象又有了死灰复燃之势,社区居民又开始了“毁绿种菜”行动。于是,L社区又开展了一次“除菜还绿”运动,但是此后“毁绿种菜”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难以根除。在这一阶段中,社区主要采取“堵”的办法来应对“毁绿种菜”,社区与种菜居民一直处于长期对抗的状态。
(三)“走访劝说”的尝试
经过多次“除菜还绿”,L社区的“毁绿种菜”现象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社区发现采用“堵”的办法应对“毁绿种菜”只能取得短时效果,无法达到治本的效果。于是,社区想办法变“堵”为“疏”。2015年3月,社区组织3名管理人员,对于一些反复“毁绿种菜”的社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劝说,对他们的种菜行为进行劝告,并疏导他们的情绪,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种菜居民进行自我反思,从主观意识上放弃“毁绿种菜”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规劝,一些社区居民主动放弃了私自开垦菜园,一些居民表面上答应不再种菜,但仍然会偷偷种菜,还有一些居民据理力争,不听劝导。在这一阶段中,社区主要采取“疏”的方式应对“毁绿种菜”现象,希望通过劝说、讲人情等非正式制度手段破解“毁绿种菜”难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未能根除该现象。
(四)“开心农场”的建立
在与种菜居民的沟通与交流中,社区管理人员发现每个种菜居民种菜的动机都不尽相同。这些动机包括经济需求、农耕情结、食品安全、休闲娱乐等。同时,社区管理人员意识到“毁绿种菜”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居民种菜需求与社区没有空余地块之间的矛盾。因之,如何利用现有的資源引导并满足社区居民的种菜需求是解决“毁绿种菜”现象的根本办法。于是社区转变思路,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2016年4月,社区在东侧开辟专门地块建设了约10亩的“开心农场”,引导有种菜需求的居民有序地种植,并成立了“种菜者协会”。有种菜需求的居民自愿入会,每年交纳100元的会费即可获得一小块家庭菜园。同时,社区要求协会会员需认领一块“责任绿化带”,有义务对绿化带进行日常监管巡查。另外,社区将“禁止毁绿种菜”写进《社区居民公约》,鼓励互相监督,并建立一套日常巡查机制,杜绝了“毁绿种菜”现象的再次发生。
二、“毁绿种菜”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
探究社区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构是理解社区层面治理的关键。[6]L社区对于“毁绿种菜”现象的治理过程可以分为“堵”“疏”以及“疏堵结合”等三个阶段,呈现出由“硬治理”到“软治理”再到“复合共治”的实践逻辑。
(一)“堵”:硬治理
乡村社会的“硬治理”是建立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的一种治理理念,推崇“政府本位”,推崇法律法规、强制等“硬权力”,并具体化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一整套治理体制,包含精神文明建设、户籍管理、卫生管理、社会治安等等具体的制度和机制。[7]76-77在农村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硬治理”是指依托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采取行政化治理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种方式,其具有标准的明确性、方法的原则性、手段的强制性以及效果的即刻性等特征。[8]在L社区整治“毁绿种菜”现象的起始阶段,通过强制性手段铲除菜地的“硬治理”方式是主要的治理策略。
我们制定了“毁绿种菜”整治方案,并联合街道办、物业公司一起强制执行,开展“除菜还绿”运动。在推进过程中,一些居民拒不配合,我们8个人轮番上阵用铁锨和小铲车,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完成任务。(社区主任LQS)
从社区主任LQS的话语中可知,对于“毁绿种菜”现象的治理发生于该现象严重之时,且主要以“堵”的方式进行,体现了“硬治理”的基本特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应归全体业主所共有共管,如若改变公共用地的形态和用途,应由业主们共同决定,单个业主无权擅自分配使用。显然,“毁绿种菜”是部分业主的个体行为,并没有得到全体业主的同意,侵犯了小区所有业主的权利,是一种越轨行为,这为社区治理“毁绿种菜”现象提供了合法性基础。L社区制定了治理“毁绿种菜”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据此联合T街道办和物业公司使用强力铲除的方式强制性执行,并在极短时间内消除了“毁绿种菜”现象。然而,“硬治理”只能暂时将“毁绿种菜”现象强压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引发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矛盾,增加了社区治理成本。究其原因,社区“硬治理”注重约束、处罚、法治等强硬手段,而忽视了人心、精神等方面的治理,这就使得治标不治本,陷入周期性的治乱循环。
(二)“疏”:软治理
虽然L社区通过开展运动式治理,达到“除菜还绿”的短期效果,但是“毁绿种菜”现象反复出现的事实证明,“硬治理”并非遏制社区居民“毁绿种菜”行为的长效机制。于是,L社区开始采取上门劝导、宣传告诫、情感沟通等“疏”的“软治理”方式。所谓社区“软治理”是指采取说服、教育、讲道理、沟通交流感情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治理,治理对象由公共事务本身转变为其背后所指涉的人的思想和情感等行为意识,更关注于“社区心态”的培育。相比较于“硬治理”关注于有形的物、制度等,“软治理”更关注于无形的“人心”。[9]
对于“毁绿种菜”的反复出现,与其用“堵”不如用“疏”,硬的不好使咱就来软的,我们对一些顽固的种菜居民以上门劝导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情感疏导,变被动为主动,引导他们意识的转变。(社区副主任WD)
从WD副主任的话语中可知,L社区组织一些管理人员,对长期反复种菜的社区居民进行劝导,通过转变种菜意识以防止“毁绿种菜”行为的发生,并取得不错的效果。可以说,“软治理”相较于“硬治理”,其治理方式更加柔性化,更易于得到种菜居民心理认可和情感认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软治理”,社区内“毁绿种菜”现象发生的频率降低、面积变小。
然而,并非所有的种菜居民都会听从社区管理人员的劝导。一些种菜居民在表面上答应,但暗地里仍偷偷地种菜。还有一些较为“顽固”的种菜居民不听劝阻,依然故我。“毁绿种菜”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种,因人而异。笔者在询问这些人“毁绿种菜”的原因时,发现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土地情感。社区居民通过“毁绿种菜”只能获得微薄的经济收益,土地情感是驱使他们“毁绿种菜”的深层次原因。他们种菜更多地是为了追逐一种亲切感、自我获得感以及生活的归属感,是土地情感的现实性表达。种菜居民看到自己种的菜茁壮成长,精神得到愉悦,心理有满足感和幸福感。因之,“软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当其“遭遇”种菜居民真切的土地情感时,便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换言之,正是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软治理”效果。由此来看,“软治理”亦并非长久之策,因为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是长久而弥坚的,不会随着居住空间变迁而损失殆尽,也不会因情感疏导而即刻淡化。
(三)“疏堵结合”:复合共治
L社区相继使用的“硬治理”和“软治理”方式并未能有效遏制“毁绿种菜”现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治理方法。L社区采用“疏堵结合”的治理方式作为应对之策。一方面,L社区采取“疏”的“软治理”办法,在社区东侧开辟了一块“开心农场”,并成立了种菜者协会,引导有种菜需求的居民在“开心农场”有序地种植,解决了社区居民种菜需求与社区内部土地空缺的矛盾,而种菜者协会的成立使得种菜居民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公共空间,促进了社区居民间的社会融合,使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有了寄托。同时,经过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及居民代表的讨论,将“禁止毁绿种菜”写进《社区居民公约》,充分利用其“软法”的约束力量,并鼓励社区居民互相监督以充分发挥“闲话”等社区舆论的力量。[10]210-213另一方面,L社区采取“堵”的“硬治理”办法。社区居委会要求种菜者协会会员在“开心农场”获得“家庭菜园”的同时,要认领一块“责任绿化带”,并有责任和义务对其所认领的绿化带进行日常监管巡查,发现绿化带有损害后要及时报修。L社区通过强制性认领“责任绿化带”,充分发挥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让种菜居民参与到“毁绿种菜”治理中来,使其实现了自身角色的转型,由绿化带的破坏者变为绿化带的看护者,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式治理”。
笔者认为,无论是刚开始社区采取“堵”的“硬治理”方式的“被动防御”还是随后采取“疏”的“软治理”方式的“主动出击”,都是一种“政府本位”的治理方式,均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区种菜居民的主体性以及情感需求。种菜需求与社区无地之间的矛盾是外在形式,而内在机理则是土地情感与空间再造之间的矛盾。因之,对于“毁绿种菜”现象的治理,不应是通过各种方式压制抑或疏导土地情感,而是要“经营”土地情感,即为土地情感提供实践空间。L社区通过建设“开心农场”和认领“责任绿化带”的“疏堵結合”方式满足了社区居民情感诉求,并充分发挥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走出了治理“毁绿种菜”现象的“第三条道路”。笔者将该种治理方式称之为“复合共治”。所谓“复合共治”是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采取“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更加注重于社区多元主体特别是治理客体的积极参与,强调社区公共责任与居民公共责任的融合共担,是以实现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治理方式。“复合共治”是以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将不同的治理方式互相合作、互为补充,以达到共同治理社区的一种治理方式。“复合共治”实现了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即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有机融合于一体,实现了“问需于民”的治理转向,属于“有自治有共治”的基层治理类型。[11]“复合共治”是社区治理的一种新趋势,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呈现出治理体制复合化特征。[12]“复合共治”充分发挥了“硬治理”和“软治理”的各自优势,使社区治理实现了情感与空间的有机结合,有效遏制了“毁绿种菜”现象。
三、土地情感与空间再造:“毁绿种菜”治理的内在机制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13]6-7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根基,是农民所有憧憬的归宿,也是农民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生存的精神支柱。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农民获得社会生活安全感的主要方式。正如费孝通调查江村时,村民所言:“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14]129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使得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发生变迁,[15]但是土地情结的传统色彩依然浓厚,[16]农民对于土地仍然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土地情感源于几千年来农业生产及乡村生活的实践,是一种从未间断过的感情,它深刻烙印于国人的社会记忆深处,像基因一样根深蒂固在国人心中,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并不会轻易消失。[17]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原有的吉登斯意义上的“本体安全性”(ontological security)因生产生活空间的急剧变迁而被破坏,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18]115-118而土地是他们在急剧社会变迁中情感寄托的物质纽带,是他们能够与过往村落生活情境建立联系的现实建构。社区居民在生活上并不依赖于土地,但是在情感上仍然对土地有着依赖之情。种菜作为土地情感的“惯习”是很难消除的。“开心农场”则凝聚了情感要素,兼具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种功能,增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确定性”。在社区居民看来,土地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于生存的生产资料,更是自己灵魂深处的慰藉,是他们在现实中找寻田园生活的联结。每个个体居民“毁绿种菜”的面积有限,种菜产出较少,根本无法解决生计问题。因之,经济因素并非是社区居民“毁绿种菜”的主要因素,而根本性因素是居民潜意识中的土地情感以及延展而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等体验性感觉。一言以蔽之,社区居民的种菜需求主要来源于土地情感。土地情感是驱使社区居民反复“毁绿种菜”的深层次原因。
土地情感是一种无形的主观意识,需要借助于客观实在的物质载体表达,即依托于土地。然而,由于土地流转及家庭院落的消失等诸多因素使得社区居民很难找到可供耕作的土地,而绿化带、空荒地等社区公共用地则为其种菜行为提供了实践空间,成为土地情感实践的物质载体。因之,“毁绿种菜”现象可视为土地情感在社区空间中的表达和显现。由此来看,社区居民种菜需求与社区无地之间的矛盾是“毁绿种菜”发生的外在形式,而土地情感与空间再造之间的矛盾则是其内在机理。这也是社区治理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正是由于社区空间再造时未能考虑到居民的情感诉求,既有的居住空间结构不能让居民土地情感得到合理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毁绿种菜”现象的发生。社区空间建设标准化和通用性,其在规训和引导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但社区居民会自下而上的解读并再改变空间的用途。[19]“毁绿种菜”现象是社区居民的土地情感在现实的空间结构中找不到合法性实践空间的一种被动式越轨行为,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空间使用方式的再诠释,体现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可以视为一种“空间抗争”。抗争与空间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抗争是直接面对由威权和强者所掌控的空间,并试图通过占领、利用和改造它,从而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差异性空间”。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空间的认同政治的建构过程。[20]“开心农场”的建立实现了社区空间再生产,将种菜行为变得合乎于“法理情”,让社区居民有了释放土地情感的合法性空间。当情感有了实践的空间,便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時,社区通过要求种菜者协会会员认领“责任绿化带”的方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体性,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到“毁绿种菜”的社区治理中,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式治理。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是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农民心中的情感寄托。土地情感是在长时期人地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性的感情,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能够与过去取得现实联系的微妙情感体验。从土地情感的视角来看,社区居民的“毁绿种菜”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情感抗争”,是土地情感在社区空间中的“社会性表达”。“情感抗争”是“空间抗争”的内在机制,“空间抗争”是“情感抗争”的外在表征,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进言之,“情感抗争”是社区居民表达土地情感和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方式,是其本体安全性的自我修复。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社区对于“毁绿种菜”现象的治理可视为对土地情感的治理。“情感治理”是“毁绿种菜”社区治理实践逻辑的隐藏脉络。首先,“硬治理”策略是对土地情感的压制,即通过强制性铲除菜地的方式消灭土地情感的实践空间;其次,“软治理”策略是对土地情感的疏导,即通过上门走访的方式淡化种菜居民的土地情感;最后,“复合共治”的策略是在“经营”土地感情,即通过开辟“开心农场”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找到土地情感的实践空间,同时以通过认领“责任绿化带”的方式赋予情感以责任,而非任由情感裹挟。“毁绿种菜”社区治理的情感脉络可为“情感治理”理论作出边际贡献。作为学界新兴的治理议题,“情感治理”是指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21]在社会层面情感治理关注于社会层面的情绪和情感的引导,[22]在社区层面表现为通过干预社区情感的再生产而协调各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23]显然,当前学者们对于情感治理的研究多倾向关注于社会情绪引导和社会关系重建等“虚体情感”,对于需要依托于实物而存在的“实物情感”治理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笔者通对“毁绿种菜”社区治理的分析,认为对于土地情感等“实物情感”的治理方式既不是压制或消灭情感,亦不是疏导或淡化情感,而是通过“经营情感”的方式,为情感提供实践空间,并赋予治理客体“情感责任”的方式实现社区良性治理。
四、结论与启示: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
“毁绿种菜”虽然是件小事,却是社区经久难治的顽疾,应当引起特别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正如费孝通看到电视机下乡时所言:“这些看来都是小事情,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问题,需要我们严肃地进行科学的研究。”[24]207本文以J省N市L社区为研究个案,发现“毁绿种菜”社区治理实践过程可分为“堵”“疏”及“疏堵结合”三个阶段,并呈现出由“硬治理”到“软治理”再至“复合共治”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从土地情感和空间再造等两个层面阐释“毁绿种菜”治理的内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讨论社区是否应该支持“毁绿种菜”,而是通过对一个社区“毁绿种菜”治理的个案“深描”,提供一种可能的社区治理方式,即呈现社区治理的实然状态。对于“毁绿种菜”现象的治理,不应是通过各种方式压制抑或疏导土地情感,而是要“经营”土地情感,即为土地情感提供实践空间,并赋予土地情感以责任。换言之,对于“毁绿种菜”的治理应告别“运动式治理”的方式,通过社区空间再造的方式实现土地情感的再生产。
通过对“毁绿种菜”治理实践过程、实践逻辑及内在机制的系统性考察,笔者认为如何处理好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三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为本”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明确指出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方向。社区治理是基层的社会治理,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会遇到诸多复杂的、非传统性的问题,这促使社区治理进行着复合转向,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模式,最终目的是实现政府、社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在社区治理复合化过程中,情感和空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均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情感、空间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有助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首先,社区治理应当纳入情感和空间两个维度。长期以来,社区治理主要关注于制度和技术维度,忽略了情感和空间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治理实践及研究中情感和空间的“缺席”。伴随着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人们逐渐意识到情感和空间对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而社区治理的实践也开始了情感转向与空间转向。一方面,社区治理需要考虑社区居民情感的表达与参与。费孝通在思考其一生学术历程时写道:“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知,这种认识是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25]情感是社区心态的核心要素,构成了社区心态的动力机制以及社区运行的调控和凝聚机制,是社区秩序形成的重要保障。在社区中,情感要素无处不在,构成社区运行的基础,具有调节社会行为和稳定社区秩序等功能。因此,要注重将社区层面的情感的引导纳入到社区治理中。社区治理重在以人为本,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于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对于情感有着近乎天然的需求。情感需求是指“人们对某相应特定情感的缺乏、等待、期盼状态和获取该特定情感的对象物以实现情感满足的强烈愿望”[26],是人性的本真状态和表现。只有当人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时,情感能量才得以释放,才能形成良好的社区秩序。而当人们的情感需求被压抑,长时间得到不到满足时,情感则会驱使人们寻找释放的突破口,带来诸多社区治理难题。因此,社区治理应着眼于基层情感治理,用“情感”搭建起一座“治理之桥”,巧妙利用情感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结,让社区居民的情感需求得以满足,情感能量得以释放,实现以社区情感为基础的社区凝聚。[27]
另一方面,社区治理需要充分发挥空间的功能与作用。空间镌刻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向作用、多重关系、多种品格,映照了人生活的全部。[28]社区空间为社区居民展开社会交往以及进行社会活动提供了场所,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样地,社区治理也开展于社区空间之中,而诸如位置、地域、立场等各种空间隐喻,无不透漏着社会界线与抗衡的边界。[29]福柯认为空间是规训的机制,因为空间分割并驯顺了个人的肉体,并凸显出复杂事物的“秩序”问题,是权力的再生产。[30]168而社区空间生产也正是空间规划与社区居民能动性之间交织的一个过程,其是一个“上下分合”的过程,[31]并伴生着由于社会结构张力所带来的空间冲突与空间风险。[32]生活于社区之中的居民,他们会根据社区空间的结构和功能而“适应性”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更好地在社区空间中生活,而这个“适应性”的过程则是多方权力博弈的过程,也是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因之,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而互相关联及形塑。[33]
其次,空间是情感表达的介质,情感的表达需要通过空间来实現,空间也会影响情感的体验。空间是人们情感的聚集、施加影响的对象,也是引起人们情感的因素。人生活于空间之中,良好的社区居住环境应当是由情感空间构成的。社区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应当是社区居民的生活写照,是情感符号的再现。正如凯文·林奇所言:“人类是最有领域感的动物,既善于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从空间的控制产生心理结果,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屈从感。”[34]145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情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空间营造能够影响人们的情感表达与转换。不同类型的空间带有不同性质的情感,无论是有形的物理空间还是无形的精神空间,均是情感的表达和交流的场所。良好的空间可以促进情感表达,释放情感能量,实现情感的再生产。反之,情感一旦没有或失去了表达的空间,将会不断积聚情感能量形成情感势能,寻找甚至创造出新的表达空间,而在这过程中极易产生居民的社区失范行为,成为社区治理的难题。换言之,当人的情感得不到关注且无法抒发时,人们会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改造空间以重新获得情感的空间体验,往往会引发集体性事件,并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社区治理问题。
因此,作为人们认知和感知环境及情感表达的重要介质,空间的情感化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情感化的空间能够引导人们在相应的位置表达相应的情感,满足社区居民的情感需求,并做出相应的社会行动,形成稳定的社区秩序,从而能更好地实现社区的良性治理。换言之,基于情感需求的空间生产能够给予人们明确的提示和线索,使人们能够明白和接受空间的情感脉络和性质特征,从而引导人们相应行事。可以说,空间的情感化可以提高空间使用率,增进社区居民间的情感交流,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社区空间,对于创造社区的和谐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社区生命力的源泉。当然,情感化的空间设计并非仅是为了情感表达和表现空间,更是为了创造空间的结构关系,唤起人们切身体验和参与,去领会空间的意义,使得各行动主体在空间中实现社会行动的最佳耦合。因之,社区的融合与发展,需要依靠凝结情感的空间形态来传承,社区空间的结构和样态承载着居民情感表达的重任。这就要求社区空间营造应当关注居民的情感需求,充分考虑到空间所要容纳的情感要素。
最后,社区治理应当以情感治理为纽带,空间治理为手段,通过社区空间营造实现情感的再生产,最终实现社区的善治。社区对于居民有着情感性和易接近性的功能和意义。[35]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来看,共同体的实质是共同的情感,建设社会生活共同体则应当着重于培育共同的情感。[36]而通过社区空间营造实现社区居民情感的再生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目前,社区空间普遍缺乏社会和文化意义,忽视了原有的环境要素、历史记忆和成长机制,并且被塑造成为一个服从功利主义计算和合理化的商品,[37]不能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在社区空间建构过程中,当情感“遭遇”市场化时,受到排斥的往往是情感,空间成为无情感之物,缺乏必要的情感基调,出现了人与空间之间的情感割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情感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具有核心地位的元素,“情感治理”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治理之中的。[38]因此,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必须关注人们的情感关切和价值取向,在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加入与社区居民的情感联结机制,了解社区的情感结构和心态,建设社区的“情感机制”。[39]社区空间设计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情感。空间因为有了情感的表达才会富有生机与活力,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体验,实现社区整合,而这也是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正如威廉·H怀特(William HWhyte)在《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空间,而不是建设一个非人性化的空间,其实并不难,人性化的空间可以让城市生活大不一样”[40]10。
当然,强调情感治理并不是忽略正式制度的理性治理,而是一种补充,相辅相成。解决情感的需求和理性控制之间的矛盾是文明进程的中心问题。[41]情感之于理性,并非是其附庸。两者之间是互相映射的关系。社区要回应居民的情感诉求,但又绝不能完全被民粹情绪所裹挟,而是要有选择性地满足。在社区治理中自觉增加“情感治理”原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实现社区治理精细化。社区治理要重视有温度的情感尺度,强调文化的植根性,而非鸟瞰式的强制性权力表达。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因不同年龄层次、性别结构的人口有着不同的需求,应当在考虑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对社区空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满足不同社区群体差异化的情感需求。当然,情感与空间仅是社区治理的两个面相,应将之纳入整体性社区治理视阈,使情感、空间在“法理情”的范围内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实现社区治理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卢义桦, 陈绍军.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占地种菜”现象的社会学思考——基于河南省新乡市P社区个案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 2017(1):134-140.
[2]朱金, 潘嘉虹, 赵文忠,等.城市住区中的“菜园”现象、邻里矛盾及对策探讨——基于对杭州市古荡街道的调查[J].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2):90-97.
[3]许悦,丁山.城市菜地与社区建设——英国份地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园林,2017,33(2):82-87.
[4]朱金,潘嘉虹.城市中的“菜地”——英国“配额地”制度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 2014(3):62-69.
[5]覃文勇.居住区毁绿种菜的原因及处理对策[J].现代园艺,2017(19):165-167.
[6]吴晓林.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代理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J]. 公共管理学报,2015(1):46-57.
[7]孔德斌.农村社区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4.
[8]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13-21.
[9]刘祖云,孔德斌.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9-18.
[10]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1]易臻真,文军.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的类型化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6):741-749.
[12]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 2012(6):55-55.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5]米华.中国共产党与当代农民土地情感迁变——以湖南省溆浦县桐木坨村农民为例[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7(2):16-20.
[16]陳胜祥.分化视角下转型期农民土地情结变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2013(6):35-41.
[17]张丛军.新农耕文化浅议[J].山东社会科学, 2011(3):54-57.
[1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19]吴莹.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7(6):94-116.
[20]李志明,段进.空间抗争视角下小产权房的形成机制研究[J]. 规划师,2013,29(5):102-106.
[21]何雪松. 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 2016(11):40-42.
[22]王俊秀. 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N].北京日报,2017-3-22(15).
[23]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28-36.
[24]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5]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1(1):7-17.
[26]徐启斌, 郑爱菊, 王荣军.论人的情感需求[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8(5):6-11.
[27]杨秀菊,刘中起.生活、关系、空间: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三维逻辑——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案例研究[J].城市观察,2018(1):145-156.
[28]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 2013(1):113-131.
[29]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社会, 2008, 28(2):112-127.
[30]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1]黄晓星.“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2(1):199-220.
[32]陈进华.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43-60.
[33]张勇,何艳玲.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J].新视野,2017(4):84-91.
[34]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35]林闽钢,尹航.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7(2):91-97.
[36]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 2011(1):70-76.
[37]Fouad Makkia.Development by Dispossession: Terra Nullius and the Social-Ecology of New Enclosures in Ethiopia[J].Rural Sociology, 2014, 79 (1):79-103.
[38]何雪松.城市文脉、市场化遭遇与情感治理[J].探索与争鸣, 2017(9):36-38.
[39]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5):83-101.
[40]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M].叶齐茂,倪晓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41]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J].社会学研究, 2000(4):124-127.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