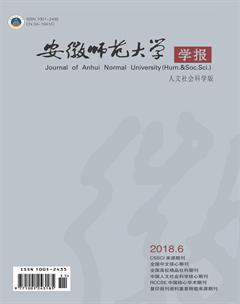抗战时期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动(1937—1941)
熊亚平 万亚萍
摘要: 1937年10月10日被日军侵占前,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及与之相关的商品流通组织等处于“自由发展”状态。日军占领后,由于铁路运输量大减,山西与河北及京津地区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及与之相关的商品流通路径、流通组织均发生变动,进入“统制”状态。由于商业在近代石家庄经济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商业发展状态的转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战争对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商业;商品流通格局;石家庄;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 K26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6011906
Abstract: Befor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the Shijiazhuang warehousing,cotton trading, cereal trading and associated commodity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s were in the state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rehousing, trading and associated commodity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 had changed into the state of "complete control" due to the great reduction of rail transport and severe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area of Shanxi, Hebei and Beijing-Tianjin. The change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situation in the wartime had showed the great impact of the war on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Shijiazhuang from one aspect.
Key words: commerce; commodity circulation situation; Shijiazhuang; Anti-Japanese War
近年来,随着华北城市史研究的深入,位于河北的石家庄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石家庄城市的早期发展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3]但关于日军占领前后石家庄商业变动及商品流通组织演变的研究尚稍嫌薄弱。鉴于此,本文利用日文调查资料,并结合其他相关中文史料,以1937-1941①年间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为例,通过对商品流通格局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揭示战争对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影响。
一、日军占领前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整体态势
本文所谓商品流通格局,是就商品流通的总体发展态势而言。其具体内容则应包括商品流通
*收稿日期: 2017-11-16;修回日期: 2017-12-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53)
作者简介: 熊亚平(1976-),男,陕西丹凤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华北区域史、乡村建设思想史;万亚萍(1986-),女,河南扶沟人,图书馆馆员。
①在1941年以后的数年中,虽然石家庄至德州铁路的建成通车和日本占领当局推行的所谓将石家庄开发成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的计划,促使石家庄的市政建设和工商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未带来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这似乎意味着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动在1941年前后已经完成。故本文将1937—1941年作为考察时段。关于1941—1945年间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记载和研究可参见张鹤魂:《石门新指南》,石门新报社1942年版;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員会:《石家庄市志》第2-3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9年版;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工商业发展的特征》,《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路径、商品流通组织在现代社会,商品流通组织的形态一般包括中介组织(信托组织、代理组织、经纪组织等)和实体组织(商人、流通企业和流通企业集团等)。对于近代华北中小城市商业而言,将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交易中的商人、货栈、粮店(行庄)、轧花房、花行、纺纱厂等视为商品流通组织,应是合乎其发展实际的。关于商品流通组织的讨论可参见[日]石原武政、加滕司著,吴小丁等译:《商品流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冯明明等编著:《商品流通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商品交易方式等方面。由于资料所限,下文将着重考察货栈业发展、棉花交易和杂粮交易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品流通路径、商品流通组织和商品交易方式的变动。
要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侵占对石家庄商业及商品流通格局变动的巨大影响,首先应明了在其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交易等在战前的整体发展态势。石家庄是随着1905年京汉铁路全线竣工和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通车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因此,依赖铁路运输生存和发展的货栈业便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行业。据调查,石家庄货栈由大车店发展而来。这种大车店多由比较富裕的农民采用合资的方式经营。参与合资经营的富裕农民一起集资购买货车,租用大院子进行营业。由于大车店与当地的杂货店、小商店关系密切,因此经常被其雇佣,从县城搬运杂货。此后,大车店不仅从事土特产、杂货的搬运,而且还在租用的院子里专门开辟一个角落,提供给从外地或附近农村运送货物来此的货车车主使用,并向其收取餐饮费、住宿费和停车费。由此,大车店便开始由专门经营运输业,向集运输业、旅店业和仓库业于一身转变。
铁路的开通成为大车店向货栈转变的重要契机。[4]1-2京汉、正太两路建成通车后,每年有来自河北及山西的大量煤炭、棉花、粮食等货物经正太路运至石家庄,再转京汉路运至保定、天津等地。其中,1916-1937年前,每年经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煤炭由30万吨增至200万吨左右。[2]运至石家庄的棉花可分为山西棉和直隶棉(河北棉)两种。山西棉产于曲沃、洪洞、翼城、霍州、赵城一带,“平时由南方产地用马车运至正太路之榆次站,由此运至石家庄,再由平汉、北宁两路以运至天津。”[5]直隶棉(河北棉)大部为中国棉种,产于正定、获鹿、栾城、元氏、藁城、赵州、宁晋、柏乡、隆平、巨鹿等县。1934年前,石家庄附近各县产棉每年约60—70万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经石家庄运至天津。[6]由山西各县运至石家庄的粮食等农产品有小米、高粱、黑豆、小麦、黄豆、绿豆等。1924年由铁路运出约2万吨,1925年运出约3800吨。[7]1937年10月以前,每年由山西运来约8万吨,石家庄本地消费约4万吨,转运他处约4万吨。[8]53
随着煤炭、棉花、粮食等大宗货物的外运,石家庄的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等在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发展态势。就货栈而言,铁路开通后,大量的煤炭不能再靠大车店那样的小规模经营者,加之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日益发展,大车店逐渐转型,向近代保管业和运输业发展,并向以煤炭运输、贮藏为主的煤栈或经营杂货、杂粮的货栈转变。在此过程中,其功能亦有所变化,没有一般货栈所具有的代理买卖(中介)和信贷的功能,而以与运输息息相关的保管费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不论是卖方寻找买主,还是买卖双方的商谈,买主将货物运走,都要花费数日。货栈便得以收取存放货物的保管费……买卖双方需数日才能达成协议,两天之内完成的情况极少发生。”[4]7
由于周围各县所产棉花“以石家庄为最大集散场”,因此棉花交易在石家庄商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937年前,石家庄上市的棉花主要来自平山、新乐、藁城、宁晋、晋县、元氏、正定、无极、获鹿等县。1936年共集散约324 000担,其中约19%由花行收购,约28%由大兴纱厂收购,约53%由石家庄转运各地。1937年共集散约232 000担,其中约25%由花行收购,约27%由大兴纱厂收购,约110 000担经石家庄转运各地。其主要流通路径如表1所示。
在上述流通路径中,轧花房、花行、外来华商、货栈、杂货商、纺纱厂、销售地交易商等成为重要的商品流通组织。其中,货栈上文已述及。轧花房均在内地。花行是在石家庄的棉花交易商的统称。1926年前,石家庄有4家花行(棉花公司),[7]被日军侵占前增至10家左右。除自己收购外,花行还替外来棉花商从当地棉农或轧花房手中收购棉花,用自家店铺里的轧花机轧好,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和轧花费后出售给委托商。[8]30外来华商主要来自天津,“每年旧历八月至十二月交易最盛,天津中外棉商临时派人来买,或指定货色价格,委托各货栈代为收买”[7]。杂货商主要依靠腹地棉农或轧花房从事弹棉花生意。纱厂即大兴纱厂,创办于1922年,1937年10月前每年在石家庄收购棉花数万担。此时,石家庄向上海销售的交易商主要有大通公司、中棉公司、通成公司、永大裕等;向天津销售的交易商主要有大通公司、通成公司、同德元、同孚、永大裕等。
石家庄的腹地为产棉区,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山西及邻近各省矣”[9]。由此,杂粮贸易便成为石家庄又一类重要商业。这一时期,出入石家庄的杂粮主要经由铁路和水路运送。其中,从山西运来时一般走正太路,运往京津地区时主要利用铁路,其次也大量利用水运(通过子牙河等)。杂粮贸易中的商品流通组织主要有货栈、客商、粮店(行庄)等。货栈上文已述及,客商主要是从山西来的卖家和从京津及京汉线来的买家。其中常年来自山西的客商约有30人,来自京津及京汉沿线来者亦有20—30人。[8]60粮店(行庄)“性质亦系自卖自买,惟资本不及货栈之大”,1926年前有50余家。[7]杂粮交易一般在货栈内进行,但货栈几乎不做客商货物的代理买卖,而由客商之间,客商与行庄之间进行交易。这种交易由客商自己带着货物前来,因而是一种现货交易。交易双方在同一货栈中住宿,进行交易时可以看到实物。与别的货栈中的客商交易时则有中间商在场。[4]22-23
这一时期,由山西运至石家庄的各种杂粮中,约有50%由石家庄(含近郊农村及县城)消费,25%运销保定周边地区,25%运往北京地区,因此,石家庄货栈内的客商和行庄便与农民发生了密切联系。其与农民之间的交易又有兩种形式。一是农民直接到货栈与行庄商谈好之后进行零售,二是农民与行庄的经纪人在集市上进行交易。
在石家庄兴起为城市的过程中,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品流通路径、商品流通组织、商品交易方式等的发展态势不仅直接体现着铁路运输的巨大影响,而且表明日军占领前的石家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处于“自由发展”状态。
二、日军占领后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动
1937年10月被日军侵占后,由于铁路运输量大减,山西与河北及京津地区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等均发生明显变动。
石家庄货栈业在1937年10月10日以后,因“国际运输、棉花统制、货车不足,以及房屋被驻屯军所占、经营者逃亡”等情况的发生而大受影响。1938年前,作为棉花交易参与方的货栈仅剩12家。“委托商及委托货物量显著减少,几乎陷入停业状态”。1943年前,参与杂粮贸易的货栈主要有11家。尽管这些数字并不十分准确,但石家庄货栈的数量在日军侵占初期大幅减少,应是不争的事实。“事变给石门市的货栈造成巨大影响,使得大部分货栈破产、关张。事变后新成立的货栈,其注册资本金竟不及十年前所成立货栈的十分之一”[4]5-6。1937年10月以后,石家庄货栈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功能也有明显变化。一方面,日本商社及诸机构的进驻和驻屯军的到来,引发了通货膨胀。货栈不得已将原来位于铁路沿线地带的极好地理位置让给日本商社及其诸机构,然后退到铁路线以外,租借当地农民的土地继续维持经营。另一方面,由于铁路运输能力的减退、山西物质统制、正太铁路轨距变动以及经济封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货栈的运输业功能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石家庄逐渐由中介市场转化为消费市场”[4]9,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货栈功能的改变,即由以运输为主,改为以仓储为主,逐渐成为日本商社的指定仓库,或在天津的日本棉商的棉花保管处,或日本商社的杂粮收购代理者。尤其是1941年“石门市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大部分货栈加入其中,接受客商委托,担任促成交易的市场交易员。当这些作为市场交易员的货栈成为市场公司的指定仓库后,其保管费及其他费用由公司统一规定,从而使货栈利益遭受一定损失。
同一时期,石家庄的棉花交易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受战乱影响,棉花无法自由流通,因此石家庄集散棉花的主要来源地由原先的平山、新乐、藁城、宁晋、晋县、元氏、正定县、无极县、获鹿县、栾城县等10县缩小到1938年时的获鹿、晋县、元氏、栾城、赵县等5县。同时,其流通路径也发生变化。1937年10月至1938年11月京汉线棉花协会成立前的流通路径如表2所示。1938年12月以后的流通路径如表3所示。
比较可知,这一时期石家庄棉花流通路径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1937年10月10日以后,石家庄大兴纱厂被日军接管,所需棉花改由日本商人收购;二是京汉线棉花协会在1938年12月以后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流通路径的改变,石家庄棉花交易中的商品流通组织也发生变化:随着日本商人的进入和一些华商经营花行,石家庄的花行增至51家;与棉花交易关系密切的货栈几乎陷于停业状态;外来华商先是只进行春季交易,进而完全停止交易,退出石家庄市场;向上海销售的交易商停止活动,向天津销售的交易商除前述华商外,还有日本商人参与其中;随着日本商人势力的壮大,京汉线棉花协会于1938年11月宣告成立并成为棉花交易中的重要商品流通组织。
同一时期,石家庄杂粮贸易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杂粮供给地、贸易方和货栈、行庄、集市、农民关系等方面。由于山西杂粮供给受阻,北京、天津、芦台、唐山、开封、新乡、安阳、邯郸、衡水等地开始向石家庄供给杂粮。商品流通组织的主要变化有三:一是货栈不仅是交易的中介,而且成为市场公司的交易员和重要的交易方,“货栈自己购买或贩卖行为,在事变后逐渐成为常态,但货栈表面还是以运输、保管业务为主。自己买卖的情况不公开”[4]27。二是战时粮食不能外运,外来粮商基本绝迹。三是日本商人成为重要的贸易方。[4]28-29在贩卖粮食的过程中,货栈不仅将粮食卖给烧锅店、行庄和日本商社的委托收购人,而且还出售给附近的农民,“有的通过粮庄,也有的直接卖给农民,粮庄有时再直接卖给农民,或通過小贩在集市上卖,以大豆、黑豆为主,货栈与粮庄间必定存在经纪人。”[4]29于是,货栈、行庄、集市、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
总之,1937年10月至1941年间,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杂粮贸易中所体现出来的商品流通格局变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由于货栈在石家庄商业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随着自身参与交易,货栈与棉花公司、杂粮行庄、集市、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于外来华商日渐减少,日本商人不断增多,石家庄棉花、粮食市场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商人建立的市场公司、京汉线棉花协会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货栈、棉花交易、杂粮贸易等开始由“自由发展”状态向“统制”状态转变。这些变化,成为石家庄商业发生整体性变动的重要体现。
三、日军占领对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变动的影响
在1937年10月被日军侵占以后的短短数年中,石家庄商业发展状态由“自由发展”转变为“统制”状态。这一转变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及占领石家庄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密切相关。
其一,日军侵占石家庄及随之而来的山西与河北间的交通中断和经济交流受阻等,对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状态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日军侵占前,石家庄货栈业的兴起和发展依赖于山西与河北,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煤炭、棉花和杂粮运输。日军占领初期,山西煤炭、棉花和杂粮输出严重受阻,石家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交易等商业大受影响。就货栈业而言,由于煤炭、棉花、杂粮来源减少,铁路运量降低,货栈业受到巨大冲击。“事变给石门市的货栈造成巨大影响,为此大部分货栈破产、关张”[4]5。“事变前当地货栈有30家左右。事变后减少了一半,原因是:①日军强占房屋;②运输禁止,营业衰退……④经营者逃亡等情况”[4]58。“事变后,由于国际运输,棉花统制,货车不足,以及房屋被驻屯军所占等因素”,货栈的委托商及委托货物量“显著减少,几乎陷入停业状态”[4]36。“石门市一直承担山西与河北间物质交流枢纽的作用,而货栈是主要承担者。铁路运输能力的减退给货栈的经营造成很大打击,而山西物质封锁则是致命的伤害,直接导致货栈运输业困难”[4]9。此时的货栈“运输业机能停止,栈内客商贸易困难,如今,货栈大多靠附近农村维持”[4]9。就棉花交易而言,由于石家庄刚被占领时很多地方不能自由运输,导致棉花来源地迅速缩小;同时,石家庄被占领前后,棉花市场行情和运费有所不同。被占领前,石家庄市场的棉花价格大都根据天津行情,由从业者共同商定后进行收购。石家庄被占领后,由于日商的进入,行情发生了一定变化。到京汉棉协成立后,棉花价格就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所控制。此外,运费也有所提高,“事变前棉花的运输都采用无盖货车,承重30吨的车能装150-170包,而事变后由于采用有盖火车,同样是承重30吨的货车却只能装100包左右。这实际上提升了每吨的运费”[4]49-50。就杂粮贸易而言,一方面,杂粮的来源地发生较大变化。1937年10月以前,石家庄集散的粮食以山西为重要来源地,以京津地区为主要销售地。而不从京津地区输入粮食。“事变前,运来石门市的杂粮中,70%来自山西,30%来自河南”[4]9。石家庄被侵占后,山西商人的输出统制以及战火导致正太铁路运输不畅,致使山西省的粮谷供给受阻,因此不得不依赖北京、天津、芦台、唐山等地供给。另一方面,杂粮的运输路径和上市路径也有变化。在运输路径上,由于“水运运费比铁路要便宜一半,故事变前大量利用。事变后由于治安恶化,几乎不用了”。[8]56-57在上市路径上,市场公司的成立、经济封锁、配给与收购机构的整顿以及随之而来的货栈自身的变化等,促使杂粮及小麦的上市路径发生改变。
其二,日军侵占石家庄后,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中的华商迅速减少,日本商人和商社迅速增加,势力日益壮大,促使石家庄市场结构发生改变。就货栈业而言,不仅华商所经营货栈数量有所减少,而且在功能上逐渐沦为日本商社的指定仓库、天津的日本棉商的棉花保管处,或日本商社的杂粮收购代理者。就棉花交易而言,加入花行同业公会的商号大多数为日本商店提供代理。从事棉花交易的日本洋行多达20家。[8]31-35就杂粮贸易而言,1937年10月以后,“山西的粮谷已运不出来了,所以外客也基本没有了”[8]60。一些为杂粮贸易服务的货栈同样沦为日本商社的仓库。“在石门,受日本商社委托,收购小麦、杂粮的货栈有两家。其中一家,近来废掉了主业,成为日本商社的仓库,提供其仓库及大院子,同时也作为日本商社的一份子参与杂粮的收购”[4]30。
其三,随着势力日益壮大,日商先后成立了京汉线棉花协会和市场公司,进一步控制了石家庄的货栈业、棉花交易和杂粮贸易,加速其由“自由发展”转向“统制”状态。京汉线棉花协会以“京汉线棉花的收购及配给,确保对日棉花输出及华北棉花改良”[8]39为目标。在该协会成立之前,不断壮大的日商于1938年4月17日成立了石家庄日本人棉花同业组合,“指使前述的花行进行石家庄及京汉沿线的棉花收购。至12月中旬,日益形成收购垄断的局面,遂组建了京汉线棉花协会”。协会成立时有资本1600万元,设本部于石家庄,在保定、彰德(安阳)设立分支机构,在京汉沿线必要地点设收购点,对京汉线棉花进行收购垄断。1939年前,加入京汉线棉花协会的洋行多达18家,其辖区涵盖京汉线北起南苑,南至新乡的20个车站,每年集散棉花达到154万担。[8]39-42其对京汉沿线棉花集散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市场公司即石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1年,共有资本50万元(一股50元,共1万股),其中5000股归华北市场助成股份有限公司,余下5000股为石家庄货栈东家们所有。市场公司以“促进杂粮上市”为主要目标。《石门市场株式会社业务规程》中规定,日本占領当局允许交易的商品主要有三类,即米、粟、高粱、玉蜀黍、绿豆、大豆、黑豆、小麦、小麦粉、花生、棉籽等;花生油、胡麻油;棉花、棉丝、棉布、麻袋等。而实际交易的杂粮主要是高粱、黑豆,其他的已不交易。由于高粱和黑豆的交易与货栈关系密切,因此石家庄货栈均作为市场交易员加入市场公司。同时,货栈也是市场公司的股东,维持公司的运营。“比如,股东刘某是市场公司的理事长,同时他是货栈的东家和市商会的会长。”[4]10-11由此可以看出,货栈的主要功能、保管费及其他费用的收取等,已处于市场公司的影响之下。故而,市场公司便成为加速货栈业由“自由发展”转向“统制”状态的一个重要促因。
其四,日军接收大兴纱厂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了石家庄商业的“统制”状态。被日军接收前,大兴纱厂是石家庄棉花交易市场上的重要买方之一。日军侵占石家庄后,大兴纱厂于1937年12月15日被日军接收,1938年1月1日开始在日军管理之下运转,原料采购工作被日商操控。
综上所述,在日本占领石家庄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下,石家庄货栈业及棉花交易、杂粮交易中的商品流通路径、商品流通组织、商品交易方式等,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动。这些变动不仅集中反映了石家庄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动,而且体现出石家庄商业由“自由发展”向“统制”状态的转变。商业发展状态的转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战争对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田伯伏.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兴起[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91-96.
[2]江沛,熊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J].近代史研究,2005(3):170-197.
[3]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北支经济调查所.石门市内货栈业调查报告——主として企业组织に就いて[M].大连: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昭和十八年(1943).
[5]大岛让次.天津棉花[J].王振勋,译.天津棉鉴,1930(4):1-18.
[6]叶元鼎,马广文.吾国重要棉市调查记[J].国际贸易导报,1934(9):33-40.
[7]石家庄之经济状况[J].中外经济周刊,1926(181):18-31.
[8]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北支主要都市ニ于ケル商品流通事情·第二编·石家庄[M].昭和十四年(1939).
[9]督辉.中国棉业概况[J].钱业月报,1923(9):14-26.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