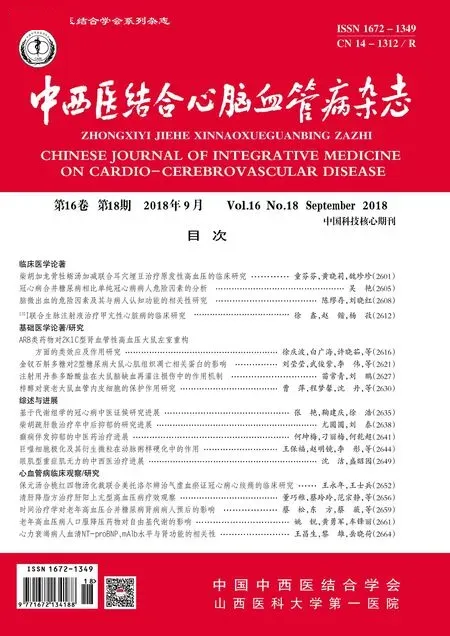巨噬细胞极化及其衍生微粒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 ,,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由内皮功能障碍、脂质代谢紊乱、炎症细胞浸润等因素相互作用所致的以粥样斑块和纤维斑块为特征的血管系统慢性炎症[1]。巨噬细胞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主要细胞组分,其亚型的极化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并影响斑块稳定和动脉粥样硬化结局[2-4]。微粒(microparticles, MPs)是在细胞活化或凋亡时脱落的微小囊泡。微粒过去被视为“细胞垃圾”而被忽视,近几年发现微粒作为生物信息载体,不仅在动脉粥样硬化中发挥促炎、促凝、促内皮功能障碍及平滑肌细胞迁移等重要作用[5-6],还会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和功能,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
1 巨噬细胞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1.1 巨噬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及发展中的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是以炎症细胞在血管内膜下的聚集为首要表现的慢性炎症性疾病[7-8]。由于血管壁长期受到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等各种危险因素的反复作用,导致血管内皮受损,低密度脂蛋白浸润,进而促使黏附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招募单核细胞等炎性细胞,启动炎症反应。招募的单核细胞游出血管壁进入组织成为巨噬细胞,巨噬细胞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最主要的炎性细胞,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各个病理环节,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结局[2]。首先,巨噬细胞通过表达E-选择素、P-选择素等黏附因子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等趋化因子,趋化单核-巨噬细胞黏附浸润和平滑肌细胞迁移增殖,促进内膜下脂质吞噬和泡沫细胞的形成,进一步形成脂质核心。其次,巨噬细胞是斑块中炎症相关细胞因子的主要来源,可产生致炎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2(IL-12)等及抗炎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7,9]。这些促炎因子通过增加内皮的通透性、升高黏附因子和趋化因子表达、影响脂代谢、促进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和增殖、调节细胞外基质重塑等多个环节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7,9]。同时,巨噬细胞和泡沫细胞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参与纤维帽金属胶原纤维的降解,加剧了斑块的不稳定性[7,10]。据报道,从不稳定型心绞痛病人的冠状动脉旋切下的病灶中发现,巨噬细胞约占14%,并围绕脂质斑块,集中于纤维帽;在冠状动脉破裂的纤维帽中,巨噬细胞约占26%[7]。有研究认为巨噬细胞还可以促进斑块内血管新生[7,11-12]。由此可见,巨噬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发展,甚至破裂的过程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
1.2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巨噬细胞的来源 传统观点认为,骨髓产生并释放入血的单核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巨噬细胞的主要来源。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在病变区趋化因子和黏附因子的作用下浸润至内膜下,分化为巨噬细胞[13-14]。新的观点表明,单核细胞分为炎症型(Gr1+/Ly6Chigh)和静息型(Gr1-/Ly6Clow),在正常小鼠体内,炎症型单核细胞表达量约为50%,高脂血症时大量增加,其可迁移至病变血管并分化为巨噬细胞,参与炎症反应。炎症型单核细胞与人体内CD14+CD16-单核细胞具有一定相关性,被认为是M1型巨噬细胞的主要来源[15-17]。而静息型单核细胞与人体内CD14+CD16+单核细胞相关,被认为是M2型巨噬细胞的前体细胞,具有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血管稳态,抑制炎症发生的作用[15-17]。而高胆固醇血症能否诱导Ly6Clow向Ly6Chigh转化,从而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的比例,仍有待探究。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巨噬细胞主要来源于病变局部巨噬细胞的增殖,并非来源于从血液中招募而来的单核细胞[18]。“招募而来的单核细胞很快凋亡,能促进邻近巨噬细胞的增殖”这一假说仍需进一步验证。
1.3 巨噬细胞的极化
1.3.1 巨噬细胞的亚型和功能 巨噬细胞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细胞成分的主要部分,其可塑性和多能性影响斑块的稳定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在斑块内微环境的作用下,巨噬细胞可活化为M1型(经典活化型)和M2型(替代活化型),分别发挥致炎和抗炎作用。M1型巨噬细胞由细胞因子IFN-γ、TNF-α和脂多糖(LPS)等诱导极化[2],高表达CD80、CD86[19],释放大量炎性因子如TNF-α、MCP-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IL-1、IL-6、IL-12等[20],具有强大的促炎、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的功能,在炎症初期发挥重要的作用。M2型巨噬细胞由IL-4、IL-13等细胞因子诱导[2],表达高水平的CD163、DC-SIGN(CD209)、甘露糖受体(CD206)[19,21],并产生大量的IL-10、TGF-β和精氨酸蛋白酶-1,具有抗炎和增加斑块稳定性的作用[22]。根据接受的刺激信号不同,M2型巨噬细胞又可进一步分为M2a、M2b、M2c和M2d[21,23]。M2a型由IL-4和IL-13诱导,高表达IL-1受体Ⅱ(IL-RⅡ)和IL-1受体拮抗剂(IL-1Ra)[21,23];M2b亚型可被免疫复合物(ICs)、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或IL-1受体配体诱导[21,23],产生促炎因子IL-6、IL-1β、TNF-α和抗炎因子IL-10等[21]。糖皮质激素和IL-10诱导M2c亚型,M2c型巨噬细胞释放大量的IL-10和TGF-β,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凋亡功能[21,24]。M2d型巨噬细胞由TLR激动剂通过腺苷受体诱导极化[23]。腺苷受体活化后,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诱导抗炎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分泌[23,25-27]。此外,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也可相互转化。尽管在斑块早期M2型巨噬细胞占主要成分,但随着斑块进展,M2型巨噬细胞会向M1型转化[28]。
1.3.2 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机制 巨噬细胞的极化不仅与STAT1和STAT3/STAT6信号通路之间的平衡密切相关,而且受到microRNA调节。M1型巨噬细胞主要由STAT1活化介导,IFN-γ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IFN-γ受体结合,激活JAK1/2-STAT1/2信号通路,诱导M1型巨噬细胞极化,产生细胞毒作用和促炎作用;此外,LPS可与巨噬细胞表面TLR4结合,经过NF-κB、AP1、IRF3诱导目标基因的表达,也可使巨噬细胞极化为M1型[22,29-30]。相反,活化STAT3/STAT6,则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产生抗炎和组织修复的作用[20]。IL-4、IL-13、IL-10通过诱导STAT6和STAT3磷酸化,形成二聚体并进入细胞核调控基因的转录,促进M2型巨噬细胞的极化[20,22,31]。STAT3信号通路产生的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蛋白1(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1,SOCS1)不仅可以抑制STAT1信号传导,阻止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而且可以抑制NF-κB,减轻炎症反应[9]。此外,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PPARγ)激动剂也被证明在体内和体外均可诱导单核细胞直接向M2型分化[32]。microRNA作为生物进程的重要调节因子,也参与调节巨噬细胞的极化。尤其是miR-155和miR-223,通过其靶基因SOCS1、C/EBP和Pknox1,参与调节巨噬细胞的极化状态[29,33]。过表达或沉默miR-155能分别促使巨噬细胞向M1型或M2型极化。有研究显示,miR-155可下调IL-12Rα1,从而抑制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34-35]。最新研究表明,表观遗传机制,包括染色质重塑、DNA甲基化(DNAm)、组蛋白修饰和调节靶标基因表达,也参与巨噬细胞对局部微环境刺激的应答,进而调节巨噬细胞极化[20,36-37]。
1.3.3 巨噬细胞的亚型与临床联系 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之间的动态平衡,不仅决定了炎症的最终转归,而且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临床研究发现,M1型巨噬细胞在不稳定斑块和出现临床症状的病人的斑块中含量丰富,而M2型巨噬细胞在稳定斑块和亚临床症状病人的粥样斑块中数量较多[28,38]。且冠心病病人的严重程度与M1型/M2型巨噬细胞的比例呈正相关[39]。在斑块发展的不同阶段,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数量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也在小鼠模型中得到证实[15]。此外,循环中相关炎性因子的变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巨噬细胞亚型对心血管事件产生的可能影响[40]。研究显示,冠心病病人循环中IL-6、TNF-α水平升高,则增加病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发生或冠心病病人的死亡风险[41-42];而IL-10水平的降低,则会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43]。IL-6、TNF-α和IL-10分别作为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佐证了巨噬细胞亚型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可见巨噬细胞M1型/M2型的比例与心血管疾病的发展和结局密切相关。
2 巨噬细胞衍生微粒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微粒又称微囊泡,是细胞在活化或凋亡时从细胞膜上脱落,携带来源于其母细胞的mRNA、microRNAs(miRNAs)、受体及特异性蛋白等,直径约为0.1 μm~1.0 μm的微小囊泡[44-46]。目前研究发现,已知的微粒可来源于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肿瘤细胞等,并释放到血浆、尿液、汗液、唾液、泪液等不同体液和体外培养细胞的培养基中[44-45]。微粒作为生物信息的载体,通过膜融合、内吞、与受体结合等方式将其携带的特异性蛋白或遗传物质传递给靶细胞,影响靶细胞的功能。研究表明,微粒具有支持细胞修复、凝血以防止出血等维持体内稳态[47-48];而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其促炎、促凝、促内皮功能障碍、促血管生成等方面,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6]。白细胞微粒(leukocyte-derived microparticles,LMPs)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关系最为密切。LMPs通过修饰内皮功能、表达细胞间黏附因子-1(ICAM-1),促进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在血管壁的黏附与募集,促进斑块内血管新生、参与凝血等推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一步发展[4,49-50]。研究发现,在健康人的外周血中,LMPs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0%),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时,循环中CD11a+、CD45+、CD11bCD66b+与CD15+等LMPs的生物标志水平显著上升[51-54]。Leroyer等[4]通过对26例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病人血浆和内膜斑块中的微粒来源进行分析发现,斑块中的微粒来源于白细胞、红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无血小板来源的微粒,其中LMPs是斑块微粒的主要成分。也有研究表明,斑块中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约为斑块内微粒的60%[4,49]。可见,巨噬细胞微粒构成斑块微粒的主要成分,在动脉粥样硬化进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1 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作用极其广泛。首先,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通过向内皮细胞递送ICAM-1,促进单核细胞黏附和迁移;也可在CD40L配体的介导下,诱导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49]。泡沫细胞释放的微粒,可通过ERK和Akt通路促进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增殖[51]。其次,巨噬细胞来源的MPs含有P-选择素配体、组织因子和磷脂酰丝氨酸,可促进凝血,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部位血栓的形成[49,55-57]。此外,巨噬细胞来源的MPs可上调促炎介质的形成,激活巨噬细胞NF-κB通路,增强斑块中炎性环境[58-60];还可诱导细胞外基质降解,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49]。巨噬细胞微粒不仅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而且对机体代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M1型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通过活化NF-κB,降低脂肪细胞Akt磷酸化水平和葡萄糖转运体(GLUT4)易位,导致胰岛素抵抗。而M2型巨噬细胞来源的MPs则可以逆转这一过程,增加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59]。
2.2 微粒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巨噬细胞在机体局部微环境的作用下极化为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并产生细胞微粒,其来源的微粒反作用于巨噬细胞的极化,同时影响局部病变的发展。据报道,佛波酯(PMA)诱导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THP-1)、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GM-CSF)诱导单核细胞,转变为巨噬细胞,并产生巨噬细胞微粒,将二者产生的微粒分别加到THP-1细胞和单核细胞中,皆可诱导单核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并显著增加巨噬细胞标记物CD16、CD206和CCR5的表达[61]。Garzetti等[62]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分别检测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的微粒,发现M1型和M2型微粒所携带的mRNAs既具有共性如促生存基因Cox5a、Clic4等,又具有特异性如M1型细胞因子编码基因Cxcl9、Cxcl10和Ccl5;M2型细胞因子编码基因Ccl9,这些不同类型的微粒能否促使巨噬细胞向M1型或M2型不同方向极化有待探究。
除巨噬细胞来源的微粒外,机体其他细胞产生的微粒亦能诱导巨噬细胞极化。研究发现,来源于高脂诱导的肥胖小鼠脂肪组织的微粒诱导巨噬细胞向M1型分化,可能与肥胖小鼠的脂肪细胞微粒显著降低了miR-155的靶蛋白SOCS1,活化STAT1信号通路、抑制STAT6信号通路有关[63]。肺泡内皮细胞来源的微粒携带miR-221和(或)miR-320a,亦可活化巨噬细胞,参与急性肺损伤的进展[64]。此外,与微粒具有相似作用的外泌体对于巨噬细胞极化亦起到重要作用。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其内脏脂肪组织来源的外泌体和乳腺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分别诱导巨噬细胞向M1型和M2型极化,调节机体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65-66]。由此可见,微粒是巨噬细胞极化重要的调节者。
3 总结与展望
巨噬细胞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炎症病理机制的核心环节,其促炎表型M1和抗炎表型M2的失衡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及最终结局。巨噬细胞的极化除受炎症因子的影响外,还受到微粒的调节。微粒调节巨噬细胞向M1和M2亚型极化的同时,其自身通过促炎、促凝、促内皮功能障碍等作用,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然而巨噬细胞与微粒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更多的内容有待深入探讨。本研究对于阐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新机制以及寻找新的药物作用靶点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