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爪猪
王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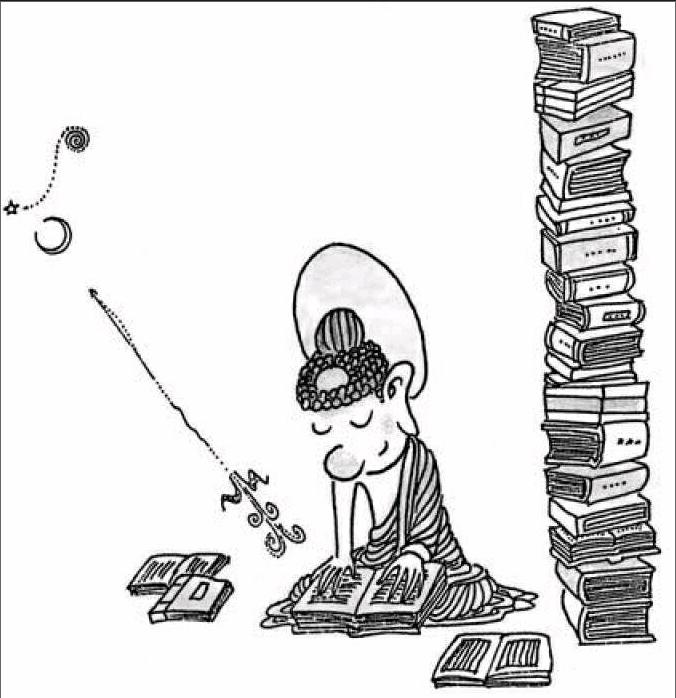
养猪不久,家中祸事便接踵而至。那头五爪猪,有人说就是祸根。吴叔却怎么也不信这个邪。
山坡地全部退耕还林以后, 粉塬村的耕地就十分有限了。今年夏末,又经受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就变得更加少之又少。没了地种,在家又实在找不到挣钱门路,年轻人就纷纷跑城里去了。吴叔年近六旬,而且没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粗加老头,外出务工鬼要!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家中。
可是,乡下大半辈子勤快惯了的人,又咋能闲得住?吴叔心里早晚憋得慌。老两口寻思了几个日夜,最后,一致的意见是:养头母猪。
好事么,养!政府不仅给每头母猪买一千块保险,还给一定的经济补贴哩。吴叔把这个想法顺便告诉村长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于是没过几天,吴叔就自己动手,在场院一角用木料夹好一米多高的围栏,在围栏里盖了方方五尺的瓦顶圈舍。乍一看,多少有点袖珍版现代休闲山庄的感觉。之后,他便从集上精挑细选逮了一头草猪,放进圈舍里。
这头母猪对主人给搭建的新家,似乎非常满意,一住进去,里里外外地嗅了嗅,就在圈舍内铺好的树叶上卧下了。狗日的,美死你!吴叔抽着旱烟,在旁边看了半天,一种新的希望悄悄在他心中燃起。
第二年春夏之交,这母猪不负吳叔所望,一窝就产下20头仔猪,且正逢俏销季节,一头就价值四百多元呢。这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无疑是一脚踩到了金窖里。吴叔老两口别提有多高兴了,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所有时间都不愿远离猪圈,生怕仔猪被母猪压着了,或者丢失上一头两头的。
在他们的精心照看下,仔猪们天天见长,胖胖乎乎、活蹦乱跳的。一天,吴叔在看仔猪抢着吃奶时,发现其中一头的两只前脚,竟都长有五个脚趾,硬是比正常的多出一个!
按照当地的说法,养这种五爪猪,或头正中有一条上下垂直白毛的“破头猪”,可是个不祥的兆头啊,迟早是要倒霉的;而杀“五爪猪”和“破头猪”的屠夫,也会碰上厄运!
一只脚长五个趾头的猪,以前也仅仅是听说过!而它,竟然是两只!吴叔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拍”地一声丢下手上的烟头,用手背擦了一下双眼,手指着那两只猪蹄子,从左到右数了一遍,再从右向左数了一遍。五个,狗日的,都还是五个!
作为一名老党员,吴叔对养这样的猪不吉利的说法,虽然并不全信。而骤然间,心里却鼓起一个不小的疙瘩,压得他气喘吁吁。晚上,他还是给老伴说了这事。
胡扯啥哩!你看清了?吴婶对吴叔的话,半信半疑。
不信你自己看去么!
吴婶一手紧抓腰间的围裙,小跑着来到猪圈旁,才想起这是晚上。她又返身回去拿出手电筒,而灯光下的猪仔们,早已跟母猪在草窝里沉睡,什么也看不见。
第二天一早趁着喂食的机会,吴婶果然看到了那两只特殊的猪脚。此刻,它就像两只随时会带来厄运的魔爪,在吴婶眼前不停地晃动!吴婶面部的表情,立刻更加阴沉起来。
猪娃儿也该出窝了。趁还没别人知道,你逮上几个,把外一个混在一起早早处理了吧……有天夜里躺在床上,吴婶对吴叔说。
屁话!还日怪哩……我看它还能成了精!就是真有那么邪,倒霉的事莫非推给别人就行,我祖宗八辈,谁害过谁?
吴婶用力蹬了老伴一脚,不再言语。
几天过去,吴叔的仔猪卖得不剩几头了,六、七千元钱一下子就装进了口袋。然而,尤其是吴婶,前一时期的那种喜悦却总是难以重新回到她的脸上,就像是久雨的天不见阳光。原因就是那头“五爪猪”还在圈舍里,不知道主人正为它犯愁,还整天前前后后四处撒欢呢。
赶集前吴叔捉仔猪时,格外健壮的它总比其它的跑得欢实,几次都侥幸逃脱了。无奈,吴叔心想跑就跑吧,不行就自己留着喂算了。
一段时间过去,吴叔家的母猪又发情了几次。这天一早,吴叔就到六、七里地的古城沟赶公猪。天气炎热,吴叔折了根细树枝握在手中,时远时近地跟在一摇三摆的公猪身后,慢慢往回赶。公猪热得张大嘴巴,直喘粗气。在经过小镇街道时,一不留神,公猪却不见了。
吴叔一阵紧张,睁大眼睛四处寻找时,正好听到有一妇人的叫骂声:谁的死猪嘛,短阳寿的,把我的罐子都挤打了!寻声望去,一位肥胖的老年妇女正伸长了脖子,从敞开的木门里向外张望和叫嚷,一副愤怒不已的样子。
我赶的,我的,崽娃子胡乱钻哩,一眼不看就不见了。吴叔的脸就像被一瓢滚水泼了,忽然一阵阵发烫,汗珠子更加狂猛地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冒。他抬起一只手袖擦了把脸,赶忙上前赔着笑脸,一边对她解释,一边拽着公猪的一双大耳朵向外拖。这老妇也顺手拿了扫把,在猪的屁股上拍打帮吴叔驱赶,好不容易才将公猪赶出屋外。
而哪料,就在他回头说话的瞬间,公猪又一头钻进了另一个闭着门的住户屋里,与刚才类似的一幕重新出现在吴叔面前。接着,又有人狠狠地叫骂——唉呀,谁要死的猪啊这?竟钻到了我床跟前,人正睡得香哩……
真的,倒霉的事这么快就跟上来了吗?吴叔一下子傻了眼,呆站在那里,双腿更加僵硬难动了。汗水,依然狂猛地从他刚剃过不久的花白头发下冒出,与脸颊上的汗水汇合而下,吴叔的衣服肩膀上全湿透了。
犯忌讳啊,猪咋能乱钻别人屋里,猪来蚀财啊……
捉住,弄死它!不能放走……
就在出来看热闹的人,也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打抱不平时,只听到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响起来。待炮声停止,烟雾散开时,只见吴叔手里正拿着大红的被面,分头搭在那两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了红,放了鞭炮,赔了那家被猪损坏的物品,又说了一大堆好话,吴叔才在镇子上找到熟人帮忙把公猪赶走,算是平息了这场祸事。
午后,才总算把公猪赶回的吴叔,比这公猪还要累。而他顾不上自己喝口水,就忙着去提水倒进猪槽,搅拌上麸皮,款待公猪。可是这畜生,既对他和出的食料毫无兴趣,也不见有与母猪交配套近乎的意思。一进圈,它就倒在那里张大嘴喘着粗气,懒得动弹,任凭吴叔软硬兼施,也总不起身。
肯定是热坏了,吴婶赶忙不停地往它身上洒水降温。天擦黑时,公猪依然躺在地上,不愿多动,对吴婶换了几次的食料,仍旧不理不睬。
不好,一定是生毛病了。在吴婶的催促下,吳叔顾不上多歇腿脚,就拿了手电消失在夜色中。深夜赶来的兽医,说是热着了,给猪打了针就走了。吴叔倚靠在猪圈的木头上,不住地抽烟,很晚才回屋去睡。
第二天麻麻亮,吴叔就去猪圈里看。公猪比昨天夜里虽说要活泛些,摸摸耳跟,却依旧烧得不轻。
完了,配上配不上,都是蛋球事,关键是这一头种公猪,要价值三千多块钱哩。万一,它要是死了,给主家咋交差呀!那事情恐怕就弄大了。吴叔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得赶紧把公猪给人家送回去才对。
事不宜迟,吴叔让吴婶做了半盆稀糊汤,晾冷后放在公猪嘴边。公猪将嘴伸进盆里,嗅了又嗅,总不肯多吃几口。若是以往,这点食它几口就会吞光的,还不满足地哼叫着再向人要。
等公猪不再动嘴时,吴叔就从圈里把它赶出来,趁着早上天凉,又从来时的路上往回赶。再次经过小镇街道时,想起赶公猪来时曾经发生的那一幕幕,吴叔就格外谨慎,紧跟在猪身后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而这畜生像是能辨出回去的路,倒不再怎么四处乱钻了。这让吴叔紧张的心,多少能宽松一些。
然而,路越走越长,天越过越热。尤其是被上年暴雨冲毁的道路,不少路段还没有完全恢复,得绕来绕去地走。接近中午,天已比早上显得热多了。到了距主家不到两里的路程,猪又不听话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或站着不动,或趴在地上。跟来时一样,吴叔还是手中扬着一根树枝,猪不听话时,就在它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抽打一下。而每打一次,总管不了几步远。
狗日的东西!又没弄上,几十块钱让我白掏了,你像是还立啥功了?吴叔在又一次停下的公猪屁股上,没敢多用力地踢了一脚。而谁料,就是这么轻易的一踢,就给吴叔带来了一场飞来横祸。——公猪猛一回头,向吴叔狠咬了一口,竟不偏不斜咬着了他的裤裆里。
哎呀,日你先人,这东西碍你啥事了,哎呀……!吴叔惨叫着,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当吴叔被路人发现时,大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时辰。他仍然昏迷不醒,脸色蜡白,下身淌着血尿。后来,终于睁开双眼神志清醒时,他已静静躺在了镇卫生院的病床上,左手臂上挂着吊瓶,一切早已处理结束。病房内没有别人,只有老伴在床前守护着自己。
犟球!……要不是短命的“五爪猪”,这回,你能吃这么大的亏不?见吴叔醒来,吴婶红着眼睛说:得花一大疙瘩钱不说,往后日子咋过啊……吴婶说着,就忍不住抱头嘤嘤嗡嗡地呜咽起来。
吴叔伸出右手摇了摇吴婶,下身猛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咬了咬呀,眼里也有一串泪水,迅速地划过他黝黑的脸颊……
被公猪咬伤以及“五爪猪”的事,吴叔尽量不想向外人声张出去,因为这无论对谁来说,毕竟都不是什么好事。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它们还是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村内外不胫而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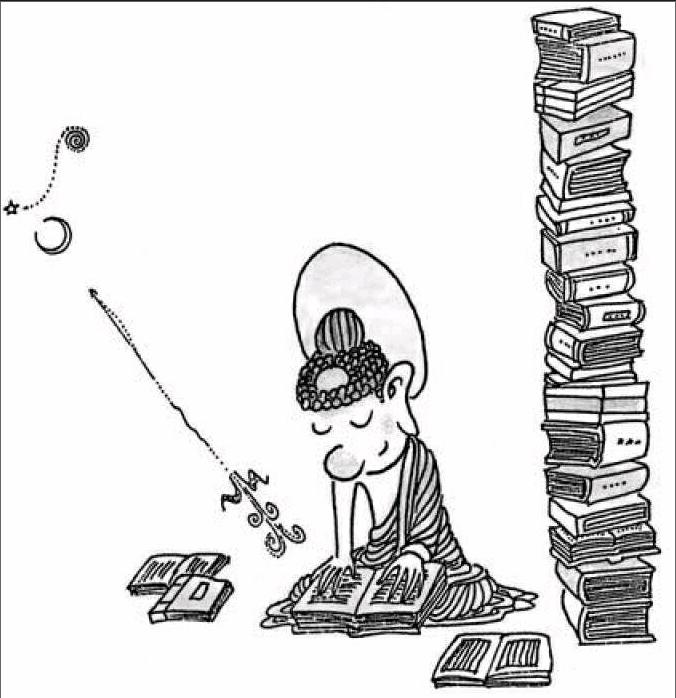
吴叔出院后没几天,家里就来了一男一女,说是某报记者,坚持要采访吴叔。虽然心里不悦,一再拒绝,而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吴叔,还是经不住两位记者的百般热情轰炸和刨根问底,最终吞吞吐吐把自己养猪的坎坎坷坷全都倒了出来。临走前,记者还用照相机对住吴叔和“五爪猪”照了一次又一次。
事后,关于吴叔养猪的长篇报道,果然就刊登在省城一家不小的报纸上,吴叔的“五爪猪”和他自己的名字,几乎被传得方圆尽人皆知。不少外乡人,也大老远赶来吴叔家看热闹。此时,在自家猪圈里活蹦乱跳的,仿佛已不是一头变异可恶的猪,而是一头可爱的小象,或者一只珍贵的大熊猫!
一天,有几个开着车、说是省城动物园的人找到吴叔家里,经过几番商议,把“五爪猪”装上车拉走了。吴叔吴婶心里那块高悬的石头,这才终于彻底落了地。
有人问吴叔,“五爪猪”究竟卖了多少钱?吴叔没有回答。只是在他的脸上,流露出一阵不易察觉而又十分惬意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