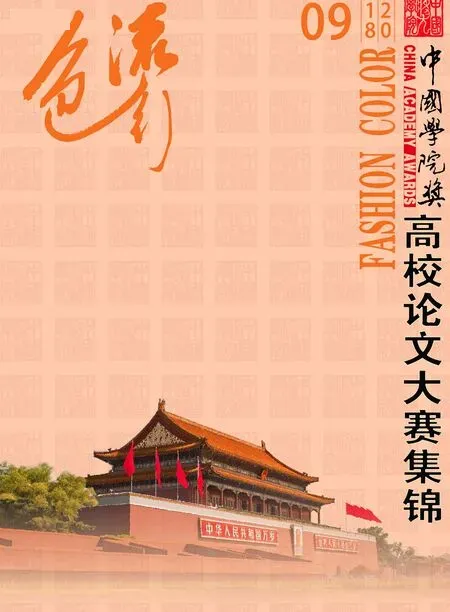虚无之境:建构影像消解空间
周夔(中国美术学院)
1 .绪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金刚经 如理实见分第五》
1972年7月15日,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布鲁特-依果住宅的爆破声震惊了建筑界,这一事件被建筑评论家查理斯·詹克斯视为“现代建筑之死”,它反映了人们对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国际式”的普遍厌倦。现代主义建筑秩序受到挑战,希望与恐惧并存。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关系被虚幻,商业影像表象被欲望引导。法国情境主义者以先锋派姿态提出建构人的具体生活情境,通过一种文化实验性运动建构情境,揭露并摧毁以影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其实早于他们二十年,萨特便提出将事件从意识中逐出,恢复意识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建筑设计发展到今天,理论和流派越来越呈现多元化,这也为建筑创作的差异性和地域性带来契机。但是另一方面,商业欲望引导的社会表象却制约着更多的建筑空间艺术实践,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太多先入为主的命题操控着设计流程和结果。
萨特在对存在的本体论探索中引出了虚无存在:对象的存在被定义为欠缺,正是欠缺指认了“非存在”的存在,也正是“非存在”的存在揭示了意识结构的超越性。“只有在虚无中,存在才能够被超越。”
情景主义者德波则深入的分析了当下资本主导社会所呈现的影像堆积现状,社会本质由消费欲望控制而展现为一种图景性,人们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在此情况下,情境主义者们以文化先锋姿态试图揭示景观的异化本质,通过建构人的具体生活情境,而恢复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自主能力。
在我国,王澍旗帜鲜明的批判幼稚功能主义,通过对阿尔多·罗西的城市类型学思考以及其背后的索绪尔语言学参考系,分析研究中国传统聚落和城市的“织体性”,这一特性毫无疑问是对罗西的城市类型学研究的回应。“虚构城市”概念的提出,试图从语言学角度解决当前城市设计所面临的问题,解决建筑语言与建筑实体的分崩离析,这为我们开启了另一种城市设计的可能性。
以否定的方式提出存在,从而引出虚无的概念。沿着萨特的路子,笔者提出虚无空间的概念:对现有空间的分解和构成,把空间设计回归空间本身叙事结构,就是空间的虚无。虚无之境并不是对空间本身的虚无,而是对空间背后指代性的虚无。它是对以往那种针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映射空间的规避,而更多地去回归对空间的体验。置身这个空间中的人们,我希望他们不意指任何环境现象,不针对任何社会热点,而只是注重自身感官的体验,体验空间的纯粹性,从而唤起人们对空间本身的兴趣。
那么,这将对现存空间设计理论带来何种思考?
1、当抛开先入为主的命题再去考虑空间设计时必然会引起对现有设计流程价值的全面重估和反思。这可能会带来空间设计理论的结构性转变,只谈论空间设计本身,而不是被过多的社会影像和命题所束缚,笔者希望以此来推动加强设计师对空间设计的话语权。
2、社会环境给了我们太多的映射与暗示,各种现象和事件充斥周遭,而观者的思绪常常会被此引导。抛开命题之后,观者于空间中将不再会被背后的指代性所引领和控制,以参与者的态度体现空间自治性。通过对空间的自主体验我们希望人们可以找回对自由的推崇,找回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找回自己对事件的敏锐判断。
3、关注空间设计语言本身,将在设计流程中加入更多城市地理学和自然生态学思考。对以往那种先入为主的命题的不思考,将推动空间设计的解放,推动空间设计向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理论先导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它往往带有先验性。建构影像消解的虚无空间,旨在通过这一理念恢复观者对空间感受的自主性,从以往的被引导转向自主选择和参与。同时,它也将为设计师提供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恢复设计师对空间设计的话语权。最终,它将带动整个社会的去“景观化”的反思,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将从日常生活开始,参与这场恢复自身存在积极性的革命。这才是“虚无之境”的价值本义。
2 .虚无空间的缘起
2.1 影像聚集
资本聚集的城市,人们所面对的社会存在展现为各种影像的堆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 5]以影像为中介,景观展现的是其背后庞杂的社会关系,这便是情境主义者德波笔下的社会“景观化”。
真实的世界幻化为影像,遮蔽着人们所见的社会真实存在。现今媒体以霸权主义的态势麻痹着普遍大众,坠入景观的迷雾中,景观成为了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只能单向度的默认,它消解了主体的抗辩能力。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每个社会行为其实早已被预设,人们的购买欲望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而是被被商家抛出的极具诱惑性的信息所引导。人们在体验空间时,每一次判断的踌躇和选择都是在既定的规则内进行。
德波认为,市场抽象空间的大规模商品积聚既粉碎了地方性和手工业生产,也剥夺了地方性自治能力,“这种匀质化的力量是击倒中国万里长城的重型大炮”[ 4]。城市化毁灭了城市,却重建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双重欠缺的“伪乡村”,这是城镇规划设计中历史缺席的后果。
当文化也成为物化的商品后,文化便走向它的解体。恢复文化的真实价值就必须通过它的内部否定来走向它的超越。
在由景观主导的空间里,人们只能被动的接受影像,设计师也对空间丧失了话语权。在景观不容争辩的展示它的强制独白时,人们在被消解了个性的同时沦为了它的奴隶。
在游走或体验空间时,导游或解说员仿佛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人们按部就班地行进,在设定好的场景中听到重复的话语。但是体验过程并不该如此,就如冯纪忠先生对访客的回答:
“客道:‘我是清楚了,但是总能经常依靠导游员解说吧?’
笔者答道:‘当然,那不可能也不必要嘛。一般,要欣赏戏,就得把戏看完;要欣赏乐曲,也得把乐曲听完,听完了也未必就懂,其实这都不用说。同样,只要有了了解建筑的意愿,那不也要花点时间和力气,进行独立体验,才能从无序发现有序,从有序领会内涵吗?’”在时间和精力的耗费的同时,冯先生指出关键的一点,唯有独立体验,才能真正理清建筑空间的思绪。体验空间,需要有独处的时间,与空间对话。在方塔园的设计中,除了景物环境之外,主体的感知体验才是其关注的重点。光影时间带来的景致不断变换,人们的感受也随之变化。
因此,在景观通过表象的垄断展现着它的绝对权威时,恢复主体的感受性就变得如此迫切。在萨特的论述中,呼唤本体的意识才能恢复主体与世界的真实关系。
2.2 唤醒意识
由于意识的存在,表象被还原为被感知物,“被感知物的存在不能还原为感知者的存在”,存在物的显现的存在引出自身揭示的现象,但是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为存在的现象。在萨特看来,这是因为存在的现象的超现象性。 这一点在刘勰对宋玉和屈原诗词的评论中也可得到印证: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在他们的诗文中,事件的描述总能在感受上得到回应,在描写“山水”、“气候”等具体事物时,循其音节查其辞藻,则能了解其所述。诗文中所记录的是表象之后的感知,但这些描述总能通过读者的感受而解读出更为直观的状貌。所以要想了解存在的现象,则需唤醒意识。唤醒意识,就需要放弃认识的第一性,“哲学的第一步应该是把事物从意识中逐出。恢复意识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这就是指,意识是对世界的位置性意识。”意识在这里作为一种实在的主观性,对象与意识的区别是由于他的不在场,由于他的虚无。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谈道:“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
若用对象与意识的观点来看,此处所提及的对象是画者在游历过程中眼见的真山真水,“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但是一旦画者将其转于纸上,便是意识之中的山水了,“取可居可游之品”。相比前者,它反应了创作者对既有素材的整理。
这段文字中还提及山水有“四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然“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这里所言及的即是山水画里身体对世界的位置性意识。行望只是第一层,身体须入画,方能居游。有了居游,才能再谈意识感受。
2.3 否定的起源
“摧毁否定的实在性,就是取消回答的实在性。”问题的存在正是应为拷问的存在,因此,存在成其所是必隐没于现在不是。由此发现了实在物的一种新成分:非存在。例:证明X是什么是通过“X不是”的命题。在宋代诗人林逋笔下的《山园小梅》中,写作手法与这一观点可谓契合: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林逋的高明之处在于咏梅却通篇不提“梅”字,开头交代位置与时间,紧接着写姿态与味道,最后通过亲近梅花的霜禽、粉蝶来衬托梅的品性。虽未有一词直接涉及梅之本体,但却又没有一句不是谈梅与自然万物之关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体现的也是这种关系。
意识对命题的否定是从某种存在着的命题那里的脱离和对某种尚未存在的目的的引入而存在。那么空间的命题或映射的影像由此开始消解,虚无不存在,它自我虚无化。虚无在存在的内部被给定,这种否定性是特殊类型的实在。只有在虚无中,存在才能够被超越。虚无空间也是建立在空间之上的虚无,如果没有空间,它将不被建构。虚无只有当它在虚无化中明确地指向这个世界以把自己确立为对这个世界的否认时,才能成为虚无。虚无把存在带到它的内心中。
2.4 时间性
只有对某一存在的过去而言,它永恒的被超越,才有它之现在。现在作为本体论的欠缺指示着将来,我是朝着欠缺而成为其存在,这便描绘出了时间性的整体结构。时间性不是存在,但是它却构成了存在的虚无化。那么在运动行进过程中,动体自身与自我的时间同一化,通过外在于自身的位置,把空间轨迹揭示出来。也就是说,空间以其趋于消失的形式延展出来。因为运动,空间在时间中产生,而观者的游览路线,是自身外在性的踪迹。这一时间延展出的空间,也能在传统国画手卷的观看方式中得到印证:
“在手卷中,很难找到一种比屏风更能创造神秘感和悬念的物象:屏风总是同时划分出两个领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因此总是同时既展示又隐藏了某些东西,总是在吸引观者去探寻那些隐秘不见的事物。”[ 13]
巫鸿在论述屏风对分隔空间场景的重要作用时,引入手卷的呈现方式,时间则更增添了画面空间对观者的吸引力。
冯纪忠先生在设计何陋轩时,进入部分用了弧墙即是想反映随着时间的变化,空间光影所随之产生的变化。在计成笔下,造园所涵盖的时间维度似乎更广阔,“两三间曲尽藏春,一二处初堪为避暑”[7 ],时景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时间变化对园林造景的影响。
2.5 超越性
因为自为在其存在中包含了它所不是的存在,任何一个否定都起源于一种特殊的超越:它被另一个存在的否定通过它的内部否定向着另一个存在的超越。譬如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了体现山高,中部用云雾隐去了后山山麓,与实体的山对比,云表现于画面中不过是留白,但正是这段留白,给了观者以猜想的余地。它既表达了后山之高,其势凌云,也将后景退去,与前山拉开了距离。
质的存在可以揭示整体,这种揭示是从存在的一个侧面完成的。因而抽象是具有超越性的,通过光泽、形状和粗糙等完成自身的虚无化。宽阔的外围台阶消解着自身庞大的建筑体量,沉重的石灰岩墙也可表明影像的苍白。
2.6 空间——作为他人对我而言的对象性
在对否定的起源和意识的实在性作完论证后,我们已经发现,人作为实在自为的存在,虚无空间也是建立在空间之上的虚无。那么,现在抛开本体论的结构,从自我反思的立场揭示为我的存在,反向论证这种“虚无之后”的空间的可能性:它的存在对于作为体验者的我有什么意义?我与虚无空间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唯有解答了这些问题,虚无空间才有立足的可能性。
萨特在为他的结构中揭示出他人的存在,它的考察起于羞耻:“羞耻是在他人面前对自我的羞耻”,在保留第一个情感动词的基础上,我们将他人替换为空间时,我们将得到这种结构:……是在空间面前对自我的……正是我体验到了空间并通过这体验揭示了对空间而言的对象-我。同时,通过空间也提示了自我的存在,这里的我作为“对我的未反思的意识而存在”。在这自我性的反思中,空间涉及并揭示了我对自我的存在,我也从我所处的空间中的我解脱出来。这便成功的消解了空间对我的映射性,也唤起了我对空间的自主性。
在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中,为了将建筑置入画中,在前端安置了一个几乎只能容下膝盖的茅草屋,在王澍看来,这表明了画家对建筑的态度,造房子造的是一个世界。它作为空间不仅揭示出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更揭示出空间中人物的存在可能性,人物与世界的位置性关系。
3 .建构策略
3.1 身体,归属中心的变革
身体的存在具有双重偶然性,我的偶然的认识自身的必然性所获得的偶然形式。对于空间来说,身体表现为我对于空间的介入的个体化。“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在谢灵运《山居赋》的开篇,因为身体的介入,空间成为居所。空间既然已被给定,它的对作为观者的我的显现是必然无疑的,但是除了空间对我的单向度的显现之外,还需要身体具备的感觉器官来建立感觉,我通过我的视觉、触摸、听觉来建立与空间之间的联系,那么我的身体便成为空间指示着的整个归属中心。
“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还江,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这是谢灵运所勾勒的理想栖居地。而元代画家王蒙画笔下的山居,虽空间密密麻麻,交叠矛盾,但居处却也能断续铺满整个画面。
作为归属中心的身体,体验空间时的感觉揭示着我的身体性。纯粹的感觉是不存在的,譬如痛苦,单纯的想体验纯粹的痛苦是不可能的,痛苦只是作为依附于世界的偶然的东西的痛苦。它是作为脱离自我并在被超越的情况下,才能非正题的存在。正是这些揭示着身体性存在的本义:“它将构成超越它自身的意识,它是偶然性本身和想逃避它的存在。”在论证了身体性之后,我们将从此出发,开始建构日常生活情境之路。
3.2 建构日常生活情境
建构情境,德波是这样定义的:“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这恰似王澍提及的城市设计概念:“一个城市设计,就是把某种生活方式的观念空间化、秩序化。”他还提到城市设计所传达的是一种心情。从空间设计入手,国画山水或古典园林无疑构造的是也一种情景。在昆曲《牡丹亭-游园》一折中,汤显祖托杜丽娘之口道出那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个小小的院子背后承载的是一段道不尽的情事。
情境主义者相信人们是有改造日常生活的能力的,每个个体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自己的乐趣。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微小变更,证明其真实性。在被景观化的日常生活中,意识的组织和创造力极端贫乏。因此,从个体出发,对意识的清晰认识便是恢复日常生活的首要步骤。
“(对)信仰(的)意识是信仰,而信仰是(对)信仰(的)意识。”意识到对信仰的意识是面对自我的在场,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只有虚无才能到达存在。人的存在使虚无存在。存在产生存在,人置身于存在之外。这种是自己独立出来的虚无的能力,被萨特称为“自由”。当人们是其所是时,便打破了存在的其他方式,唯有当人们不是其所是时,正是由于它的开放性,不同的存在方式才能涌现出来。
在被资本社会所物化的今天,社会行为普遍建立在“稳定的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之上”,领导者发布指令,执行者则需执行,这在文化层面即是理解和行动的问题。社会分工越细化,领导者也是被领导者,到执行者这里,已经丧失了他的自身理解力。
文化与艺术,作为参与这场变革的重要武器,将随着日常生活劳动分工的消失和休闲活动的持续扩张而壮大。在此情景下,艺术则作为一种更为高级的感觉直接组织而非感觉的报导,它将展现我们的事情而不是奴役我们的事情。
因此,唯有以文化先锋姿态参与日常生活批判,对重建自由作出自己的努力时,构建日常生活情境的乌托邦实践才能够实现。
3.3 漂移与异轨
在论述完个体的情境建构反思后,我们将迎来消解空间的建构的形式——漂移和异轨空间的构筑。漂移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心理地理学的感受和人们体验过程的建构行为。心理地理学被定义为“可以独自地建立对地理环境特殊影响和准确规律的研究,这一地理环境可能是有意组织的也可能不是,并研究个体对此的感情和行为的活动。”德波提出两种具体的漂移形式:直达目的地的简单游荡和和坚持对某一特定地形的直接探险。
在这种漂移中,人们将暂时放下他们的社会关系,在行进过程中发现地形和遭遇魅力,从而达到自主感受性的恢复。人们开始意识到时间流逝的过程与他们对此的抵抗。对于建筑空间设计来说,适合漂移的形式是各种趣味性的新迷宫,这种迷宫可以无终止地建构情境。
就恢复文化价值而言,德波曾指出只有文化的内部否定才能走向它的超越。异轨便是旧文化领域的一次内部否定和转向。异轨有两种主要范畴:次要异轨和欺骗性异轨。次要异轨是次要异轨元素的价值转向,它被置换到新语境中。例如一句中性短语的再运用和一份简报、一张普通照片的再拼贴。欺骗性异轨则是对于本质上有重大意义的异轨元素而言的,它从新语境中派生另一个不同的领域。如一次口号或一个著名电影情节的再演绎。
异轨用于新建筑创作领域体现为实验性的建筑联合体,它将动态环境纳入建筑空间创作思考,这将增加异轨建筑的可塑性和情感性。若是异轨被扩展至城市规划,则推动完全邻近城市的准确重建。
3.4 空间形式自治
在谈论了建筑空间创作的两种主要建构形式后,我们将谈论虚无空间的终极价值——空间形式自治。罗西以帕多瓦的拉吉翁府邸为例谈到形式的魅力, “正是形式感染了我们,它给我们以经验和享受,同时又赋予城市以结构。”当我们从功能出发主导整个设计流程时,建筑空间的形式将被功能化,失去了其自主的价值。无独有偶,王澍在谈论拉·土雷特修道院时也对建筑空间形制的价值给予了肯定,“勒·柯布西埃对使现在建筑运动陷入窘困的难题——作出有力阐述。从本质上说,修道院设计依然去确认主观形式比客观物象更为重要,秉承塞尚的构造方式,用立方体、圆锥、球、圆柱、棱锥、控制线、模度建立一个排除任何传统具象的独立结构。”
通过恢复空间形式的自主性,柯布设计的修道院“召回了形制的亡灵”。作为建构策略的最后一步,我们希望空间设计师能掌握对空间形式的话语权。唯有如此,积极性的空间营造才能得以恢复,同时观者也才能恢复积极性的空间体验。
4 .结语:虚无空间的理论复兴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正统规划理论的干预进行反思,贫民区的自我非贫民化过程像我们揭示了人们有自治空间的能力,但是随着规划预案的介入,这种能力便荡然无存了。我们也需要一种理论对现有空间设计进行反思,它将促成空间差异性和多样化的建构,让人们恢复自主建构情境的能力,参与空间治理。
本文通过引入萨特的“虚无”概念作为对空间设计命题消解的开始,并以法国情境主义者所提出的社会“景观化”,以及建构具体生活情境的努力,作为影像映射空间现状的比照和解决策略。希望以此文作为推动空间设计理论反思的肇端。文章至此虽结束,但相关具体的空间形式自治及空间感受情境的建构之路才刚刚开始,目前笔者所提也仅限于理论先导阶段,而对于具体的空间建构,还有更多的研究需要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