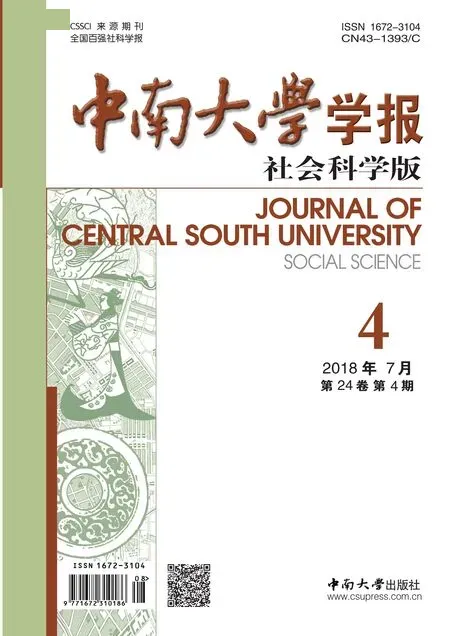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理解构与困境突围
康京涛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理解构与困境突围
康京涛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生态修复市场化在国家法律政策中予以明确,实践中呈现出“政企合作”与“企企合作”的运行模式。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政企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环境治理的单一政府管制而转变为公私合作,“企企合作”模式将污染者承担生态修复行为(行为责任)转变为向第三方修复企业支付修复费用(经济责任)。受制于当前我国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治不完善,生态修复市场化面临着生态修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督管理不畅、责任界定不清等障碍。法律作为有效且重要的社会调控机制,应从生态修复市场化的制度规范、监督体系、责任分配三个维度予以完善。
生态修复市场化;公私合作;制度规范;监督管理;责任界定
一、问题提出:法律政策推动下的生态修复市场化
伴随生态环境损害的加剧,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政策愈加明确,并在一系列的文件中明确了生态修复市场化的定位。201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出“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明确了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的第三方治理机制。之后,上海、河北、吉林、山西、安徽、陕西、黑龙江、甘肃、青海、北京、河南、四川、福建、云南、广东、内蒙古、贵州等17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2017年8月环保部也出台了《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与此同时,财政部印发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2015)把“环境治理”服务列入政府采购的指导目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及《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2016)都明确提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化机制、推动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对于责任主体明确的湿地修复,既可以自行开展,也可以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国家政策文件对生态修复的市场化定位,一方面反映出生态环境损害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表明国家推动受损生态坏境修复的决心。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生态修复市场化得到了新近地方立法和部门规章的响应。《土地复垦条例》(2011)第23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吸引社会投资对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进行复垦。《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16)第54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第三方开展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市场化机制。《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2016)第23条规定了山体损害修复治理责任人和市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实施修复治理工程。《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2012)第29条第7款规定了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单位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污染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第25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污染地块的治理与修复,但要防止治理修复中的二次污染。在没有国家法的规定下,新近地方立法和部门规章对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规定,体现了地方和部门的立法创新。
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生态修复市场化并未像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一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也较为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三种路径:一是以生态修复责任理论为核心,涉及了生态修复的市场化机制[1−4]①;二是以生态恢复性司法为核心,涉及了生态修复市场化[1,5−8]②;三是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为核心,将生态修复市场化纳入第三方治理的法治范畴[9−12]③。实际上,这三种路径对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讨论都只是映射,缺乏全面系统、独立的阐释。究其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态修复市场化属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下位概念,从属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治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不同,生态修复市场化是政府或污染企业的单纯技术治理委托,并不涉及政府的项目融资(BOT、TOT、DBFO),也不涉及污染企业的“托管运营服务”[13],其法律关系相对明确。因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理逻辑,化解其制度困境。故此,本文以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理逻辑和制度困境为核心,试图对当下日益高涨的生态修复市场化做一微观的法治观察。
二、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理解构
按照生态修复市场化合作对象的不同,生态修复市场化的实践模式可以区分为:政府和第三方企业合作的生态修复、污染企业和第三方企业合作的生态修复,即“政企合作”模式与“企企合作”模式。“政企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环境治理的单一政府管制而转变为公私合作。“企企合作”模式将污染者承担生态修复行为转变为向第三方修复企业支付修复费用,即行为责任转化为经济责任。
(一) “政企合作”模式:从单一管制转变为公私合作
“政企合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向生态修复企业购买社会服务,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政府主导实施的自然生态修复工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三河、三湖”重点水污染治理工程,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以及我国草原、森林、海洋、矿山等领域的生态修复工程。二是政府主导的历史遗留污染场地的修复。如,2010年苏州市政府与苏州同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对苏化旧厂址地块的修复;2014年1月,湖南湘潭市岳塘区政府与永清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合资组建“湘潭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司”,对工业园区污染场地进行修复。三是损害者支付生态修复费用由政府组织修复。如,在海洋生态损害中,如果经海事法院审判损害者需承担责任的,法院可以判决损害者向海事局支付生态损害赔偿款,海事局将其所得款项用于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政企合作”模式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是基于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生态修复责任主体不明或灭失的情况[14],政府委托专业生态修复企业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被称为担保国家模式下国家对公用事业的建设及公共产品提供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属于政府公私合作模式之一,亦称公私协力[15],也称之为公私合作。所谓公私合作,美国学者Stephenson认为是公、私部门之间一种动态的相互合作过程[16]。Langton认为公私合作关系意味着政府、企业、非营利团体和市民共同合作并分享资源,以满足社会需 求[17]。简而言之,“公私合作”中的“公”,是指代表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私”则与“公”相对,是指普通的自然人和法人;“合作”是指为履行公共任务公私双方的协作行动[8]。
基于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政府所要承担的生态修复义务之所以要选择政企合作模式予以完成,而不是亲力亲为,是出于生态修复效能的考虑。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专业性极强的技术工程,在现代公共治理的理念下,国家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的不足,无法亲自执行生态修复行为,为人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而让专业修复机构对受损生态环境代为修复,弥补了国家自身量能的不足。另外,伴随环境问题的加剧,国家环境管理任务日益扩张,从最初的污染防治已经转变为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面对环境问题所带来的行政公共性范围的扩大,许多行政机关的职权产生了混乱的情形,其所造成的不仅是未有法律授权而行政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行政部门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19]。通过“政企合作”实施生态修复,政府由生态修复的主导者转化为生态修复的引导者和协作者,摆脱了长期以来政府对生态修复项目全权负责的局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助于国家行政任务的完成,进而实现生态修复项目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已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新加坡实施的著名的ABC水计划示范项目——加冷河修复,就是由德国戴水道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持[20]。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污染治理体系,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环境产业的发展。截至2012年,环境产业的从业人员达到243万人,市场规模约86万亿日元,占全国所有产业规模的9.6%[21]。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政企合作”依赖于契约行政,是通过招标与第三方修复企业签订协议、购买修复服务实现的。按照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实施行政任务为目的的契约,其法律属性为行政契约[22]。但生态修复政企合作具有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和行政任务目标实现的双重特性,其契约的达成赋予了生态修复企业的充分自由,保留了行政主体单方面合同履行、变更、解除的权利。诚如柯坚教授所认为的,协作契约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契约目的和契约合意为平衡点,一方面维护了契约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另一方面又实现了行政主体在民主行政中的“契约当事人”与“公益代表人”双重身份的自由切换[23]。因而,这种契约既具有行政性,也具有私法合意性。
(二) “企企合作”模式:从行为责任转变为经济责任
“企企合作”模式是指负有修复义务的责任人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第三方生态修复企业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合作模式。2007年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北京红狮涂料厂土壤修复项目和2013年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苏州安利化工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治理修复项目,都是负有修复义务的责任人委托第三方修复企业代为修复的“企企合作”模式。同时,自2015年我国试点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来,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下,呈现出一些污染企业委托修复企业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的司法判决。如,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判决被告需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订土壤修复方案①。在“企企合作”模式下,委托方和第三方生态修复企业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基于自愿达成生态修复委托合同,其合同的属性为民事合同。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企企合作”模式,使得“产污”与“修复”主体分离,使生态修复模式从“谁污染、谁治理”转变为“谁污染、谁付费、第三方修复”的新模式。简言之,就是将污染者的修复责任(行为责任)转变为经济责任,污染者向第三方修复企业支付费用,由第三方修复企业完成污染者造成的环境损害 修复。
“谁污染、谁治理”源自1972年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关于环境政策国际层面指导原则的建议》中提出的“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提出之初,只是一项经济原则,其目的在于指导污染治理和控制费用的分配,防止政府通过补贴治理污染、企业无需承担治污费用,造成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他将治污费用纳入产品成本和服务的国家,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公平。之后,由于该原则契合了污染责任公平分担的要求和呼声,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的响应,转化成一种法律原则[24]。在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经历了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到“污染者治理原则”,再到“损害担责原则”的演进。1979年我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曾提出“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并在1981年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得到了强调。由于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已经产生的污染治理,责任范围较少,属于事后补救的原则,所以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将其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从宏观上明确了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强调“治理”。但实际上,污染者治理原则在运行中被异化为污染者的技术改造、污染者的限期治理、污染者的排污收费等制度,并未落实对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为此,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污染者治理原则”的基础上,将其升华为“损害担责原则”。根据吕忠梅教授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法律释义》,损害担责原则是指在生产和其他活动中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损害他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主体,应当承担赔偿损失、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的责任[25]。由此看来,“损害担责原则”中的“责”包含了污染者的生态修复义务,并且这种修复治理义务是一项强制性义务,在污染事故所导致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中,属于一种行为责任,并不是简单的民事损害赔偿。
“谁污染、谁治理”是传统的环境管理理念,强调污染企业为自己的污染行为买单。污染企业是治理主体,适用于一般性污染治理。一般性污染治理属于废水、废气、废渣的点源治理,即工厂排污口的治理,是通过污染处理设施,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净化,以达到国家的环境标准。通常状态下,治理的难度要远远小于生态修复,只要排污企业配置了污染处理设施,保证污染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污染物就会得到净化。而生态修复是对受损生态环境的面源治理,属于补救措施,技术要求高,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借助外力使其功能恢复。受制于这种专业技术性的限制,大多污染企业根本不具备生态修复的技术。同时,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要求污染企业自为修复,消解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将自为修复义务剥离出来,交由专业第三方,污染企业可以专注于生产活动,提高经济效率。另外,生态修复企业专门从事修复技术的研发,不仅避免了污染企业自主研发生态修复技术的费用,而且具有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利用。当规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以形成聚集经济,产生企业聚集而成的整体系统功能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能实现的功能之和,环保产业园区便由此形成[13]。生态修复市场化的“企企合作”体现了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由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的转向,突出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改变了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主体格局,将“谁污染、谁治理”转向“谁污染、谁付费、第三方修复”,从而将污染者的承担生态修复行为(行为责任)转变为向第三方修复企业支付修复费用(经济责任)。
三、生态修复市场化的现实困境
国家法律政策的生态修复市场化导向,一方面为污染行为戴上了“紧箍咒”,另一方面促进了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然而,要推动生态修复市场化仍然面临着“知易行难”的困境。
(一) 生态修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
生态修复市场化需要形成自发的市场秩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市场配置中,生态修复行业作为生态修复的实施主体往往直接决定着修复工作的效能。与传统污染治理机理不同,生态修复是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技术措施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功能得到恢复,这一过程任务重、难度大,对于行业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态修复行业已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仅土壤修复领域 就占到环保总产值的30%~50%,占GDP的0.5%~ 0.7%[26]。而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属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新兴领域,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从事土壤修复的企业数量在900家左右,大部分在近5年出现,企业收入在1亿元以下[27]。同时,土壤修复行业每年的订单不足百亿,市场集中度较高,行业的前5家单位占到了订单比例的60%[28]。这充分暴露出我国生态修复行业专业化、规模化的不足。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由于生态修复行业投资大、风险大,导致了融资难。生态修复的科学技术性决定了其投入资金巨大,同时也面临着修复过程中的再次污染或其他事故的风险,这些因素制约着生态修复行业的融资。融资难问题导致生态修复行业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致使一些企业或专注于水体修复或专注于矿山修复或专注于土壤修复,整个市场结构分散,集中度不高。其次,在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下,污染企业的自为修复行为无须缴纳相关税费,所耗成本可以计入企业生产成本,而生态修复的市场化意味着生态修复企业需要缴纳相关税费。这对于目前整体实力偏弱、盈利有限的生态修复企业来说,无疑又是一个经济压力。最后,生态修复涉及了众多的产业,其上游企业为检测机构、修复用剂供应商、设备供应商等,因而仅有技术没有相关产业配套无法实施修复行为,需要有一个大的环保产业为其提供基础。作为社会调控强有力的保障,法律政策亟需针对以上三个原因,做出规范。
(二)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监督管理不畅
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手段,生态修复市场化监督管理的最直接法律规范来源于环境第三方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虽然这些政策法规将完善监管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予以强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监管措施,但由于缺少国家层面的硬性规定,生态修复市场化监督管理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是生态修复行业准入、考核、退出机制缺位。实践中,一些企业通过成立关联公司,进行“伪第三方治理”,还有些地方出现了项目招标暗箱操作、低价中标等乱象[29]。二是生态修复监督主体和监督内容不明确。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前言第(16)款规定“环境恢复工作应当以有效的方式进行,以确保实现相关的恢复目标,并应在主管机关的监管下正确实施”[30]。受制于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分散+统一”的模式,生态修复的行政监管机关分散在不同的环境管理部门,监管形式尚未固定,这为生态修复的行政监管带来了挑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责任人进行生态修复的,谁应当对生态修复行为实行监管,是法院还是环保行政机关?环保行政机关如何对生态修复进行监督?规定不明。
举例说明,2016年震惊全国的江苏常州“毒地”事件,在暴露出“毒地”治理责任问题的同时,也暴露出生态修复市场化的监管问题。一是修复主体层层转包,自由任性。2014年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总公司牵头启动了对常隆地块的修复工程。修复过程中,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总公司先是将修复工程委托给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委托给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又委托给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又委托给了其他公司。二是修复方案随意调整,不受约束。“毒地”事件爆发后,常州新北区政府在未征询利益相关者意见的情况下,组织专家制定并实施常隆地块应急处理方案,对原有的毒地修复方案进行了调整,将常隆地块的规划用途从商业开发改为公共绿地。在常隆地块修复中,修复主体的层层转包与修复方案的随意调整,充分反映出政府只关注常隆地块的治理结果,对于第三方接手后运营的好坏置之不问,缺乏对第三方修复的全过程监管。
(三) 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责任界定不清
在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中,污染者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并作为行政相对人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生态修复市场化改变了传统治理模式搭建的单向责任关系,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之外引入了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使法律责任问题更为复杂[10]。“政企合作”模式下政府基于国家义务履行生态修复的职责,而“企企合作”模式下污染者基于环境侵权承担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的义务,两种合作模式最终都将生态修复工作委托给了专门的生态修复企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生态修复责任本身的转移?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和地方发布的关于第三方治理服务的意见来看,都只是笼统规定了“排污企业承担主体责任,被委托方承担合同约定的治理责任”。也就是说,在生态修复市场化中,污染者依然是生态修复责任的主体,而生态修复企业承担的是合同约定的生态修复工作,因而污染者环境侵权造成的生态修复责任并未发生转移,委托者仍肩负着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
然而,生态修复本身存在较大风险,作为服务于政府或污染者的生态修复企业,如果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出现二次污染或存在违规,相应的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如何界定?由谁承担?是不是可以依照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中“排污企业的主体责任”予以认定,由排污企业来承担呢?对此,欠缺法律依据。诚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若修复企业只承担治理责任,一旦出现事故由排污企业承担,显失公平[31]。所以,问题的核心是主体责任到底是什么责任?法律中有没有主体责任这一概念?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中只有责任主体并未有主体责任。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一些排污企业借第三方治理之名,推卸自身责任,排污企业与生态修复企业之间的责任边界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修复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四、推动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法律保障
生态修复市场化顺应时代潮流,但面临着诸多困境。法律作为有效且重要的社会调控机制,应从生态修复市场化的制度规范、监督体系、责任分配三个维度予以完善,发挥其“保驾护航”作用。
(一) 构建生态修复市场运行的制度规范
首先,建立生态修复企业的经济激励机制。经济激励是利用市场手段支持产业或行业发展的政策。按照采取的手段不同,可以划分为正向的经济激励政策和反向的经济激励政策。正向经济激励政策包括了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政府贴息或低息贷款,以及价格优惠等。反向经济激励政策主要通过税收来解决产品的“外部性”,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针对生态修复市场化所面临的融资、税负、环保产业化的三重压力,需要通过税费优惠和金融支持政策促使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就税收优惠而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第27条规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企业可以免征或减少所得税。生态修复属于环境保护项目,理应享受法律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优惠实施中可以参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实施“三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即企业前3年免征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所得税征收一半。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相比,由于其依托市场发挥作用,具有“可持续性”。就金融支持而言,应当为生态修复企业上市融资提供政策支持,对生态修复企业银行的贷款项目进行免息、减息或政府贴息,拓展生态修复企业的融资担保范围。同时,国家还应该通过科研立项大力开展以恢复方案、恢复成本为导向的技术研究,支持相关技术的研发,加强对评估人员的专业化指引。
其次,建立生态修复行业准入、评价及退出机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行业准入门槛,从事生态修复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从业者相应的专业素质也是参差不齐[32],这将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在专业技术不达标的情况下,进入生态修复行业市场。对此,2017年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议,鼓励构建第三方治理信息平台,强化第三方治理信息公开,依法公布治理效果不达标、技术服务能力弱、运营管理水平低、综合信用差的第三方名单。因而,为了确保该实施意见的落实,在生态修复行业,各级政府一方面应通过诚信管理、“黑名单”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和市场化评价制度,将生态修复技术服务能力弱、管理水平低下、信用等级差的生态修复企业向社会公布,让生态修复服务技术能力强、管理水平高、信用等级好的企业优先享受政府优惠措施,对于多次违法或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生态修复企业,依法清理出市场,逐步形成规范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应从生态修复行业标准、市场准入标准、执业标准着手,严把准入关,将不符合标准的生态修复企业拒之门外。
最后,编制生态修复技术指南,确定环境服务质量标准。2016年6月环保部颁布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的纲领性文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虽然该指南对生态修复方案的制定做了规定,但过于笼统,忽略了对可供利用的最佳技术、实施的成本、获益的程度、修复所需时间、修复标准等因素的考虑,尤其欠缺对不同环境要素的考量。按照环境科学的一般认识,环境要素不仅存在着自然属性的差异,而且其污染特征与修复技术也有所不同。尽管我国在土壤修复领域已经制定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术语》,但在水体修复、生物多样性修复领域还未有相关技术指南。因而,有必要按照环境要素特性和行业特性分类制定修复技术指南,在指南中明确相应的生态修复服务质量标准,与生态修复目标对接,形成可量化的付费依据,建立公平的绩效考核标准,避免无序竞争。
(二) 完善生态修复市场化的监督体系
首先,强化政府的行政监管。行政监管是环境监管的一种方式,它是以加强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和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为目标的公法性制度,是保障环境法律制度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生态修复技术复杂、隐蔽性强、时间跨度大,包括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修复方案的制定、修复工作的开展,以及修复工作的验收评估等环节,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紧密,出现任何差错,都将影响修复的效果。因此,对于“政企合作”的生态修复项目,政府应当履行主要监管者的职责,从方案的制定、实施、效果的保证等实行全过程监管,对于方案的调整和变更应依据科学决策并做到信息公开,防止修复不够彻底从而产生二次污染。对于通过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责任人进行生态修复的,有学者提出了生态修复性司法的监督方式:一是应当发挥以法院、检察院为主导的监督作用;二是公安机关、司法局、环保行政主体应对修复过程实行监督,对拒不履行修复责任或修复标准未达到相应要求的,向司法机关提起监督意见改正书,由司法机关责令修复主体改正;三是引入第三方监督[33]。笔者认为这是以生态修复性司法为前提的监管方式预设。对于通过公益诉讼由法院判决责任人进行生态修复的监管,应当由环保行政机关来履行。因为从环保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职能来看,法院主要行使的是审判功能,如果让法院对其进行监管,加大了法院的工作任务,浪费了司法资源。而环保行政机关不同,它的职能就是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能够保证监管的实效。当然,科以负有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机关以裁决执行的监管义务,这就需要法院与环保行政机关在执行中将任务具体化,做好执行工作的衔接,将责任人委托的专业生态修复企业以及责任人都纳入监督对象范围。
其次,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公众参与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的民主方式,是民主理论和行政控权理论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有效形式,公众监督在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契合了环境法治的特性,是环境民主决策、监督生态环境执法的重要机制。生态修复的社会公众监督既包括了对政府生态修复相关工作的监督,也包括了对生态修复方的监督。这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专家和利益相关公众可以对生态修复规划、方案以及污染场地风险管理表达意见,为决策提供建议;二是公众对政府生态修复责任落实等相关工作进行监督;三是对生态修复第三方的修复过程以及质量进行监督。而要确保社会公众监督的有效性,则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一是生态环境损害的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二是生态修复目标、方案的信息公开,让公众知晓生态修复目标方案,表达相关建议;三是生态修复实施过程以及效果的信息公开,让公众能够对生态修复的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以美国的污染场地修复为例,公众对于政府的监督一般是通过行政公开和公民诉讼实现。就行政公开,《美国超基金法》从污染场地信息公开、反应行动计划的行政记录公开、技术转移信息公开三个方面做了相关规 定[34]。如,对于污染场地信息公开,第104条“反应权限”中第e款第(7)项,规定了信息保密要点:①公开是原则、不公开为例外;②如何获得信息保密;③不得纳入保密范围的信息;④保密资料的递交;⑤泄露保密信息的处罚;⑥国会委员会获取保密信息的 权力。
再次,构建第三方监督机制。第三方监督是环境多元共治的一种新型手段,目前还只是一个新事务,是指通过政府或企业向环保第三方购买监督服务,对环境领域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如,贵阳环保法庭为了确保案件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引入第三方(环保NGO、志愿者)对判决或调解协议执行进行监督;2014年清镇市政府通过购买环保组织的服务,委托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对政府和产业进行第三方监督[35]。在生态修复中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契合了环保组织法律地位独立性和技术专业性的要求,有助于提升生态修复的监管水平,增强环境管理社会公信力,减轻行政机关的监督压力。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法》(2015)构筑起的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也为在生态修复中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后,探索生态修复的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依托于行业协会对行业的一种监管方式,目前在金融业、食品卫生业、互联网业已经广泛开展。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行业协会作为经济法调控主体之一,与国家调节相配合,共同矫正市场缺陷,克服政府行政监管的缺陷。同时,作为经济法调控受体之一,限制竞争行为,维护自由竞争秩序[36],与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共同构筑了严密的监管网络。生态修复技术性强、周期长,依托行业自律对修复工作监管,一方面弥补了政府监管专业性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缓解了生态修复市场化立法滞后的缺陷,并且通过生态修复行业规范和自律公约提高了生态修复的服务质量,从而促进生态修复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 明确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责任划分
第一,明确违约责任的划分。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违约责任是违反修复合同的民事责任。政企合作模式中所建立的契约关系属于具有民事合意性的行政合同关系,因而其违约责任既具有违约性又具有违法性。具言之,作为生态修复工程委托方的政府如果违约,一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承担的具体责任情形应当包括:任意变更或解除修复合同、不履行修复合同或者不正确履行修复合同、滥用行政优益权②。生态修复企业一旦违约,首先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其次是民事赔偿责任,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应为不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修复义务或迟延和不履行修复义务。其违约责任的分配应当区分三种不同情形;一是污染企业未支付修复费用或指示不当时承担违约责任;二是生态修复企业未按照合同要求在履行修复义务时承担违约责任;三是双方订立的合同均存在过失,无法实现修复目标,双方应当根据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第二,明确侵权责任的划分。生态修复市场化的侵权责任是指生态修复过程中造成的人身、财产、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在政企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生态修复企业虽签订了委托修复合同,但并不能以此转移其对公众的环境职责。为此,对于生态修复过程中造成的环境侵权,政府应根据情势先承担法律后果,再向生态修复企业追索费用,此种追索权也可采纳惩罚性赔偿机制以发挥威慑效果。在企企合作模式中,侵权责任承担的症结在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依照此规定,在发生侵权行为时生态修复企业是直接的侵权行为人,其有无过错均需承担相应责任,而污染企业只是委托方不是侵权行为人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这显然大大地抑制了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依据环境损害担责原则,污染企业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是为了履行自身责任而委托生态修复企业代为完成修复工作,其相应责任不应笼统通过合同转移至生态修复企业,应当以公平原则为基础,通过完善合同责任条款,明确双方的责任边界。其中对于因修复造成的侵权责任,应允许过错与无过错原则的交错适用,区别不同情形予以认定。具体而言,当生态修复企业与污染企业均无过错时,出于对生态修复企业的保护,适用《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污染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当生态修复企业无过错、污染企业有过错时,污染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当生态修复企业有过错、污染企业无过错并履行了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时,生态修复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当生态修复企业和污染企业均有过错时,依照《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5款③规定,生态修复企业和污染企业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被侵权人既可以向污染企业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生态修复企业请求赔偿,若生态修复企业向被侵权人承担了赔偿责任,生态修复企业有权向污染企业进行追偿。
第三,明确行政责任的划分。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行政责任是指生态修复过程违反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在政企合作模式中,行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产生,从其行政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企企合作模式中,污染企业的行政责任在生态修复企业不存在违法或过错的情形下,不能依据契约关系转移给生态修复企业,应由自身来承担。这是因为,污染企业是法律上造成污染不利后果的直接承担者,生态修复企业只是依照委托合同对污染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实施修复治理。如果在生态修复企业没有违法和过错的情况下,让生态修复企业承担行政责任,是污染企业行政责任的逃逸。相反,如果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治理的过程中,存在违法或过错行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但如果在修复治理过程中,污染企业与生态修复企业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行为,其行政责任应共同承担。
五、结语
生态环境损害的加剧,推动了生态修复法律政策的出台,并在法律政策中明确了生态修复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实践中,生态修复市场化表现为“政企合作”与“企企合作”两种模式。政企合作模式是基于修复主体不明或灭失时,政府主导的通过招标、购买第三方服务,由生态修复企业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运行方式。其隶属于公私合作的范畴,合同属性呈现出行政性与民事自愿性特征。与政企合作模式不同,企企合作模式是生态环境损害者通过向生态修复企业支付修复费用,由生态修复企业代为修复的运行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损害者将自己的行为责任转变为经济责任,其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审视当前我国生态修复市场化运行的现状,不难发现,其面临着生态修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管不畅、责任界定不清三个困境。为此,要破解以上困境,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应通过建立生态修复行业的经济激励、市场准入、评价及退出机制,完善其制度规范。其次应通过强化政府行政监管、构建第三方监督机制、探索生态修复行业自律机制,完善其监督体系。最后需明确生态修复市场化中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及行政责任的边界。
注释:
①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等环境公益诉讼纠纷案([2015]常环公民初字第1号)。
② 行政优益权指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所享有的职务上或物质上的优益条件。参见:邹瑜、顾明的《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1] 王菁. 环境修复责任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适用刍议[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 38(10): 59−62.
[2] 吴贤静. 我国土壤环境修复制度反思与重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10): 89−96.
[3] 朱晓勤.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探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 57(5): 171−181+208.
[4] 王立新, 黄剑, 廖宏娟. 环境资源案件中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J]. 人民司法, 2015(9): 9−13.
[5] 胡卫. 我国环境修复司法适用的特色分析[J]. 环境保护, 2015, 43(19): 58−61.
[6] 任洪涛, 严永灵. 论我国生态修复性司法模式的实践与完 善[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19(4): 86−94.
[7] 赵春. 生态修复机制在环境司法中的实现路径探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0(2): 19−24.
[8] 周兆进. 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应用[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2): 99−103.
[9] 周五七. 中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形成逻辑与困境突破[J]. 现代经济探讨, 2017(1): 33−37.
[10] 任卓冉.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困境及法制完善[J]. 中州学刊, 2016(12): 49−54.
[11] 刘宁, 吴卫星. “企企合作”模式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侵权责任探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3): 61−68
[12] 范战平.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2): 41−44.
[13] 董战峰, 董玮, 田淑英, 等.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改革路线图[J]. 中国环境管理, 2016, 8(4): 52−59.
[14] 康京涛. 生态修复责任: 一种新型的环境责任形式[J]. 青海社会科学, 2017(4): 49−56.
[15] 周佑勇. 公私合作语境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问题与制度完善[J]. 政治与法律, 2015(12): 90−99.
[16] STEPHENSON M O. Whither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1, 27(1): 109−127.
[17] LANGTON, STUAR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Hope or hoax?[J]. National Civic Review, 2010, 72(5): 256−261.
[18] 李霞. 公私合作合同:法律性质与权责配置——以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领域为中心[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 18(3): 139−146.
[19] WECHSLER S. Law in a flash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M]. Boston: Emanuel Pub Corp, 1997.
[20] 刘京一, 吴丹子. 国外河流生态修复的实施机制比较研究与启示[J]. 中国园林, 2016, 32(7): 121−127.
[21] 任维彤, 王一. 日本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 环境保护, 2014, 42(20): 34−38.
[22] 施建辉. 行政契约缔结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6−7.
[23] 柯坚, 吴隽雅. 环境公私协作: 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113−121.
[24] 柯坚. 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嬗变[J]. 法学评论, 2010, 28(6): 82−89.
[25] 吕忠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4: 41.
[26] 2017年中国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预测[EB/OL]. (2017−08−16). [2017−09−06]. http://www.er-china. com/index.php? 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6&id=8 7042.
[27] 行业集中度待提高土壤修复竞争向产融互动靠拢[EB/OL]. (2017−07−13). [2017−08−19]. http://www.er-china.com/index. php?m=content &c=index&a=show&catid=16&id=87134.
[28] 2017年中国危废与土壤行业政策及市场规模分析[EB/OL]. (2017−08−23). [2017−09−12]. http://www.sohu.com/a/1667988 91_276904.
[29] 庄媛.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还须把好监管关[N]. 深圳特区报, 2017−11−24(A02).
[30] 王轩. 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J].国际商法论丛, 2008, 9(1): 397−424.
[31] 孙佑海. 第三方治理背景下环境损害责任转移和不转移[EB/OL]. (2017−06−09). [2017−10−18]. http://huanbao.bjx.com. cn/news/2017 0609/830253. shtml.
[32] 王硕. 你脚下的土地是否有毒?[N]. 人民政协报, 2013−10−31(C01).
[33] 徐以祥, 王宏. 论生态修复性司法[J]. 人民司法: 应用, 2016(13): 79−83.
[34] 贾峰. 美国超级基金法研究:历史遗留污染问题的美国解决之道[M].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 86−88.
[35] 王太师, 胡俯茂, 陈忠林. 政府主导+第三方监督: 共守碧水蓝天[N]. 贵州日报, 2016−06−22(007).
[36] 汪莉. 行业协会自治权性质探析[J].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 28(4): 189−191.
The legal analysis and predicament breakthrough for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KANG Jingtao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s a new typ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s clearly stipulated in the national legal policies, and in practice, it is manifested by the operation mod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breaks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the sole control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nvert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hil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transfers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havior from the polluters (behavior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third party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Being subjected to its imperfect law in our country,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faced with such obstacles as lack of specialization, poor supervision, and unclear liability. Therefore, law should function as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social regulating mechanism, perfecting itself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and liability distribution.
the mark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stitutional rules;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liability distribution
[编辑: 苏慧]
2017−11−09;
2018−01−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治的生态转型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4ZDC030);2017年江西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生态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规则研究”(FX17206)
康京涛(1980—),男,陕西宝鸡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江西师范大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科研人员,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联系邮箱:kangjingtao2011@126.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08
D912.6
A
1672-3104(2018)04−0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