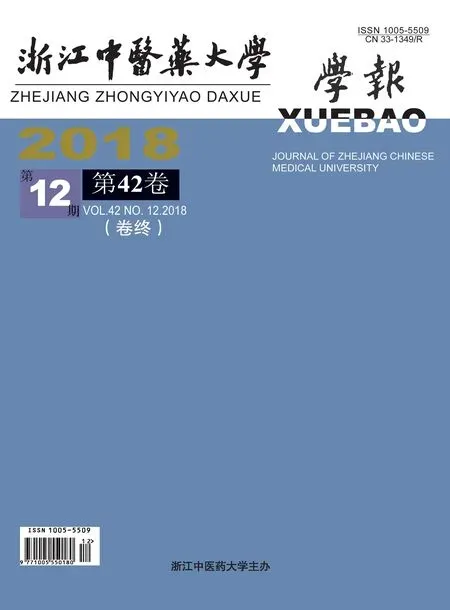杏苏散方证论析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杏苏散源于吴瑭《温病条辨》,并几乎得到所有教材《方剂学》主编的认可,列为治疗凉燥的代表方剂。其具有轻宣凉燥、宣肺化痰之功,主治外感凉燥证,症见恶寒无汗,头微痛,咳嗽痰稀,鼻塞咽干,苔白脉弦。初学杏苏散,对凉燥伤肺,同时兼有痰饮,理解有些困难。外感风寒如麻黄汤证者,因感风寒,风寒束表,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肺失宣降,则见气喘,直接明了。也不如同类方剂桑杏汤证者,感受燥(温)邪,燥邪伤津,一切以干为特征,症见干咳、鼻干、咽干、口渴、苔薄白而干等。凉燥虽为次寒,但总属燥邪,有伤津耗液的特征,杏苏散证感凉燥,症见咳嗽痰稀,尚可理解,但组方中却用上了二陈汤,殊为骇观与费解。对此问题,现予以论析。
1 杏苏散表出
吴瑭曾云,“杏苏散乃时人统治四时伤风咳嗽之方”[1],说明杏苏散的创制者另有其人,并且是吴瑭同时代或前代医家的一首常用方。清代能得到大家公认的,或大家能读到的医书,首推皇家教材《医宗金鉴》。《医宗金鉴》卷58载有杏苏饮方,其由苏叶、枳壳(麸炒)、桔梗、葛根、前胡、陈皮、甘草(生)、半夏(姜炒)、杏仁(炒,去皮尖)、茯苓组成,生姜为引,水煎服。主治风寒客肺作喘等[2]。对照二方组成,杏苏散相当于杏苏饮去葛根,加大枣。据此可以认为吴瑭所言的当时流行的杏苏散,即是《医宗金鉴》杏苏饮。由于杏苏饮苦辛温润,外可解散风寒,内能宣肺化痰,因此吴瑭遵《素问·至真要大论》“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之旨,对于次寒的凉燥外袭,肺有停饮的病证,用杏苏饮稍作加减,化裁而为杏苏散以治之。吴瑭的杏苏散一经表出,就得到医界公认。清·张秉成《成方便读·自序》言“润燥之剂”,第一首方剂就是杏苏散。
2 感受凉燥,即生痰饮
何以外受凉燥,即生痰饮?引据经典,《温病条辨》引沈目南《燥病论》曰:“燥气起于秋分以后,小雪以前,阳明燥金凉气司令。经云: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癲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据此经文,燥令必有凉气感人,肝木受邪而为燥也……燥病属凉,谓之次寒,病与感寒同类”[1]。深秋燥令气行,气候干燥且渐冷,一有不慎,感而得之,遂成凉燥。邪自外来,先犯皮毛,卫阳阻遏,出现恶寒无汗,头微痛等表证;皮毛受邪,内应于肺,则肺失宣降,咳嗽乃生。至于咳吐稀痰,系肺受凉燥,津液失去正常的输布,复加以阳气被阻,聚而成之,痰饮即生。肺开窍于鼻,今受凉燥,肺气不得宣发,故鼻塞。咽干,系燥伤肺津。凉燥兼痰饮,则脉弦苔白;同时,脉弦也与燥金克木,以致肝病有关。
外受凉燥,内生痰饮。它与麻黄汤证的区别在于:一为感受邪气的季节,彼为冬天受风寒,我为秋分以后,小雪以前受凉燥;二为感受风寒的程度与性质,彼为冬天受风寒,我为次寒兼燥,所以在临床上,表现为风寒轻证,但又有燥邪的特点,同时兼有痰饮。次寒兼有痰饮,一如小青龙汤证轻证,吴瑭提到:“按杏苏散,减小青龙一等。……若伤燥凉之咳,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正为合拍。若受重寒夹饮之咳,则有青龙。但细辨之,其间又有区别,小青龙汤证,其痰饮为缩饮,杏苏散之痰饮为即病之饮。
3 饮邪新生,还是宿饮
前述杏苏散之饮邪,应为即病之饮,是新生之饮。邓中甲[3]、李飞[4]等方剂名家,在其著作中均指出,其饮邪是肺受凉燥,津液失去正常输布,阳气被阻,聚而成饮。但吴瑭的理解是:“按杏苏散,减小青龙一等……若受重寒夹饮之咳,则有青龙。把杏苏散视为小青龙汤证轻证。众所周知,小青龙汤证是外有风寒,内有缩饮。从论治而言,无论是即病之饮,还是缩饮,均是化饮,吴瑭之言符合临床。但从辨证而言,其饮邪是新生之饮,还是缩饮,则区别颇大,不可不察。
细辨之,吴瑭杏苏散及其汤证,也非新创。在杏苏饮前素百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其卷13载参苏饮,由人参、半夏、茯苓、陈皮、甘草、枳壳、紫苏、前胡、木香、桔梗组成[5]。具有益气解表,理气化痰之功效。《医宗金鉴》之杏苏饮,系参苏饮去人参、木香,加葛根、杏仁而成。去人参,则无益气扶正之功;去木香,则减弱了和中的作用;加葛根、杏仁,则加强了解表宣肺止咳的作用。这样就从参苏饮之扶正解表,一变而为杏苏饮之单纯解表宣肺,化痰止咳。杏苏散汤证,也与参苏饮相关,其症见恶寒发热,无汗,头痛,鼻塞,咳嗽痰白,胸脘满闷,倦怠无力,气短懒言,苔白脉弱或痰积中脘,眩晕嘈杂,怔忡哕逆。除在脉象上,气虚为脉弱,凉燥为脉弦,及气虚证候如倦怠无力,气短懒言等外,其外寒症候与痰饮症候与杏苏散差别不大。但从其所治痰饮症候分析,尚难辨析其痰饮是即病之饮与缩饮,吴瑭化裁杏苏饮后,也不辨其痰饮症候是即病之饮,还是缩饮。
4 感受凉燥,化饮即润
肺受凉燥,津液失去正常的输布,复加阳气被阻,聚而成饮,则成凉燥兼痰饮证。其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燥者濡之”,又云,“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吴氏云“若伤燥凉之咳,治以苦温,佐以甘辛,正为合拍”。但是,细究杏苏散。其组方苏叶、半夏、茯苓、前胡、苦桔梗、枳壳、甘草、生姜、大枣、陈皮、杏仁(原书未载用量与用法)11味药中,具有辛温者4,苦温、甘温者各1,辛苦寒者2,苦辛者1,甘平、甘淡平者各1,都具有辛味者7,且都性温,苦味者5;其中半夏、陈皮、茯苓为燥湿化痰之药;尤其是半夏在历来中药学书中被列为燥湿伤阴之品,其条下每注:“阴虚燥痰慎用。”显然组方中除杏仁性润外,其余大多为辛温之品,与濡法相去甚远。辛味药的作用能散能行,多治表证,苦味药能泄能燥,含有泄火燥湿之意。本方唯有杏仁苦温而润,虽有润性但非是能益阴生津滋燥之品,在方中又处在大剂辛苦,燥剂之中,并不能发挥其润的作用。因此有人认为,本方辛温,只宜于凉燥与风寒表证,不宜于风温,也不能作为四时咳嗽的通用之方;还认为,该方不是润剂,不能用于治燥证。有的方剂书上,还把杏苏散归入解表剂。
其实,从本方证病机及组方分析,杏苏散确实不是润剂,套用经旨,片面从润理解,难以剖析凉燥的病理。杏苏散是解表剂,针对肺受凉燥,津液失去正常输布,阳气被阻,聚而成饮的凉燥最相适宜。凉燥表散,痰湿消化,肺宣降功能恢复,津液输布如常,故云化饮即润。
5 苏叶解表,代桂枝、麻黄
从陈言参苏饮到杏苏饮成为“时人统治四时伤风咳嗽之方”。其实代表着用苏叶为主组方的风寒解表剂的兴起。期间有张元素者,鉴于宋以前治表证,长于发汗、短于祛湿的局限性,以及“有汗不得服麻黄,无汗不得服桂枝”[6]之戒忌,遣羌、防、苍、芷等辛温香燥药组成方剂,“以代桂枝、麻黄、青龙、各半等汤,此太阳经之神药也”[7]。羌防与苏叶解表剂的出现,打破了麻桂剂一统解表方的局面,开创了解表方的另一模式。随着对温热病认识的加深,与温病学的兴起。有人提出“南方无真伤寒”,并视麻黄、桂枝类方剂如虎狼。典型的如绍派医家胡宝书,其言“南方无真伤寒,多系温病,而吾绍地处卑湿,纯粹之温热也少见,多类湿邪为患”[8]。当然也有反对意见,如清岭南医家陈焕堂,批评王叔和、陶节庵、张景岳等曲解伤寒与麻黄、桂枝类方剂[9]。章次公指出“近世畏麻黄不啻猛虎,而尤以上海为甚,问其理由,莫不以麻黄发汗之力太悍,不慎将汗出不止而死”;又说桂枝:“自有清中叶,苏派学说盛行以后,桂枝之价值,遂无人能解,病属外感,既不敢用之解肌;病属内伤,更不敢用之以补中……苏派医生,所以不敢用桂枝,其理由之可得而言者,不外南方无真伤寒,仲景之麻、桂,仅可施于北方人,非江南体质柔弱者所能胜”[10]。在这样的背景下,故而杏苏散一经表出,未经细考,便迅即得到医界相应。
6 结束语
综上,杏苏散其实是参苏饮、杏苏饮的化裁方,主治外有“次寒”或风寒表证轻证,内有痰饮证。在痰饮治疗方面,主要针对即病之饮,新生之饮,对缩饮的轻证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温化之力略嫌不足。无论是杏苏散,还是九味羌活汤,都是对仲景伤寒学说及治疗的深化。就杏苏散及其主治等的讨论,若认为杏苏散可通治四时外感咳嗽,则有欠缺,因它适宜风寒,不宜风温;它不是润剂,也不治燥,只为凉燥而设,其意义在于解表与化饮,表解痰化,肺畅气调,诸证自愈。单纯从润理解,套用经旨“燥者润之”去理解杏苏散的方义,显然与组成不符。
在临床中,以肺为中心,津气干燥为基本特征的燥证,并不少见,但是,如何达到正确的辨证,认清燥病的病因,病机,成为了治疗的关键。凉燥是一个兼寒邪,有燥邪共同特征的病证。在治疗中,如果将一味强调“燥者润之”,将内燥、外燥混为一谈,外燥证投用滋阴养阴之药,或是将凉燥误作温燥治疗,投之辛凉甘润之药,则可能发生它变。知名老中医蒲辅周先生有云:“凉燥既是凉气,需当小小的伤寒医治,若误用润药,越吃越燥”,可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