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比不安更深彻的阴影[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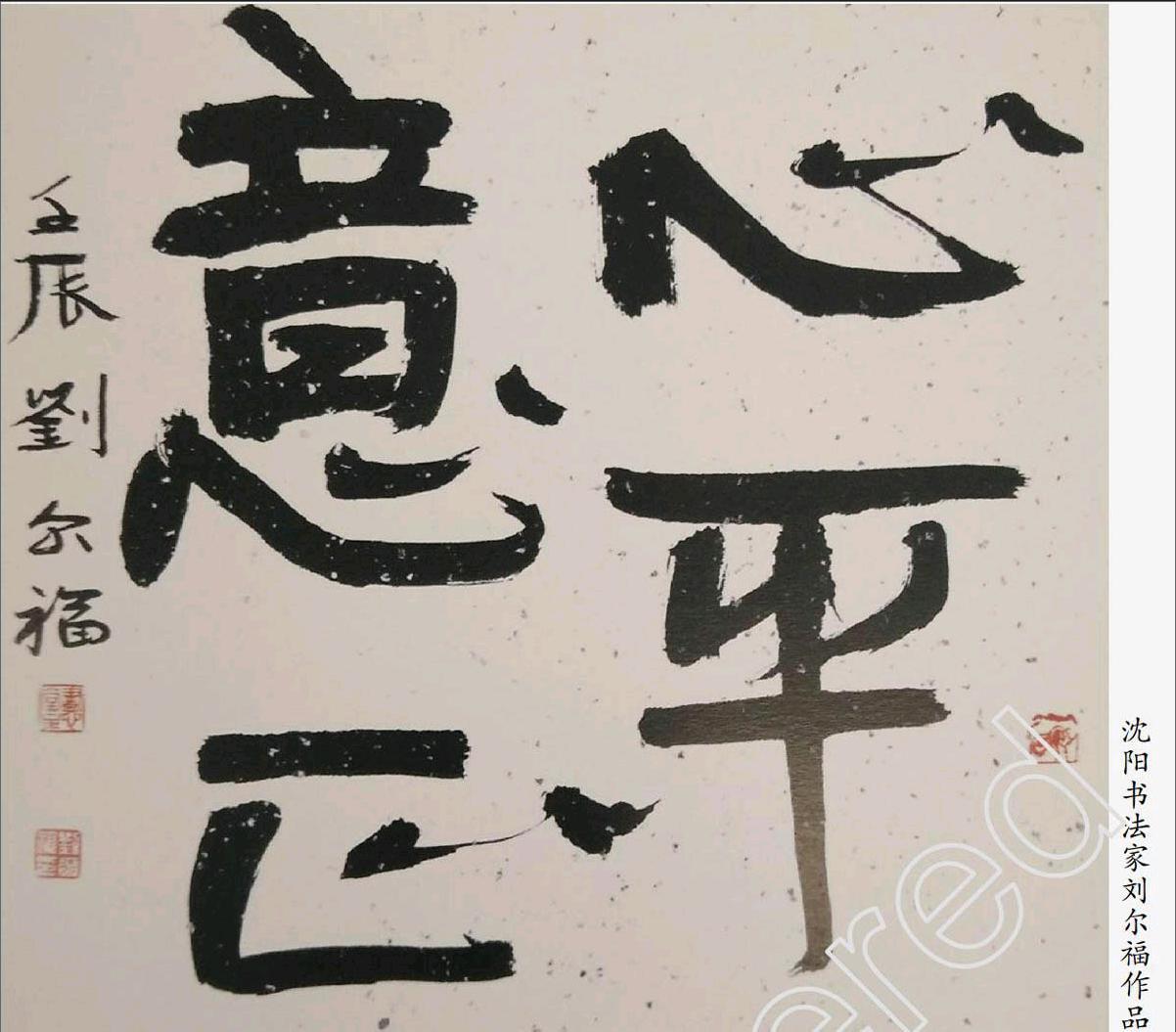
苕溪,若耶溪
有些流水总让人想起故人的名字
一个38岁的人把这条溪写进了诗里
此刻,有人指着远处
我一切都没有看见,声响也没有
陌生人仍指指点点
白鹿化身山野
寺庙在革命年代曾经改为茶厂
还俗的人去了哪里谁也无从知晓
相逢的人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他们多希望像书页一样折叠在一起
心脏压着心脏
前世压着今生
柳絮正飘,无水可浮
有朝一日我们成了古人
成了那将徐徐打开的发黄的册页
或者成了一个黑色的二维码
渔人早已隐入文字丛林
那么多的人在电子屏幕上钓电子的鱼
那么多的人坐在四个轮子的车里
那么多的人挤满了不再崎岖的山路
那么多的人在草地上烧烤
那么多的人在相拥热吻
那么多接听手机的人
那么多急匆匆掉转车头的人
那么多的人
谁也不认识谁
人形兔与一只野兔相遏
多年后回想起来
那时经历的一切都仿佛是预先安排
不可见的手
同样下可见的旋开黄昏的按钮
走出家门时候
已是大雪封路
母亲说百年都未一遇
冷亮的乡村雪路
闪亮光碎片和空旷的白瓷杯盏
我穿过厚雪积满的麦田
一只野兔的草色身影
在眼前一闪
多年后
我仍然感激那只野兔
在冬天的旷野我与它偶然相遇
它就像我的前世或来生
我出生在1975年
一只化身人形的兔
那时我还未来得及多想
它蹦跳的身影已经不见
杨树上随风抖落的积雪
恍惚是时间的睫毛微闭
银杏,以及那些隐形的时光
山路正展开颠簸的躯干
而往日
和远处的峰峦一样清晰而遥远
陌生,却与生俱往
塔林映照着陌生人乌黑的面庞
乌黑的枝干
构成灰蒙蒙的点彩画
年轻僧侣似乎无所事事
夕阳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银杏树此刻在风中响得更紧
孩子跌跌撞撞遵守着游戏规则
年轻母亲对换季的蔬菜满含抱怨
布满阴影的草坡
老式的割草机正在轰鸣
乌蒙山的雪或一个友人的亡故
现在是秋天的乌蒙山顶
时间的冷和词语的冷刚好相遇
一团团的雪斜斜地吹向下面
除了眼前的白,就是阴冷的黑
由不知名的手调制好的色调
多像是一纸亡灵书
隐隐地有人在唱着歌
时断时续的雪却带来一条确切的消息
一位友人刚刚在昨夜亡故
那时中原的庄稼头颅刚刚被砍落一地
雪阵回旋的下午
人们正忙着灰蒙蒙地呼吸
提前到来的寒冷
山脚下的洼地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
有不知名的野兽留下了几行脚印
也许它们刚刚消失在远处的树丛里
那些可食用的块茎还深埋地下
而有些人再也不会和你见面了
如果你偶尔想起了一个人
可以在这样的大雪弥漫的时刻
可以在一些缓缓的事物降落之后
可以在些越来越快的消失和溶解之前
石家庄原来有这么多高楼
——悼先生陈超
石家庄
原来有这么多楼
这么多需要抬起头
仰望的高楼
从2014年万圣节起
每一座高楼
都会
有一个人
跳
下
来
然后微笑着
走过来
拍着我的肩膀说
——“俊明,我没事!”
不大不小的一次复活
赫拉巴尔的墓园和故园
离得太近了
生死只隔了两英里
红色拖拉机正在垦荒
椴木上刻着陌生人的篇字
一只手臂从石头墓碑里探出
抚摸那些大大小小的玩具猫
米黄风衣的女子侧身在十字路口
风不大却吹乱了她的头发
一辆蓝色的乡下班车会晚点开来
一半光亮一半阴影的墓园
一只猫突然翻墙消失在树林里
它是为了离去还是为了寻找?
在我看来
这是一次
不少不小的复活
我们都有自己的木马
依次展開群山的绿斗篷
此刻,车正在穿越秦岭
这多像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次次寻找
又一次次陷入黑暗和虚空
我试图记下
那些或长或短的隧道名字
但狂灌过来的山风
如十字架闪亮的叶片眩晕
没有任何一个夜晚会拥有秘密
灰色的松鼠正抱食杉果
我们都有自己的木马
日复一日地原地打转
并以为正在向前的路上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