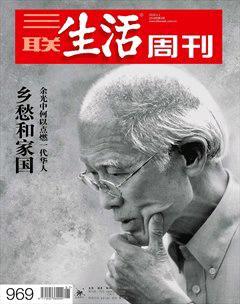一场大火之后再看北京疏解:空间策略与空间权利
贾冬婷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最近北京一系列“休克疗法”式的城市治理引发的震荡格外剧烈。由此浮出水面的是,城市的空间权利和空间正义由谁来参与,谁来决定。

北京最近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图为北京胡同
激起震荡的第一颗石子是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一起突如其来的火灾。事故发生在靠近南六环的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处聚居了400多人的集生产、仓储、居住于一身的“三合一”公寓里,造成其中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随即展开了针对隐患群租公寓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而且限定“紧急清退,限期五天”,逾期不退则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迫使很多打工者连夜寻找住处,或不得不举家离开北京。
清退之外,各种风貌治理也不断深入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比如为了“亮出天际线”,北京开始集中清理建筑物上的牌匾,甚至规定“3层以上只能安装一块牌匾标识”,以致有人无奈调侃:“没有了那块熟悉的招牌,迷路怎么办?”还有封堵“开墙打洞”,初衷是整治90年代遗留下来的“居改商”问题,但同时伴生着对一些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区活力的损伤。

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市场和行政的共同作用。图为骑车人夜晚穿越混乱的停车区(摄于2016年) ;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此形容这一轮城市清退措施。“灰犀牛”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在2013年提出的,形容一种大概率的潜在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对于极其罕见、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的危机其实大多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常常被忽视,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那样——灰犀牛体形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时看似毫无威胁,而一旦它狂奔而来,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灰犀牛”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或者金融领域,而如今看来,社会领域尤其是城市领域的灰犀牛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中立的物理场所,而伴随着城市持续性的拆迁和改造,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的竞争,由此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当城市的粗放发展期过去,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更会触发新的空间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大城市中空间不平等的问题尤为突出,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也引发了旨在争取“空间正义”的都市社会运动的出现。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他同时提出了“市民权”的概念,即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以及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空间正义”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1967年曾经论述“中国盒子”问题,他指出社区层面的民主最容易实现,但这一层面享有权力的机会最少;越往上走,权力越大,但是民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在城市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治理都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力量较弱,公众参与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城市中正义价值的缺失和损害,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公问题,例如空间的剥夺与隔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资本化等等。

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在“地瓜一号”——改造前的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
空间正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落脚城市”,或者说是城市里的“飞地”。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类飞地常常被视为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或者都市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纳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在世界各大城市“块茎型”空间体系中,城中村、地下室、桥洞等灰色空间,并不存在于繁华的城市中心之外,而是直接内嵌在城市中心内部的死角中,也是城市秩序最为脆弱的标靶。对于这些“落脚城市”,是直接暴风骤雨般地“一刀切”,还是寻求多方参与和共生的精细化治理,是对一个追求精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城市政府的一大考验。
城市里“有序”都是好的、“无序”都是不好的吗?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的工作室就设在方家胡同里,他原本是被胡同生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吸引而迁入,近一年却目睹了封堵“开墙打洞”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以前他骑车穿过胡同时,可以碰上卖菜的、卖花的、剃头的、晒太阳的,现在那些熟悉的门脸都封上了,一切都干干净净的。“真干净啊!混乱的东西没了,有趣的东西也没了。”他提出,这些历史形成的“违章建筑”既然长期存在,就蕴含着合理性,能不能把问题变成答案——“向违章学习,向无序学习”?

周子書对地下空间的初期改造实验在花家地一间地下室进行
某种意义上,在基于“落脚城市”的建设性实践中才能发现空间正义,并有可能实现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周子书这几年一直针对北京的地下空间进行社会创新实验,在其中创立了“地瓜社区”。最初引起他关注的是当时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1.7万个地下室空间里,他想要探索如何为这些城市新移民改善居住环境,以及通过社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获取发展机会。后来地下室不再允许居住,他转而探讨如何将它们变为公共空间,激发社会潜力,创建未来共享社区模式。他告诉我,基于景观猎奇意义上的地下室空间改造只是吸引人走进来的开端,更关键的其实是创造可持续的社区共享和空间消费。第一个“地瓜社区”位于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当他重新去看这一社区的居民时,发现每个居民背后都有不同的职业:有全国“三国杀”总冠军,有在戛纳拍电影得金奖的导演,有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舞蹈老师,还有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员……这些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区,就形成了高度重叠和混杂。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来激活社区。周子书描绘了一个在地瓜社区可见的具体场景:两个家庭在周末相约来到这里,爸爸们到健身空间健身,一个妈妈在阅读空间看书,另一个妈妈带着两家的孩子在游戏空间玩乐高,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网上预订了一个麦当劳套餐,然后花40块钱租了社区里的电影院,两家人在这个电影院里一起看了一部动画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的社区生活模式。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遍布全市各处的城中村和地下室中,他们被称为“蚁族”和“鼠族”,其实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建筑工人、快递员、厨师、保安、保姆等。“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的第一个台阶,那么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市的正义?封堵‘开墙打洞,在恢复风貌和秩序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街道的活力?”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这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協同发展以及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那么,这一收缩型空间策略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北京为什么要疏解?又将疏解什么、如何疏解?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他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北京“大城市病”是市场和行政的共同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十八大以来,在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同时,还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收缩型战略。你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可否阐释一下背后的政策逻辑?
李晓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调整型、优化型的战略,甚至是一个减量型的战略。中央在其中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核心任务:一是治理首都大城市病,一是优化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的开发模式。
有人说“雄安新区是天上掉下来的”,真不是。在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里就很清晰地提到,要建设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同时对北京市的人口和机构的扩张作了严格规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核心城六区的人口开始下降,由此引来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大城市的聚集,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
我认同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大城市也因此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同时,大城市又是最开放包容的,所以也是吸引人才聚集的空间。但是即便在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从供需关系来讲,核心城市或顶端城市也永远是稀缺资源。如果大家都往超级城市走,那么中国只需要两个城市就够了——北京和上海,但这不可能。一个健康的城市体系,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机会和成本相匹配,大城市可能是机会最多的,但成本也是最高的;小城市机会少一点,成本也低一点,人们在这样一个经济逻辑下选择适合的城市。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大都市,都曾经历过城市病爆发的黑暗时期,而且度过黑暗时期不只是依赖市场的力量,都有行政力量的介入。更何况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面,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都在于市场,当然也就不能依赖市场去解决所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大城市病的形成基于什么机制?
李晓江: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病的首要根源,在于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城市政府划分了不同的行政层级的国家,由此带来高度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再加上GDP的单一导向、财政税收制度、长期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这些是中国大城市过度聚集资源和机会的制度方面原因。
以北京为例,我记得2015年,在一份非常重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督察报告中曾尖锐地指出,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关键在于北京滥用了行政和财政资源,导致非首都功能的过度聚集。
一个表现是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比如,北京的水电气暖价格居然比河北有些县城还低。2015年北京票价改革之前,公交票价才4毛钱。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在北京坐一次公交,能拿到3块8毛钱的补贴。类似这种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北京成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成本洼地。
二是非正规土地供给的滥用。北京有14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受到国家土地和城乡规划制度严格管控的。而除此以外,还有1500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均到260万农村人口身上,人均高达600平方米。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身是大城市非正规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被严重滥用了,以至于在这15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大量和首都功能毫无关系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物流业,甚至整个华北地区的服装制造业和家居制造业的重心就集中在北京的五环到六环之间;此外,六环内外来人口约630万人,其中四、六环间就聚集了423万人,农村集体用地是主要承载空间,像是大兴西红门火灾的事故发生地,就是在一个农民自己建的2万平方米公寓里。
三是项目竞争。北京有四大汽车企业,其中两个是从天津、河北“抢”来的;此外2008年以后,北京通过大量优惠政策引进了很多央企总部,这都不是一种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
大城市病的第二个根源,是资本和社会“两个流动性”都唯一地存在于超大特大城市这一层级。我们的资本流动性,要让钱保值,最有效的就是在大城市买房;社会的流动性也只在大城市,逃入和逃离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与此同时,这两种流动性在大城市又出现了剧烈的矛盾,经济不景气以及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吸引力和容纳力下降。据我们观察,最近五年几乎所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速都在快速下降,人们开始考虑其他选择。除北京和上海的人口下降有管控的原因,其他超大特大城市这五年的人口增量也只是前五年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题
中国大城市病的第三个根源,是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无法适应大城市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增长。因为资源的错配,导致了空间的错配,北京聚集了那么多产业、那么多人口,但却提供不了相应的公共服务,陷入一个怪圈。
因此,中国大城市病的根源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大量的行政作用和政府干预。那么,反过来用政府的力量去改变,我认为存在合理性。解决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通过规划、行政和经济调控来缩减核心城市的功能;二是优化我们的区域布局,比如用北京城市副中心来优化北京市域内的布局,而通过雄安新区来带动河北,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应对大城市病有什么共同经验?
李晓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经专门研究过全球几大首都的经验。我们发现,世界上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發展,都是时起时伏的,都经历过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不同时长的调整期。比如伦敦和纽约这两个世界级城市,都曾出现人口下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这些大城市碰到问题的时候,应用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行政、经济手段,适时、适度调控超大城市的供需关系是必需的。也因此,大城市问题和全球城市区域问题总是争论不休。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管控是需要的;经济不好的时候,都在抱怨管控过多。
比如伦敦,他们的城市规划是“二战”期间编制的。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战后恢复应该是大发展,但英国在战争后期为伦敦准备的规划是限制性的,明确设定了一个边界“绿带”,绿带里面有特定的开发政策,就是防止日后过度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伦敦政府又从工业、环境和交通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多轮调控,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优化整个区域布局,一是建设新城,二是在伦敦市中心区采取交通拥堵收费的政策。巴黎也是如此,既有非常严格的对工厂和办公建筑的管理,同时采取财政补贴政策来激励企业和机构的外迁,还有空间布局上的优化调整,从这几个方面来优化核心城市功能。东京则经历了两轮功能调整,第一次是50~60年代,第二次是80年代,把首都圈划分为不同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管制和限制政策。首尔也在2006年的规划中,把首都圈区分成拥塞抑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三类政策区进行分类管理,而且都有非常严格的评估制度。总结几大城市的共同特征是,纽约、东京、首尔都采用了中心区和外围的税率差异化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机构外迁,优化区域布局。另外,采用行政手段对大城市病进行治理是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旦跨越这一黑暗时期,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预了。因此,目前中国大城市病的有效治理,需要政策与资源在区域空间和城市层级上实现更加均衡的配置。
疏解功能,不是疏解人口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300万的人口上限是依据什么提出的?为什么以往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都提出人口控制目标,但都一次次地被突破了?

伦敦城市治理中,在市中心区采取了交通拥堵收费的政策。图为上世纪90年代的伦敦牛津街
李晓江:2300万是控制规模。目前北京总人口2100万,那就再稍微给一点空间,在目前阶段来看,2300万是一个合理的规模。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约束条件。环境承载力不是绝对的,不是简单的“1+1=2”算出来的,比如北京的水资源其实也是弹性的,首钢搬迁以后一天可以节省下来几十万吨水,此外还可以通过阶梯收费来控制用量。但完全忽略环境承载力也有问题,不能过度利用资源来发展,特别是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其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更应该相互适应。
以前我们说控制人口,但其实只是一厢情愿地写一个数字,在实践层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GDP导向下,地方政府并不把这个数字放在眼里,继续一种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所以北京才会出现1500多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总规提出了有效的规模控制手段了吗?具体要疏解什么?
李晓江:北京市这一次是下决心要控制规模的,在总体规划中也提出了具体目标,比如生产性用地减少、生活性用地增加,整个平原地区的开发强度降低等。
此外,这一版总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降低200万,这就需要很多政策和行政的联动。疏解对象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等等。具体到执行层面,包括严控在京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严控新增事业性服务单位和社会团体;京津冀三省市制定各自产业准入目录等。
疏解的对象是非首都功能,不是人口。最典型的是批发业,它在首都功能里面属于“寄生功能”,其实买的人不在北京,卖的人不在北京,生产不在北京,消费也不在北京,可以放在区域内其他城市。另一个就是部分制造业,它们是之前被北京的低成本黑洞吸附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很多人认为,是处于人口结构“低端”的那部分人先被疏解。
李晓江:不能简单地这么划分,因为在产业和功能转移的过程当中,链条当中的高端和低端是一起跟着走的。
人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城市有高端就有低端,而且高端和低端需要保持一定配比,往往越高端,就需要越高比例的低端。当某些低端功能被疏解出去,还会有其他低端功能进来。当链条上的低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就会带来价格上涨来调节供需,所以大城市价格上涨本身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如果想要降低成本,就要靠政府补贴,或者靠非正规渠道,比如“三合一”的群租公寓,但最后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北京一些功能疏解政策的具体落实,包括火灾后的清退、天际线恢复、封堵“开墙打洞”等,都让人感到“一刀切”式的缺乏弹性。
李晓江:这确实是政府要反思的,现在经常是只讲治理,却不讲治理的智慧。北京的群租公寓一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治理一直是遮遮掩掩,这一次因为大兴的火灾,才下决心了。但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公寓都关掉,让大家天寒地冻地去找住处,就是用力过猛,最后引起社会反弹。包括封堵“开墙打洞”,应该适度留点生机,其实在一楼经商,在很多城市都是一种普遍行为;但是开餐馆就要干预,因为这意味着给楼上的邻居增加了安全风险。
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元的,有高端有低端,但多元中必须要有管理,有约束,有监督。可是我们的城市治理往往走向两极:要不就放,一放就乱;要不就管,一管就死。
城镇化开始出现多向多次的流动

在北京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外来人口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图为2015年,北京郊区的农民工聚在一起吃晚饭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中国城镇化整体在放缓。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已经出现聚集的边际效应递减了吗?
李晓江:据我们对中国7个千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分析,确实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人口占比在提高,但经济占比在下降。所以疏解大城市功能,一方面是治理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小城市带来增长机会。
这次大兴火灾,其实也是北京长期以来过度追求GDP的一个后果。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什么产业和服务都要,放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搞工业大院,导致大量违法建设行为,甚至监管也无法覆盖。其实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GDP,借这块地皮发自己的财,最多跟村长和镇长分一杯羹,对城市财政的贡献很少,但隐患却很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事了。2011年旧宫就发生过一起重大火灾,我当时就跟北京的规划同行说,这把火应该把北京烧醒了,该下决心调整了,没想到又搁置下来,一直到六年后的这场火灾。
如果任由北京这么发展下去,那么目前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房价问题,都难以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逻辑也在于此。以往是北京用行政资源打造出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洼地,但也剥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成了一个黑洞。北京有那么低的成本,又有那么好的公共资源,当然所有的企业和人口都要流进来。这么一来,就违背了大城市高成本、中小城市中低成本的经济规律。所以我一直说,京津冀发展的问题就出在北京走了天津的路,天津走了河北的路,让河北无路可走,最后河北就只能干一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因为除了水泥、玻璃、钢铁,别的产业它都没机会干。然后这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导致的污染,又将整个华北地区淹没其中,所以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尤其从环境角度来看,不能独善其身。
三联生活周刊:从城镇化的方向来看,开始向中小城市流动了吗?
李晓江:不能简单这么看。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增速減少,跟我们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有关。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次流动,而是多次流动、多向流动,然后逐渐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城镇化的前半段发展很快,也就导致后面的调整期会更长。
在我国城镇化的初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对这些城市来说人口流动的压力巨大。2000年以后,农村转移人口数量是最多的,但同时流入的城市也多了。2014年以后转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流入的地方更多了。
目前城镇化的另一个趋势是,从长距离迁移转为近距离迁移。据我们对三大城市群的分析,周边省份的流动占到了70%以上,中西部地区开始出现回流,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在下降,城镇化的整体格局倾向于更加平衡。这跟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度的城乡二元化都有密切关系。农民工的流动有这样一个现象,农民工20岁在服务业,30岁在制造业,40岁在建筑业,50岁返乡或就近就地城镇化。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人人都要到北京,人人都要到大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应该为流入的农民工负担市民化成本吗?
李晓江:我一直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个伪概念。这个概念的一个根源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税收的绝大部分是企业交的,不是个人交的,所以城市政府就认为农民工在北京没交税,如果他要落户,政府要额外花一笔钱。实际上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企业的雇主在替他们交税,他已经为城市做了贡献,但是没有被纳入计量。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无所谓额外成本,只是把他们缴纳的税收合理返还给他们,但政府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像是我们家保姆,从我的孩子出生到现在,她在北京已经24年了,小保姆已经变成老保姆,还没有成为北京居民。城市不负担她的养老,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
2014年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到现在也没有进展。诚然,大城市吸纳不了这么多人,农民工的流动也开始多次多向,但重要的是,不管农民工在哪里打工,都应该有他的一份权利,这个权利应该跟着人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缴纳,于是联邦政府直接对个人负责,公民权跟着人走,不会出现今天在上海交,明天在北京交,回到家里就没人管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在城镇化的调整期,如何实现市民的空间权利?
李晓江:空间政策与城市治理中市民参与的缺失,是一个长期形成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市民文化的传统。解放后,城市的基层治理体系一直不完整。后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人群阶层分化。再加上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城市中既有的社会关系瓦解、历史文化受到冲击、社区意识丧失。
而在我们的财税制度与土地财政依赖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要企业,要税收,不要人;要高净值、高知识的人,要人才,不要人。相应地,企业对城市的话语权也远大于市民,政府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都指向企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企业经济活动的社会与资源环境外部性被严重忽视。
对城市治理的重视近几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从管理到治理的重要创新。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而且特别强调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中,我们目前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单一化治理模式,以后应该转向政府管制力量弱化,市场机制在受约束和界定的前提下发挥重要作用,而新的社会结构应与政府、市场形成博弈关系。
市民的空间权利,或者说应对“人的城镇化”的空间供给政策,应该是城镇化中后期空间调整的一个重点。从城市规划的关注点来看,包括构建满足不同城镇化人口流向的城市体系;关注不同人群多元化需求的差异化空间供给:中等收入人群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中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老龄化、二胎化的需求;关切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非正规居住、就业、服务空间的合理存在;關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空间关系和乡村发展等。所以我个人认为,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多元化、差异化的空间供给,是当前最重要的供给侧改革领域之一。
(实习生洪铭宇、郑院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