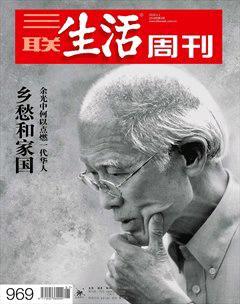病友陈凯
徐蓉
父亲在血液科,住过一天双人病房。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是一位大男孩,十八九岁,长得很帅,就是脸色特别苍白,显得眉毛又浓又黑,唇上的胡子大约还从没剃过,柔柔顺顺的,带着这个年纪男孩特有的青涩。他叫陈凯。
我们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吃着红提,胃口很好的样子。只是进了新病友,让他有些烦恼。因为他的病特别怕感染,前几日他发烧刚退,住进一个病友,又开始发热。这人走了,他刚松口气,我们又进来了,他很有些郁闷。
陳凯患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天看白先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王国祥君也是这个病,这个病的凶猛,我是在看了白先勇的文章之后才有所感知。他不爱和我父母聊天,我们却聊得不错,那时我以为他很快就会康复,所以心情轻松,和他东拉西扯。
其实,久病成医,他对自己的病很有些经验。他向他的妈妈抱怨,烧刚退医生就停了药,害得他又热起来,再挂就不管用了。妈妈安慰他,让他相信医生,他委屈地说:“你就不知道我烧得痛不欲生。”抱怨完了,他开开心心地看起电视,是一部青春校园剧,电视里的男孩住进了医院,有女孩去医院探望、照顾。电视里的病房,让在病房看电视的我们产生了特别的情境感。我不能不感觉到遗憾,在我们的病房,没有电视里那样年轻的女孩来看望陈凯。这个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看着电视里的青春校园剧,兴致盎然。
晚上8点多钟,他的妈妈赶几十里路回单位上夜班,舅舅来替班,第二天妈妈再带上做好的饭菜继续陪护,他这样的病人特别需要补充营养,饭菜往往准备得特别丰盛。妈妈忙着买、洗、烧,只能在上夜班的时候略略休息一下。
第二天,陈凯又发热了,戴上了口罩。那天有了单人病房,父亲住进了单人病房。他的妈妈过来打招呼,说陈凯担心是因为他的缘故,父亲才搬走,一直问他的母亲“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调病房的吧”,让母亲跟我们解释。父亲对我说,这孩子虽然和我们没什么话讲,可和你倒是挺谈得来,这个病,又刚这么个年纪,孩子也真挺可怜。
后来,陈凯也住了单人病房,在我们隔壁房间,58床。他的母亲不去上夜班了,在医院里整天陪护。陈凯一直时断时续地发热,热度而且很高。在走廊上看到妈妈的脸色,就能知道陈凯今天有没有发热,陈凯不发热的日子好像是节日,陈凯妈妈的脸上是溢出来的喜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他的病房门口,远远地和他打个招呼,尽管气色不佳,他仍然会开心地和我们打个招呼。
又一天在走廊上碰到陈凯妈妈,我知道陈凯又发热了,一发热,陈凯妈妈就茫然失措,眼睛里没有焦距,完全看不见任何熟人。我和她打招呼,她停下来,告诉我他们准备去苏州了,等陈凯不发热就走。主治医师也帮他们在苏州联系了医生,他们准备去换骨髓,已经向中华血型库申请配型了。“换骨髓要100多万,我们准备把房子卖了。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也不可能再生孩子了,现在100万会觉得很多,过两年这些钱也不算多了。”
“陈凯换了骨髓就会完全好的,他的病不是恶性病,只要换了骨髓就不会复发。”妈妈讲的时候,很有信心,认定前面是一片光明的前景,我也相信一切都会顺利。我打电话给苏州一位认识的朋友,请她帮帮陈凯妈妈的忙,后来我们就匆匆而别。
陈凯转院到苏州那天我不在医院,我想他大约已经治好了。4月里吧,那天出医院下楼梯,遇见一位老太太,她40多岁的儿子也是再障,我说没事,这个病治得好的,有一个小男孩到苏州去看了,他妈妈准备给他换骨髓,换了就好了,以后也不会复发。那位老太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天有一位医生告诉他,有一位十多岁的姓陈的孩子,到了苏州后就没能治,现在人已经走了。
我一下子蒙了,好像是听明白了,又好像是完全没有听懂。说的是陈凯吗?他走了?不是都已经准备换骨髓了吗?我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向医生求证,只悄悄告诉了母亲。过了好多天,母亲告诉我,是的,就是陈凯,他已经走了。我们后悔当时没有向他的母亲要一个电话,可是,要了电话又能怎么样,谁又能安慰那样一位母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