裟椤船
舒飞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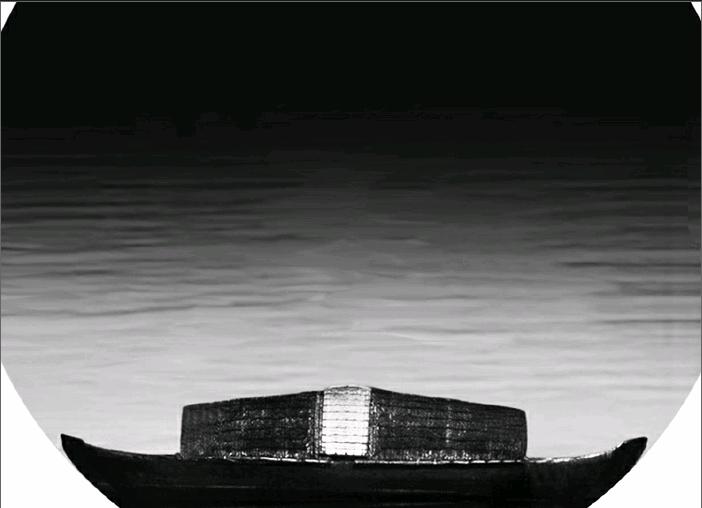
“保明保明,那才是北斗星,正好七颗,弯得像扯棉梗的铁钩子。”黑暗中,邦胜的白牙一闪一闪,为两面针牙膏打广告,他圆胖的长满了雀斑的脸看不清。
保明斜着身子,靠在村口枫杨沟壑纵横的树干上,抬头往上看,银河横亘在头顶,自西南河边郑流向东北匡家埠,瓜瓤一般的月亮漂泊在舒家塆粼粼黑瓦上,星星密密麻麻,又深又远,银河里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看得人眼睛酸胀发疼。一根“游泳”的烟头,红光在他脸前寸余远的地方,亮瓦虫般,一闪一闪。他不想跟邦胜讲话,一个一天到晚喋喋不休的家伙真是令人讨厌,但他就是你的朋友,在村里,人家看到邦胜,会问:“保明呢,保明在哪儿?”哪怕是家里人,喊保明回家吃饭,也会去问邦胜:“我家保明小狗日的,又到哪里荡路去了?”听起来,邦胜是跟着他在玩,事事听他的,但实际上,到底是树聽藤子的,还是藤子将树缠弯了腰,谁知道呢!一想到这点,保明就隐隐对自己不满意。
“赵永生中了枪,何翠姑用担架抬他,爬台阶,这个女将好狠,髁膝骨都磨烂出血了,这个歌是李谷一唱的,亮堂!”邦胜说。临时的电影场离他们一里路远,在肖家坝村西头的水稻田里。收了早稻的田,马上就要拉来水牛犁开地,重新灌满水种二季稻,之前的一两周,却被进伏的大太阳晒干,裂得像乌龟壳子,三四寸长的早稻桩还在沿镰刀割口向上长,一簇簇扎脚板。换黑胶卷的时候,场上一片喧哗,小孩哭,老人骂,青年男女打闹,小贩叫卖一角钱的瓜子,站在这棵树下面,都能清晰地听到。当然,也可以由银幕的反面,远远地,模模糊糊地看电影。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片子,5,4,3,2,1,放映机上已经换好胶卷了。《小花》,老片子,几个月前,还是在肖港镇的电影院里放头道的时候,保明和邦胜就去看过,邦胜说何翠姑好看,像牡丹。保明却觉得赵小花更美,像玫瑰。程小琳臭美,比起她俩,就是一朵棉花。肖红霞?一朵南瓜花!其实他们哪里看过牡丹和玫瑰,要等到十多年后,保明才分别在哈尔滨的红豆花店里看到玫瑰花,在武汉的东湖牡丹园里看到牡丹花,才明白城里的花,乡下的花,都是濡着露水,还未开足时好看。
“如果我死掉了,我要埋在路边,这里也行,晚上可以看着天上的星斗,白天,这棵树可以替我遮着阴,下雨了,也能挡住雨。”保明说。
“我也埋在这里,和你做朋友,你成了牛头,我就去阎王那里要做马面,这附近的人,命都在我俩手心里捏着,阎王要他三更死,我们就扯着铁链子去箍他,不让他拖到天光。听到头趟鸡叫,他已经眼泪汪汪站奈何桥上,将几十年活出来的鸡一脚鸭一脚的事都忘得精光。”邦胜赶忙说。
保明在心里冷笑了一下,说:“你妈都让人和肖家坝的肖红霞说亲去了,到时候,你还不得和肖红霞一起埋在蔡家河的坟林里,一起闭着眼睛听蔡家河的鸡公叫。你他妈的见到娘儿们连腿都迈不动。”
邦胜闭上嘴,沉默了半天,说:“我是比不过你,我可不愿为一个娘们去拼命。世界上娘们多了,都不是两个奶一个洞,我凭什么一定要和肖红霞那个蠢婆娘呆在一块?她小学都读了八年,留了三次级,肖家坝的姑娘,她最胖,有人讲她一次可吃一碗红烧肉。”
“肖家坝长得最好的姑娘是肖翠娥!”保明掐灭掉烟头,转过头向着电影场的方向眺望,一脸邦胜艳慕不已的冷峭的样子,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在他的眼眶里,北斗七星就安在他头顶似的。他这样子,都可以去电影里扮侠客的呵,佐罗,霍元甲,觉远!如果他愿意剃光头的话。高悬在人群头顶上的银幕,影影绰绰布满山岭与村庄的影子,子弹嗖嗖响,赵永生带着解放军攻进县城了!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赵小花不知道哥哥在哪里,一条街一条巷去找,走迷宫,怔怔地站在城市的废墟里,像清早晨刚睡醒的模样,邦胜知道呵,真是恨不得跑到电影里,帮小花指个路!“我的乖!看到她掉眼泪,我心都要碎了,唉!”邦胜叹气。
“将刀拿出来。”保明低声说。
邦胜转过头,小心翼翼地将刀子由帆布包里抽出来,一柄屠夫剔骨的尖刀,磨得雪亮,保明接过来的时候,寒光在空气中一闪,好像往夏天的夜里,印入了一道白霜。
“这是我爸爸用得最顺手的一把,上个月弄丢的时候,他心疼得要死,好几天都没喝谷酒。出门前我磨过,快。”邦胜说。
“总不是一把刀,能杀人就够了。”保明心里也是高兴的,但他嘴上却是淡淡的。
“程小琳会吓坏的。”
“我管不了她,她自找的。”
“刚开学时我确实看到她走进陈高的宿舍里,她坐在陈高的椅子上,点着台灯,直着腰,在桌子上假模假样写作业,一会儿找不到橡皮,一会儿又说钢笔没墨水。好不容易绵条下来,陈高站在椅背后面,伸手摸她的奶。你知道为了挡北风,陈高的窗子还是我俩替他砌的,左下边有一块砖是活动的,能够抽出来。”
“右手摸,就剁右手;左手摸,就剁左手!”
“我昨天确实看见陈高和她由中学里走出来,一人捏着一把三节电池的手电,到小澴河堤上的杉树林子里照麻雀。麻雀晚上在窝里,又呆又乖,软软暖暖地称手,一摸一个准。前几天月亮还没出土,天黑着呢,手电筒的两道光在河滩上缠着追来追去,河滩上种白萝卜,比开水瓶还大。他们真会玩!”
“我恨不得连这个婆娘也杀掉。”
“不行,你说你只给陈高来两下子的。”
“我知道。”保明将刀递还给邦胜,自己由怀里掏出棉梗钩子。
“你不用杀猪刀?”
“还是棉梗钩子好使!”
“用棉梗钩子,就像《少林寺》里秃鹰用铲子,能攻其不意!”
“一会儿你先不要帮我。如果陈高将我打死了,你就用杀猪刀给我报仇。”
“陈高不是你对手!”
保明说:“他找四平学过武的,会军体拳。”每天早上学生朝读时,陈高一个人在学校池塘边的草地上练武。一排杉树又粗又壮,喜鹊绕着它们飞,叫得比读书的学生们还有劲。保明与邦胜站在池塘对面的田埂上,假装钓鱼,偷偷看。“黑虎掏心”,陈高用拳头将草地边的楝树冲打得乱晃,楝树籽雨点一样往地上掉;“乌龙绞柱”,陈高躺在地下,可以靠双腿剪刀一般的旋转站起来;“鲤鱼打挺”,陈高躺在地上,腰上用力,双腿兔子踢老鹰似的,一送弹跳起来。保明回去偷偷练好了黑虎掏心和鲤鱼打挺,乌龙绞柱不会。邦胜鲤鱼打挺都不会,他用手将门口碗口粗的泡桐拍得啪啪作响,掉下几朵泡桐花,臭得冲鼻。邦胜说如果能每天打一百下,再过十年,就可以一拳将泡桐打成两段。十年!麻子哥,泡桐都长到水桶粗了,不,跟肖红霞的腰一样粗了!肖红霞正怀着你的第四个惜春丫头!
邦胜说:“陈高会乌龙绞柱也没用,你都能抱着稻场上的石磙走一个圈。”
保明不理邦胜,低头用左手抚弄着棉梗钩子。他家里一共有六把,扯棉梗的时候,父母与四个兄弟姐妹一起上阵,一人一把,一个星期下地,钩子就会被棉梗磨得锃亮。他这把是新的,前年由初中辍学,冬月匡埠的铁匠来塆上打铁,父亲让老匡给他用生铁打了一套农具,镰刀锄头都有。保明说:“生铁会锈!”老匡抽着父亲敬的游泳烟说:“有汗,就不锈。见了血,就飞快。”父亲讲,扯棉梗的时候,要腰上用力,力气通过脚往下走,再粗的棉梗也会被钩子扯着往上走。秋天,棉花根长深入了,地也变板结了,棉梗不好扯,一天下来,一手的血泡,腰也像断了一样。对,一会儿就应该将陈高的大胯当棉梗,钩子吃进肉,腰上用力,氣从胆边生,力由脚下起……保明一出神,食指被钩子的尖头划开了,他立起食指放到眼前看,已经有血珠渗出来了。好在是左手的手指,不会碍事,不管它。邦胜却很热心,替他将手指头含在嘴里,止住了血。
后来保明在哈尔滨的工地上刷墙,跟当地人争沙子,他们行蛮供黑龙江里捞上来的沙,贵,不划算。沙霸领着混混追打,保明挥舞的,还不是这把棉梗钩子?外地人哪里是地头蛇的对手,保明在医院里躺了好多天,头上手上打石膏缠绷带,好无聊,一个人去医院外的红豆花店给自己买花——其实他是喜欢看那个由湖南常德来的卖花的女人,薄嘴唇,尖尖的下巴,头发遮住半边脸,眼睛龙眼核似的。有一天保明盯着床头柜上粉色的康乃馨,想起邦胜,想起这个他帮他含着手指止血的晚上,是的,邦胜也在哈尔滨,那天晚上他们不怕死,一个用棉梗钩子,一个用杀猪刀,街头杀到街尾,街尾杀到街头,滴着血往前走,纵横四海上刀山,他们也没打赢,保明住院,邦胜则被打死装进了骨灰盒子。后来卖花的女人拿着花来看保明。保明说,他的确还在打光棍,只是已经答应邦胜,准备回老家和肖红霞搭伙过,替他养四个女孩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
是血,不是汗,将土地变成我们自己的。死了,埋了,也可以将土地变成我们自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银幕上终于吹响冲锋号,在桐柏山的密林里,到处是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发动总攻,中间不停地有人死掉,小花与翠姑湿淋淋地站在湖水里搭人桥,子弹像梭子鱼飞快地在水中游,接下来翠姑就会被子弹咬到,半生半死,血咕嘟咕嘟地将湖水都染红。
保明深深地吸气,好像要将星斗的光吸到丹田,丹田在脐下三寸,他知道的。
“绒花到底是么事花?李谷一又唱歌了,出字幕了,电影放完了!”邦胜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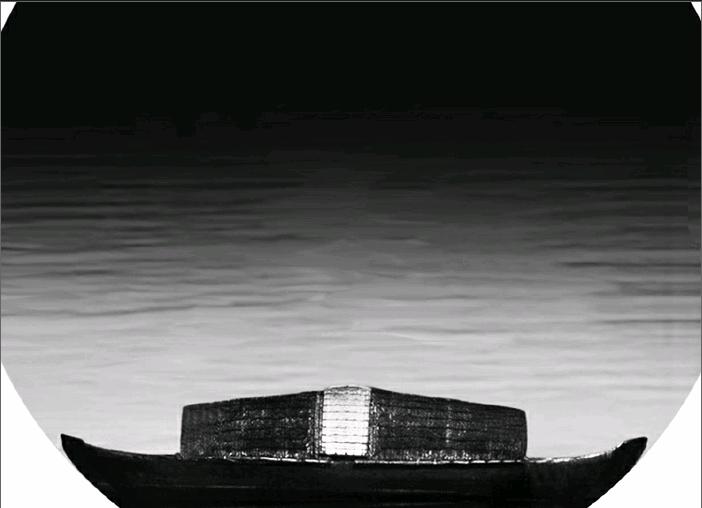
这时候电影散场了。就像搬家的蚂蚁,回埘的鸡鸭,像夜游神,人群沿着田埂向周围的村子走,肩上扛着高脚板凳,无精打采就像踩着棉花,小孩多半已经睡着,一动不动趴在父母怀里。邦胜喜欢看电影散场的样子,有一点像年过完了,放光鞭炮与烟花,熄了香烛,歇了锣鼓,村里的龙灯家伙也被收起来,年轻人心满意足,心也就空了。心一空,就要去找事做。
“他们肯定是走在最后面,这样好的月亮,他们说不定还要坐在棉花地里再聊一会儿,棉花长得高,谁都看不见,说不定,他们还要亲嘴,唉,赵永生都不敢亲何翠姑和赵小花,也是,主要是他搞不清楚,哪个是他干妹子,哪个是他亲妹子,瞎搞不得!”邦胜说。
保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做声。
“你说陈高比得上我吗?”保明问道。
“比不上。”邦胜说。这是他的心里话。附近几个村的小伙子,没有比得上保明的,保明壮得像牛牯不说,还义气得很,不像赵永生长得白,笋桩,婆婆妈妈,会搞思想教育,像唐僧转世投胎似的。
“但他是老师,会在黑板上写字,他戴眼镜,还会吹口琴,唱歌,还会打军体拳。”
“他不晓得荷花莲蓬藕,对了拳头巴掌手,还能对鸡巴卵子毛!”
“可是程小琳迷他那一套,娘们都喜欢小白脸,吃商品粮。”
“这不能怪你,要怪程小琳没有眼光,她是个虚荣的女人,她想到肖港镇上去过不种田的日子,陈高答应给她开一个理发店,墙上贴香港明星的画子,她就照着那些画子给人家剪头发。”
“我不会放过陈高的。”
“你再仔细想一想,现在还来得及。”
“不用再想了!”
“那你答应过我的,只用棉梗钩子戳他的屁股,让他一个暑假,都只能趴在宿舍的床上由程小琳糊溏鸡屎膏药,像赵永生那样养伤,再也不能去河边杉树林里照麻雀!”
也就是十来分钟的工夫,田野上的人群散得了无踪影,余下两根木杆支棱着幕布空悬。这块幕布讲过多少活色生香的故事,《少林寺》《武林志》《神秘的大佛》《地雷战》《芙蓉镇》,去过多少乡塆,舒家塆匡家埠蒋家台子魏家河梅家河,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稻茬的谷气、棉花的甜香、枫杨的苦涩与土壤蒸腾的肥腴混合在一起,还要加上收敛翅膀的蜻蜓、飞蚊、豆娘、灰蝶细细的鳞粉,隐密的甲虫们古怪的气色,遥远河塘里的鱼腥,每一个夏天的晚上,晚上不同的时辰,田野的气味闻起来,都会有不同吧。一轮弯弯的白月亮照着的世界,现在终于由电光声色中安静下来,竖起耳朵,几乎能听得见露水滴落在宽阔的棉花叶上的声音,听到棉铃虫轻轻地咬动着棉桃的声音。棉花开花变少,多半已经结成棉桃。棉桃嫩绿的时候,是可以掰开来吃的,像后来保明在一户装修人家,尝过的女主人递给的一颗山竹似的。棉桃长到碧绿,变硬了,就不能吃,再过半个月,最性急的棉桃就会爆出雪白的棉花,星星点点的,全村老少顶着毒日头,兜着包袱捡棉花的季节就到了。
那对青年男女,陈高与程小琳,果然落到了后面。女的将头倚靠在小伙子的肩头上。前面村口有一棵枫杨,又粗又壮,他们手拉手,恐怕都围不起来,像一把在月光里撑开的巨伞,翼形的翅果垂垂累累,子孙绵绵。“我们在树下坐一会儿吧。”小伙子看着姑娘的眼睛。姑娘脸圆圆的,眼睛像龙眼核似的,黑得真好看。
“不行,回家太晚了,狗会叫,我妈醒了,又会吵我的。”
“要不去棉花地里坐一小会儿,你喜欢闻棉花的香味。”
“不,我怕棉花里的蜜蜂蜇到鼻子。”
“哪有蜜蜂,晚上它们都回巢去了。”
“我还怕瓢虫爬进衣领子。”
小伙子只好闷声不响地接着向前走,走进枫杨树的阴影。这时候,姑娘看到,树下的棉田里,两道银白色的光闪现,好像西边天空里扯露水霍一般。
“什么鬼东西呀,好怕人。”
“没什么,田里的瓷瓦砾在反光。”
“过几天就是七月半了。”
“没事,要是遇到鬼,我就一脚踢花他的脸。”
“好吧,我答应你,就坐一小会儿……”
小伙子心满意得地搂着心上人的肩膀往前走,穿过村前的土路。半个多月没下雨,土路被晒出来一层浮灰,他们穿着塑料凉鞋的脚踏上去,觉得温热温热的。男人是白衬衣,女人是黄的连衣裙。他们的身影很快就化在棉田之上融融泄泄的月色里。
唉!
保明由棉林里爬起来,将棉梗钩子扔到地上,让邦胜将杀猪刀重新包起来。保明捂着脸,坐在棉花地边的田埂上,半天不说话。
“我刚才该推你一把的,人一紧张,就会发蒙,忘了本该做什么。”邦胜说。
“我的确是爬不起来,好像一只团鱼,被人家用脚踩住了壳子。我是不是遇到鬼了,鬼上身?鬼压床?鬼打墙?”保明又觉得这样解释,邦胜不会相信,可是,他为什么要给这个麻子兄弟解释呢?他刚才的确是爬不动,就像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
“你的确应该给陈高的屁股来一下子。你用棉梗钩子钩住他的屁股,一扯,他就会像娘们一样捂着伤口瘫在地上,看他还怎么乌龙绞柱,怎么鲤鱼打挺。程小琳这个婆娘就会在一边尖叫,就像被挨了一棍子的白鹅。”白白地守了一晚上,说好的觉远斗秃鹰呢?霍元甲痛打大力士呢?邦胜并不甘心。
“钩掉他的卵子才好呢!”保明用钩子划着田埂上的马鞭草。
“是不是魏家河的瞎子画的咒,还没有散干净?”邦胜说。
邦胜的爸爸外号叫洋人,上个月在这里杀过猪。保明家的黑皮老母猪,到殷家塆找公猪配种,回头过梅家桥的时候,在桥面的青石槽子里将脚别住,扑通掉进小澴河。下丝网的,弄鱼鹰的,去金神庙赶集的,河边放牛的,一群人七手八脚下了水,捞起来时,母猪后腿断了。打个夹板多麻烦,干脆将它杀了。夏天里猪肉金贵,母猪肉顾不上嫌弃,裹米粉,拌腐乳,灶膛上,多蒸几个柴火把子。村里的男人将它绑在枫杨上,洋人将刀都插进了它的脖子,它还是将拇指粗的麻绳扭散了,带着杀猪刀,喷着血沫子,一瘸一拐冲进棉田。棉田尽头,是密密麻麻,种满杉树的小澴河堤。这头母猪叫惠惠,养了七八年,是生了一百多个猪崽的“聚宝盆”,保明奶奶说太造业,莫杀,莫杀,保明的爸爸国庆不同意,一心要请洋人来一刀将它送进六道轮回。
四五个男人分头钻入棉田找了好久,也没逮到惠惠,它驮着洋人心爱的杀猪刀,消失在了棉花田里。保明奶奶说它这么半生半死,会变成妖怪,跑到小澴河里做猪婆龙,招呼它生的一百多个猪崽做跟班,这些猪崽多半过年的时候,都已经当年猪杀了。洋人与国庆,你们两个以后搭船要念佛,走水路要小心。国庆无所谓,准备明年开春,再捉一个母猪娃回来喂,还取名叫惠惠。
洋人却有一点怕,他的杀猪刀,还在人家母猪脖子上呢!他叫魏家河的瞎子魏林堂过来。林堂杀了一只公鸡,用鸡血在树干上画符,又烧了几个五丁五甲的纸马,一包黄裱纸,让洋人作了揖,才放他回家。瞎子自己拎着母鸡回家烧水烫毛开膛炖汤不提。第二天保明跟邦胜钻进棉花地,准备用钓鱼钩穿了棉蛉虫钓肖家坝钻棉田的鸡,来解被魏瞎子勾起的馋虫。
邦胜又担心,钓上来肖红霞家的鸡,被他未来的岳母骂。他岳母是肖家坝端着砧板剁菜刀骂街的头名状元,她在肖家坝骂谁偷了菜园里的南瓜,郑家河的婆娘们,都会竖起耳朵取经。而那偷瓜贼,已经全世界在找后悔药,去抢救沦陷在污言秽语中的显考显妣们。世上的事,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偏向虎山行,一定遇到虎,问君什么虎,一只母老虎。肖家坝的公鸡领着母鸡挨挨蹭蹭走入保明邦胜埋伏的棉花地,刚刚入巷,母老虎肖红霞就出现了。她正提着水桶给菜园里的萝卜菜浇水,大半桶水就淋在她乖乖的小女婿与日后做陪亲的好伴郎身上。“你们两个没长进的强徒!下次我用一桶粪泼你们!”这样一想,被水泼一身,还真是好运气。保明跟邦胜落荒而逃,邦胜在后,又被田埂上的马鞭草绊了一个跟头,他趴在地上,抬头就看见洋人的杀猪刀,像条死白鱼,平平躺在棉垄间,刀尖上的血已经干枯了,一片暗红色。邦胜将杀猪刀送给了保明。
保明在哈尔滨做粉刷有七八年,刷了多少墙?折成银幕,会有几万块吧?折成宾馆的白床单,会塞满由东北回湖北的火车?谁知道呢?接着是去武汉拖板车,去靠上码头的船上搬货,一天几身臭汗,将换来的钱打到肖红霞的卡上。他住在汉江边的平房里,推开后门就是汉江。平房掩映在一排白杨树下,白杨树又粗又长,树干纹路密集,疤眼团团,树冠落满乌鸦。程小琳也在武汉混日影,有时候会洒花露水来找他,三五个星期来一回,没得准,就是成公知琼会弦超的节奏。有一年中秋她跑来,带鸭蛋黄月饼给他吃,要他陪她去看电影。电影票好贵,电影的名字叫《寻龙诀》。他认出来,里面的一个女人就是何翠姑,老了,长得真叫人难过。看完电影回宿舍,他睡程小琳。程小琳说你跟你那个肥婆娘离婚,保明不吭声。程小琳说那个瓦窑,我还能给你生儿子,保明不吭气。好在四个姑娘长得像邦胜,聪明,念高中的念高中,上大学的上大学,是牡丹跟玫瑰,不是南瓜花丝瓜花,对得起她们的名字元迎探惜。名字是邦胜取的,他初中时读《红楼梦》,下学后,上册被肖红霞盖了腌鸭蛋的坛子,下册盖了腌菊芋的坛子。等到保明跟肖红霞结婚,将两册《红楼梦》合起来,硬着头皮读了一遍,就像打着手电走夜路,一脚高,一脚低,才明白当日为么事同学们都将程小琳叫“林妹妹”。肖红霞结的两次婚,第一回他去做伴郎,没淋到水,也没淋到粪,被肖家坝的女人抹了一臉锅灰,那个肖翠娥最起劲,像个做炭圆的。第二回,他是新郎了,像由银行取出来的一百块钱一样崭板,肖红霞却是旧的,也不开心,莫说提桶水,她哭,恨不得往她自己脸上抹锅灰。
睡到深更半夜起来,保明推开后门,去汉江边撒尿,鼻子里是他跟程小琳混合在一起的骚味。脚下露水答答,荒草离离,头顶上的天,被城市的灯光照着,星星点点,混混沌沌。风吹白杨,声音回环悲戚,偶尔有乌鸦由梦中惊醒,哇呀两声,也很凄凉。好在他已经不怕了,世上纵有鬼神,也没空撩他。纵有神佛,也无心保佑他。穿着裤衩浑身清凉,一身肌肉吹着西南风,他小时候学武,参军后又接着练,丹田鼓鼓的,力气用不完。他摸黑坐在江边抽一根“蓝楼”过瘾,再回床上继续睡。他将烟头往江里扔的时候,发现波光里,忽然哗啦跳起来一只江豚,黑亮亮的,总有一百来斤,跳起来一米多高,身子弓着,头脸盆大,看他一眼,“嗷嗷”叫两声,又扑通落到江水里。惠惠?小时候他提着猪食去喂惠惠跟它的孩子们,惠惠听到打开猪栏的声音,就会嗷嗷叫着,将头霸住猪槽,猪娃们左骖右骖,七星拱卫北斗似的,围着妈妈。他将热热的猪食往它头上淋,也不恼。他忽然想起奶奶讲的母猪惠惠变猪婆龙的事,那时候,奶奶已经死了二十年,她跳进村边的池塘里,将自己淹死了。或者是:奶奶?奶奶做了一辈子的接生婆,积下的阳寿其实是花不完,她也能变成猪婆龙的。他抽完“蓝楼”去睡觉,程小琳汗津津的,腻腻地哼一声,他没跟她讲看到江豚的事。因为一讲江豚,就会讲到惠惠,讲到枫杨,讲到那个看《小花》的晚上,讲到邦胜,讲到他们的棉梗钩子跟杀猪刀,棉梗钩子与杀猪刀卷在他的被褥里,硬硬的,还在的。
陈高去了哪里?白脸的小曹操,他摸程小琳梨子一般的奶子葡萄一般的奶头的学校,都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三层楼的砖瓦房还在,空洞的门窗像老婆婆漏风的瘪嘴。一楼的小黑板上,最后一期的黑板报,抄的《一剪梅》,“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风雪不能掩没”,在上面写字的癞痢孩子是谁?现在在哪里?保明还记程小琳站在他搬来的椅子上,翘着兰花指,捏着粉笔写字。程小琳要他画线打格子,他偷瞄她写字,结果他站的椅子被邦胜一推,两个人滚倒在地。邦胜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狗日的。他们站立过的椅子,写过作业的桌子送隔壁李家塆的人,当劈柴烧了吧,杉树被锯掉,装了五卡车,卖了六万块钱。这一排杉树,除了给学生读书,陈高学武做背景,保明还记得两件事,一是第一年入学,他跟邦胜两个人花了一早上时间,一棵一棵树找,折了最笔直最称手的一根新枝,用小刀削成教鞭,用砂纸打磨一个早自习,油光水滑,送给了陈高。那时候,陈高老师刚由师范学校毕业,十九岁,分配到他们初中教书,穿蓝夹克衫,领子后面有帽子。另外一件事,邦胜不知道的。保明站在塘陂上一边早读,一边将杉树塔果里含住的花粉磕出来,夹在英语课本里,到教室,再转到文具盒里,这样攒了一学期,才得到一包明黄细腻的花粉,他将花粉包在一张破天荒刚好及格的数学卷子里,一天趁着放学值日扫地,放进了程小琳的抽屉。
往事不堪回首,未来的事,谁又知道呢?用手电筒划开时间,两个乡下少年,一起穿越到2017,正在看华为手机的您身边?唉。掉回头,月亮哥,杉木船,裟椤树,做桅杆。裟椤树是沙树吗?做成的船,像担架?跳板?板车?猪槽?你们俩,保明和邦胜,用棉梗钩子与杀猪刀作桨吧,左一桨,右一桨,为了避免原地打转,保明的钩子使得快,邦胜的刀使得慢,顺着幽暗的时间之河上溯,载着一船星斗,回到那个棉田繁花的晚上。
邦胜还在跃跃欲试,想顺着干爽的棉垄,交替着手肘与膝盖,黄鼠狼似的爬三五百米,保明跟在后面,侦察员们就是这么干的。到前面去看陈高跟程小琳亲嘴?除了亲嘴,说不定,会有更好看的戏码上演?程小琳不会学翠姑,掉到水面将衣服弄湿,露出一身的线条吓死人,可陈高的手,不是吃素的呵。邦胜不怕害眼,他本来就火眼低。路上还印着她搽的花露水与痱子粉的香气。程小琳的奶子多结实,她的屁股怕比冬瓜还要粉白肥腻。这些陈高摸得出来,邦胜看得出来,保明想得出来。“要不,我们一起去学学陈高老师的手艺?你死了心吧,你搞不到她的,将她当亲妹妹,你就不会痛苦!”到底是将初中念完的邦胜,他会用“痛苦”这个词了。没拿到毕业证的保明,只想再抽一枝“游泳”烟。
保明不同意,他说:“你看你妹妹光屁股洗澡?邦胜你要去看的话,爬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我这个朋友,你抱着你的杀猪刀走人!”说完,保明站起来,提着钩子走到枫杨树下,他闻到树干与树根上,隐隐还有鸡血与猪血的腥气。远远的天上,夜空炯炯有神,云朵如同鲸鱼,由南游向北,月亮由白变红,北斗七星更亮了。他抬起左手,食指上的血早已经止住。他将食指重新放回嘴里,用力一咬,血立马流了出来。他扬起手指,让指头上涌出来的血一点一点地滴在枫杨的树干上,好像这十几滴童男的精血,就能将由魏瞎子树堂布下的“结界”破除掉似的。
“我决定了,我要去当兵,我要忘记程小琳这个女人。”他将他的新鲜人血跟惠惠陈旧的猪血混合按在树皮上,右手握紧钩子,在血印里刻了一个“林”字,回头对跟在他身后,提着杀猪刀的邦胜说,“肖红霞的屁股大,能生儿子,你娶她!”
“你寫错了,左边还有一个玉。”
“她做梦呢,林妹妹,草木的命,哪来的玉。”
责任编辑 楚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