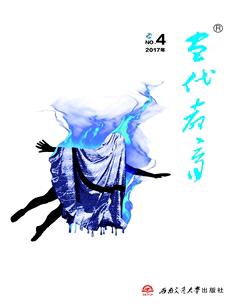“知识考古学”视野下“档案共同体”的建构
朱力
【摘 要】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多元性的建构性的档案观,拓宽了档案原有的疆域和边界,使得为不同群体所认同的“全景”档案,以及由档案的历史关系所形成的“档案场域”成为可能。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启发下,在“知识考古学”的支持下,本文大胆提出了“档案共同体”的界说;同时论述了其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相关策略及其意义;着重强调了“档案人”(档案工作者和利用档案的人)和档案制度在建构“档案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最后,提出了要规避“档案共同体”空心化。
【关键词】 “知识考古学”;“档案共同体”;互构性;记忆认同
档案是“记忆的碎片”吗?既是,又不是。这是由档案记忆客体——文件、案卷、全宗、档案馆——的层次性和互构性决定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致使不同时代、国家和地区的档案分布(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对象分布、存址分布),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地域或时空方面的特征,大体有规律可循。
但是,由于历朝历代、世界各国的档案浩如烟海,太过庞杂,既不便于整理,也不利于使用,出现了几家独大、各自为政的“档案帝国”局面。
随着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切和为之努力的方向。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信息资源,档案及档案工作无疑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既要内部盘活,又要敞开胸怀,走出“档案帝国”,建立“档案共和国”,加入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
安德森在他那本伟大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里论述道: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下,世界上一些弱小民族,随着古典王朝的衰落与瓦解、资本主义的潜滋暗长、现代传媒兴起与发展、“国家方言的发展”、乃至“宗教信仰领土化”,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开始产生,并流布开来。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既是一种意识、一种思想,也是一种主义,还是“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1]我在想,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档案,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关于档案的“想象的共同体”呢?
福柯说:“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系统”“是那些在陈述一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2]而在实践中,“陈述出现多样性”,但多样性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始终受到“书写权力”的规训和检查。“他要求突破线性和等级逻辑下的档案及其历史叙述,强调全景敞开权力,充分发掘和利用被传统和主流范式所遗弃和遮蔽了的非连续性、边缘性历史文化信息”。[3]其实,福柯的“反记忆”理论、“反博物馆”理论,是对传统和主流的记忆理论、博物馆理论的修改和补充。这里的“反”,不等于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讲求辩证的联系和发展。也就是说,福柯呼吁:注意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基层群体的记忆及其档案。这种“知识考古学”“反记忆”论、“反博物馆”论,为我们建构多元共生的“档案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我们把突破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官方和民间的、中心和边缘的、政治和日常的界限,让所有档案进行融通和互建,为不同群体所认同的“全景档案”,且拥有档案空间或档案关系网络的历史场域,称之为“档案共同体”。
“档案共同体”不但是文件库、案卷库、全宗库,而且还是记忆库、知识库。对它们的认同,应该是多方的认同:既需要“档案人”自我的认同,也需要档案从业者以外的人群的认同。认同与否,决定是否属于“档案共同体”。由此,“认同的重量”在“档案共同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档案共同体”,是“形成之物”,而非“先在之物”,既有可以是某一档案实体,如“天府”“皇史宬”,也可以指某一共同的档案观念的集合。根据档案记忆的层级性和互构性,我们可以把“档案共同体”区分为不同的层级和类别。比如,第一层级,从整体档案的角度,我们可以划分出主流的官方的“档案共同体”和边缘的民间的“档案共同体”;第二层级,从边缘的民间档案的角度,我们又可以细分出诸如犹太人大屠杀“档案共同体”和柬埔寨“赤柬暴行”的“档案共同体”,等等。
档案与档案馆原本在业内认同度就不高,在业外尤为如此。档案和档案馆不说是死水一潭,那也只是水死微澜。人们对档案和档案馆的认识比较冷漠,甚至偏误。同时,人们对于档案的利用率不高。虽然,档案馆的馆藏不计其数,但是却出现了“馆藏档案无人用,需求档案馆无藏”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此种矛盾?首先要做的是整合不同地域的档案资源。就中国当代文学档案而言,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大陆与台港澳一度处于隔绝时期,大陆与台港澳之间的档案也就处于分割状态,同时,大陆也与海外当代华文档案处于分离状态,使得大陆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大陆以外的当代汉语文学写作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记得,本世纪初,大陆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即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著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國当代文学史教程》,就因为两者均因资料不全而未涉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被有的专家开玩笑地分别改名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教程”。此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益外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都应该划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因此,要完成理想状态中的比较完备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完备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资料,而要有比较完备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资料,就必须对中国大陆文学史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史料、外国文学当代汉译资料、海外译介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等进行跨时空、跨政治、跨文化、跨语言的大整合,以便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共同体”,即中国当代文学的“档案共同体”。
形成了“史料共同体”“档案共同体”并未大功告成,还要对其进行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重藏轻用”。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樊骏说:“那些珍藏起来的图书文献,不管内容如何重要,数量如何庞大,保管如何妥善,只要不为人们所应用,与根本不存在没有多大区别,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了”[4]
从档案利用主体需要来看,“档案共同体”是不同利益主体怀旧的情感皈依处,乃至是他们所追求的信仰的依持。简而言之,对档案的情感需要,乃至对档案的崇拜,是形成“档案共同体”的感性基础。
档案的制度安排是构建“档案共同体”的制度保障。档案历来都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根本”“模法”。因此,历朝历代、各地各国均有各自的档案制度安排。单以中国历代档案制度为例,它演进的历史轨迹如下:“从商代的甲骨档案窖藏,西周王朝将档案‘登于天府‘藏于金匮‘置之宗庙,唐代‘三年一拣除的档案鉴定,宋代的‘置册分门编录,明代的黄册”,清代的大库分类目录,到今日中央和地方大大小小的档案馆、档案室的建立”[5]。正是这些档案制度的制订与推行,使得我们档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此间也出现了极大的波折。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的破四旧,都给我们档案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延缓了“档案共同体”的建立。
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利用者(下称“档案人”)是“档案共同体”建构的主体。他们在建构“档案共同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档案人”是“档案共同体”建构的“角色丛”,是它的建构者、控制者、守护者和传承者。这是由“档案人”的主观取舍以及“档案人”的中介性决定的。后者与“档案共同体”的建构性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就是在建构“档案共同体”的过程中,“档案人”要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大力编纂开发。历史上,统治者为了垄断记忆资源,对绝大部分的历史档案进行封禁,使历史真相处于晦暗未明状态;但是总有一些档案解密的勇士挺身而出,大胆向世人披露真相,比如轰动世界的“维基解密”,就有力地防止了世界霸权主义对档案妄图实施纳粹式的结构性遗忘。第二,努力从事科学研究。档案不是死的,也不是因为死了才成为档案。“档案人”要加强对档案的研究,使档案“黑箱”变成档案“白箱”,让档案存在的记忆出现天日,让“昔日重来”。第三,通过档案教育活动,促进档案事业。第四,依托重大活动对外宣传档案。第五,把档案作为作为国家记忆工程,乃至人类记忆工程,借助文化事业,扩大档案事业。第六,利用现代传媒,尤其是“融媒体”,把握“人人都是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契机,更便捷、更高效、更充实地建构“档案共同体”。
像上文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家樊骏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两点:第一点,对档案藏储而言,“保管不等于保密”,而且,保管不是密不示人,不能使档案幽灵化,而是要“铭记未来”;第二点,在现行的档案制度里,“以人为中心”和“以物为中心”,孰轻孰重?[6]值得我们再思。即使是以“以人为中心”,但也要尽可能地淡化档案监视和档案控制的组织化与管理化的色彩。毕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档案组织内部,在管理层面,档案是监视和控制个人行动与记忆的基本手段;在档案组织之外,也存在档案操控,这种操控是反向控制的有组织忘却,即官方强制和自我压抑。
“档案共同体”的建构有利有弊,利弊同在:一方面,它在操控、重组、强化、留存记忆;另一方面,它又在减缩记忆。总之,“档案共同体”,以有形凝聚无形,化有形为无形,有无共生,生生不息。
“档案共同体”的建构,廓清了以往人们对档案和档案馆的认识,纠正了人们对档案和档案馆错误的或者偏颇的认识,有利于弄清楚档案的整体分布和价值系统研究,也有利于对中国历史档案分布规律的揭示,还有利于对其信息资源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发掘。
此外,“档案共同体”的建构,提高了档案的社会认知度,加大了档案的显示度,扩大了档案的知名度,提高了档案的利用率,使得档案能够更好地着眼于世界和未来,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档案共同体”的建构是有难度和限度的。“档案共同体”建构的专业性(档案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我们不能奢望“人人都是档案人”。那是如帕蕾丝·伯克所希冀的宗教般的“对档案的崇拜”[7]的“档案乌托邦”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可以逐渐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档案共同体”。“‘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那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8]“档案共同体”,虽然是累积性的,但它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开放敞亮的;不是本质主义性的,而是建构主义性的。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档案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资源和资本。换言之,“档案共同体”是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具有社会再生产的巨大潜能。我们要警惕将“档案共同体”过度资本化、市场化,以便其出现断裂、破碎、失根、无力。我的“热情的思考”告诉我:決不能让“档案共同体”空心化。
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44.
[3]吴秀明.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J].文艺研究,2014(3):42.
[4]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91.
[5]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29.
[6]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98.
[7]转引自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3.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