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肖像(三) ???? ????
钟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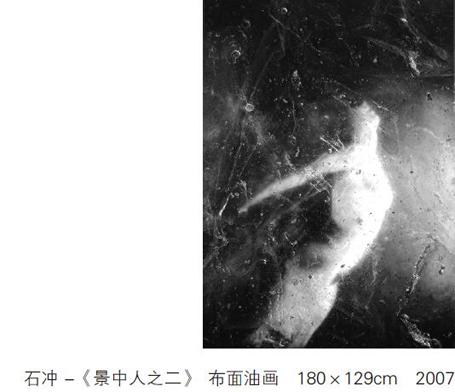
七
张枣君从德国来电,让我为他德文版诗集作篇短序,集子由那边的汉学家顾彬先生翻译,按情理,序该由他写才是,或许他生出小私心,要让我作个铺垫,热窝一下别人,想想有些话还可以说,也就此说说。
本世纪就要过去了,前不久,曾回头重读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有两件事是很令人感佩的:其一,作者在代序《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里所表现的“……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的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的勇气,看来今天是得了不少回应。那时中国正值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融会之际,文学上,也正好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演变期,语言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约定俗成的,何以那时特别地强调出来,回忆那时的各家宏论,怕未必说清过,各有各的理由,可以想见,古典精神和现代主义精神之碰撞和递嬗,对所有的人都很难。到现在,虽不敢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若一民族的文学演进,不光是期待语言外在结构的变化,也在乎内涵改变的话——但看天下皆白话文,翻译用语,技术时代一切的文化特征日益突出,比如表达造句,像本雅明说的,已和工人阶级的精神活动与生产相近,或许本来就没什么区别。随机的文艺,甚至像马戏团的猴子打情骂俏,泛滥到了人人可为的程度,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大众的数量,跟摄影相似,罗兰·巴特表现得十分乐观,他认为,让摄影走上正途,被视为艺术,其最好的办法就是索性任其大众化,通俗化,疯狂泛滥到不再显示其特色,不再有人视它和绯闻为特殊,而作为艺术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诗歌怕也是这样的,现在,就让它泛滥为好,三呼“老干体”万岁,也没关系。先驱者预见大众时代的到来没有错。
其二,《尝试集》中作者有首《梦与诗》,读来虽简单了些,但对今天中国诗人在自由表现和形式限制中获得张力,对流派各领风骚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勉励:“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或许,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在我纵观中国当代诗坛时,才发现张枣是那样一个重要的诗人(并非因为他已不在世了)。可以说,在保证汉语诗歌水准,不使其成为任何一种偏见或附庸这点上,他不愧是正宗的继承者,而在捍卫风格多元化这方面,他也是身体力行者。
首先,他多数的作品,是在现代汉语和德语(第二母语)相互交融的背景下生效的,他深得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因古典文学修养和开放的眼界而使“朦胧诗”以来的诗歌有了很新的样式,几乎可与德语之海涅相比——像勃兰兑斯在《海涅评传》中说的:“向抒情诗里引入人物性格的这种描写的天赋,是贝朗叶与海涅两个人共同之点。但贝朗叶是一个歌谣作者,而海涅是一个天才”——虽这点非由他最先开始;其次,他在方法和精神上兼容并蓄,和世上一切发展的事实少有隔膜,故使汉语在诗的表现力上异常丰富起来,以现代趣味和折中的精神,给了长久以来枯燥乏味的“朦胧诗”一种“休克疗法”,这是许多人盼望已久的事情,它终于发生了。
说来也怪,从他生活的地理位置上看(尤其自他八十年代移居德国后),他未必尽在诗歌主流之中,但他却尽得主流的要领,形式上,他也未必是激进的变革者,那种文白相间的化用,是很独到的,因他都回到了口语,用乡音给予修正,尽得南音变化的风趣,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恐怕也正是了解他的关键所在。
我不知道人们意识到了没有,长城很隐秘地构成了汉语双重的封闭性,从体积(质感)到精神:一种是累积的(比如虚假意识形态中的数字表现法),就像秦始皇麾下的民工,用最原始的方法筑城一样,于是也就不能排除用“磨洋工”来反叛这样的可能性,德语的卡夫卡对此似乎心领神会(指小說《中国长城建造时》);另一种是感伤,郁达夫似的“三底门塔尔”。感伤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言语,表情,一方面是更内在的损益,都会偏向缓慢的保守治疗和相反的激进革命,革命为什么会引起感伤呢,用拿破仑的话说,就是因为革命以过火开始,而以过火结束,而精神层面拖泥带水,却并无实质性的变化。这点,换个视角,恰恰又为另一位德语诗人歌德观察到。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指出,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中的“凝固人”其实就是指中国人:“在歌德看来,中国人并非一种已死而无形的集体,而是代表一种不能更加发展,而属于凝固了的形式”(《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言“丧失了挑战能力”,于此有无干系,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卡夫卡和歌德都未曾到过中国,却所知甚深。而如是观察更准确的德国人,还有黑格尔、马克斯·韦伯。黑格尔所言的吾民的“精神没有取得内在性”(《历史哲学》),韦伯说的“卡理斯玛”(Charisma指一种超凡、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人格品质)支配力,都和幻想性神话社会的关系紧密。
当然,张枣的幻想性气质,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它所要打破的固然是那种僵持凝固的状态,给予诗学的考虑,在美学和意识形态内,最重要的是触及某个范畴,——就我现在的理解力看,是历史意义的边界,他的“格物诗”,“修竹耳畔的神情,青翠叮咛的格物入门”,就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唤醒人们对各种旧王室(或党锢)或各个时代导致混乱的记忆,显然,在诗里,那种力量是耗散性的,人民、时代、仇恨、冲突和凌乱,最后的新秩序,都是先天性的,他想归纳出来,——或至少寻出部分更真实的线索。中国诗人自胡适起,也一直就想着要干这样的事情,只是时间不同,氛围不同,使命不同,最终是现实感不同而已。这正是汉语诗歌“言志”传统连续性的表现。这在胡适、郭沫若一代(二十年代),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三十年代),卞之琳、艾青、冯至一代(四十年代),黄翔、北岛、舒婷一代(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相当明显的。还有许多层面,未被发现。正是在这点上,张枣较之前驱者,似乎显得更轻松自由些,选择的可能性也更多,也更具包容性。包容性可以依赖懒无心肠,也可以是知仁爱人。要分辨这点,光凭语言还很难甄别。他诗句间蔓延的调侃戏谑的成分,也模糊了真实性。
记住了,任何诗人,我们都不该为其表面的氛围迷惑,没人了解,张枣许多诗里混杂的航空知识,均来自地摊上各种军事刊物。有时,浅薄涉猎是必要的。就像有人临时翻翻车工技术手册,便可以一目了然地谈顶针的生产运动。谁能说,航空技术在张枣诗中不管用呢。他最好的诗作《大地之歌》里开篇即飞来“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发动机的“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是什么呢,真的是双簧管吗?另外,你看见过一只鹤口衔说明文成了传真机的故障吗?当然没有,它只在刻意的荒诞和想象力里存在。
他的方法,用他早期的话说,就是你要把诗写得让别人认不出来。就像毕加索把一条吃过的鱼的骨头变作陶盘的花边。或像超现实主义那样,在酣然大睡的时候,门口却挂个牌子,上面写着:“诗人在工作。”
他的作品并不多,没有诸多诗人那种特有的寻找便宜“搞法”(作诗方法,或风格化),急速累积的现象,虽幻想,却辅以写实的能力,精神既现代甚至很现代,又古典,且世俗,哀而不伤,甚至还有不少游戏的成分,都融合在他的微妙之中,包括所摘的各种句子,通过歧义,分散开去,这些还是很容易察觉的。总之,他更聪明。
他虽身处漫长的历史或知识的“累积”(汉语里,或许可用“宿弊”和“阴疾”来讲)以及“缓慢”(他常用很快花出去的分币和重生的蛾子,也叫广殖,作为精神内化的速度对比)这样深层的文化结构,却借了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揶揄着,破坏着,或冲淡,以更见机智的口吻,反省两者,而又不失幽默的一面,以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故他并非无缘无故在《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这首诗前引了那位俄国诗人的句子,C est un chinois, ce sera long(这是一个中国人,会有点慢)。后面所谓的“灰烬即历史”固然过于悲观,但它螺旋形回到原处(俄国只是一个例子),确实令人迷惘而沮丧,因为我们的生命和精神,都无不是昂贵的消费品,一直是高蹈着的,拒绝重复,但它又不得不以社会或革命的形式交替循环,比如他的“蝶化”意识,可叙之为不能当真的某种拯救,相信不是,不相信也不是。此种冲突矛盾构成了他作品那种充满细节折磨而瞬息变化万千,犹如行云流水的风格,其浓淡程度,要视个人和社会在何种问题上进行摩擦而定,像前面提到的那首诗,像他早期的成名之作《镜中》《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和后来一些较重要的作品,《空白练习曲》《卡夫卡致菲丽丝》《云》《德国士兵曼斯基的死刑》《希尔多夫村的忧郁》等。把个人限定在社会的组合关系中观察,这不仅是现代意识的一种必要,而也因为中国诗歌传统封闭而自大的表现十分欠缺这个。“俄罗斯完蛋了——黑白时代底片”,然后,又是“巴黎也完蛋了”,接着是“人,完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发生在巴黎的法国大革命曾有着适得其反的表现,给人自由,最后却变成了对自由可怕的摧殘,至于现代的人,却是在技术上重蹈覆辙的,羁绊无处不有,人无时不落入陷阱,故无论何种形态,都有重塑的必要,这正是张枣在诗里大量运用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原因,因为他有了历史这样的调节阀。
他生前很少被收入诗集的《刺客之歌》,就曾指涉过这种个人和历史的冲突以及历史本身的矛盾:“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而矛和盾这样的古兵器,在汉语里却一直是哲学术语,也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偶然,必然,循环等,都是史学的老问题和难题,但把它缩微到诗的经验中,便有了许多对应的坐标,以观察人个别存在的微妙和尴尬,而就此成为作品的主题,这是他和许多诗人的不同之处。比如在《哀歌》中,他就描述过那种交流的失语症。他寻求知音,寻找对话者,而同时,他对现实中的谦逊、睿智,又视而不见,恍若喧嚣中的孤独,书籍里已成为历史记忆的英雄品质,要安全得多。他的对话者,其实,也就是人人企盼而又无法践约的对象,故对话始终是他表述的主要方式之一。所谓的“对话”,在其作品中,有着感情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并由此导向内心的企图,但,他没有很大的作品来完成这点。在其他诗人热衷于语言游戏时,他既没有偷懒玩对称法,大排比,也没有对中国之现实简约而化之,更不去直接作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做时间的探访者,尤其是在这样复杂的小丑叠罗汉似的历史语境中:
照镜,革命的童仆从原路返回;
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
这首诗有许多交织的层次,玛琳娜赴法国、布拉格寻夫,然后重返革命后的俄国,导致悲惨结局的原型,叠加作者的海外流寓,因了苏俄革命的复调,遂生出政治逸民的空幻。诗中提供的许多细节是俄语的。我们这代,家庭里怕多少都有一个舌头曾反复练习弹音学俄语的。作者想寻找的不是发音,而是骨肉可以摩擦的现实感,为了获得这种感受,他落在了各种器皿上,持有某种观念,也未必在形而上,但溶解到形而下的器上是一定的,这是他的秘诀。就这首诗而言,他不得不旁敲侧击历史进程一类的观念。但这些,是历史学家E. H.卡尔和以赛亚·伯林这样的漂泊者咀嚼已久的话题。历史的真实性,固然像塞涅卡形容的命运女神,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那些不愿意的,但,那绝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像克利奥佩特拉的鼻子,成为一道难题。
张枣作诗不大爱记日期,所以,没人确切知道,其具体琢磨的过程和时间,最后看到的都是成品,给人没有败笔的感觉。胡适先生晚年和秘书的谈话(《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曾涉及过文章落日期的琐事。先由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的话题引起,他认为陶氏书是绝大的荒谬,没啥价值(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古今刀剑录》是由他开始撰的),但一千多年前,便知道记年记月日的重要,颇有价值。然后,又转向《章实斋年谱》,先生作的序文,引有别人的话:“……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考证”。接着又说自己:“我的文章,无论写张便条,也都有年月的……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功,给后人省多少事!”秘书胡颂平由此提到《歌德谈话录》里也记有“每篇诗注明时日的利益”条。歌德对温克尔曼说:
……“每篇诗都得注明写作的时日,”你心里想,“这种事情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诧异地看着他。他又加上说:“那么诗就成为你的境遇的日记;所以绝不是无谓的事情。我每年这样做,很知道这是非常有益的。”
在我为他写了“序言”后不久,德文版诗集是出来了,之前,张枣用传真机给我传过翻译者顾彬的序言,日期是1999年7月1日,德国时间下午4点零6分。传真件上自动标有日期。那段时间,他喜欢电传诗稿给我,但这本诗集他却从未送过我,想必是德文的,拿了无用,特拉克尔的德文诗集,他却送过我,想来,还是因“序言”的事。他也从未提及,即便后来见面,也不谈此事。显然,那本诗集不会有我的“序言”。读顾先生的文字,心里倒是明白,他是读过的。而且,我坚信,汉学家也未必真的读懂汉语写的诗。
八
我早期随笔中有篇叫《方块的介入》,想通过建筑学观念稽考官僚政治制度下诗的思维方式,自然涉及到罗马的维特鲁威(Vitruvius),实际上,这边与他同样伟大的建筑设计师是鲧和禹父子,成熟的城郭、宫室,由他们开始,《世本》有载。而我认为,更具体画方块的则是垂,他发明了规和矩,专事方圆形的绘制,经常使用的人才会发明这等工具,遂又孳乳文字的○□匚(后者被训释讹以为“报”),国家之“國”、井田之“田”即由此生。说方块规限城市乃至人的语言行为至呆板,没什么不对,只是转换论述详细起来,十分困难,因为方圆都是流动变化的,像城市一样,甚至面目全非,所以,现代主义之父波德莱尔说:“老巴黎不复存在(城市的模样,唉,比凡人的心变得还要迅疾)!”达芬奇著名的人体画,也窥其流线型奥妙,遂称作《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建筑师要设计规划,住在里边的人也要规划,打小算盘,按维特鲁威设计的首要概念即“工艺”和“推理”,说到推理,便又涉了价值和机遇(有次,我把这个词嵌入写海子的文章中,似乎犯了众怒,而竟没人听明白,我说的啥意思),遂冲突难免。
所以,任何城市都作用于官僚行政管理和市民冲突的两种引力,以便形成其魅力无穷的反环境:建设和破坏,规划和反规划。想想,如果地球没有引力,量子力学,概率,零点法……我们会站在哪里胡思乱想呢?
关于冲突和反环境,叙述最生动的便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那段(注意法国大革命的背景):“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时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关于上海,关于城市,历史的记忆是元代立县(1292年),打败仗后的开埠、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渔盐、青浦、黄浦、吴淞、外滩、洋泾浜、豫园、外白渡桥……而伴随这些场景变化的则是一场一场的革命、密谋、拒俄、反清、孤岛、驱蒋……无尽其数,一代一代的大亨,遗老,或一个又一个俟圣人而不惑的人物。最早行秘史党锢的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學,叫东文学社,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旦成为大众人,剪了辫子,便离不开那里的气氛,那里的建筑,他们甚至不知道一幢房子会使他们有怎样的转变。
与愚忘年交的紫葛先生在时(已故《心香泪酒祭吴宓》作者),听他讲过宋氏姊妹的故事,她们曾青睐沪地一位希腊船长的别墅。蒋公兵败,美龄去台前,知庆龄恨蒋该死(儿时语),不会去台,遂特地购下此房遗给了她。上海是个大名利场,东方、西方的名媛、革命家、文人雅士、间谍武弁,都喜欢来这里过一水。龚自珍、辜鸿铭、康有为、章太炎、胡展堂、胡适、吴宓共慕的杜威、罗素……都晃荡过,即便瞿秋白,也曾在阁子楼里改变着观念。
他的《赤都心史》,大学时我曾读过,所以知道,他是共产党里唯一见着列宁的人。列宁的普罗党和转移语境的Marx能比沙俄更好地给我们一个中国吗?按理说,他的地位应很高,都轮不到那些人。而你也很难想象,他最后的死,是因为他在福建逃跑时丢了眼镜。如果配的是上海眼镜行的,怕还继续活着,问题是他会改变历史的偶然性吗?他那引了颇多猜测的《多余的话》,据说是被篡改过的,便难知真相,但,里面谈及的文人那一段,怕是用不着改的。他称“文人”是高等游民,称蒋公黄埔军校培养的铁杆哥们是“黄埔少年”,至于诗人,——国难当头,大概是猫咪诗人(原文是“猫样的诗人”)。他们自然要写英雄,“不过,美人在英雄的怀里,马却是英雄的坐骑,它的死所是战场,不是红绡帐里。”但,十里洋场并非这样。
城市,一部分看得见,一部分则看不见。难怪卡尔维诺叹道:“宽宏的忽必烈啊,我怎么样描述齐拉,那座高垒环峙之城,都徒劳无功。”(《看不见的城市》)因为,组成城市的不光是台阶、街道和拱廊,还有空间的量度和过去时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等等,故有新闻、出版、文学、相馆、茶肆、妓院、会馆、南社雅集一类。文学的体积之于建筑体积,无法等量齐观,故也负荷最重,青年急不可待要荡涤一切老的,而也有思想比青年还激进的老先锋(林玉堂语),却嗤之以鼻,所以生活其间的人,需要鲁迅的杂文,张爱玲的小说,也需要林语堂的“平民政治的真诠”和郁达夫的狎妓和钱塘,“新思想旧道德”,泛滥沪地下来,正是语堂所观察到的一种语境:“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海描写黑幕捧场妓女的文豪,同时又有如雨后春笋的新文学家正在诉述他们震动的心弦及幻灭的悲哀”。对造成这一切西洋机器文明的享用或宿怨,和吾民政治风俗的腐败与改易,混淆下来,便一直是现代诗的纠葛所在。看穿了,也就是语言的“反环境”所在。
倘若“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是成立的,那么,陈先生的诗,就是最地道的上海诗,其别名,即“都市主义”。没有人能在内心长期忍受那种不安的徘徊与冲突,遂又不得不导致变换角度的观察,对扭曲变形的城市建筑及立面。维特鲁威于建筑规划叙之“工艺”和“推理”,我们不能不说这恰好也是现代诗学的。陈东东的“宇航诗”,包括“月全食”一类,便是此语境作用的后效。他的一切作品,都带有报刊工艺和侦探推理的特征,精细至砖头瓦当,闸口的自行车和“花边消”,恢弘至宇航员。诗人一下跃入太空舱,可以想见,那地面的压力有多大。
宇航员驰往未来之前。他回顾的那颗
蔚蓝色行星,被昼夜、国度和
经纬线划分——迷信和反迷信
犹如奇异的物质和反物质,是世界观对称的
两个方向……
反物质若换作“暗物质”呢,会不会更精彩?汉语的阅读,要么是概括、超越性的,要么是慢条斯理性情的,叽叽咕咕,啰里啰嗦,器具相互摩挲,简单说,即才子佳人,或英雄才女。英雄,自然容易入彀中,皇帝老儿的,小人的,才女细人以姑息,易新鲜,也易断肠。怕鲁迅和张爱玲正好代表了都市主义的两端,都是憎爱阶层分明的——抑或即胡兰成所谓“破坏佳话”的,结局便都未必好。一个字改变街区不无道理,比如,煤,换作石炭,城市换作国际大都会,再如“月季票”从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到现在,已成“月票”,《沉香屑》所议上海之中国,在洋人眼中显得荒诞、精巧、滑稽,至今怕未必改过,精巧也是朽烂的。爱玲有篇极短的小说叫《中国的日夜》,怕是她写得最快的一篇,因她是在菜市场听来的,这是法国大革命陈仓暗度养成的一种语言习惯,散发出的噱头,“菜市场”语,革命的,密谋的,清高哦哟的,大众咿呀的,再配了无线电娓娓的时代曲调,大家都争相利用,民俗都有动人的一面,所以,爱玲说:“我真喜欢听,耳朵如鱼得水”。但凡这种引车卖浆街头巷尾有其语不一定有其事的谚语,若“屁股里吃人参”一类,怕诗比小说捕捉得更快些,于是,爱玲这篇小说里竟藏了自己作的白话诗,由那菜市语,想到了中国:“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的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就概括性而言,诗歌的确比小说还要精微、抽象和换位,故更有理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现在,陈东东的诗已据其中。
他并非无缘无故在那首最为优美的短诗《插曲》前面,引用华莱斯·史蒂文斯“本地的抽象”这一句,因为他的作品,也一直都有着人文地理诗意性的尝试,描叙这座城市和周围的一切。他气质偏弱,遭了新旧上海的双重挤压,故不能像爱玲那么沾有富贵气,也莫如鲁迅,还能直接地针砭时弊,在文人的讥诋中还嘴,弄得自己也常灰头鼠脸,毕竟,鲁迅每日尚有两尾小黄鱼补一补,更莫说巴尔扎克,或本雅明之于他们的巴黎,那需要几万杯咖啡和叠若高山的书籍材料。诗歌有诗歌之道,显然,抽象是通向城市看不见的那部分最为有效的桥梁之一,就像一个弱者在向强者挑战时,肯定据有自己的无影剑。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面对他的“驼背小人”。驼背小人,也就是“小矮人”,蒲松龄小说称之“耳人”,他因人而异,栖居在我们最爱使用的器官中,——或者说,依赖于我们的某种习惯,也就是我们的影子,影子即我们的反环境,需要时,便不请自来。我有首诗就是叙此的:
蹦呀蹦呀,小矮人,
耳朵触耳朵,你
听见什么,细叶梨么,
还是吼闹的鱼?
……
小矮人不怕枭首,
小矮人没有头
抽象实际上是一种方法,就像本雅明形容的“接種疫苗”,在一个接一个的城市中,把过往深刻的经验(尤其个人传记性质的)要转换为“经验画面”。今日爱说“图像”。我们不能忍受太过具体的东西长久的折磨,所以,就必须看紧我们每个人平日臆造娇惯的“驼背小人”。弗洛伊德也谈到过他,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洞穴地下室与之搏斗的也是他。按本雅明的说法,这个小矮人,会盯着你看,凡被他盯着看的人,就会心不在焉,困惑,蛮像上海旧话说的“仙人跳”。当然,性质有些不同。
国民党时期的便衣和后现代之契卡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就易容技术而言,所以,诗人尤其要提防小矮人蹑踪而至,锒铛入狱,或更有效的方法是反过来巧妙地与他们周旋、游戏,讬言迂回、象征、隐匿,甚至写实或以写实之名……东东似乎更擅长折射,也就是镜像,变换场所,毕加索、福楼拜、怀特海也用过此法,颇为有效的世界的经验必须和我们的现实重叠在一起。东东的折射,和上海的地理有关,濒东海,临长江,界杭州湾,湖泊、岛屿、水路、鱼米之乡,无不曲折蜿蜒,古塔庙宇,无不含沙射影,最后,都仿佛集中在外滩为高楼所障,为现代文明所障,为无线电所障,而同时,也为高楼和都市主义的眼光所释放,因为大海,也因为烟云(淞南古时就有“云间”之称),固然,也因为意识,这些都是他作品离不开的,不光作为词,而也作为间离效果所必依赖的属性和量度。
在云海之间,在玻璃和钢架的投射之间,各种奇幻大楼,一切关系都是投影折射关系,一种本能而偏冷的关系,也是遗忘和记忆的关系。他早期有诗表达过这点:“我的眼里,我的指缝中/食盐在闪闪发亮/而脑海深处的那一段记忆/这时被镶上绿边……当云层终于断裂/鱼群被引向临海的塔楼/华灯会突然燃遍所有的枝头/照耀你的和我的语言。”(《语言》)东东的作品,在给它加温,因为流年,记忆,放逐,也因为少年就投放其中的爱,而爱却被城市看得见的、慢慢老化的那一部分苛责,甚至切割,淡化,分解,粉碎,最后幽禁在令人不得不发狂的筒子楼里。这是城市给自己施加的不透明的侮辱,因为它在实际的湮废变化中拒绝变化。
如是一来,就必然会循环产生一套被压制(贬低)的知识(米歇尔·福柯语),说异化的意识也行,但,狭义的意识形态远远落伍不能概其全。陆忆敏的《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王寅的《说多了就是威胁》《斧子来了》《悲伤太多了》《羔羊》,陈东东的《偶然说起》《垂暮之年》等等,都是这类典型。抽象说来,城市对于使用它的人来说,表现为一种磨损关系,而这也是物质的一种递进方式。尤其现在,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点,像时装,口语,建筑,支付手段,空间密度,空气,水源,汽车,性感化,微信之自恋与误读。我在最早描述东东生活与写作的那篇《走廊》里,就曾描述过这种磨损关系,而这本身,就来源于东东早期诗作对城市的感受。
所以,某种程度上可看出,东东一开始,就准确地为都市主义诗歌的表达找到了栖身之地,他只改变方位,汉语叙之六合。这点,他是对的。当然会非常吃力,正像他在《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里描述的人和建筑的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即便换作里尔克,也一样会给搞得灰头鼠脸。他的冲突,困惑,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倒也不是完全围绕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像希腊诗人说的“条条街道和人间的市场,尽是宙斯”(阿拉托斯《天象》),而是封闭和敞开这样的问题。剩下的,则是工艺流程和衍生思想。介入和反介入,敞开和封闭,恰好是城市和建筑磨损表现的两个方面,只要它们是可以感知的材料,就一定是互动、矛盾而辩证的,在诗里,它依附于某种隐秘的时间和地点关系,也就表现出踟蹰性来。而这样一来,时间地点的更迭、盘桓或上升,也就必然成为东东的诗歌主题,或引力。就像T.S.艾略特读过赫拉克利特,或琉善,就不能不在时间地点上穿梭。
在上海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即日本人在那修了幢高楼,有称“军刀楼”,涉风水案,东亚旧时的战争又浮现出来,于是,便又有一幢楼必须超过它。此种“体魄摩擦”,其实,并“不知道比喻的吊诡”,比如,史蒂文斯就会问:猪猡拖了鼻子在河岸淫荡起来会不会就是大象呢?
的确河流探着鼻走像猪猡,
拖拉着堤岸……并且
重载着雷霆的噼里啪啦,
他慵懒,无聊日子的时光,
因堤岸里的这番探鼻而奇形怪状,
这场困睡与噼里啪啦,
它们似乎在用他无聊的存在哺育自己,
如同猪猡似的河流哺育自己
当它们朝着海走向入海口。
(东飚译《青蛙吃蝴蝶。蛇吃青蛙。猪吃蛇。人吃猪》)
幸好东东,1986年就开始培养其精神超越性的“宇航员”了,他先是荷马地理学意义的,也就是面积意义的,目标是希腊罗马。但,所有的历史学、希腊罗马文化学都指出,希腊和罗马的灭亡,是被耗竭掉的,也包括了它们的征服者,所以,俯瞰废墟的最佳位置,不是单一的物质问题。这点,不同时代的诗人,完全可以就地取材。歌德在漫游雅典城堡时就提到了“神殿入口”和“向上的教养”,这又关乎镜像的主题。东东吃过大苦头后,写了《解禁书》,也接近那样的意识:“宇航员驰往未来晦暗……宇航员见过的,厌倦的神。”文字层面有些零碎,但看得出来,他的目光开始转向信念一类。但,大众人的语境淹没一切,也令人担忧,因我们每个人,无论才华如何,内心的困惑,苦头,诗的可交流性,多半都与他们相关,包括无数诗人那种启蒙的意识,要么遭遇强大的无神论,要么就是万物有灵,或汉学家所言的“胡作非为”,——几近于迷信,还缺乏常识。
陈先生的诗,一直有个现象困惑我,就像陆忆敏的风格过去困惑我们一样,显然,关于她,张枣持不同看法。至于陈先生,很奇怪的是,就诗与沪地——中国之门户而言(美国总统、印度小厮都在那显身),几乎是它无数个对立面身心俱焚的剪贴簿,是它的日志,踏脚板,记录之细致,恐怕比海关文件还要清秀繁密,就现已有文本,重要性已逾任何沪地诗家,这是没说的。但,我们几乎见不到关于他很专业的讨论,偶读年青一代评论,也是自说自个的“陈先生”,或顾左右而言其它,或我孤陋寡闻吧。
陈先生的身量不大,也不善言辞,早期,识他后,我感觉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易受伤害的江南乡下的冬烘先生对待,越国之逸民,深怕言重,故都护着,索性说顺口溜话。怕恶棍要谗陷、吃他,也未必下得了口,其实是我们异想天开。毕竟“五·四”时期的警察,请乱撒传单的陈独秀到局子里去,也是不捆而做手势真请的,且称“先生”,而“刮民党”(我代儿时语)时期的便衣和后现代之KGB又不能相提并论。反观文字,则知他是可以苛责宏论的,没想象那么弱。何况,只要他敢拿都市作背景,多少尝过语言反环境的滋味,便不能不感知强大的对立面,反馈技术,“新上海人”的铜臭,老上海人的逼仄,异乡人的漂流属性……他用诗的工艺,对抗城市的膨胀和反规划之不规则,用他的推理——可惜就理性的分析性弱了些(这是现代诗的根本),既訾议又消遣物质的异化,由古代残篇断简掏点如东瀛密色般的琉璃珠,对抗银行机器比诗还要抽象的数字和东亚的光彩工程:“小贩们渡过腐烂的河/而银行的华灯照亮的屋檐下……”。幸好他飞起来的鸟,是宇航员,而非其它。
这些都不能不让我想到,对城市报以最悲观描述的乔伊斯。陈先生恰好在叙及宇航经验时,提到了尤利西斯。乔伊斯打1904年第一次离开都柏林,约1912年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在他流寓的二十多年中,描写的全是关于都柏林的。都柏林就是他的反环境。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天都柏林被毁灭了,它可以从我的作品得以重建。”显然,这是针对其《尤利西斯》这部荷马史诗般的都市小说来的。在他离开时,它就塞满了马拉的出租车、煤气灯、英国大兵,和50万人口的正人君子与势利小人。于欧洲,最大和最小的比喻都是它。至此,或我可以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可能未来,一旦沪地景观社会需摭拾自身的回忆时,犹如我们现在去翻乾隆年上海报关的钟声和船只,怕也只有到陈先生的诗里去寻了。
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诗歌的宇航员,爆烟花上去往下看时,光学仪器是否精当,数字化语言能否转化为地面可接收的经验,道理很简单,陈先生的诗,现在,物化的质感是够了,精致得不能再精致了,回到开篇所言的工艺性,而概括呢?——推理呢?推理之结论,或半结论呢?什么工具能保证我们观察的精度,透过云层寻觅地面的界线,需要多大倍数的放大镜呢?陈先生的诗是内向的,一切的问题、矛盾、冲突,现实感——瞎子荷马的也好,曼杰尔斯塔姆的也罷,伪古典也好,真现代也罢,问题就在于,全抹进诗歌含蓄修辞的砖缝里,连个恶霸、坏人,水墨里的豆人,甚至一只现实主义以上的蝙蝠都看不到,上海的这一切,就真的是自然主义解释得通的吗?
所以,德勒兹最后才发现,文学的秘诀,不是其它,就是寻找边界线和未区分的领域。重新分类。陈先生的都柏林和乔伊斯的雄心恒业,我们是看到了,宇航或许是侦察范畴,但,分类,则必须在现实的经验中。这是,许多同行,或评价,摸到陈先生的诗,固觉其妙,却不知如何说清。可能溯其原委,在文学,尤其非曲折语的汉语诗歌的建筑立面,有时,略粗犷有缺陷的轮廓,比美丽的无可挑剔更有力量。歌德何以如此久的时间,消磨在罗马废墟,徘徊不去?拜伦、雪莱何以把废墟置于他们个人哲学和诗艺的中心,后者的《普罗米修斯获释记》,就是由罗马浴场蜿蜒的废墟形成。倘若我们看不见废墟,——上海?那是因为我们内心绝不是废墟。读读居伊·德波便知,尤其诗人,不能成为景观社会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现实,则正安排着这壮丽的景观,将一切的冲突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