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 ???? ????
哥舒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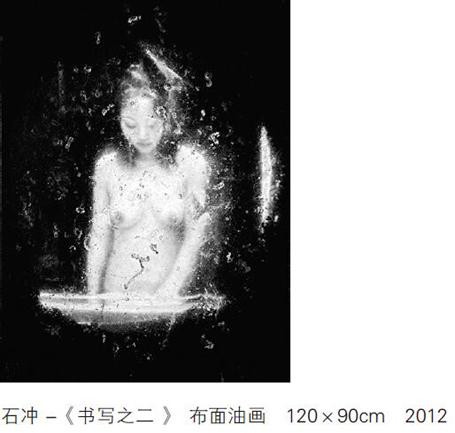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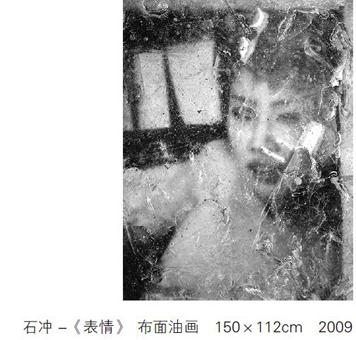
我背着行李走在泪街上,在车站看见了一位姑娘,好像在等去向别处的公共汽车。她不知道这个公交车站早已经废弃了,再没有任何公交线路通过这里。这个姑娘穿着裙子坐在栏杆上晃啊晃的,露出了苗条的腿,过了会儿她瞄向长街的另一端,瞧见了我,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问。
“你好,请问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泪街,以前这个站是泪街车站。”我说。
她转过脸去看站牌,秀气的脖子戴着一根银色的项链,吊坠是一颗透明的星星。
“以前?”
“站牌早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车站已经不存在了。”我说,“整条公交线路都取消了。你是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是不小心掉到这里来的。”她偏头想了想,“你刚才说这里是泪街?哪个泪?”
“泪街。”我说,“眼泪的泪。”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整条街就像一条泪痕。大家都说泪街就好像是石城流下了眼泪。”
“石城?”
“这个地方叫石城,开采矿石的城市。”我耐心解释。
她又眺望了一下街道,点了点头,貌似理解了我的话。
“石城是吗?”她顿了顿,小声问,“那么,这里是地球吗?”
我看了看她,她也在看我。对视了一会儿后,她脸红了起来。我背起背包,往石城的城区走去。她跳下栏杆,跟在了我的后面。
“你是本地人吗?”
“算是吧,我小时候住在这个城市。”我说。
“那你可以带我看看这里吗?”她说,“我刚来这边,还不太熟悉……”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她大概只是个旅行者,故意来偏僻的已经荒废的地方旅行。她的样子挺好看的,好看得有点不合时宜,仿佛是脏乱背景里出现的花朵。我很担心她会被这个城市吞没,尽管石城已经废弃了很久,我也刚回到这里。
我们沿着泪街往东走,走出街口基本就是石城的城中区了。不过就算站在城中区的中心街道往四面看,也看不到什么人影,这里尽管是石城的中心地带,可是仍然看不出繁华的景象,一副城乡接合部的样子。灰扑扑的街道,到处是灰尘的地面,不超过五层楼的建筑,水泥墙都裂开了,露出了里面红色的砖头。贴了瓷砖的楼面,马赛克都掉了,像被机枪扫过的枪眼。
“这里好像那些生命绝迹的行星。”旅行者姑娘说,“我在来的路上经过那些地方,我还以为这是座大城市呢,石城是吧?以前这地方也是这样?”
“以前这里不是这样,起码我小时候不是这样。”我说,“二十多年前,石城是北方一座还算热闹的小城市,荒废是后来的事。你看见那个操场了吗?这就是石城的中心广场。”
我和她正好走到了中心广场,操场现在也没了当初的气派模样,只余留了空旷的形式。煤渣铺就的环形跑道上杂草丛生,中间方形的足球场彻底变成了狗尾巴草的海洋,只有主席台还保留了一丝威严。外围的铁栏杆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和姑娘随便找了个缺口,走到了跑道上。她低头,无聊地用鞋尖踢一块大煤渣。她这样让我感觉怪亲切的。小时候我也这么干,把白球鞋前面都踢脏了,家里人骂我费鞋,跟小混混没两样。
“这里的跑道让我想起了土星的光环。”她说,“不过这个操场是干什么的呢?做广播体操用的?”
她居然也知道广播体操。
“开运动会就用这里,不过用处最大的还是公审大会。一旦开公审大会,不但操场上,连围栏外面都站满了人,有的孩子还爬到树上。看见那个主席台了吗,有点像天安门城楼吧?”
“没见过天安门。”她摇了摇头,“外太空最多能看见长城。”
“城楼下站着一排犯人,法官就站在主席台,用高音喇叭宣读犯人的罪行和审判结果。当然通常是死刑,枪决,立即执行。犯人们脖子上挂着涂了大红叉的牌子,低垂着脑袋,从卡车上被武警押下来,然后又押上去。卡车开上人民东路,再开上人民西路,然后是人民南路和人民北路,绕市中心一圈以后,从泪街开出石城,在城外的矿场执行枪决。”
“判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年轻人,有的是小混混,有的是大混混,也有贪污犯和杀人犯什么的。有一个年輕的小混混,因为羡慕别人有自行车,就去学校里偷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结果当场被抓住了,很快被判了死刑。枪毙的子弹是需要花钱买的,五分钱一发,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价格。”
她打了个寒颤。
“我不想听这些。我感觉很不好。”
我还以为她想听这些,旅游的人不都是想听这些吗?当地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典故。不过我说的只是我的记忆。那个记忆中的石城,有很多人的,很多年轻人的,很多年轻小混混的地方。
“接下去,你想去哪里?”
“我有点走累了,”她说,“能找个地方坐一下么?”
但我也不知道哪里能休息一下,我好久没回来了,这里现在都没人了。中心广场对面本来是石城中学,是这里最大的学校了,可是年轻人都离开了这个城市,所以学校里早就空无一人,校门向两边敞开着。门左边是原来的文化宫。文化宫现在也不在了,只有底层开着小门面,上面写着“超市”两个字。走到跟前,发现这家店虽然号称是超市,实际上也就是个杂货铺,什么都卖一点,从五金小件到火腿肠方便面,从洗发水到饮料酒水。店主也在,一个脑袋形状怪异的老头,在柜台上摆弄一台杂牌收音机,不时调一下频道,电台发出语焉不详的人声,忽然有个声音亮了起来,玻璃柜面都震得嗡嗡作响。“第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
玻璃桌面上一层浮灰。我敲了敲桌子。
店主抬起头,目光在老花镜的镜片后闪烁。他脑袋的右半边瘪了进去,像是一个摔变形的鸡蛋。瘪掉的半边脑袋上没有毛发,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他看起来又怪又老。姑娘往我身后躲了躲。
我和他的视线在空中某点对峙了一会儿。
“你要买啥?”他问。
“我要个打火机。”店主拿出一个纸盒子,从一堆五颜六色的廉价打火机里拣出来一个绿色的。我打了一下火,没有质量问题,把一块硬币放在桌上。硬币像煎饼一样陷进一堆灰里。
“附近有没有喝茶或者喝咖啡的地方?”我问。
瘪脑袋店主用手掌把一块钱和一堆灰都扫进了零钱盒,然后用手指了指街道斜对面。我和姑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了五个霓虹灯大字。
星吧客咖啡。
“那里以前不是个舞厅吗?”我问,“现在是咖啡馆了?”
店主再次抬起脑袋打量我,一边晃动着收音机的天线。
“哦?你以前来过这里?”
我点点头。这时收音机传出了另一个频道的声音。
“昨天……狮子座流星雨掠过地球,有流星坠入大气层……”
接着收音机里的声音又变成了广播体操。瘪脑袋店主拍了拍收音机,举起来贴在耳朵边上摇晃。
我和姑娘走到咖啡馆的霓虹灯下面,然后“星吧客咖啡”的“客”字闪了两下,啪地冒出一股青烟,大概是报废了。进到里面,我们才发现整个咖啡馆也差不多到了报废边缘,所有的桌椅都摇摇欲坠,咖啡的看板很像是山村小学的破黑板。环顾四周凄惨的景象,就跟刚刚有两帮小混混在这里打过架一样。整个咖啡馆唯一的优点是地方够大,也就是说足够容下更多的混混在这里打架。毕竟以前是舞厅。以前舞厅里真的经常有两帮混混打架,为了姑娘或者为了面子,或许两者都是一回事,跟公狗撒尿标识地盘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我们在靠街的窗边找到了还能坐的桌椅。过了两分钟,服务生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猫着腰踱到我们桌前。
“抱歉没看见你们,今天没什么客人,所以刚才一直在开小差,玩手机呢。”服务生是个发育不良的女孩,看起来只有十五岁,手里拿着一台白色的爱疯四,她麻利地套上带着咖啡馆标志的围裙,“说吧,你们想喝啥,我们这里只有速溶咖啡。”
“……那还点什么?随便上吧。”
“雀巢还是麦斯威尔?”她好心地问,“麦斯威尔口感更柔和,而且雀巢的快过保质期了……”
我和姑娘都纷纷点了麦斯威尔。服务生女孩又猫着腰回去了吧台那里。
“我不是很爱喝咖啡,容易在飞行时睡不着觉。”姑娘说,“咖啡有股陨石坑的烟尘味。”
“小时候没喝过,倒是经常喝中药,”我说,“我是长大以后才习惯喝咖啡的,咖啡的苦感有点像是中药,或者也可以说是回忆的一种。”
“你在这里长大的?”
“我出生在这里。”我说,“你呢?你从哪里来?”
她想了想,指了指天上,大概是说坐飞机来的。这时服务生女孩在吧台那里用力敲桌子。
“咖啡好了,自己来端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吧台那里,只有两杯咖啡,也用不着托盘了。
“哦,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愿意端过去。”服务生女孩小声说,“我端不动……我的腰坏了。”
“你的腰怎么了?”我问。
“很多年前砸断的。……不然早就和大家一样离开石城,去南方的大城市打工了。”
我看了一会儿她的脸,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的事。
“平时生意怎么样?”
“没有什么生意,”她说,“这个城市没几个人留下来了,年纪轻的都出去了。我一天都卖不掉十杯咖啡。”
“那怎么办?”
“晚上老年人会来这里包场跳交谊舞。白天做咖啡不为赚钱,就为了打发时间。可以认识陌生人,聊天什么的。”她说,“你女朋友挺漂亮的,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姑娘。”
“不是我女朋友,刚认识的。”我说,“我来端咖啡。”
我端着两杯咖啡回了靠窗的座位。姑娘双手托腮看着外面的大街。秋天,叶子落在水泥路面上,我想起打工后认识的一位姑娘的话,北方的秋天,就是竹扫帚扫去落叶的声音。我是石城长大的,石城是北方的城市,所以我理解她的意思。
现在又是秋天了。
“叶子从树梢上飘下来的样子很好看。”姑娘说,“它们好像慢吞吞的老太太。”
我开始喝咖啡,捧着杯子看著外面的街道。她也学我的样子。
“知道吗,”我说,“这里以前是个舞厅。”
“跳舞的地方?”
“舞厅当然是跳舞的地方,不是游泳的地方。”我说,“白天基本上都关着,到了晚上七点才开门,然后全城的小年轻都汇聚到这个舞厅来了,大多数都是混混,也有我这样的还在读书的中学生,我记得门票很便宜,两块钱。”
“舞厅里有很多漂亮女孩?”
“没注意,可能有一两个。但我那时有个喜欢的女孩,是我的同学,她是个好女孩,从来不去这种地方。”
“你喜欢跳舞吗?”
“我不喜欢跳舞。”我想了想,“而且也跳得很烂,那时大家都跳二步三步四步什么的,我一直没学会,所以没什么舞伴。就跟瘪脑袋一样。”
“瘪脑袋?”
“一个经常被大家笑话的小混混,因为太笨了,可能智力上有点问题,大家叫他瘪脑袋,个子又矮小,整个发育不良。所有人都拿他取乐。没有女孩愿意当他舞伴。也没有女孩和我跳舞。那些喜欢跳舞的女孩像逃避苦难一样避开我。再说我也不是去跳舞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舞厅?”
“可能是逃避孤独吧。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感觉很孤独。”我说,“可是实际上在这种地方待着对减缓孤独感没有任何帮助。到了高三以后,我就不再来这里了。因为要准备复习高考了。”
“在孤独这一点上我挺有发言权的,我好像孤独地在宇宙呆了二十年。”她喝了口咖啡说,“偶尔会遇到超新星爆发,我远远地看着那烟花一样的绚烂,然后继续我的旅行。”
她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姑娘。我笑了笑。
“你为什么来到石城?”我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旅行线路,可能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吧。是引力让我掉到这里。”她蛮随遇而安地莞尔一笑。
“这个地方早几年就破落了。矿场也关掉了,以前倒是可以来碰运气找找石头什么的。”
“石头,什么石头?”
“钻石。非常特别的钻石。”我说,“很多年前这里的名字不叫石城,人们叫这里鉆石城。”
姑娘手捧着咖啡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服务生女孩在吧台里鼓捣了一阵,打开了音响。音箱里响起了模糊的歌声。
“我有点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了。”姑娘说,“城外的矿场,就是以前的钻石矿是吗?”
“那是一个天然的大坑。谁也记不得这个大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直到人们在那里发现了钻石。”我说,“他们说,那是一个陨石坑,很久前有一颗流星坠落到这里,因为高热和高压,流星就变成了钻石。有个美国作家叫菲茨杰拉德的,就此写过一篇小说。我读书以后特意去找来看了,小说名字叫《像里茨饭店那样大的钻石》。真的就像一个酒店大厦那么巨大的钻石,钻石就在那个陨石坑里。据说这些钻石非常罕见,打磨以后,里面好像可以看见星光。”
“可能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颗星星。”姑娘轻轻说。
“但在我小时候,钻石矿已经采光了。整个矿场都找不到几粒钻石了。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钻石枯竭了,矿场关掉了,整个城市也跟着破落下来,人们陆续下岗,年轻人没有出路,混迹在游戏厅,录像厅,桌球室和舞厅,城市治安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但我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我正在读高中,心里有个喜欢的女孩。我用功读书,每天来到学校,只是为了能看见她。那时我们就在对面的那个中学读书。这是石城唯一的中学。”
服务生女孩在吧台后大声问我们要不要续杯。我端着两个空掉的马克杯过去。她倒热水冲速溶咖啡,把包装袋丢到吧台下的垃圾桶里。
“我觉着那个姑娘有点喜欢你,”女孩猫腰低声说,“只有喜欢一个人,你才会愿意听他说故事。”
我谢过服务生女孩,接过两杯咖啡,端了回去。
“继续说你喜欢的女孩,”姑娘说,“她是你的初恋吗?”
“是的,但仅限于暗恋。”我低头喝了口咖啡,“表白信或许写过,但没有勇气寄出去。这是个封闭的小城市,这种事情很难去想象后果,会把一切都搞糟的。我不知道她会怎么看待我,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对我有一点好感。对我来说,就算整座城市都变成钻石,都不如她。”
“平时你们接触得多吗?”她喝了口咖啡,小声问。
“我们隔得很远,差不多是教室的两端。她的座位在窗边,我常常借看风景的机会看着她。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年级数一数二。家庭条件也比一般人好得多,她的父亲是石城矿务局的局长。可是在班里她没什么朋友,上学放学都是一个人。我们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方向,都会经过泪街。有时候会在路上遇到,然后默默地同行一段。每天她都在你刚才待着的那个车站等车。”
“她长的什么样?”她问,“和我像吗?”
“应该很好看吧,可是我有点记不得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要是没有回到这里,我几乎不再想起她来。”我说,“我觉得你们的样子不太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的时候,我还以为看见的是她。”
姑娘好脾气地笑了一下,她笑起来像夜空的星星发出柔和明亮的光。我凝神听了一会儿咖啡店里模糊的背景乐,是一首摇滚乐。
“我们的交集可能还有音乐。”我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都喜欢摇滚乐。你喜欢音乐吗?”
“我大部分的旅行是在寂静里度过的。”她有些难过地说。“音乐方面我几乎什么都不懂,但在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哼唱给自己听。”
“你能听出这是哪首歌吗?”
她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后来呢?你和她怎么样了?”
我听了一会儿歌。
“死了。她很早就死了。在高考之前就死了。”我说,“我说过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小混混们很容易就死掉了,有的是死在了别的小混混手里,有的是被捉起来,枪毙在废弃的矿场。但我没有想到像她这样的女孩会死掉。我以为她会离开石城,那时她已经确定被保送到南方的大学了。”
“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了?”
“那时整个石城都很混乱。在我们读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这种混乱到了顶点,出现了连环杀人案。被害者几乎都是年轻的女孩,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被人从后面敲碎了脑袋。这就是恶名远播的石城敲头案。”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被害的女孩多吗?”
“受害者一共是十三个女孩。”我说,“死了七个,有六个人重伤,变成植物人,或者痴呆,或者残废了。你看见咖啡馆这个女孩吗?我现在才想起来,她是其中一个,不过她很幸运,凶手失手砸断了她的腰。从那以后她再也直不起腰了。”
姑娘转头望了望服务生女孩,女孩在吧台里抬起脑袋。
“还需要什么吗?续杯还是饼干?”
“不用了,谢谢你。”我说。
姑娘收回目光,低头望着杯子。
“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凄惨的事发生的。”她说。
“是的,但是世界上偏偏就会发生这种凄惨的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好像更喜欢悲剧。”我说,“第一次谋杀就发生在舞厅门口,当时已经散场了,那个女孩从现在角度来说就是个不良少女吧,凶手敲碎了她的脑袋,把她拖进了一条死巷。第二天早上,上学的学生发现了尸体。去舞厅跳舞的大多认识这个女孩,因为几乎都和她跳过舞。舞厅就此关门,再也没有开张过。她是第一个受害者。”
“凶手为什么要杀她?”
“不知道,凶手也和她跳过舞吧,可能因此才会选择她做第一个目标。”我说,“受害者都是女的,所以这些谋杀里很大程度上含有性的意味。那个罪犯是个很变态的家伙,下手很重,几乎都是一击必杀,敲碎头骨。把受害人身上的钱和手表都拿走,但那些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为了钱。”
“为了什么?”
“只是心理扭曲了,想杀人而已。就像在一个又黑又深,又爬不出去的井里,他因为无聊,空虚,绝望,将井里的一切都毁坏掉,来获得一丝满足感。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根本就是有另外的原因,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
“他伤害了十三个女孩……”姑娘犹豫了一下,小声问,“那你暗恋的那个女孩……”
“她是第十三個。有一天下晚自习,她一个人在泪街车站等车。凶手敲碎了她的后脑。她当时没有死掉,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星期后才死的。”我说,“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想跟着她到车站。那段时间我一直都跟在她后面试图保护她。但是我被留下来打扫卫生。只耽搁了几分钟,但一切都来不及了。这也是最后一起敲头案,因为那天晚上凶手就被捉到了。”
“凶手是谁?”
“一个智力有点问题,看起来发育不良的小孩。所有人都拿他取乐,叫他瘪脑袋。”我说,“被抓到的时候,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拿着一把铁锤,对着周围人龇着牙笑。”
“你认识他?”
我点点头。
“这是个小城,大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都相互认识。算起来他和我念同一个小学的,算是小学同学吧。实际上他只有十五岁,还不到量刑年龄,但是他做的事太恶劣了,又可怕又恶心。据说他不但敲碎了那些女孩的脑袋,还对尸体做了过分的事。他被抓后,没有一个人去看过他,连他父母都不认他了。审案的直接把他户口上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岁,直接枪毙了事。于是一切就都结束了。”
“那个女孩,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真是很不幸。”她说。
“我觉得她的死亡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既是我青春期的结束,也是石城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说,“很快我就去了南方的大学读书,后来就没有回来过。而石城的年轻人,也从那时开始,逃离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年轻女孩。没有了女孩,就没有了希望。这个曾经出产钻石的城市,已经死了。留下来的只有贫穷和绝望,没有未来。我读完了大学后,就留在了南方的城市。已经有十几年时间,时间久得连我都忘了自己是哪里人了。”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这十多年,我好像一直都在做梦一样,在长久到无法醒来的梦境里,我一直想起过去,想起这座我早就离开的城市。我没有觉得这里是我的故乡,哪里都不是我故乡。我只是在做梦时想起它,想起那个过去的时代,想起那个悄悄死掉的女孩。我休了个长假,不知不觉买了开往这里的火车票。也许我是想再到这里来看看,看看北方的秋天,看落叶飘满街道,看看我曾经喜欢的女孩消失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脆弱,那么可怜,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
我低下头,停了一会儿。
“人的生命就跟流星一样,一闪而逝。不管你怎么追寻它的光芒,它最后都会消失在黑暗的星空。”
她“嗯”了一声。
“流星的生命就跟人一样,始终是孤独的。我们跟随着命运的脚步,来到不可知之地,迎接不可测的命运。”
我们沉默下来,听咖啡馆里不可靠的音响里播放的不可靠的歌曲。直到此刻我才听出来这是什么歌。
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
“流星……”我说。
“你叫我?”
“我是说这首歌的名字,你听过这首歌吗,原来是Coldplay的Yellow,但我更喜欢郑钧的这首,他把这首歌起名为《流星》。”
姑娘听了一会儿,轻轻哼了起来。
“我很喜欢这首歌呢,就好像是为我写的一样,”她说,“我完全能够理解这首歌,因为啊,我就是一颗流星。”
“你说什么?”
“我说,我就是一颗流星。”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在开玩笑吗?”
“这是真的。我飞了很远的距离才来到这里。在你和我说这些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直到听完所有的故事,我才明白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我的命运。我会在这里遇见你。”她说,“世界上有很多的女孩,就和宇宙里有很多的流星一样。”
我记得自己是在车站碰到她的。她的样子有些迷茫,就好像一头迷路的小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和这个小城市格格不入,石城无法容纳这样一个姑娘。这样的姑娘只会待在一个小城男孩永远的梦幻里。可是我已经不是什么容易做梦的孩子了。我早就离开了黑乎乎的街道,用外面世界的自来水洗干净了脸和手。
“当然,这里没有人知道我是一颗流星。从星光的等级上来说,我是中等亮度的,现在我刚成年,所以这次是我的成年旅行。”
“你多大了?”我问。
“换算成你们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岁吧,”她说,“你觉得我太小了吗?”
“不,我觉得你正好。”我说,“你看起来就是二十岁。”
她笑了起来。
“可是……可是为什么大多数流星都成为了陨石,而你却是个女孩?”
“因为她们都坠落了。就像城外那个陨石坑,也就是你们说的钻石矿,那应该是我的同类,可是她消逝了。”她低声说,“只有活着的星星才会是女孩。”
姑娘举起胸前的吊坠给我看。
“你看,这是我的星光。”
她的星光比所有的钻石加起来都要明亮。我看着她,她身上散发出璀璨的微光,犹如彩色的标本一样浮现在黑白的背景里。咖啡馆破旧得好像是百年前的建筑,说不定真有这么旧。很多年前我还是个男孩时,一个人站在舞厅里,激光灯在头顶转个不停,一束束光点像刀子一样落在人们的身上。现在没有激光灯了,可是我仍然感觉有点眩晕,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闭了一会眼睛,好让她的光芒在我脑海里褪去。她是那样醒目,仿佛一颗星星坠入了蓝色的大气层那样周身明亮。
“可以抽烟吗?”
“当然可以,我不反感烟味的,因为闻起来很像是在大气层燃烧的味道。”
我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只找到了打火机。
“我要去对面买包烟,你能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好啊,等你回来,我要告诉你关于星星的一切。”
她垂下眼睛,低声说了一句话。
“你在说什么?”
“在星星的語言里,这是一句祝福的话,”她说,“希望宇宙里所有坠落的星星,都能找到夜空的归宿。”
我起身离开咖啡馆,走到刚才买打火机的小卖部。小卖部的店主还在那里听收音机。我要了包中南海,他弯腰从柜子里给我找烟。我一边等着,一边看着货架上的小商品,看起来确实没什么人买。货架上一层灰。
“那个拿给我看看。”我指了指右边的位置。
店主瞥了一眼,和烟一起拿了过来。
“这是工艺品,镀银的手工锤。”他说,“以前采钻石用的,现在卖给游客做纪念品。”
我拿在手里掂了掂,锤子很小,银光闪闪的,看起来挺精致的,不过也只能做纪念品,派不上什么用处。真的矿工锤比这个要大很多,也重很多。
“这个我也要了,”我说,“一共多少钱?”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店主问。
“纪念品,买来送人。”
店主斜着眼看我,看了一分钟。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你是那个男孩。”他忽然说。
“什么那个男孩?”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敲头案,十几年前石城有名的连环敲头案。你是敲头案最后那个受害者的同学,后来顶替她保送去了南方的大学。你就是那个男孩。我记得你。”
我抬起头,静静地望着他形状怪异的光脑袋。
“就算我是那个男孩,又怎么样?”
“他们说,保送名额只有一个。你是全年级学习最好的人,但是那个女孩的爸爸是局长,如果没有出事,她会被保送进大学。”
“你到底想说什么?”
“虽然那个变态枪毙以后,再也没有人被敲头了。可是大家都觉得,凶手仍然游荡在石城的街道上。”
我继续注视着店主的光脑袋。它奇怪的形状让我想起那个瘪脑袋的小混混。我一直在想,究竟那个罪犯是因为脑袋是瘪的才这么变态,还是因为是遗传了瘪脑袋和变态才变成了罪犯。不过归根到底,他也是石城的孩子,就和我一样。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男孩。”
“我就知道。”店主嘀咕说。
“而且我确实保送去了南方的大学,这是当时能够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的唯一的办法。”我说,“我去了南方的大城市,先是读书,然后留下来工作。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回来过,一次都没有想过。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一直很害怕。每一个晚上都很害怕。我害怕回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觉得有人在跟着我,有把榔头随时会敲在我的脑袋上。我就和所有出生在石城的年轻人一样绝望,最后我们都离开了这个噩梦般的故乡,并且再也不愿回来。”
“但是现在你回来了。”他说,“也只有你回来了。”
“因为我不害怕了。我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荒谬。”我把那把工艺品小锤拿在手里,看着店主的眼睛。“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我可以做任何我要做的事。如果有人要敲我的脑袋,如果有人想要敲碎我守护的东西,如果有人想从我这里夺走什么,我一定会用种种方式,反过来敲碎他的脑袋。不相信尽可以试试。”
瘪脑袋店主和我对视了一会儿,垂下了眼睛。
“不管怎么样,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没有必要为过去的事争吵。”
他像垂死的老人那样叹了口气。低下头继续给我找烟。
这时,玻璃柜台上的收音机响了起来,信号不良的沙沙声。
“俄罗斯……科学家在西伯利亚东……发现了刚坠落的……陨石……罕见的……价值数亿美元……”
沉默。
“这是昨天夜里落下的几颗流星里的一个。”店主说,把一包中南海搁在柜台上。
“是么,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她是一颗流星吧?”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烁,“我是说那个和你一起的姑娘。”
“你在说什么?”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漂亮的女孩。我看见了她的吊坠。那块吊坠里,有她的星光,和昨天夜里的流星一样色彩的光芒。”店主说,“我就是靠这个认出来的。要知道,很多人都在找掉下来的流星,有很多想要改变命运的人,都想要找到昨天夜里那颗落下来的流星。也就是你身边的这个姑娘。”
“你疯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都疯了。”
“所有石城人都是疯子。只是原因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钱,有的人是因为变态,有的人是为了别的摸不着的东西。”他说,“你呢,你是哪种疯子?”
我把钱扔在柜台上,拿起那包中南海。店主收起钱,将一个核桃放在桌上,拿起另一把小锤。
“听着,活着的流星是不值钱的,”店主压低声音,“只有陨石才值大价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甩起锤子。啪地敲碎了核桃,仿佛敲碎一个脑壳的声音。
我把烟和工艺锤都放在口袋里,转身往街对面走。
我向对面的咖啡馆走去,秋天的落叶落在我的身边,好像能够听见落叶被竹扫帚扫走的声音。远远地就能看见坐在咖啡馆窗边的姑娘。我望着她,内心有一些忧伤。
越是走近咖啡馆,那首歌就越是清晰。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幸福能有多久。我想起来许多个漆黑如噩梦般的夜晚,想起那些夜晚的流星。那些流星美得让人心碎。在那些夜里,我像信仰神灵的古人一样,对着星光许愿。我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小城男孩和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当梦醒的时候,我茫然地站在街道上,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里,舞厅里已经没有人在跳舞,只有音乐流淌在黑夜。我想起窗边的身影,想起我跟随在那个孤独的女孩身后,她在车站上落寞地等待着仿佛永远不回来的班车。她回过头,仿佛看见我了,露出了微笑。
我看见了那个如同流星般的姑娘。她看见我回来,对我笑了起来。愿所有坠落的星星,都能找到夜空的归宿。
我向她走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