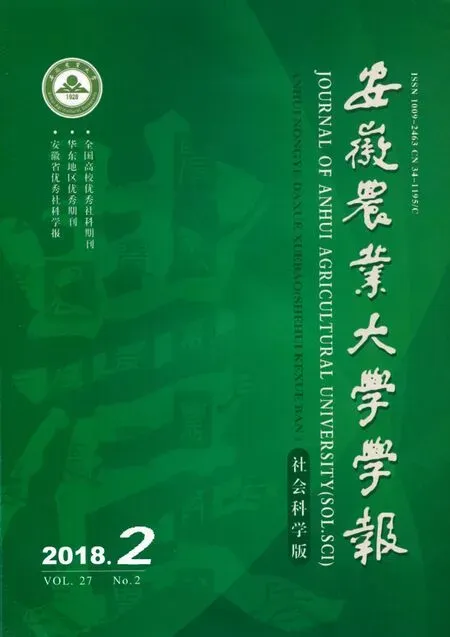全面质量管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
包先康
(1.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大学 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51)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是质量备受关注的世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的竞争实际上显性地表现为质量的竞争,从经济层面来看,是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质量之争;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之争,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否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才能的施展,以及能否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恰如朱兰所言:“20 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 世纪则是质量的世纪。”[1]杰克·韦尔奇就曾将“追求质量”和“发挥员工优势”视作公司成功的两大法宝,而他更看重质量,将其视为赢得忠实顾客最有力的保证、战胜国外竞争对手最强有力的武器、公司获得成长和利润的唯一途径[2]。可见,当今质量在企业或公司发展、市场竞争等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是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因此,20世纪90 年代末西方企业界掀起了全面质量管理运动,这对提高西方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此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改革或再造”的需要,美国学者史蒂文·科恩等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了政府管理,引发了政府管理的深刻革命。
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西方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开始广泛应用之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20年,但是质量管理理论并未得到国内企业界和政府的重视,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处于重规模、重数量而轻质量的阶段,企业和政府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认识仍处于强调“符合性”,而忽视“适用性”阶段。进入21世纪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瓶颈期,要突破这一瓶颈,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必然之势。国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正是对这一转变的顶层回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实质上是对顾客对产品和服务“适用性”要求的回应。因此,这样的政策变革较好地体现在经济层面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视。相较于经济层面对顾客“适用性”要求的回应,我国政府对民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适用性”要求的回应相对滞后,在公共部门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至多处于起步阶段,这在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基于W省的精准扶贫调研,我们发现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着突出的重数量、轻质量倾向。W省A市Y区调研时获得的相关数据显示:该区实施帮扶项目4 725个,户均4个,总投资1 908.377 7万元,总收益16 522.750 6万元,户均收益12 730.554 9元。从数据上来看,帮扶效果显著。但对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帮扶项目中,产业发展项目占比低,仅占项目数的4.53%,投资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只占3.31%,而资助性项目占60.53%,具有“重帮轻扶”的倾向,导致的后果将是贫困户的“造血”功能不强,返贫的可能性大。第二,贫困户家庭收入结构极不合理,根据统计资料分析,贫困户中工资性收入为0元的有559户693人,分别占48.40%、27.50%;家庭经营性收入大于1 000元的75户225人,分别占6.49%、8.92%,大于5 000元的23户80人,分别占1.99%、3.17%,大于10 000元的10户36人,分别占0.87%、1.43%。后来从同期开展的W省其他地区的调研结果看,各县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式扶贫,以提高扶贫的质量。同时,精准扶贫作为政府主导的“资源输入”式扶贫,强调地方政府对扶贫的管理,并试图通过强化管理提高扶贫的质量。如果政府在扶贫工作中能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秉持的“质量第一,顾客第一”的理念运用于管理工作中,将会更好地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
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要旨
全面质量管理概念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其理论也愈来愈成熟,其应用也由最初的经济领域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较早提出全面质量管理概念的是菲根堡姆和朱兰。当时他们是这样界定的:“为了能够在最经济的水平上,并考虑到充分满足顾客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研究、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把企业内各部门的研制质量、维持质量和提高质量的活动构成为一体的一种有效的体系。”[3]从这一最初的界定来看,其中包括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市场研究、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要以“考虑到充分满足顾客要求”为条件;二是质量管理不仅仅是质检部门的事,所有的部门都要参与到质量管理中。因此这一界定已经包含了“顾客第一”“全员参与”的质量管理的基本思想。后来,ISO8402 进一步明确将其界定为:“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4]ISO9000:2000将其更为概括、精炼地定义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其目的是以持续降低的成本,持续增加顾客满意。”[5]基于前述界定的概括性、抽象性,为了让人们对全面质量管理有更明确清晰的认识以及更具可操作性,有人将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较为明晰地概括为:“以顾客为中心;持续改进;确定基准点;准时制;雇员授权;各种质量管理工具。”[6]从对全面质量管理概念的梳理来看,全面质量管理的本质是由顾客需要和期望驱动的、企业持续不断改善的管理活动、过程与体系。
最初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主要倾向于帮助企业通过改革管理方式、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改进,以获得竞争力而提出的。它的运用使得很多企业实现了“再造”,并通过这种再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强调“以人为本”,是一种瞄准改进顾客满意的组织范围的哲学[7]675-694。基于哲学层面的考虑,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运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企业再造”,同样可以运用于“政府再造”等诸方面。“企业再造”是为了解决工业化以来企业生产过程中组织管理失灵问题,以提高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回应能力。而“政府再造”是为了解决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的弊端引发的组织管理失灵,所造成的政府对民众需求回应能力不足的问题。恰如霍哲所言:“全面质量管理主要强调的是以顾客为中心。如果将这个中心应用于政府部门,那么其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增进公共机构对公众的回应性。”[8]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将企业产品生产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念、工作原则、运筹模式应用于政府机构之中,以达到政府机构工作的全面优质、高效”[9] 95-98。 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关注顾客价值。即政府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时,要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适用性”需求。第二,崇尚质量至上。即政府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时,将质量作为优先考虑。第三,强化流程管理。即采取先进、规范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将政府工作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消灭在业务流程之中,使得问题没有出现的机会。第四,强调授权和全员参与。即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旨在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的公共品和服务时,要让利益有关者参与进来,授权基层,以便对公众的合理的、多样化的需求得以及时回应。第五,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即政府在对基层管理者进行绩效考核和提供激励时,更加关注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尽量减少那种“没有功劳有苦劳”式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仔细审视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发现提高精准扶贫质量的基本路径。
三、提高精准扶贫质量的基本路径
精准扶贫就是为了提高扶贫的质量。但在实践中,精准扶贫并没有根本消除传统扶贫中“重数量、轻质量”和“重符合性、轻适用性”的弊端。为此,需要我们引进新的理念以改变此状况,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恰可为提高精准扶贫质量提供指引。
(一)以扶贫对象的需求为导向,关注扶贫对象的价值诉求
传统的政府扶贫更多地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政府能给什么”和“政府应该给什么”。前者考虑的是政府的供给能力,“有多少面摊多大的饼”,量力而行;后者侧重于政府道德考量的政府责任,更多关注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共同点是:供给导向,强调的是扶贫主体的“给”,而不是扶贫对象的“需”,遵循的是“施舍”的逻辑。这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会让那些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的对象产生现时的(很难是永恒的)“感恩戴德”,而让那些在比较中感觉到没有得到其期望的满足的人“愤懑”;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被政府判定为局外人感到不公。在精准扶贫调研中,我们发现对精准识别中存在问题举报的主要有这两类人:一类是认为自家符合贫困户标准而没有被纳入贫困户,要求增补进去;一类是自己也认为自家不符合贫困户标准,但与他家境况差不多甚至好于他家家境的人被纳入贫困户。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前者会产生“愤懑”,后者会感到“不公”。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要改变这种政府行动困境,必须实现由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需求导向即是以满足扶贫对象的需求为目的,为他们提供“适用性”的产品或服务。国外有学者曾提出以下三种影响顾客满足的因素:“不满意因素。这类因素通常不是由顾客所提出,而是产品或服务本身所固有,如果产品或服务不包含这类因素,顾客将感到不满意。满意因素。这类因素是顾客所表达的需要,实现了这类需要,顾客就会感到满意。愉悦因素。这是顾客没有提出而且又是顾客所没有预想到的新需要,企业提供这类因素将会给顾客带来意外惊喜,顾客将感到特别兴奋。”[10]这就要求:第一,在精准扶贫中,政府主导下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是“适用性”的。因为“公共品和服务的价值主要不是指其经济价值的高低和技术含量的高低,而是指公共产品或服务对于满足顾客需求特别是个性化需求所具有的价值”,“如果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不能满足顾客需求,其价值就下降为零,而成为多余功能”[11]3。产品和服务的“适用性”是顾客最基本的质量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质量就是适用性”[12]。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政府和帮扶单位、个人在提供项目帮扶或实物帮扶中,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方式,大多未能考虑到扶贫对象的需求,结果造成:项目很多,但其作用很小;送去的实物很多,但成气候的不多。正是这种“适用性”不足,造成了扶贫对象对产品和服务的不满,降低了扶贫的质量。第二,畅通扶贫对象的表达渠道,加强与他们的交流沟通。顾客导向强调顾客才是质量的最终鉴定者。依此,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中,要变革工作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的沟通方式,重视、学会、善于倾听他们的抱怨,因为从他们的抱怨中能够传递出政府扶贫工作的不足和他们的真实需求,如果能够对他们的抱怨予以妥善而及时的回应,并能对他们表达的需要予以合理满足的话,那么他们将会由最初的不满意变得满意;同时,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要谨慎并重视对扶贫对象的承诺,一旦做出承诺,就要努力践行承诺,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满意。为此,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与扶贫户之间的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互动,让他们在融洽互动中充分表达他们的真实需求,并建构针对扶贫对象的灵活及时的抱怨处理机制和反馈系统,进而使之由“被动接受”变成为“积极行动者”,使之在积极行动中获得更多的满足。第三,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改进工作方法,发现扶贫对象的潜在需要,并予以满足。对于很多贫困成员而言,由于知识和信息的局限性,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眼前的、显性、现时的需要,这样的需要主要是一些浅层次的,它的满足难以对其生活现状的改变产生持续效应;而对较为长远的、潜在的需要缺乏敏感性,而恰恰这样的需要的满足,可以带来其生活的持续改变。这就要求扶贫主体积极主动地通过精心细致的工作发现贫困对象的长远、潜在、并能够对其生活带来持续改变的需求,并适时地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获得意外之喜,体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依据TQM理论,顾客还包括“内部顾客”。在压力体制下,在特定的时期政府有时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满足外部顾客的需求上,而忽视了内部顾客的需求。这种现象在我国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为了完成国家的脱贫计划,压力体制下的政府采取层层施压的方式来推动工作,在巨大的层层压力下各级公务员“不敢不为”,但没能解决好他们“想为”和“愿为”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来自上级的频繁施压,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疲于奔命、身心憔悴,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产生了“抱怨和不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上级的只有压力而缺少人文关怀,他们的诉求达不到充分的表达,需求无法满足。“无法想象一个连内部顾客——国家公务员都不满意的政府,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品和服务给外部顾客。”因为“作为内部顾客的国家公服务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影响着外部顾客的满意度”[11]4。从某种程度上说,“采纳全面质量管理会从一种类似霍桑效应中受益,因为管理部门对员工关注程度的提高会使他们作出反应来改进每日的工作”[13]。哈佛商学院赫斯科特教授指导的一项研究表明:员工满意度下降后的 2个月内,顾客满意度会随之下降;如果员工满意度上升,顾客满意度、忠诚度也会随之上升[14]79。也就是说,当处于扶贫一线的人员在感受到来自上面压力的同时,也能切实感受到来自上面的关怀和认可时,他们才会对上级政府感到真实的满意,从而“愿意”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甘心为扶贫对象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总之,要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工作中既要关注外部顾客的需求,也要关注内部顾客的需求,给内部顾客更多的人文关怀。
(二)精确测量,消除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工作中,精准测量就要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扶贫工作全流程的关键变量进行度量,它包括:贫困村、贫困户的精确测量;进村项目的数量、效率、受益人口的精确测量;政府可调动的资金性资源的测量;减贫人口的精确测量,等等。还要将这些测量结果与相对应的标准和扶贫目标相比较,准确找到扶贫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关键环节,然后集中力量解决,提高扶贫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测量过程中对基层的过度依赖,实践中这种过度依赖已经造成了信息的失真。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种数据失真并未能根本改变,在有的县区按照现行的国家贫困线标准,甚至超过50%的家庭实际收入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而在部分县区却因国家下达的指标少致使应纳入扶贫人口却未能纳入的情况。这种失真造成了如下问题:精准识别不精准、精准施策却出现项目微效。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精确测量为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组织专业化的工作队伍进村入户,运用现代统计工具进行精确统计、精确计算。这样的工作队伍可以保持情感中立、价值中立,从而保证测量的精确性,降低精准扶贫中问题出现的机会。
(三)再造扶贫工作流程,持续改善扶贫质量
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组织产品或服务应坚持质量第一,但为了能够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并不能仅看重产品或服务本身,而应更看重工作流程并将其视为产品或服务质量得以持续改善的关键。从工作流程来看,全面质量管理实质上是要颠覆传统的组织结构原则、工作方式,实现业务流程的再造,以达成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目的。业务流程再造具有如下特性:“强调团队合作;降低决策层级;关注更大范围的、根本的、全面的业务流程;关注顾客满意;使用业绩改进的量度手段;改造企业的价值观;高层管理者的推动。”[15]业务流程再造就是打破传统组织的职能和等级的障碍,实现产品或服务生产的源头、过程、经销商和顾客全面检视和利益关注,实现利益的合理共享,从而为实现让顾客获得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开展全面合作。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机构十分广泛,需要通过跨职能和等级的过程管理,强化扶贫工作业务流程管理,以提高组织扶贫效率。但是,在当前体制下,上下一盘棋,全员参与,缺少利益关联的统合,结果精准扶贫出现“碎片化”和“内卷化”。精准扶贫的“碎片化”表现在扶贫主体的碎片化、扶贫项目的碎片化[16]、扶贫政策的“碎片化”、扶贫对象的“碎片化”等方面。精准扶贫的“内卷化”表现在:大量扶贫主体和督查频繁进村入户使得扶贫对象满意度出现边际递减;大量的扶贫资金和项目集中进村也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边际递减;在层层压力下,扶贫干部疲于奔命,工作效率边际递减、热情降低。要改变这种局面,提高精准扶贫质量,需要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流程再造。通过这种流程再造,加强扶贫主体间的合作,在源头上形成资源供给合力;实现扶贫过程全面检视;降低一线扶贫干部的身心压力,以便他们更好地成为扶贫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增强扶贫对象的话语权,使其需要更好地满足,从而保证扶贫工作流程的顺畅,实现扶贫工作和扶贫对象境遇的持续改善。
(四)扶贫工作需要全员参与和团队合作
TQM 理论认为,产品或服务质量与组织内所有部门和员工存在密切关联,最终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与他们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因此,若要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就需要全员参与质量管理,而不是少数人或部门的单打独斗。所谓“全员”,ISO8402 质量标准中将其界定为 “该组织结构中所有部门和所有层次的人员”[17]。具体包括高层管理者、一线员工、质量监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其中高层管理者在质量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按照TQM理论,组织领导者要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并以此制定组织发展的策略性规划,同时还要直接参与到全面质量管理中。若高层管理者都不能将质量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则很难对其员工提出质量要求,他们也就不会把质量放在心上。在这个问题上,质量专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没有组织领导,质量与生产率只会是幸运的意外事件。”[18]55但组织领导正确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有效的员工领导方法更为重要。传统的组织领导是一种对员工“羔羊式”的规训,以追求员工的被动性和一致化为目的;而秉持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的组织领导,更注重对员工的循循善诱,赋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追求员工的主动性和个性化为目的。故秉持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的领导的着力点在于授权员工并创造和谐的学习与持续改进工作氛围,激励并驱动员工坚定“顾客第一,质量第一”的信念,并开展有效的行动。所以,对高层管理者而言,在制定全面质量管理战略时不仅要考虑组织规划质量的远景目标,而且还要为实现此目标,确立将一条“以顾客为导向”和“以员工为本”的核心价值并贯穿始终的路径与标准,最终建构一个能让顾客满意的质量战略的评估价值指标体系。高层管理者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为组织内团队合作奠定了基础,但要形成有机的团队合作,关键在于授权一线员工。所有员工的真诚合作参与,方能更好地取得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成就。因为,一方面一线员工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了解,另一方面一线员工由于与外部顾客频繁接触更知晓其真实的想法、需求以及其满意度。另外,授权一线员工,充分体现了组织对他们的尊重、信任与能力的承认,会强化他们的责任和主人意识。因为“授权会带来生产力之间更高层次的满意度”[19]203。 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扶贫工作中,首先上级政府要秉持“扶贫质量第一”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只有他们坚定了这种理念和正确的工作方法,下级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扶贫工作中才会把质量放在心上;其次,若上级政府能适度、合理地授权于扶贫一线的工作人员,会大大提高他们的满意度,从而激励他们更好地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工作中就会多一些“阳谋”,这有利于提高扶贫的质量。若能如此,扶贫工作队才不会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给政府做“糊墙的工作”(出自一扶贫工作队长语)。至此,扶贫工作中真正的全员参与、团队合作才会出现。然而,在我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的是指标完成的情况,而这些指标基本上是数量性的,缺少能够反映对质量要求的指标,实际上造成了对质量的无视;再加上指标的刚性,一线员工把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视为工作目标,导致“手段—目标”的倒置。从形式上看,精准扶贫工作是全社会动员、全员参与,但这种参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被动的“配合”行动,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合作行动,且在整个配合行动中一线工作人员始终被放在被检查的位置,缺乏必要的尊重与信任,也是对其能力的贬低。如此,一线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被激发,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合作,这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效率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五)变革扶贫工作中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
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是有效保证组织高效运行相互关联的两种基本机制。传统的组织绩效考核具有“重数量,轻质量”和“重符合性,轻适用性”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弊端在于:忽视员工和团队的工作质量、非正式化的灵活的合作和对顾客的奉献。结果使得员工和团队习惯于为追求数量而粗制滥造、捆绑式的僵化的配合和对顾客的忽视、冷漠与伤害。传统的激励体系以X人性假设为前提,强调对员工的全面监控,主要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方式。其弊端是忽视了对员工的尊重和信任、与员工的情感沟通,强调对其意志的遵从。结果使员工在工作中懈怠和不负责任,并在利害得失的权衡中更加注重通过关系管理建构与上司间的良好关系,以寻求组织内的庇护,而减少甚至排斥与其他员工的协作,组织内员工间的友谊与合作变得不可能,甚至建构出组织内部“互害式”竞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组织内关系紧张,与顾客的有效沟通必然会遭忽视,损害顾客的利益,顾客的不满意递增,从而使其走向制度设计者期望的反面。正如戴明所言,传统的业绩评估会“破坏团队合作,员工之间为了有限的利益进行恶性竞争;滋生平庸之辈,工作目标只由数字确认或只是符合老板的意愿;注重短期结果,削弱承担风险的能力;忽略服务于顾客的目的”[19]203。全面质量管理是以Y人性假设为前提,认为员工在工作中具有主动性、责任心,并能够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优点是:员工受到充分尊重和信任。组织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更加强调以员工为中心,关注流程与质量,充分一线授权,不断激发组织内生活力,以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故戴明指出,其实“质量无须惊人之举”[20]。对于领导者而言,持续改进工作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最基本因素[21]。在全面质量中,领导的权力是鼓舞,是激发责任感,是促使员工充分信任组织,并且自由地做出改变[22]。也就是说,质量管理并不需要管理者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和举措,关键是管理者持续改进工作,变“施舍者、恫吓者”为“授权者、激励者”,并能身体力行。总之,全面质量管理要求改变以往“重数量定额和结果、轻质量和过程”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建立一种以“以质量为中心,以顾客为导向,以员工为本”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但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从绩效考核看,仍沿用的是传统绩效考核机制,造成了部分一线帮扶工作人员将其工作看作是给政府“糊墙”,做做面子工作,而不愿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从工作激励来看,当前工作的激励机制是一种“严惩轻奖”的机制,完不成任务的就“一票否决”“就地免职”“摘官帽子”。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集体造假、隐瞒真相的事时有发生。同时,在高压之下,部分基层公务员为了完成指标采取诱骗、恫吓等不当方式对待扶贫对象,引发和加深了扶贫对象的不满。
由此看来,要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需要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精准扶贫指标的设计中需要引入质量指标和过程指标,注重对质量和过程的考核,并依据考核的结果对相关人员予以激励,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惩罚;多一些关怀,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引导,少一些督控;多一些互动,少一些命令。
四、结论与思考
精准扶贫工作中,扶贫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倾向;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重数量和结果、轻质量和过程”的现象;绩效考核和激励存在着“重惩轻奖、奖惩不对称”的问题。要改变上述倾向、现象和问题,在精准扶贫管理中,需要引入TQM。因为“TQM 能帮助政府组织实现它们的目标”,“TQM 的真正的成功之处不仅指它能解决类似的问题,还在于它使用的消除交流障碍的方法,使得问题没有机会出现”[9]95-98。同时,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倾向、现象和问题,也引发我们如下思考:政府主导下精准扶贫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由于政府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权力驱动、科层驱动、自身利益以及宏大愿景的驱动,在政府行政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信息歪曲。“在等级结构中,每一个官员都倾向于歪曲向上传递的信息,进而夸大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数据资料,并且最大限度地缩小对自己不利的数据资料”[23]。表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经费、项目的安排是政府运用权力、科层组织将其分解成任务指标层层下达,并作为上一级政府考核和奖惩下一级政府的依据,以此来达成国家的宏大愿景;而自下而上的各级政府面对自上而下的压力,为了规避惩罚,总会设法对已有的真实信息和数据进行修饰,以趋利避害,致使统计数据和信息失真。精准扶贫工作中对这种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再加上政府主导下的精准扶贫,往往会出现坚持错误行动和回应不及的问题。当政府或其工作人员出现坚持错误行动和回应不及的问题时,政府的扶贫工作就难以精准回应扶贫对象的需求,精准扶贫也会不精准,精准扶贫的质量也会难以保证。此外,在自上而下的层层压力之下,一线的公务员实际上往往缺乏自主性,更谈不上创造性的工作,只是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对照指标逐项想方设法凑足数据、做好台账,从各地精准扶贫的汇报材料可见一斑:在一省内各县、乡镇精准扶贫的措施基本一致,只是任务指标不同,上报的指标数据大多是超额完成,但如果对这些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经过了修饰)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将会发现这些数据背后精准扶贫的质量被忽视。
综上,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中心”观念根深蒂固,扶贫对象的需求被忽视,缺少对一线员工应有的尊重和信任;虽然通过压力的传导,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特别是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在扶贫工作中“不敢不为”,但并没有解决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特别是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能为”和“愿为”的问题。如此,精准扶贫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政府回应性不及的问题,结果造成了内部顾客——公务员自身和外部顾客——扶贫对象的不满,不满就是低质量或无质量。因此,透过精准扶贫这项宏大工程,我们看到在我国开展“政府再造”来提高政府效能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陈建.中国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系统的构建[J].行政论坛,2010,17(2):38-41.
[2] WATSON G H. Cycles of leaning: observations of Jack Welch[J]. Six Sigma Forum Magazine,2001,1(1):13-17.
[3] 杨林岩,詹联科.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我国公共部门的运用分析[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7(6):120-125.
[4] 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等.GB/T6583-1994 ISO8402: 1994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术语[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8.
[5] SPENCER B A. Models of organization and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 comparison and critical evalu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3):446-471.
[6] DEAN J W J,BOWEN D E. Management theory and total quality: improv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ory develop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 ,19(3):392-418.
[7] CUA K O, MCKONE K E, SCHROEDR R G .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TQM, JIT, and TPM and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1 , 19 (6) :675-694.
[8] 霍哲. 公共生产力手册[M]. 英文2 版.纽约:马赛尔·迪克出版社,2004: 636.
[9] 朱丽君.政府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5-98.
[10] 刘石兰.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组织变革:一个变革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5):114-120.
[11] 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王大海,吴群芳,等译.合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 JURAN J M,GRYNA F M. Juran’s quality control handbook [M]. New York: McGraw-Hill,1988:6.
[13] 科恩,布兰德.政府全面质量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14] COLLIER D A. The customer service and quality challenge[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87,7 (1):77-90.
[15] 哈默,钱皮.改革公司:企业革命宣言[M].胡毓源,徐荻洲,周敦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0-29.
[16] 李耀锋.连片特困地区的“项目进村”碎片化与精准扶贫:研究进展及理论构想[J].学术论坛,2016(11):111-117.
[17] 张锐昕,董丽.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的缺陷及其纠正[J].社会科学战线,2013(11):244-246.
[18] LEVINSON, HARRY J, DEHONT, et al. Leading to quality[J]. Quality Progress, 1992(5):55.
[19] 埃文斯,迪安.全方位质量管理[M]. 吴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0] DEMING W E. Letters from Edwards Deming[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2(11-12):134.
[21] REED R, LEMAK D J, MERO N P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Quality Management, 2000,5(1):5-26.
[22] CIAMPA D. Total quality:a user’s guide for implementation [J]. A.m.a.archives of Pathology ,1992,62 (4):272-284.
[23] 唐斯. 官僚制内幕[M].波士顿: 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6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