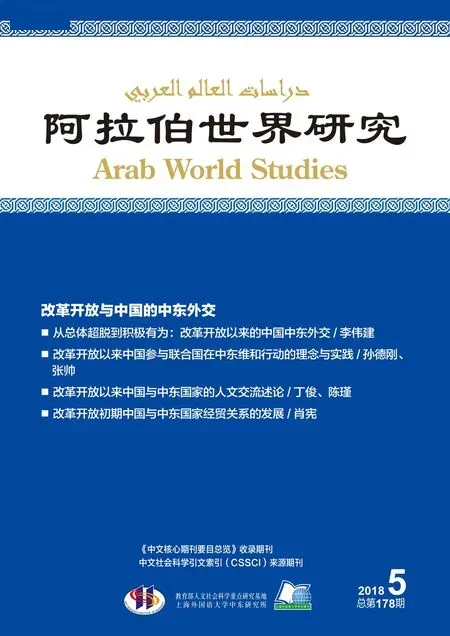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
张楚楚 肖超伟
“马格里布”(Maghreb)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日落之地”,引申为“西部”。中世纪时,阿拉伯人远征北非,抵达大西洋,以为到了世界的最西端,因而称当地为“马格里布”,泛指今天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传统上,马格里布地区主要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1989年马格里布联盟成立后,马格里布地区又囊括了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本文主要探讨传统意义上的马格里布地区三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
历史上,马格里布地区屡遭外族入侵,曾沦为腓尼基的殖民地,之后相继被纳入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版图。在腓尼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与法国人的影响下,地中海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非洲文明等不同文明在该地区汇聚与相互激荡,构成了马格里布地区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即不同统治民族的交替出现成为该地区历史长河中的突出现象。
马格里布地区三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同时也是初建不久的年轻国度。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摩洛哥王国则是阿拉维王朝的延续,三国都曾遭遇过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三国成为边界较为明确的独立主权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仅从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角度看,三国从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仍面临重重障碍。“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仅有36.4%和34.1%的民众认为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Data Analysis Tool,” Arab Barometer, http://www.arabbarometer.org/survey-data/data-analysis-tool/, 登录时间:2018年7月8日。。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与非洲司令部调查,2013年仅有30%的突尼斯民众将自己视为“突尼斯人”,到2015年,这一比例仅增长了8%*Mansoor Moaddel, “Tunisia: An Oasis of Peace and Tolerance: Findings from a Panel Survey,” Middle Eastern Values Study, http://mevs.org/files/tmp/Tunisia_Findings_2015.pdf, 登录时间:2018年8月11日。。
作为2010~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始发地,北非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反思政治变局直接诱因的同时,也开始探讨长期困扰该地区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构建问题。目前,关于北非国家构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埃及和利比亚两国。*有关利比亚国家构建的研究参见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30-145页;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115-133页;Zahra Langhi, “Gender and State-building in Libya: Towards A Politics of Inclusio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9, No. 2, 2014, pp. 200-210。有关埃及国家构建的研究参见毕健康:《文明交往、国家构建与埃及发展》,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41期,第36-49页;Kirk J. Beattie, “Nasser’s Egypt: A Quest for National Power and Prosperity,” in Sarah C. M. Paine, ed., Nation Building,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32-150; Ramy Hanna and Jeremy Allouche, “Water Nationalism in Egypt: State-building, Nation-making and Nile Hydropolitics,” in Filippo Menga and Erik Swyngedouw, eds., Water, Technology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81-95。相比之下,有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地区核心三国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探讨三国的经济模式*Dirk Vandewalle, “Political Aspects of State Building in Rentier Economies: Algeria and Libya Compared,”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Oxon: Routledge, 2016, pp. 159-171.和民族冲突*Jonathan Wyrtzen, “Coloni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Negotiation of Arab and Berber Identity in Protectorate Moroc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3, No. 2, 2011, pp. 200-210.。本文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时空范围,以地缘政治为切入点,考察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与挑战,尝试为学界思考和理解当前马格里布地区局势的发展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 外族入侵与马格里布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学者中有不同的理解,主流观点认为地缘政治是指“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客观而言,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过程,且不同时空背景下对各国政治的相互影响程度各异。具体到马格里布地区,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的“边缘地带论”与科恩(Saul B. Cohen)的“地缘战略辖区”理论曾将之列为影响世界局势的边缘地带*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 23.。但其实不然,马格里布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之地,且在外来文明角逐的地缘政治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碎片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复合型的民族文化。
马格里布地区的原住民为柏柏尔人。早在公元前21世纪,马格里布地区的平原和山区中就已出现了一些相互隔绝的柏柏尔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原始公社,以狩猎和畜牧业为生。约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向西南扩张,在马格里布沿海海岬和附近岛屿建立殖民点,成为马格里布地区最早的外来居民,并与柏柏尔原住民融合,产生了布匿人(Punics)。随着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开展,一些定居点成为繁荣的殖民贸易城邦,其中迦太基(Carthage)最为强大,也最为有名。随后数百年间,迦太基逐渐控制了马格里布地区大部分腓尼基人的殖民城邦,至公元前5世纪已经发展成为雄踞西地中海的强国,势力范围遍及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科西嘉岛、撒丁岛及西西里岛西部等。布匿文明对本土柏柏尔人影响较大,后者将布匿崇拜仪式融入了他们的民间宗教。马格里布地区原住民最初信奉万物有灵论,乞灵于风雨和阳光等自然力,之后开始接受布匿人的多神信仰,包括对最高神灵巴阿勒(Baal)及女神塔尼特(Tanit)的崇拜等。*Bernard Marcel Peyrouton,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aghreb, Paris: Albin Michel, 1966, p. 21.
马格里布地区因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自古以来对欧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迦太基与地中海北岸的罗马人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马格里布地区随之成为罗马帝国的非洲行省,但罗马人在三次布匿战争中损失惨重。在彻底打败迦太基后,罗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迦太基的一切建设成果”*[美]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9-450页。,致使马格里布地区此前灿烂的城邦文明遭遇毁灭性打击。在重塑当地城市格局与大规模移民*公元前123年,古罗马颁布移民法案,将罗马比较富裕的公民向南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进行移民,以解决人口过剩和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法案颁布后,从罗马城和意大利北部向北非的移民多达8万人。参见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的同时,罗马人将拉丁文作为官方文字,同时将罗马多神信仰传入马格里布地区,与原有的迦太基多神崇拜融合,形成颇具当地特色的多神信仰体系。例如,布匿文化的巴阿勒神被等同于罗马主神朱庇特,塔尼特女神被等同于朱诺·卡雷斯提。*Susan Raven, Rome in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84, p. 153.基督教兴起之前,迦太基的神庙中同时供奉着朱庇特、朱诺、弥涅乐瓦、塔尼和萨图恩等神,其中既有迦太基旧有的神祇,又有罗马人传入的神祇。*Michael Dumper and Bruce E. Stanley, C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7, p. 370.基督教诞生并传入马格里布地区后,基督教文化在一些城市中兴起,基督教堂渐具规模,且出现了奥古斯丁等对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后,马格里布地区东西部分别被纳入拜占庭帝国和汪达尔—阿兰王国的领土范围。公元647年,上埃及总督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奉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之命,率领一万步兵和一万骑兵进攻突尼斯,拉开了阿拉伯人西征马格里布地区的序幕。*Robert Cornevin, Histoire de l’Afrique: Des Origines Nos Jours, Paris: Payot, 1956, p. 102.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地区历时60多年,止于710年大西洋港口城市丹吉尔的沦陷。阿拉伯人的到来给马格里布地区带来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对该地区产生了持久影响。相比之下,马格里布地区“阿拉伯化”的过程比“伊斯兰化”漫长得多。直至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马格里布地区才真正完成了阿拉伯化。不过,马格里布地区使用的阿拉伯语同标准阿拉伯语相去甚远,它杂糅了标准阿拉伯语、柏柏尔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元素,形成了被称为“达里加”(Darija)的独特方言。
与腓尼基人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征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的控制,而广大乡村与偏远山区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家族、部落首领权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城乡二元风貌*Abdallah Laroui,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ive Essay, Ralph Manheim,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7; Michael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2.。尽管马格里布地区伊斯兰化的过程较快,但在偏远山区与广大农村地区,人们更青睐苏菲主义*“苏菲”(Sufi)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羊毛”。苏菲主义主张穿羊毛粗衣,倡导俭朴禁欲的生活方式。在7~8世纪时,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潮出现。早期的苏菲主义主要提倡苦行、禁欲,反对奢侈、浮华。至阿拔斯王朝时期,苏菲主义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的瑜伽学派以及佛教等外来思想,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思潮。参见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并将其与部落风俗和政治传统相融合,形成了带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伊斯兰信仰体系,且各地出现以部落首领为精神领袖、以家族或部落为主体成员的苏菲教团。同时,虽然西迁的阿拉伯人口逐渐超过本土的柏柏尔人,成为第一大民族,但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地区。许多内陆山区仍然是以柏柏尔人为主体民族、以塔马齐格特语(Tamazight)为主要语言的文明圈。
8世纪,随着阿拔斯王朝对西部疆域的控制力减弱,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柏柏尔人抵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运动,导致该地区陷入分裂。诸多短命的柏柏尔王朝不断交替,直至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马格里布地区中部与东部地区,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才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分支族裔萨阿德人和阿拉维人先后在马格里布西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摩洛哥)建立封建王朝,后者延续至今。
与阿拉伯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方式更为松散,帝国分别建立了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市为中心的“摄政国”,由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帕夏*又译“巴夏”、“帕沙”,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Pasha)担任最高长官。但帕夏的实际权威非常有限,行政区长官贝伊*又译“贝格”、“巴依”、“伯克”,该职位是奥斯曼帝国时对地区行政长官的尊称,次于帕夏。(Bey)们各自为政,成为所辖城区的实际控制者,而内陆山区和南部沙漠则由各大柏柏尔部落所控制。*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1页。在马格里布地区西端,由于阿拉维王朝控制力衰弱,摩洛哥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但国内呈分裂割据之势。16~19世纪,马格里布地区各地分离主义趋势日益增长,并对现代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疆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摄政国的大致范围奠定了当代两国的疆界基础,而奥斯曼帝国与阿拉维王朝的边界大体上决定了当代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界走向。*Michael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18.
新航路开辟后,作为贯通地中海与非洲南部的战略要地,马格里布地区成为西欧殖民者向亚非拉地区扩张的重要枢纽,日益强盛的欧洲列强开始觊觎地中海南岸各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同奥斯曼帝国进行反复博弈后,法国最终分别于1830年、1881年和1912年占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大部分土地。摩洛哥狭长的北部沿海地带被西班牙纳入势力范围,丹吉尔海港则成为国际共管区。
除了侵占良田、掠夺矿产与农产品资源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外,欧洲殖民者主要使用文化同化与分而治之的手段在马格里布地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后,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创办法阿*法国人创办的双语学校中教授的阿拉伯语为马格里布方言达里加,而并非阿拉伯标准语。双语学校与纯法语学校,并规定政府公文与公共场所的标语、公告牌一律采用法语书写。1938年,法国甚至在阿尔及利亚颁布3月8日法令,规定标准阿拉伯语为外语。*Mohamed Benrabah,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Alger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1, 2004, p. 63.同时,法国人开设教会学校,宣扬“天主教是最好的宗教”,同时贬低伊斯兰教,声称伊斯兰教是导致伊斯兰世界落后的主要原因。*Alison Tarwater, “French Colonization in the Maghreb: A Central Influence in Both Regions Today, ” Howard college, 2005,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493.3332&rep=rep1&type=pdf, 登录时间:2018年7月8日。此外,殖民者通过在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矛盾来分化被征服文明。鉴于一千多年来阿拉伯人较柏柏尔人为强势族群,法国人刻意宣扬柏柏尔民族比阿拉伯民族更具“欧洲特性”,更具民主与世俗的潜质。*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Question in Algeria: Nationalism in the Making?,” in Ofra Bengio and Gabriel Ben-Dor, eds.,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31-52.
综上所述,异族在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呈现出几大特征:其一,各族在征服马格里布地区后均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将自身语言作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并制定人口移民政策以改变当地人口构成,同时注重在当地推广自身信仰、服饰等;其二,由于统治马格里布地区的外族通常来自较远的地中海北岸或东岸,马格里布地区长期作为帝国的边缘行省或属国而存在;其三,外族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权威与控制力集中在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权力分散,家族与部落首领、地方行政长官成为家族、部落或地区内部的实际统治者。
二、 民族主义运动与马格里布地区三国的建立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催化了马格里布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 自发地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
由于各地沦为殖民地的时间先后不一,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时间也不尽相同。19世纪,反法抵抗运动最先在阿尔及利亚爆发。由于殖民势力集中在城市,疏于对偏僻山区的防范,在阿尔及利亚山区聚居的柏柏尔人首先开展了反殖民运动。早期的抵抗力量主要以苏菲教团为单位,呈现出自发、分散的特征。在诸多教团中,卡迪里教团*卡迪里教团是12世纪在巴格达创立的苏菲教团。15世纪时,包括卡迪里教团信徒的一批难民从安达卢西亚逃亡马格里布地区,此后逐渐在当地发展壮大。(al-Tariqahal-Qadiriyyah)领袖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 El Djezairi)所指挥的抵抗运动实力最强。1832~1834年,该教团曾迫使法国承认其对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的管辖权。除卡迪里教团外,其他自发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教团包括拉赫玛尼教团、达尔卡瓦教团等。*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La Conquête et Les Débuts de La Colonisation (1827-187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96; Edmond Doutté, L’Islam Algérien en l’An 1990, Alger: Giralt, 1900, pp. 75-77; George R. Trumbull IV, An Empire of Facts: Colonial Power, Cultural Knowledge, and Islam in Algeria 187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5-126.
同阿尔及利亚相比,突尼斯和摩洛哥被占领的时间较晚,首轮民族独立运动爆发于20世纪以后。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山区等柏柏尔人强烈抵抗的前车之鉴,使得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在突尼斯与摩洛哥山区与农村地区的戒备。因此,摩洛哥激烈的反殖民抗争首先在西属殖民地爆发。在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Abd al-Krim al-Khattabi)领导下,里夫地区的柏柏尔人击退西班牙军队,于1923年建立里夫部落联邦共和国。
20世纪20年代以前,马格里布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地域主义特征。反殖民运动多发生在偏远山区,主体力量为柏柏尔村落。各地抵抗运动具有自发性,且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部署。早期马格里布地区的反殖民运动虽然基于反抗外敌的情感,但尚未形成现代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反抗运动实为“卡比利亚地区的独立运动”或“里夫地区的独立运动”,而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或“摩洛哥的独立运动”,因而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能被称为传统的或前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这一时期马格里布地区的反殖民运动影响力局限于偏远山区,加之斗争力量分散和装备落后,同欧洲殖民者的实力甚为悬殊,极易被各个击破,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埃米尔国”(Emirate of Abdelkader)还是“里夫共和国”(Republic of Rif)都在数年内迅速夭折。
(二) 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大量前往欧洲参加一战的马格里布地区军事人员返回本土,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被带入了马格里布地区,加之当时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广泛兴起,马格里布地区的民族意识显著增强,诸多意识形态各异的现代民族主义团体次第出现。*Michael Willi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ghreb: Algeria, Tunisia and Morocco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Arab Spring, p. 24.随后,马格里布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从乡村与偏远山区转移到城市,其主体也由柏柏尔人转向人数更多的阿拉伯人,争取独立的传统观念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所取代。
20世纪30至50年代,影响马格里布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股:第一,工人阶层为主体、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第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包括突尼斯的宪政党、新宪政党,摩洛哥的行动委员会*1937年和1944年该党先后更名为“民族党与独立党”。,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党、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等;第三,以宗教学者和精英为主体、以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为指导的社团组织,其典型代表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贤哲会*伊斯兰贤哲会(Association of Algerian Muslim Ulema)是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elhamid Ben Badis)于1931年在阿尔及利亚创建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旨在通过回归经训、推动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振兴阿尔及利亚社会。,特点在于宣扬“一族一教(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如伊斯兰贤哲会公开声称“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4-135.。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股力量并非像早期反殖民力量那样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与合作密切。民族独立运动朝着组织性更为严密、活动更为自觉的方向发展。
二战期间,法国戴高乐流亡政权为打击法西斯势力,向马格里布地区民众许诺,只要该地区援助法国人抵抗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法国将承认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独立地位。二战胜利后,法国殖民当局却出尔反尔,最终招致马格里布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集中爆发,三国的多股民族主义潮流出现合流态势。
1946年,突尼斯以新宪政党为核心的各派民族主义力量共同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新高潮,终于在10年后与法国签订《法突联合议定书》,实现了国家独立。1957年,新宪政党*该党自1957年以来长期为突尼斯的执政党。1964年新宪政党更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1988年再次更名为宪政民主联盟。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阿拉伯之春”后,宪政民主联盟于次年解散。成为突尼斯执政党。在阿尔及利亚,1952年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的民主联盟、共产党、伊斯兰贤哲会与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共同组建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解放军,历经多年奋战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阵线也在独立后成为执政党。在摩洛哥,1955年民族主义者组成民族解放军,以阿特拉斯山区为起点同殖民者展开武装斗争,次年收复西属摩洛哥和丹吉尔,并迫使法国废除《非斯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独立后的摩洛哥更名为摩洛哥王国,尽管保留了阿拉维王朝统治,但国家开始实行以国王为最高领袖、国王与议会共同执政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
总体上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现代国家构建的轨迹具有相似性,受到大国干预的影响。但三国具体的国家构建过程亦呈现出个体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均在民族独立后建立了共和国,而摩洛哥则采用了君主立宪制。此种差异与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及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大国的角色密不可分。
首先,阿尔及利亚自16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行省以来就已失去君主制传统,而摩洛哥由于未曾被纳入奥斯曼帝国行省,其君主制的历史存续了12个世纪,当前的执政王朝阿拉维王朝统治了摩洛哥长达3个多世纪。尽管突尼斯独立前也存在君主制,但侯赛因王朝为奥斯曼帝国驻突尼斯行政长官于18世纪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而建,君主制的统治基础不如摩洛哥稳固。其次,摩洛哥君主穆罕默德五世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阶段已积极投身反殖民斗争,较早确立了执政合法性,而突尼斯的侯赛因王朝则与民族主义者保持距离,故而在突尼斯独立后难逃被废黜的命运。最后,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曾支持穆罕默德五世,力保其在摩洛哥的统治*Jonathan Wyrtzen, Constructing Morocco: The Colonial Struggle to Define the Nation, 1912-1956,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9, p. 337.,但在突尼斯君主制的存废问题上却置身事外,也是造成摩洛哥与突尼斯建立不同政体的重要原因。
三、 地缘政治演变对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的影响
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6.,也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现代国家的建设包括基于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基于权力分享的民主国家构建。在地缘政治演变过程中,马格里布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民族关系、文化认同、语言教育冲突和伊斯兰因素,对诸国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构建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地缘政治演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也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6期,第92~94页。。马格里布地区多种文明交汇与碰撞的地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由于地处亚欧非交界地带,马格里布地区极易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造成民族碰撞与冲突。7~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地区后,阿拉伯民族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而作为原住民的柏柏尔人则被边缘化,成为少数民族。19世纪,面对欧洲人的入侵,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一道展开抵抗。然而,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主体民族与反殖民运动的主力,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阿拉伯人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了民族主义运动中“一族一教”的口号,推行自上而下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三国均承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通过兴修清真寺、在全国中小学增设伊斯兰课程推进伊斯兰化进程。阿尔及利亚还将周五(伊斯兰教聚礼日)、周六定为法定休息日。同时,三国均推动公立中小学的标准阿拉伯语教育,增设教授伊斯兰教的课程。由于马格里布地区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标准阿拉伯语授课的教师,三国还时常从埃及引进外教。*Mohand Salah Tahi, “Algeria’s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A Frustrated Hop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6, No. 2, 1995, p. 214.
然而,片面强调主体民族主义的政策使得曾经与阿拉伯人并肩作战的柏柏尔人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柏柏尔文化随之成为边缘文化。马格里布地区诸国不仅没有制定保护与推广塔马齐格特语的政策,而且阿拉伯政客常常抨击柏柏尔民族流行的苏菲派是落后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主体民族极易受到“次”民族主义的挑战,后者试图“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原住民,柏柏尔人长期对阿拉伯人的入侵与压制极为不满。此种情绪在法国人“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被进一步激化。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柏柏尔人作出过巨大贡献,却没有在独立后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于是,反殖民运动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在民族独立后立刻消退,而是在柏柏尔人聚居地得以延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爆发过多次柏柏尔人的反政府运动,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运动是1980年的“柏柏尔之春”与2001年的“黑色春天”。在摩洛哥,“人民运动党”、“柏柏尔民主党”等柏柏尔政党纷纷兴起。柏柏尔人分别在1994年与2004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并与摩洛哥政府发生冲突。
第二,统一文化认同的缺失。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构建“共同文化”是民族构建的一项关键性任务。然而,多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使马格里布地区形成了包括非洲地缘特性、阿拉伯民族特征以及地中海文明特质的复合型文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这也是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独立以来,长期在本土文化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所在。尽管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独立以来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标准阿拉伯语教育,但不少政客、学者与民间人士认为,标准阿拉伯语并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日常用语,也是一种强加于本土民族的“外来语”。在他们看来,马格里布地区方言作为当地人的习惯语言,并未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政客提出“方言进课堂”的议案。而更多政治精英主张把法语和法国殖民统治区别对待,认为学习法语有助于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马格里布地区良好的法语基础恰好是该地区相较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优势,因而应当继续保持而非放弃法语教学。“方言派”、“法语派”的主张受到了地区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后者常常援引法国殖民者曾经允许方言教学、打压标准阿拉伯语的做法,试图说明“方言派”与“法语派”一样,是殖民者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在官方主导下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阿拉伯语化运动,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掌权精英多为具有法国留学背景、熟练掌握法语、崇尚法国文化的人群,他们以法语为骄傲,在行政管理与交流中依然使用法语,并将自己的子女从小送入双语学校接受教育。于是,阿拉伯语化运动的结果是使法语成为“贵族语言”,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和影响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在突尼斯,19个国家部委中仅有3个部委完全使用标准阿拉伯语文书。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虽然多数部门都要求使用阿语文书,但熟练掌握法语几乎是入职政府机关的必备敲门砖。对于仅在公立学校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高等教育的选择范围极为狭窄,阿拉伯研究与宗教研究成为他们的主要出路。至于就业,不懂法语让他们几乎与体面、高薪的职业绝缘。*Mohamed Daoud, “Arabization in Tunisia: The Tug of War,”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2, No. 1, 1991; George Joffé, “Trajectories of Radicalisation: Algeria 1989-1999,” in George Joffe, ed.,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and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18-119.
第三,民族与文化自信的缺乏。文化自信与民族振兴是构建民族认同的必由之路。多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使不同民族与文化进入马格里布地区。在此过程中,该地区在不同文化碰撞中陷入迷茫,以至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独立后,无法像埃及、伊拉克,乃至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那样从本土文化中进行民族寻根,从而获得文化自信。*黄民兴:《论20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第16页。至于“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等马格里布地区历史上的辉煌时刻总是与殖民侵略记忆相伴,属于“他人的辉煌”,而非“自我的辉煌”。
与此同时,多元异质文化的交融在塑造马格里布地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之余,也让该地区陷入族群归属的尴尬。诚然,共同的教义和信仰基础,深厚的民族渊源,特别是共同的历史和命运,使当代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具有一定的认同度。但马格里布地区诸国城市中,多数人口的法语好过标准阿拉伯语的文化现状又使其在地中海东岸国家面前感到某种文化自卑。此外,马格里布地区三国至今仍属于法语圈国家,但法国未曾平等对待马格里布国家,甚至连已经移民法国的北非裔居民也常常遭遇法国社会的歧视。如此一来,马格里布地区诸国陷入既非“柏柏尔国家”,亦非典型的“阿拉伯国家”,更不属于“西方国家”的尴尬境地。
(二) 地缘政治演变对民主国家构建的影响
除了民族国家构建,民主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另一个基本构成形式与重要任务。作为现代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实质在于权力的制衡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将世界各民族的国家构建方式分为公民模式(civic model)和族群模式(ethnic model)两种,认为后者广泛存在于亚非和东欧地区,其特点在于对血统和谱系的认同超过领土,对语言和习俗等本土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1991, pp. 11-15.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变对于该地区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现代关系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从古罗马到法国殖民统治时代,异族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集中在部分北部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呈现权威破碎化结构。这一地缘政治演变的遗产在当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三国依然清晰可见,家族认同、部落认同乃至地域归属感普遍高于国家认同,不利于现代民主与多元文明的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起,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均开展了政治民主化试验,然而成效不彰。这既是由于执政精英往往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选举舞弊与操纵屡见不鲜,也与民主文化缺失导致的政治参与不成熟密切相关。2011年“阿拉伯晴雨表”在阿尔及利亚的民调数据显示,55.3%的人表示会考虑候选人是否与本人来自同一家族或部落。*“Data Analysis Tool”.于是,先天性的血亲关系与地域归属感超过了后天性基于利益与理念而建立的关系,致使选举政治与政党政治带有鲜明的传统血缘色彩与庇护特征。
2010年底“突尼斯革命”爆发后,突尼斯政府全面解除建党禁令,执政党也随着宪政民主联盟的解散而不复存在。然而,就在突尼斯开展选举之际,该国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但却鲜有共同政治目标与明确施政纲领的现代政党。大多数政党规模极小,有的甚至是仅由数十名乃至数名来自同一家族、部落或地区成员建立的亲友团式的“泡沫党”,导致突尼斯政坛上政党频频重组,大大阻碍了突尼斯政党政治走向成熟。
第二,伊斯兰体制的遗存不利于世俗化改革与政教分离制度的建立。从7世纪阿拉伯帝国攻占北非到19世纪法国殖民统治之前,马格里布地区长期实行伊斯兰政教合一的体制,国家政治首脑与宗教领袖同为一人,宗教学者具有司法解释权与裁定权。摩洛哥阿拉维王室以圣裔后代自居,并籍此获得政权合法性。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由于反殖民主义运动后期以“一族一教”为口号,且独立后新兴政权加强伊斯兰教育,致使两国难以推行彻底的世俗化政策。20世纪50年代突尼斯政府将达尔文进化论与大爆炸理论纳入理科教学内容,2005年阿尔及利亚教育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伊斯兰科目等世俗化措施,都在本国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乃至抗议。*Mohamed Benrabah,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Algeri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Issues,” Language Policy, No. 6, 2007, pp. 225-252; Muhammad Faour,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Pluralism in Egypt and Tuni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3, 2012, http://carnegie-mec.org/2012/08/13/religious-education-and-pluralism-in-egypt-and-tunisia-pub-49078, 登录时间:2018年7月8日。“阿拉伯晴雨表”2011年民调显示,70.6%的阿尔及利亚民众认为候选人的宗教虔诚度是其投票时考虑的重要因素;2013年民调显示,46.2%的阿尔及利亚人、49.1%的摩洛哥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基于伊斯兰教法、无选举或政党的体制适合本国。同一民调还显示,58.1%的突尼斯人、76.3%的阿尔及利亚人、77.8%的摩洛哥人认为政府与议会应当制定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法律。*“Data Analysis Tool”.
第三,弱者心态、保守心理与媚外心态并存阻碍了政府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与外族入侵给马格里布地区带来多次战乱与动荡,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与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一方面,马格里布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弱者心态与对大国的恐惧心理,将国家目前的发展困境归咎于外族入侵与殖民历史。同时,不少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建议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乃是“另有阴谋”,倘若本国政府采纳此类建议会有损于本国利益。“阿拉伯晴雨表”2013年民调显示,当被问及阿拉伯世界发展受限的原因时,仅有11.7%的阿尔及利亚人、25.6%的摩洛哥人、37.7%的突尼斯人认为完全是内部因素所致,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是外部因素所致或内外因素兼有导致发展受限;当被问及能否接受外部对于改革的要求时,43.4%的摩洛哥人、55.8%的突尼斯人、80.9%的阿尔及利亚人表示不能接受。*“Data Analysis Tool”.此种心态被不愿放权的统治精英加以利用与放大,形成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地区国家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马格里布地区长期缺乏民族自信,导致当地居民在恐惧大国阴谋的同时也对大国充满向往。2010年盖洛普民调显示,在希望定居他国的人群中,75%的阿尔及利亚、60%的突尼斯人与50%的摩洛哥人表达了移居法国的愿望,而排行第二的理想目的国是沙特阿拉伯。*Neli Esipova and Julie Ray, “One in Four in North Africa Desired to Migrate before Unrest,” Gallup News, April 29,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7344/one-four-north-africa-desired-migrate-unrest.aspx, 登录时间:2018年7月8日。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曾经殖民马格里布地区的西方国家,另一个是典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两国都是地理位置相邻、马格里布人接触较多的地区大国。据突尼斯外交部直属的海外突尼斯人办公室2011年公布的数据,目前突尼斯海外移民人口中,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者占比25%,从事商业活动者占比22%,医学行业者约占比11%。*“Répartition des Compétences Tunisiennes L’ Étranger pas Spécialité,” Office des Tunisiens l’Étranger (OTE), 2011, http://www.ote.nat.tn/fileadmin/user_upload/doc/Repartition_des_Competences_tunisiennes_a_l_etranger_2011.pdf, 登录时间:2018年7月8日。可见,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占据马格里布地区海外移民的主力军,而大量资产与人才的双重流失,不利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四、 结 语
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变是横向维度的文明碰撞、外族入侵历史与纵向维度的马格里布民众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交互影响的结果,对该地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受外族入侵者的民族政策以及历史编纂的影响,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的认同呈现多元性与模糊性特征,并存在对于柏柏尔、古罗马、阿拉伯、法国及非洲等多元异质文化的认同,缺乏统一的文化认同。当代马格里布地区不仅难以建立政治文化共同体,而且陷入了文化定位的尴尬与身份归属的缺失,从而导致民族文化自信的极度缺乏。其次,多次外族入侵史引发弱者心态与媚外心态并存,外族入侵者“外紧内松”的统治模式导致前现代关系根深蒂固,而伊斯兰体制的历史遗产则致使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体制难以确立。这些因素也是当前阻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三国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马格里布地区诸国实现了主权独立,形成了边界较为明确的国家,但各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依然漫长而曲折,面临多重困境。其一,在多种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和大国频繁干预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部族社会和地方政治元素遗留至今,造成当前马格里布地区高度分裂型和冲突型的社会。其二,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革命”后,法国、美国、土耳其等世界强国与地区大国积极介入该国事务、输送资本与扶植代理人,凸显了当前马格里布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围绕该地区展开的大国博弈依然激烈,并对诸国内政产生深刻影响。更糟糕的是,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政府的失能加剧了三国的国家构建困境。后“革命”时代的突尼斯面临恐怖袭击频发、安全秩序混乱、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等困境。其邻国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政权虽然避过“革命”,但布特弗利卡总统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2011年所承诺的政治经济改革至今进展缓慢,且两国也同突尼斯一样面临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问题,以致近年来两国抗议示威时有发生。政府执政能力的孱弱严重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增加了三国建立国家认同与民族自信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如何打破现代国家构建的困境与国家政府失能的恶性循环,成为当前马格里布地区诸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和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