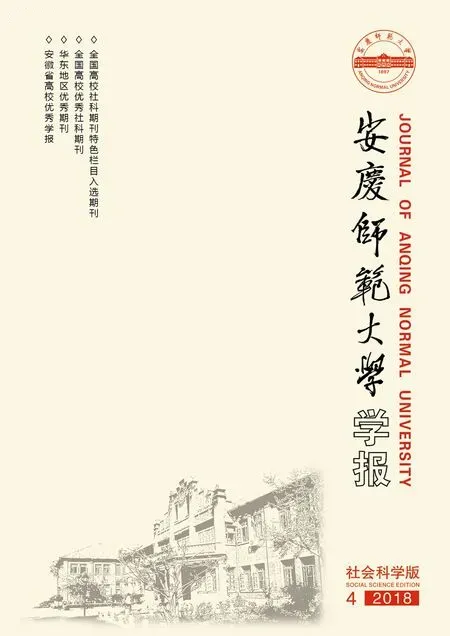建国初期中小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
——以山西省档案馆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张耀耀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63)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改造的热潮。教育界也不例外,国家提出实施劳动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中小学生受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影响,起初大多数人对劳动教育并不能完全接受,甚至公开反对。本文以建国初期中小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为切入点,根据山西省档案馆的调查报告,分析中小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及原因,进一步探究建国初期中小学校的学生、教师与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与看法。
一、建国初期中小学生接受劳动教育的情况
自从新政权提出在中小学校实施劳动教育的方针后,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学校生活中都陆续融入了劳动的元素。1954年贯彻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精神,长治市各小学校开始加强对学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与就业)”的教育活动,掀起向董加耕、徐建春、邢燕子等全国优秀回乡知识青年学习的高潮[1]。1954年,学校针对毕业生轻视劳动,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倾向,开展了应届毕业生应如何对待升学和就业的问题讨论,号召小学毕业生回乡当第一代新式农民。同时把劳动课正式列入课程表,对小学生进行生产劳动教育[2]。尽管劳动教育已经开始实施,但对于参加劳动生产的学生们并不是乐意接受,甚至公开反对。太原第三中学、太原第五中学和太原市第十一完全小学等几所学校就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陕西省教育厅“根据初步调查、了解,三中全体师生一般说对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认识态度是不够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3]38-42。对于即将毕业的初三年级学生来说,劳动教育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他们轻视体力劳动,因此反对参加劳动生产。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他们认为劳动教育暂时不会临到自己身上,对劳动教育漠不关心。劳动教育实施初期,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响应,受到了来自不同背景学生的敌视与漠视。
(一)主动接受劳动教育
面对劳动教育时,一些学生选择了积极接受,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山东掖县后吕村完全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徐建春主动接受劳动教育,参加了农业互助组,由于表现优秀而加入共产党。当《人民日报》采访她时,她这样说:“没有党我会有什么呀?旧社会我是个被人瞧不起的穷孩子,是党解放了我,给我上学的机会,下学后,我曾一度不安心农业生产,是党培养、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正确道路。”[4]徐建春的报道传递了新政权的暗示:学生在毕业之后,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到农村参加生产活动。太原五中初十八班学生张思贞说:“现在国家干部很缺乏,为了祖国工业化,愿意服从祖国分配”;“上学为了什么,也是为了工作”。以太原五中初十八班为例,这一类仅有4人,仅占全班人数45人的8%[3]43。可见大多数中小学生并没有接受劳动教育。
除主动响应劳动教育号召外,还有一批学生因家庭条件有限或学习成绩不好,升学希望比较渺茫,愿意参加劳动生产。如同在太原五中初十八班的白俊英说:“我家有姊妹五个,靠父亲一人赚钱,家中很困难,供不起念书,所以要求参加工作,毕业后我要去工厂工作,学医,不去农村去。”[3]43由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许多农村家庭并没有能力供子女继续升学,但也不愿意子女回家种地,希望国家分配到工厂当工人,这反映了建国初期广大农民对工人政治地位与经济条件的向往。同在五中初十八班的许培兰说:“我爸爸在电业局工作,我家有房,就只有我、妹妹二人,家里也不困难,反正我是考不上高中了,五中的社会主义大楼我住不上,也希望他不要修成。如果分配我到电业局作个轻快职员还可以,如果分配不合适,让我去农村,宁愿休息一年,也不去当工人和农民。”[3]43这一部分学生由于自身条件限制,选择劳动教育正好符合其自身利益,并不是真心实意愿意接受劳动教育的。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生由原来的轻视劳动逐渐转变为参加劳动生产,并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态度。太原三中初三年级两个班共101人,其中对劳动生产和劳动教育的态度有所转变的有12人,他们能够主动服从组织安排,参加劳动生产,并带动自己的家人参加劳动。如初九班女同学胡瑞琴,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当劳动教育开始实施后,其母亲让她好好学习,继续升学,不想让她上师范学校,更不愿意让她参加劳动生产。其姨夫也劝告她好好学习,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考,不能参加劳动生产与合作。胡瑞琴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党团教育,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觉得自己有责任参加劳动,说服母亲与姨夫同意自己的想法。
建国初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无法容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继续读书,因此,急需一大批学生分流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徐建春等人的行为选择,无疑成为了对国家政策一种完美的诠释,那就是:虽然回乡劳动,但仍然可以成为模范。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流动方式发生变化,读书做官不再是唯一的出路,像徐建春一样的中小学生毕业后积极投身于农业生产,成为劳模,从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由于积极劳动获得荣誉,成为国家宣传的楷模,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二)对劳动教育摇摆不定
无论自己内心的想法是如何,一部分学生至少在表面上都接受了劳动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对劳动生产、劳动教育的认识是片面的,思想紊乱,过于强调个人志愿、兴趣。在建国后,在国家权力高度向社会扩张的背景下,个人无法与国家政策相抗衡。一些学生虽然内心不想参加劳动,但不敢公开反对国家的劳动教育政策。他们由公开不满转向隐蔽,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到一些问题:怕回家生产被人耻笑;体力劳动太苦;种田不如升学,将来当干部、当专家的希望没有了。非农家学生反映:家中无田无地,到哪里去生产?家庭是地主成分的学生反映:回去生产会不会当地主看待。一些持观望态度的学生担心自己受到别人的嘲讽,表面上接受劳动教育,但内心却想读书继续深造。在建国初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学生也自然感受到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土地改革、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让学生感受到只有向国家主流价值观念靠拢,才能在社会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本。因此,有些学生虽然并不认同劳动最光荣的理念,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只是在观望和徘徊,寻找合适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
太原第三中学初六班女学生张先举,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家长劝她学技术,自己也觉学技术比较不错,后参加了劳动生产的教育后,认为应服从组织分配,但个人创举与国家利益始终是脱节的。她只愿去工厂,而不愿去农村。看见她妹妹表示高小毕业后参加农业劳动,自己也想参加劳动生产。但又想考学校,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只好先考学校,考不上再参加工厂,工厂不行再回农村。同样的案例不只这一个,初九班男学生陈绍泽,中农出身,父母劳动一辈子,受苦受罪尽量供他读书,一心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母亲经常对他说:“你要好好念书,看人家你叔叔们,多么幸福,你看你父亲受了一辈子罪,还是不能过好的生活。”“好好念书,改变改变门分。”总路线学习与劳动教育开始后,他心中一再不安。自己不愿当工人、农民,想当技术员,想升学,但是又怕同学们笑话自己思想太落后,一直拿不定主意。
像张先举和陈绍泽等,在对待劳动教育的认识上态度不够坚定的学生占很大一部分。他们强调个人志愿,并没有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进工厂、去农村成为这类学生的最后选择。这说明劳动教育实施初期,只是追求表面的顺从,并未从思想上对中小学生进行系统的普及。
(三)抵触劳动教育
建国初期,中小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仍然轻视劳动,对劳动生产、劳动教育有抵触情绪,埋怨政府不多设立学校。山西省太原三中初三学生坚决不参加工、农业生产,亦不服从组织分配者共33人,占两班总人数101人的32.6%。这说明仍有相当多的学生不想参加劳动,存在排斥劳动教育的心理,认为劳动是下贱的、没有出息的事情。参加劳动是“大材小用,埋没人才”,“一辈子即完了”,“没有出路”。有的学生说:“我怎么早活这些年,如果晚生十五年,就可以马上到社会主义享福了”;有的学生认为体力劳动不是我们念书人所能干的,就是干的话,也干不好;有的学生愿意当作家,当工程师,挣钱多,生活舒服[3]38-42。
太原三中初六班学生孙志武,资本家出身,家境殷实,平时生活散漫,功课不好,不参加学校课外活动及任何体力劳动,怕参加农业劳动,后来把个人户口由郊区孙家寨移到南肖墙。听李部长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后说:“叫谁回去?老子就不回去,叫回去,非把教育局的门给他砸烂不可。”初六班学生吴履倍,太谷延龄营老板儿子,说:“考不上学校就回家,不参加农业生产。”初九班学生张仁杰说:“考不上学校休息一年”,“明年考不上再休息一年”。初六班女生文陶,老板的老婆,平时不用功,功课不好,说:“考不上即回家当太太。”初九班程鸿,资产阶级出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升学,他说:“师范也可以,要叫我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死也不干。‘组织分配’我从来就未想过。”[3]38-42这一部分学生公开反对参加劳动,发布一些抵触言论。
二、学生复杂思想存在的原因
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这些态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国家不能用更多的财力、人力来办更多的学校;其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建国以前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读书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实现向上流动。但新政权建立之后,国家对劳动和工农态度实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这让一些学生很难短时间内实现思想转变。另外,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对劳动教育方针是否贯彻到底。重视劳动教育的学校自然能够从教学的方方面面融入劳动教育,老师也能够起到表率作用。
(一)国家层面
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贫苦家庭子女还获得了上学识字的机会。然而,随着中小学生人数的增加,即将毕业的中小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升学困难,有限的大中专院校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升学需求。据统计,“1949年底,山西的普通中学为34所,1952年发展到105所,到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山西全省的普通中学数翻了两番,仅高中就发展到120余所。”[5]“1949年,山西大学的招生人数仅有228人,但是到了1956年,招生人数就增加到1 301人”[6],“山西农业大学1952年招生人数59人,1956年增加到381人,”[7]“太原理工大学1953年招生人数338人,1956年招生人数达984人”[8]。纵观山西几所重点高校,学校的数量和学校的招生人数虽然增多了,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广大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1949年全区有公立小学4 785座,其中高完小90座,学生总数199 962人,其中高级生8 524人,到1953年底,公立小学已增至5 478座,其中高完小240座,学生总数达288 160人,其中高级生28 716名,学校数比1949年增加12.7%,其中高完小座数增加16.7%,学生总数增加三分之一左右,而高级生比1949年增加二倍半。”[9]据新华社报道:“山西省今年暑期高小毕业学生有106 300多人,加上去年近3万名未升学的共达136 000多人。全省今年初中毕业生有9 000余名,超过今年高中招生名额1 000多人。今年初小毕业学生更多,全省共有266 000多人,而今年高小仅能招收112 300余名。”[10]与此同时,中小学毕业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与政治觉悟,这对于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都是有及其重大的意义的。但是受现实条件的影响,教育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只有使工农业的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办更多的学校,招更多的学生。因此,面对“升学”与“劳动”的矛盾中,学生一时难以接受劳动教育政策。
(二)家庭
家庭是学生生活的场所,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会决定学生的个人思想。家长的出身、言行、教育等都会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也一样,尤其是在强调阶级出身的建国初期,家长对劳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
1.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如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军官)一般强调不劳而食、贪图享受,用仇视劳动、仇视劳动人民、升官发财的思想教育子弟,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完高等教育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这种落后思想灌输其子弟。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子弟轻视劳动,尤其鄙视体力劳动。如太原三中初九班学生梁大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走在街上看见拉洋车的,指着对他说:“你将来想坐上洋车就要好好念书,要想拉洋车你看着办吧!”“你考不上学校一辈子就完蛋了”[3]40,因此梁十分轻视劳动,学习上也怕用脑子。这些学生出身地主或者资本家家庭,父辈生活的经验已经让他们形成了通过读书强化社会地位观念,因此,他们在面临劳动教育时,存在抵抗和排斥心理。
2.农民及小生产者。农民及小生产者家庭,因为在旧社会受压迫,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认为自己劳动是受苦受罪,没出息,是没奈何的事。每日省吃俭用,积一点钱供子女上学,希望其念书“成”人,改变门分,光宗耀祖,不赞成孩子回家生产,以为那是给老子丢人。如初六班学生王思若的父亲时常教育他:“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靠天吃不好,靠地吃不饱,要想吃的好,还是读书好。”[3]41因此,处于尊崇文化、劳动辛苦等原因,农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即通过读书实现向社会的上层流动。劳动教育主张学生放弃升学机会,参加工农业生产,这与农民家长的期望相反。当自己的子女接受劳动教育时,他们并不支持。学生受家长影响,在毕业选择方向时自然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志愿,因此在接受劳动教育时多犹犹豫豫,摇摆不定。
3.工人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当家做主。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是相当不错的。大多数工人家庭者认为升学最好,升不了学参加劳动也行。如王莲香父亲说:“升不了学,就参加工作,同时家庭经济亦困难,参加工作可减少我的负担。”工人子弟如果参加劳动的话还是进入工厂,与父辈一样当工人,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大多数响应国家号召,进入工厂参加劳动生产。
4.干部。干部家庭,这部分人比较复杂,主要看干部出身成份,觉悟不同。一般不轻视劳动,但希望深造。如魏耀明父亲说:“我没文化,感到困难,你好好念书学习文化。”赵瑜先的父亲(老干部)说:“你不好好念书,我不管,你当家庭妇女。”“像你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写的两个爬爬字,提茶壶也没人用,将来也当不了个啥。你看我工作这样困难,就是没文化的过。”陈苏海父亲(老干部)说:“文化低工作能力差,好好念书吧,组织分配你,你就服从。”[3]41干部家长都有过穷困的生活经历,很多人因文化程度有限工作吃力。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他们现在有能力提高自己后代的文化水平,所以经常鼓励子女好好学习。干部子女受父辈影响,不轻视体力劳动,但更有条件升学。因此,他们参加劳动教育,同时坚持学习。
(三)学校领导及教师
学校是培养学生的重要场所,校领导和老师的态度决定了劳动教育能否顺利实施。建国初期,学校领导与教师来源复杂,对于劳动教育普遍不够重视,很少有计划、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影响了中小学生思想改造的进度。教师对劳动教育的位置很不明确,只是在课堂上进行一些教条的讲授,也正如太原三中六班学生王思茂反映:“一听就知道在进行劳动教育”,缺少说服力和感染力。
1.学校领导。学校领导上对劳动教育也不够十分重视。太原三中有些了解情况的同志去问温校长,他说:“这几天学校正忙,劳动教育我掌握的材料不够,过几天再说吧!”[3]41学校校长不主动了解劳动教育的实施细节,也没有对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反而来回推诿,拖延时间。领导不重视,关于如何贯彻劳动教育也具体掌握的不够,既不能将上级关于如何下一步进行劳动教育继续推进,又无法实际中出现的问题立刻上报,使得有关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出现断层。学生参加劳动教育主要是在学校进行的,学校只是做表面工作,学生也就应付了事,不重视劳动教育。
2.长年从事教育工作者尊重脑力劳动,但是轻视体力劳动。虽对“饱食终日,不劳而获”的人们存在着卑视和轻蔑,但对劳动勇敢的劳动人民在他们眼中是“辛苦终日,仅得一饱”的人。他们受旧思想的影响,对劳动与劳动人民不够充分尊重。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弟“成材”,能有一个“高尚”的地位。这些教师课上课下的一言一行中都鼓励学生升学,不要参加劳动生产。
3.专业教师认为“工作有贵贱”,“职业分上下”,“不劳而获是清闲纳福”,“唯利是图”是最高标准。经常埋怨自己挣的钱不够,作的活儿不见少。对劳动教育抵触情绪很大。
4.青年教师对劳动与劳动教育不明确,认识不够,先初有转变。如美术教师王鸿宝说:“过去只知道教育学生当红色专家,不知道教育学生成为劳动中的能手。”他曾为一个年轻工务员不能升学而惭愧,认为劳动没有出息。教导员张珩,在上政治给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时说:“让你们到农村去是当会计,到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工作,并不是让你们种地”。教导员杨惠兰说:“不能升中学,住师范也好,叫我妹妹去工作,我就想不通。”[3]42张、杨二人想升学,继续深造,不愿当教导员。语文教师李如云认为代语文课改作业太苦重,不如代史地清闲,想转教史地。
三、结 语
总之,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改造非常复杂,仅就中小学生对劳动教育的不同认识就可以看出,这反映了家长、学校领导与教师等多方面对劳动与劳动者的态度。通过分析中小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态度及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中小学生对劳动的态度不一,这主要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像其它方面的改造一样,中小学生爱劳动价值观的树立不可能立见成效,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