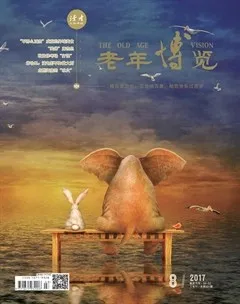古诗词里的喷嚏
在英国留学那会儿,每次我打个喷嚏,旁边的人就会脱口而出:“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打喷嚏那么微不足道的生理反应,怎么还要惊动上帝他老人家?原来,这跟西方人的迷信有关。有人说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而打喷嚏就是黑死病的一大症状,因此一旦某人喷嚏连连,周围的人便都陷入惊恐与同情中,只能搬出上帝来安慰这位时日无多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人在打喷嚏的时候灵魂也会被“喷”出来,所以要赶紧念叨声上帝,让他帮忙把灵魂留住。
同样是打喷嚏,中国人则绝不恐慌,相反还会有点沾沾自喜。因为按照民间的说法,打喷嚏说明有人在想念你,打喷嚏的次数越多,想念的程度就越深。这个说法的历史相当悠久,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里有一首名為《终风》的诗,说的是一个女子嫁了个暴虐无常的丈夫,丈夫离家而去,妻子“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漫漫长夜无心睡眠,一边数绵羊,一边痴痴地想:那冤家最好现在不停地打喷嚏,这样便知道我在想着他了。女子抓不住那个风一般的男子,只能祈祷,愿自己无穷无尽的思念化作他的连连喷嚏,让两颗隔阂已久的心能有一点感应。
打喷嚏原本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举动,偏偏出现在了被尊为“经”的儒家典籍中,于是文人骚客便也堂而皇之地把它写进了诗词里。比如苏东坡。有一年的正月初一,东坡在外地出差,路过丹阳时想家、想朋友了,就写了首诗,最后一句很可爱:“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我这糟老头子还有谁惦记啊?可要是真无人惦记,我今儿早上怎么喷嚏打个不停呢?!还有黄庭坚。他的朋友即将离去,在告别晚宴上,黄庭坚提笔写诗为友人践行,其中有这么一句:“举觞遥酌我,发嚏知见颂。”以后你喝酒的时候别忘了举个杯,就当远远地给我敬酒了,而我只要一打喷嚏,就晓得正被老兄你念叨着呢。
还有人因为不打喷嚏而埋怨别人不想自个儿的。辛弃疾在与友人唱和的词作《谒金门》中就说:“因甚无个阿鹊地,没工夫说里。”—“阿鹊”不是鸟儿,而是打喷嚏的拟声词—我一个喷嚏也没打,难道是你不想我?没料到“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也有如此温柔娇憨的一面。
除了朋友之外,男人最希望被心爱的女人牵挂。一般男人喜欢幻想女人“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总之是想自己想得茶饭不思、粉泪盈盈。宋朝诗人梅尧臣却是个例外:“我今斋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他出差的时候,希望年轻貌美的夫人在家大打喷嚏,这样便能感知自己的思念—多么贴心的暖男哪!相比之下,《笑林广记》里的乡下男人就太没风情了。他从城里回家,告诉妻子:“我在城里打了无数喷嚏。”妻子说:“皆我在家想你之故。”一日,男人挑着粪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连打几个喷嚏,差点掉到水里,便骂道:“这骚婆娘,就算想我,也得看看在啥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