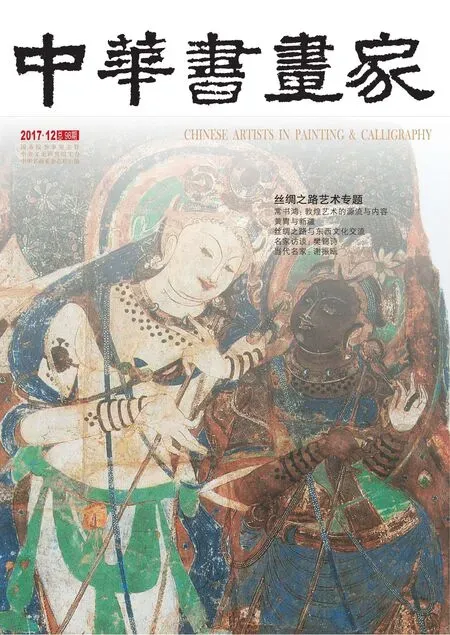《李柏文书》与楼兰书法
□ 李 青
《李柏文书》与楼兰书法
□ 李 青
《李柏文书》是指1909年橘瑞超在罗布泊考察时,在楼兰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书信草稿,以及与这两件草稿同时出土且文字多有近似的40馀枚文书残纸。从内容和书体来看,在40馀枚残纸中,至少包括两封与上述信件内容一致的部分书信残纸。这也就是说《李柏文书》至少书写了4个草稿。这些实物发现时已揉成团块,多数残纸似在书写完后不久即撕成碎片。1914年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史料图版(2)—史料图版(8)刊布了《李柏文书》的全部资料。1962年日本法藏馆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卷卷头图版第13至19刊布了李柏两封书信稿及39件残片,但内容不及《西域考古图谱》所载资料完整。由于对于《西域考古图谱》所载资料的残纸件数的划分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定(即有些残纸有学者认定是1件残纸,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应是2件残纸),因而也就很难确定《李柏文书》残纸的全部件数①。
《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中所出现的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由于《李柏文书》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文书十分重视。同时,围绕着《李柏文书》之发现地、书写年代等问题,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对于《李柏文书》的艺术研究,必然离不开对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整体把握。

楼兰L.A古城出土华督与五月二日文书

楼兰L.A古城出土三月一日文书

楼兰L.A古城出土仓卒不备与永嘉六年文书
关于《李柏文书》的出土地问题是李柏文书研究的关键问题。1909年3-4月间,橘瑞超由焉耆、库尔勒南下,穿过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汇合点,于3月上旬进入罗布泊荒原,并在楼兰一带进行了挖掘,获得了《李柏文书》。当时橘瑞超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并未受过考古训练,他所获得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许多文物当时并未做详细记录,而其本人的日记又失于火灾,因而《李柏文书》出于何处遗址,即成为历史悬案。1909年4月13日,橘瑞超离开罗布泊之后,他将《李柏文书》等文物交由同行者野村荣三郎运回日本,自己则赴英国伦敦。在伦敦橘瑞超会见了斯坦因,并向斯坦因出示了《李柏文书》的照片。他们两人都认为此组文书应出自楼兰L.A古城。1914年日本刊行的《西域考古图谱》及1937年刊行的《新西域记》都以野村荣三郎所说《李柏文书》出自孔雀河岸的一个废墟中的说法加以解说。对此,身在日本的橘瑞超并未发表不同意见。1914年王国维在编著《流沙坠简》时又针对《李柏文书》中出现的“海头”地名进行了考释,他认为《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在楼兰“海头”城,因而指出楼兰与海头是两个不同的古城。L.A城应为海头而不是楼兰古城②。1959年5月当《李柏文书》出土50周年纪念之际,日本学者森鹿三会见了橘瑞超,询问了斯坦因所说《李柏文书》出土于L.A城的由来,橘瑞超提供了一张他记忆中当时出土文书地点的照片。森鹿三根据橘瑞超提供的照片资料与斯坦因1914年2月在罗布泊荒原发现的L.K城图片相对照,认为两者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李柏文书》出土于L.K古城。森鹿三的论文《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发表在《龙谷史坛》第45期,并在同年出版的《书道全集》第三卷《西域出土的文书》一文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并附有橘瑞超提供的出土地实景图片③。由此,引发了关于《李柏文书》出土地以及楼兰城的位置等问题的争议,诸多学者如ƒ一雄和片山章雄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1968年橘瑞超又清楚地告诉金子民雄,谓《李柏文书》是在楼兰佛塔附近发现的④。《李柏文书》究竟是在何地发现的?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应在L.K古城⑤,孟凡人和余太山等则认为《李柏文书》应出自楼兰古城,也就是L.A古城⑥。同时孟凡人还引征冯承钧在《鄯善事辑》一文的观点认为楼兰L.A古城即为海头城。


楼兰L.A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残纸

楼兰L.A古城出土六月廿九日文书
上述诸家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考古、地理方面进行论证的,而笔者认为,对文书的书法风格之图像比较亦应是断定文书出土地的不可忽视的证据之一。从书法风格的比较结果来看,《李柏文书》书体形式和书写风格与楼兰L.A古城出土的残纸文书书法多有近似之处,而且出土地点亦与斯坦因所记《李柏文书》出自L.A.Ⅱ.ⅳ的小房间(三间房之一)为同一地点。其次,被认为有可能出自LK古城的简纸文书除《李柏文书》外,其他仅存5件木简,而这5件木简之书风亦与楼兰L.A所出之木简书法近似。就连认为《李柏文书》出自L.K古城的学者侯灿也指出:
我们将4件文书(指与李柏文书共出的残纸)与楼兰古城和楼兰其他遗址出土简纸文书进行比较,注意到它们与L.A.Ⅱ.ƒ出土的一些纸文书有关联或相似之处。如“已呼”中的“烧奴”其人,在孔纸25.1中就有出现,孔纸33.1中连续出现3次,成为重要人物,而且字体写法极为相似;又如“已呼”、“何奈”中的“何”字,与孔纸7、孔纸8、孔纸9中的“何”字十分酷似,且“奈何”字句在孔纸7、孔纸8中也反复出现。因此,我们认为此4件文书,当与L.A.Ⅱ.组点中的某些简纸文书有联系,似应出自L.A.Ⅱ组点。⑦
由此可推测,如果认为《李柏文书》出自L.K古城,那么L.K古城所发现的汉文简纸文书就仅有《李柏文书》残纸及其他5枚汉字木简⑧。这种状况岂不是有太大的遇然性和孤立性吗?何况《李柏文书》出自LK说的最关键证据,即是橘瑞超所提供的出土地照片。橘瑞超在《李柏文书》发现50年之后拿出一张并无特殊标志的照片来证明文书之出土地,这是极不可靠的。橘瑞超所提供的照片的确与斯坦因所摄L.K遗址地貌相似,问题是这个无任何人工痕迹的雅丹地貌在罗布泊随处可见,事隔50年,橘瑞超尚能有惊人的记忆指出文书出土于此,而在50年间却始终对此缄默,值得怀疑。何况在1968年橘瑞超又说文书出自楼兰佛塔附近⑨。看来橘瑞超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2005年,陈凌根据新刊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L.A古城所获的5件汉文纸本文书的状况,与《李柏文书》作了对比,指出,斯文·赫定这5件文书中有一件为《张超济信稿》,该文书中有“太平在近”之语,此句与《李柏文书》一同所出之《平在近残纸》在词语和书风上极为相近,因而作为同一批收集品《李柏文书》无疑也应出自L.A古城⑩。这又为《李柏文书》出于楼兰L.A古城说增添了新的依据。
结合上述有关学术争议之观点,并从书法艺术风格上进行比较推断,笔者认为孟凡人等所持《李柏文书》应出自L.A古城是有一定根据的,而楼兰L.A古城亦别称“海头”,这已得到冯承钧和孟凡人等人的充分论证,此不赘述。
文献所载李柏之名出现在《晋书·张轨传》中,李柏与前凉张氏政权有一定关系。西晋永宁年间(301-302),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其时“八王之乱”已开始,诸王混战,局势极不稳定。张轨出任凉州,即有“阴图据河西”之意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之后,张氏世有凉州,虽然效忠晋室,实质上已成割据政权,史称前凉,都姑臧。张轨亡后,相继有张寔、张茂执政,时间都较为短暂。至张骏时期,前凉政权达到了一个昌盛阶段。张骏字公庭,其执政时期勤修政治,慎于刑赏,以致“刑清国富”,“士马强盛”。先后征服龟兹、鄯善等国,威行西域。李柏本为晋西域长史,驻兵楼兰,后依附前凉张骏,任前凉西域长史,封关内侯。《晋书·张骏传》载:
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⑫
李柏归依前凉之后,曾向张骏献计“请击叛将赵贞”。后为赵贞所败,众将建议杀柏。张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李柏免于死罪。文献是作为张骏的“善政”书于史册的。《李柏文书》内容与“请击叛将赵贞”之事有密切关系,因而可断为书于“击赵贞”事前,张骏执政之间,即公元324年至346年间。王国维考证《李柏文书》写于永和元年(345)之后⑬,但此时张骏已死,李柏早已被贬,不可继续自称“西域长史”。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李柏文书》写于公元328年至330年左右。松田寿男认为书于公元328年⑭。侯灿认为此信写于公元346年及其以后不久⑮。孟凡人则认为书写的时间应在公元325年⑯。
对于《李柏文书》的年代学研究,离不开对文书内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请击叛将赵贞”而“为贞所败”之后,险被诛之。因张骏“善政”,李柏免于死罪,此后李柏之下落文献无载,即便尚在军中任职,亦不可能继任西域长史。然文书起首便自署“西域长史李柏”,尚显无丢官夺爵之迹。而李柏书写此信目的乃是“慰劳诸国”,慰劳的对象是焉耆王龙熙,慰劳的原因与欲讨“逆贼赵”有关。“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海头”,可能是李柏自凉州商议击赵贞事后返海头。文中所谓“北虏”,据王国维考证:“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已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⑰焉耆“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严参事不是西域长史属吏,而是凉州官员,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凉州与李柏分手后绕道北虏至焉耆。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发”北虏,五月二日回到楼兰的李柏猜测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书信遣使,慰劳通消息。从书信残稿“逆贼赵”等文字来看,李柏给焉耆王写信是与击赵贞事有关。迫于形势,李柏急于在击赵之前得知北虏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军高昌,西晋亡后,西域长史李柏归顺于张氏政权,而赵贞不附于骏。《晋书》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⑱孟凡人考证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间,并推断《李柏文书》似应写于公元325年5月7日⑲。此说较为可信。

[晋]楼兰L.A古城出土李柏文书(之一) 23×39cm 纸本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晋]楼兰L.A古城出土李柏文书(之二) 23×27cm 纸本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出土于楼兰L.A古城的公元325年的《李柏文书》是否为一个人的手笔呢?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李柏文书》两件较完整的书信草稿可分为两组手笔,也就是说较完整的两件《李柏文书》草稿并非一人所书,有可能出自两人的手笔。侯灿认为“其说颇有见地”⑳。孟凡人亦认为藤枝晃的推断是较为可信的㉑。余太山亦认为两种书迹的不同,“显然出自两位书吏之手”㉒。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其根本原因乃是忽视了用毛笔书写汉字时由于墨水的含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效果。细观文书之书体、用笔、点划、结构及其韵味,笔者认为《李柏文书》应为一人所书。其间或有笔墨干、湿、浓、淡、粗、细之变化,或有结体之敛、纵及书体或行或草之差异,然所书之风格神韵相似,而形式上的差异仅可推断为两件(严格地说,包括毁坏的另2件残片在内至少应为4件)文书并非连续书就,有可能相隔了一定的时间。这从信稿的残纸状况即可反映出来。书写者是反复调整了书写的文字内容,并将至少两件稿件撕碎,透露出书写在草拟信稿时的复杂心情。两件较为完整的书信草稿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笔墨的变化并不能遮盖其书体神韵及风格的一致性,它仅仅反映出书写的时间不同或所用笔墨的状况不同(如其中一件文书墨色水分较多,而另一件文书墨色较干枯)所产生的外在形式的差别,但其结体、用笔及神韵之一贯则是无法遮蔽的。
《李柏文书》两件较完整的书信及其他残纸构成了李柏书法的一个完整的艺术风貌。孟凡人指出,《李柏文书》是研究前凉时期楼兰史的一个线索㉓。笔者认为《李柏文书》的研究,还有可能是探索楼兰书法艺术年代学和类型学的一个主要途径。其书皆为行书体,作为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而非为创作所谓书法“作品”而书写的文稿,在不刻意求工的状态下,最能反映书写者对书法技能的掌握程度。相对于同时代其他诸多名家之书迹大都为后人钩摹或伪作的情况来说,《李柏文书》及楼兰残纸墨迹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李柏文书》行笔方圆转折自如,略带隶书遗韵,点划静动相间,结体聚散分明,每字皆具态势而通篇气脉相连,用墨干润结合,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活的生命力。
《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实质上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所谓“南帖北碑”说提出了质疑。楼兰出土的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也就是说“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所谓“帖学”风格的书法早已成熟于凉州及楼兰地区。王羲之所崇拜的书圣之一即是敦煌人张芝,而在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文书出现的时代。如前所述《李柏文书》书写时间有诸种说法,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写年代在公元325年至346年之间,这一点亦是无疑的。而有关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于《晋书》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传》中仅记“卒年五十九”㉔,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关文献又较为缺乏,因而王羲之的生卒年代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各家所说的年代基本在公元303年至379年间㉕。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时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于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从传为王羲之的作品来看,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法,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来。这一方面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稍早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而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法风格及样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影响。因而,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迹传世,今人所见所谓王羲之书法大多为后人摹本,我们不排除许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却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所谓中国书法之“南帖北碑”之说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实证来看敦煌和楼兰地区当属中国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李柏文书》及其李柏书法艺术的出现也并非是偶然现象。孟凡人曾将《李柏文书》与楼兰出土的《张济文书》作以比较,认为李柏与张济在楼兰一带活动的时间有一段是并行的,两者的文书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似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楼兰残纸中发现署有济逞、张济逞、超济、张超济、济等名款墨迹数件,学者们考证其书写者为张济一人,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的署名都应是张济一人的名和字,而这些书法作品的风格亦十分近似,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等。从《张济文书》笔法特征来看,楼兰残纸中还有相当多无署名残纸,极有可能亦为张济所书。据考,张济本为中原人氏,为避战乱而举家迁居凉州,后张济在楼兰为官,而家属乃居凉州一带。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大量民众纷纷流向相对安定的两个地区,一是江东的东晋政权,另一是割据河右的张氏凉州政权。楼兰世属凉州刺史节制,因而迁徙于凉州的中原人在楼兰一带的活动日趋增多。这种人口的流动亦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楼兰书法的出现与中原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有直接关系。同时,如上所述,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楼兰书法毕竟与同时期的中原和江南的书法风格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出了楼兰书法的风格特征。另外,如按前述陈凌的观点,署名张超济的文书与《李柏文书》在词语和书风上具有相似之处,这就不排除在楼兰所发现的李柏文书系列和张济文书系列,以及诸多书风相似的文书都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既不是李柏,也不是张济,他一定是军中的一个书吏,一个来自中原的书法高手。
据孟凡人考证张济在楼兰活动的时间其上限约在公元4世纪初,其下限约在公元4世纪30年代左右㉖。这不但证明了《李柏文书》和《张济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书法作品的相对年代,同时也为楼兰乃至中国魏晋书法尤其是帖学书法风格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年代学标尺。如果用这种标尺再结合其他地区考古发现的晋人书迹风格来验证传世的“晋人法帖”的话,那么,包括《兰亭序》在内的诸多法帖的年代或作者的可靠性便会大打折扣了。或许只有用这些考古发现所获得的真实材料去检验那些传世法帖的真伪,才有可能揭示出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真实面貌。
西安美术学院)
郑寒白
注释:
①参见[日]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学苑出版社,1999年;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孟凡人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②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9年,第8页。
③[日]下中邦彦编《书道全集》第三卷,平凡社,1959年,第12-18页。
④[日]橘瑞超著《中亚探险》,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6页。
⑤例见侯灿《论楼兰疆域的发展及其衰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另见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1-293页;[日]森鹿三《西域出土的文书》,《书道全集》第三卷,平凡社,1959年,第12-18页;陈世良《李柏文书新探》,《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⑥孟凡人著《李柏文书出土于LK遗址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另见孟凡人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54-265页;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⑦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550页。
⑧参阅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521-550页。
⑨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⑩陈凌《斯文·赫定收集品的新刊楼兰文书》,《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105-131页。
⑪《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221页。
⑫同上,第2238页。
⑬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第281页。
⑭[日]松田寿男著《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第133页。
⑮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第285页。
⑯孟凡人著《楼兰新史》,第243页-244页。
⑰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第280页。
⑱《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38页。
⑲孟凡人著《楼兰新史》,第238-244页。
⑳侯灿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3页。
㉑孟凡人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㉒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第273页。
㉓孟凡人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㉔《晋书》卷80《王羲之传》,第2093-2101页。
㉕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841页。王玉池著《二王书艺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28-132页。
㉖参见孟凡人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第2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