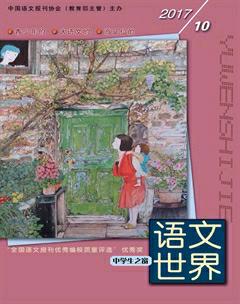学养是这样炼成的
范昕+姜方
陆谷孙1940年3月3日出生于上海中行别业(时为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他曾对人说过,最初的人生记忆来自日后搬迁至的建国西路合群坊: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他理发,他扑腾挣扎……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由于上海的战事,全家会商后,父亲陆达成携妻儿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新中国成立后,陆谷孙回到上海,195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八年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陆谷孙留在了复旦。
人们眼中的陆谷孙,专于莎士比亚研究和英汉辞典编纂,无所旁骛而以学问为旨归。
父辈教育带来的影响伴随了陆谷孙的一生
陆谷孙日后的学养,与他自小从父亲陆达成那里受到的教育不无关联。
在合群坊,陆达成教幼时的陆谷孙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还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等。长大后读到都德的其他作品,陆谷孙发现印象中不时远离巴黎的尘嚣、隐居普罗旺斯乡间的都德本人,也曾长年遭受隐疾的痛苦煎熬,为此大吃一惊。他不免忆起父亲晚年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其实人生‘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还是人性。”
在余姚老家的五年,父亲陆达成一直对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严格管教。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孩子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他们便得摇头晃脑跟着吟诵。那段时日,父亲要求陆谷孙背诵了很多晦涩的古诗,据陆谷孙后来的猜测,父亲大概是借儿子背诵的古诗寄托对亡妻的悼念。另一方面,父亲也每晚给他讲授法国文学——陆达成毕业于上海中法学堂,曾经“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叙事文。夏日,听得父亲开窗的声音,陆谷孙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练颜体,他则学柳体。父亲给陆谷孙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后来读书多了,他才知道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
父辈教育带来的影响伴随了陆谷孙的一生。当陆谷孙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希望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习法语,不料第一志愿落榜,转至复旦外文系学习英语。
对儿子,陆达成灌输这样的信念:书一定要读好,做一点一畫、规规矩矩的读书人,把书香一代代传下去。
中学时代,陆谷孙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种子已种下。放学以后,他常常走很远的路到沪江电影院旁的小书摊,每个月花上两块钱借来各种文学书籍。《红与黑》《三剑客》《茶花女》《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复活》《父与子》等翻译的外文书,尤其是他的心头好。他还背了许多散文和诗歌的片段,如莎士比亚、普希金的诗。日后回想起来,他深感“背诵给人的好处是永恒的”。在陆谷孙看来,这些经典都是对人内心世界的震撼、冲击和淘洗。
陆谷孙的英语学习来得有些晚,却幸运地赶上复旦外文系的黄金时期
直到17岁考上复旦大学外文系,陆谷孙才正儿八经学习英语。他曾坦言自己这一代人的教育是“有缺陷”的。这指的是一个时代的症结: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与苏联如胶似漆,掀起“以俄为师”的风潮,俄语也因此成了中学生们的必修课,而非英语。很多原先教英文的老师只能从字母训练起,边自学边教学生俄语。
陆谷孙在复旦外文系总共求学8年(本科5年,研究生3年)。那正是复旦外文系的黄金时期,除了被学生戏称为“the big three(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和葛传椝,还有学识渊博、英汉语造诣卓群的“蛋头教授”林同济,从事文论的伍蠡甫,从事文学的孙大雨、戚叔含、杨烈、林疑今,从事语言的程雨民,再加上“金童”刘德中、“玉女”杨必……阵容不可谓不浩大。陆谷孙幸运地受过其中20多位老师的教导。
杨必给研究生开的英国小说课是当时复旦外文系的“招牌”课。这也是陆谷孙求学期间最喜欢的课之一。他曾回忆道:“她平时穿着大方,举止端庄,沉默而好深湛之思,给人孤高的印象,但上课一进入‘角色,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吐字清晰,台风活泼,像是换了个人。有时还边讲边演——她模仿《雾都孤儿》中老贼费金的走路姿势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学界并无理论痴迷,杨必给学生布置的课业都是可读性较强的“琐屑之言”,一本本读来却让他感觉实际得很。更令陆谷孙钦佩的是,杨必显然对中国的小说也深有研究,常常讲着讲着就会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作品上去。
求学时期,陆谷孙没少读书。那时年轻,陆谷孙坦言爱看刺激点的书:福尔摩斯、阿加沙·克里斯蒂、艾伦·坡、《三剑客》《基督山伯爵》等。他始终坚持看书一定要有兴趣,没兴趣根本看不下去。
在复旦外文系,陆谷孙不仅如饥似渴地读书,也饶有兴味地和同学们排戏、演戏。这得益于系里的演剧传统,据说由大师级人物洪深等开创。1962年,陆谷孙本科5年学习期满时参演由王佐良先生等译成英文的曹禺名剧《雷雨》,这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很难说排戏给他们真的带来了什么,是背出的大段台词对英语有长进吗?那段时日背过的好些台词,陆谷孙的确一记就是一辈子。不过更让陆谷孙感念的,或许还是当年同学们台前台后的齐心协力,甚至有同学夜半扛个大录音机到校区周围的稻田旁去录取蛙噪,准备用作舞台效果,结果杂声灌满耳根,自然失败。
陆谷孙第一次执起教棒,是在1963年。当时他才是复旦外文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代替当时身体不适的系主任杨岂深,为本科五年级学生开设新课“英美报刊选读”。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充满挑战的一门课。
当时杨岂深决定开课,选完教材后只上了一节课,便将教棒移交给他所信任的学生陆谷孙。接过重任的陆谷孙其实是捏了一把汗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因为英语而感到紧张:一方面,当时英美报刊进入中国的很少,我们读的大多数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刊物,而英美刊物是“资本主义内容”没法读到;另一方面,当时工具书奇缺,只有一本1940年代末编的《英华大词典》,已经很老了,而英美报刊上的新词新义很多。何况,当时英语教学注重读写,口语训练少,而这门课要求全英文授课,陆谷孙只得四处借原版词典,在备课上下苦功。每回上课的前一晚,他都要把所有上课时要说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对着镜子一遍一遍操练,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就这样,陆谷孙的“英美报刊选读”成了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陆谷孙那口漂亮的英语也正是这样练成的。
(选摘自《文汇报》2016年7月29日,有删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