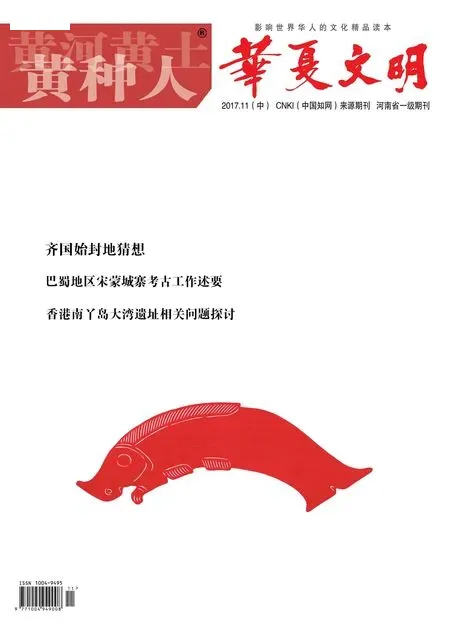忆何琳仪先生
□重耳
忆何琳仪先生
□重耳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何琳仪先生相识。那是1999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准备报考葛英会先生的研究生,于是开始自学古文字学。一天下午,我在校内的小池塘边上看书,忽然来了一人,拿了几本杂志,坐在我对面的石凳子上翻阅起来。我看了一眼他放在桌子上的杂志,竟是《文物》《考古》之类的东西,当时我就很纳闷,这人到底是谁呀?看这种书刊的人大多是我们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老师,可他们我都认识啊,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啊?我突然一下子又想起来了,前一阵子,我听老师们说过,吉林大学的何琳仪先生来我们学校工作了。对,他就是何琳仪先生!于是我便站起来冒昧地问他:“请问您是何琳仪先生吗?”“是的,我是何琳仪。”他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着我回答,眉宇间流露出一种俊逸与洒脱的气质,看起来很亲切。
“你是谁啊?怎么认得我啊?”我赶紧汇报。“噢,准备考古文字的研究生啊?为什么不考我们的啊?我们这儿也正在招学生啊。”然后拿起我递给他的北大往年考卷,说:“那我先考考你吧。”初次见面,他就考起了我。他问了几个陶文的释读,那时我刚刚开始自学古文字,才看了一点通论和甲骨的材料,因而无法作答,他说:“哎呀,你在自学呀,这有点难,你可以到我们中文系去听课嘛,我们现在各段都有专门的老师开课。”他还告诉我:“明年8月份中文系要主办一次古文字年会,请了学界的一些大腕,到时候你可以过去听听。”又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去火车站接人,于是我们便匆忙道了别。
后来我因准备考试,事情很多,又赶上田野实习,一直没有机会去中文系听课,只是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他忙碌的身影。直到考研完毕后,才有点清闲时间,适逢那一学期何老师和徐在国老师都开课,我便做起了旁听生。记得我给何老师打电话申请旁听时,他很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见面后,他很关切地问我考得咋样,平时都看些什么书。那时上课人很少,只有何老师刚开始带的几个研究生程燕、吴红松、房振三人。记得那时何老师开的是《诗经》课,主要讲音韵和训诂,每次上课的时候,每个研究生都抱着厚厚的《十三经注疏》,战战兢兢,低着头等何老师提问,若回答不好,当然要挨骂了,而我是外系来旁听的,自然就轻松多了。何老师每次来上课都提个小布袋子,里面装了一本发黄又有些破烂的《诗义会通》,课间等他离开了,我们便跑上去翻看他的书,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批注。何老师讲《诗经》,意在教学生音韵与训诂,然而他对很多诗的意境的把握,比起一些专门的研究者也毫不逊色,他常常用极简单的语言,讲出其意蕴,又时时夹杂一些风趣的语言,说起来神采飞扬,且头头是道。他的课听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可惜享受没多久,我因外语不过关没上成研究生,就跑到淮北的考古工地去了。后来我去了北京,又考了一次,成绩勉强过线,因竞争激烈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于是便四处打听调剂事宜。我的老师周崇云先生得知后,找到了何老师(我当时并不知道),问能否把我调回安徽大学来(以下简称“安大”),据说何老师当时有些“不客气”,说:“这小孩心很高的,看不上我们啊!”
没多久(2002年春),他到清华大学开会,我去看他,他很开心,很热情地和我谈调剂的具体事宜。就这样我们初步商定,我回安大历史系,跟另外一个搞传世文献的老师读,跟他学习古文字方面的课程 (那时他已到历史系兼职)。
事有凑巧,我刚刚同何老师说完,转身去倒了两杯茶,回来时发现我的位子上竟坐着一人,一看是黄锡全先生,我便将茶递给二位先生,黄先生很热情地问我:“你是谁啊?怎么认得我?”我便告诉他,以前在安大开会的时候见过他,顺便也说了我当时的情况,何老师也做了一点介绍。黄老师一听,说:“葛老师我很熟啊,我帮你问问吧。”说完就出去给葛老师打电话。然后跑回来跟我说:“葛老师很想招你啊,他说你学得很不错,专业也是考得最好的,就是外语低了点,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吧,我推荐推荐你,看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调剂一下。”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在会场里找人挨个儿问。后来找到武汉大学 (以下简称“武大”)的李天虹先生,李先生说罗运环老师那儿好像还有名额,应该可以接受调剂,于是黄老师准备和罗老师联系,这时,他看到了武汉大学的陈伟先生,就对我说:“我和陈伟说一下,他现在是副院长,让他从侧面帮帮忙。”于是跑去和陈老师谈。陈老师听说后,让黄老师转告我,他今年刚开始招出土文献学方向的硕士,还没有人报考,要是我愿意的话,他可以接收。我一听,特别高兴,于是就和陈老师见面商定此事。
然后,我赶紧跑过去征求何老师的意见,他好像有些不高兴,说:“那怎么办?你就随陈老师去吧。”
就这样,2002年秋天,我到了武汉大学,开始随陈伟老师学习。不久,在系里遇到罗运环老师,他告诉我,何老师专门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武大读书,叫他多关照我。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记得寒假回家路过合肥的时候,我给何老师打电话问好,他很高兴,叫我有空过去玩。
2004年9月,何老师到武大开会,我听说后,赶紧到珞珈山庄去看他。那天何老师兴致很高,我们邀请他到学校附近遛弯儿,他很愉快地接受了,于是我们从珞珈山庄出发,沿着蜿蜒崎岖的小路,边走边聊,聊的多半是文学与艺术的话题,以及旅游的见闻和学界人士的逸事。后来我们在整理他的书籍时,发现有一本他用楚简文字写成的《楚辞》,做成线装书的样子,看起来古香古色,很有味道。他对乐律也颇通晓,他家的客厅里就摆着五线谱的架子。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我和他说话时,他好像总是“听不进去”,有时要说上两三遍他才会明白,当时就很是不解,直到最近两年我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才明白原来他一直在思考问题。
他忽然对我说:“你晚上回去帮我查查《三代》,有个铭文我要核对一下,准备明天上午的讲座 (那次陈伟老师代表历史系邀请何老师为我们做了一次报告)。”我如实回答:“这恐怕不好办,我手上没有《三代》,去资料室来不及了。”他很吃惊地说:“《三代》你们都没有啊?那怎么搞古文字?唉!也难怪,我们当学生时很穷,只好抄书,像《三代》这样的书都是手抄一遍,人手一册。”我们听了,深感自愧不如。
走着走着,出了凌波门,我们在东湖边上信步闲聊,不一会儿到了水果湖边上的放鹰台,对着李白吟诗放鹰的雕像,何老师诗兴大发,顺口就吟了几句,可惜我记性太差,如今一句也记不得了。转了良久,我们又从茶岗往回走,走到校门口,他忽然说:“对了,你们陪我找个商店,我要买胶卷,明天开完会要出去玩。”我忽然记起,何老师是十分喜欢游玩的,据说国内的名山大川他差不多都走了个遍。于是我便问他会议安排去什么地方,他像小孩子一样很开心地告诉我去神农架,而且自己只掏一小部分钱。
买过胶卷我们往回走,走了差不多一晚上,我们两个小伙子累了,准备送他回珞珈山庄,他却没有丝毫倦意,且谈兴甚浓,说的内容多是文学上的名人佳作,可惜我的文学修养不好,只好唯唯诺诺,疲于应对。不知不觉走到了樱花大道,他又想起了程千帆,于是又评论了一番,还特别提到了程先生的夫人,说她的诗写得很好。至今回想起来,何老师当年那遛弯儿论英雄的形象仍历历在目。
2006年,我又回到安大,跟从黄德宽老师继续读书。那年夏天,武大举办了一次简帛学国际研讨会,我无事可做,在一帮朋友的鼓动下,决定去凑凑热闹,于是便与何老师同行,同去的还有房振三兄、历史系的刘信芳先生与他的两位弟子。到了武汉,刘老师请我们吃早餐,何老师对我说:“黄,待会儿刘老师他们几人坐一辆车,你和我们(他和房振三)坐一辆车。”见我是“没大人领着的孩子”,他特意这样关照我。
第二学期,何老师开了两门课,我都选修了,这样,每周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当面向他请教了。这时的他虽然已被病痛折磨得很苍老,但仍然精神矍铄,尤其是讲起课来,兴致非常高,常常是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尤其是读起铜器铭文来那种摇头晃脑、怡然自得的神态,就像是一幅画。
上铜器铭文研读课的学生较多,而何老师却经常向那几个学生发难,一般来说都是他的学生。他曾明确地要求:“你、你、你,以后上课都坐到我身边来,别找都找不着你们。”在《诗经》课上,他就曾更“露骨”地宣布:“你们其他人的学生要想好好学就好自为之啊,我的学生嘛,我要经常提问的,你们要做好准备,谁叫你们是我的学生呢?”所以上他的课时,大家一般都比较紧张,有时他会特意地逗大家开心,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诸君啊,难道你们中就没有人知道这字该怎么读吗?”说完,便笑眯眯地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至今仍在我的脑中萦绕。
《诗经》课上,他经常讲一些“题外”的话,告诉我们怎样打好小学的基础,如何吸收乾嘉以来清人的优秀方法与成果。“我们用的就是教私塾的办法,但这法子最管用。”他很明确地说,“这就是于老传承下来的家法。”其实平时他所说的,有很多也是他个人的体悟与参透。
转眼一学期就过了一小半,他开始布置作业,要求每人写一篇和课程相关的文字给他,限定6月20日之前交给他,并说“6月20日我要去西安开会,完了我就不回来了。”不知为什么,当时一听这话,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开完会我要去东北旅游,要到下学期开学才回来。”他又补充道。这天是星期二。
又到了星期五,下午是何老师的《诗经》课。眼看着上课的时间都过了,何老师怎么还没有来呢,今天是咋啦,他平时可是不迟到的啊。我心里犯起了嘀咕。有人问:“何老师怎么还没来?”“可能是睡过头了。”我打趣道。又过了一会儿,何老师拎着包来了,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好像很不高兴,气鼓鼓的样子,一进来就把包往桌子上一撂:“去,给我倒杯水!”说完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上不停地流汗,我以为他走得急,身上发热了。不一会儿,水来了,他喝了一口,又坐了半晌没说话,我抬头看他,见他脸色很不好,汗还在不停地流着。终于他开始讲课了,讲了没几句,不停地擦汗。我抬头看他的脸,见汗流得越来越多,脸色也比刚才苍白了许多,就赶紧拿出纸巾给他擦汗,问他是不是不舒服。“没事,我就是觉得有些不舒服,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们稍微等一会儿,我休息好了再讲。”他说。“那今天的课就不上了吧,等你休息好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劝道。“不,没事,我休息一会儿就行,没事的。”“不,今天就不要再上了,下周再说吧。”我说道。“那好,我就坐一会儿,和你们聊聊天吧。”“那敢情好!”于是我们便聊起了天,他说他刚才在路上吐了,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所以迟到了,不过没事。他说以前吐过血,接着又大出血,都抢救过来了,这次应该没事。
他又吩咐刘刚把他刚刚审完的材料送到学校,说是外校送来的,急着返回。于是我们接着聊,顺便等刘刚回来。没想到那竟是何老师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
我同何老师的交往很零碎,他去世以后,这些点滴记忆的碎片,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但正如我那破碎的心情,始终无法缀连、修复。我一直想写一篇简单的文字来悼念他,可每想至此,心情总是很沉重,直到最近我完成了学位论文,有一天,我打着雨伞走在去医院探望病人的路上,眼前忽然浮现出何老师的面容,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像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在我的心头回放。终于有一天,我的心情好了许多,虽然记忆还是那么零碎,但我将它如实地介绍给大家。细心的读者,由此会
何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可他那沉稳的神态、安详的笑容、浑厚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却始终那么完整、清晰。一想起他,就会感觉到一个勤勉、谨严、博学、睿智而又儒雅的学者,一个率真、豪爽、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又充满了灵性与真性情的文人,一个温良、恭谨、谦让而又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的身影在我的面前徘徊。
何老师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我觉得他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他的著作里。那充满智慧与深情的灵魂,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仍在永不停息地跳跃、绽放着……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赵建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