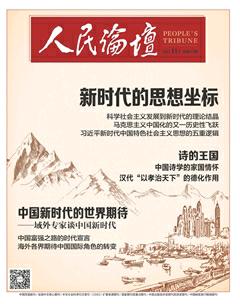诗的王国
【摘要】中国诗歌来源于宇宙本体之根本规律,彰显了天地自然之大美。温柔敦厚是中国诗学的永恒追逐,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诗学艺术至极境,能于苛酷的艺术规律中得到自由,具有音韵之美、对仗之美、哲思之美,是人类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学瑰宝。
【关键词】中国诗学 诗韵 诗歌格律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温柔敦厚是中国诗学的追逐
《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人对“诗”的三字箴言。“志”所包涵者,应是儒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人生大德性。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愿必在其中。“诗”,既是语言的艺术,必有诗人之情感在焉,这情感既是诗人心灵情态的自由,而又必然不会逸脱儒家的根本持守。子夏《诗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儒家为“诗”所设之大限。
孔子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儒家论“诗”之为用。“兴”,感发也;“观”,鑒赏也;“群”,唱和也;唯一“怨”字,应有说也。“怨”非止怨怼、愤懑、哀叹,“怨”有难忘之忧思、悲怀之流露、悱恻之同情、往迹之喟叹。不得通其道,则怨悱以生。故较“兴”“观”“群”三字蕴意既广且深,不可一言以概之也。“迩之事父”,孝也。或于朗月清风、朝霞暮雾、春江花朝之时日,与乃尊偶尔相对闲沽酒,酒意微醺,或为联语,或作诗钟,或限韵为诗,推敲琢磨,情不自胜。此家庭之乐中最上乘者,亦孝父悌兄之无上法门。“远之事君”,忠也,“君”非仅君王也。宗庙社稷、疆土山川、民情风俗,凡“君”所管辖、代表者,囊括四海八荒,亦皆诗人所澄观遐思、吟咏嗟叹之材料。则所事者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者矣。“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诗经》《楚辞》中俯拾即是也。草木若《诗经》中蒹葭、葛覃、卷耳、黍离等,《楚辞》中江离、辟芷、秋兰、宿莽、申椒皆是也。鸟兽若《诗经》中关雎、鹿、雉等,《楚辞》中骐骥、封狐、玉虬皆是也。余著《〈尔雅〉说略》中所举草、木、虫、鱼、鸟、兽,亦多有论列,固不止于《诗经》与《楚辞》。若《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白虎通义》《方言》诸著,皆有涉及。而选《诗经》中最多,缘先民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与鸟兽草木感情自不同于后之来者。中国诗人在源头即重视大自然万类之状貌、性情,往往因以“比”“兴”,孔子亦以为多识之庶可扩大视野、丰富情感。这虽是诗家余事,然大诗人往往只眼独具,“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何等境界清且俊!“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真个奇绝非人造。
孔子又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则不虑而知的良知在,不受尘嚣污染的本心在,天所赋予的“根本善”在,则诗人之所为作,自可“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司马迁赞屈原所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岂无由乎?“思无邪”的终极境界是什么?杜甫,诗圣也,大儒也,然在他“艰难苦恨繁霜鬓”之后,在他“潦倒新停浊酒杯”之际,他忽由儒而庄,突发千古之奇句:“篇终接混茫”,这五字有分教: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已在时代溷浊波涛中击碎,在他“白头吟望苦低垂”的《秋兴八首》吟毕之后,杜公忽在庄子的“古之人,在混茫之中”找到了知己,得到精神上的最大解脱。
诗的大用无非“美”“刺”两端。“美”者,歌之、颂之、趋之、赴之,激励当代,勖勉后人。“美”而不谀谄,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备极景仰,使人走向崇高,用词不奢,而意味隽永。“刺”者,警之、醒之、避之、戒之,鞭笞穷奇,讽谕低俗。“刺”而不詈,谑而不虐,如《诗经·卫风·氓》,虽叙述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然不作泼妇骂街状,读之令人顿生凄恻同情之心,古往今来闺怨之诗,此其上品。
诗非口号,亦非命令,温婉中有哀愁,最是使人心旌摇动。《出其东门》中的“匪我思存”“匪我思且”,描写了爱情专一的男子不为“有女如云”所动,言简而淡,意深而赅,方称高手。温柔敦厚是中国诗学的追逐,其中的道理深宜思之。
庄子是毋庸置疑的东方诗神,刘勰《文心雕龙》是典型的庄子美学之演绎者
刘勰谈“风骨”,将诗“六义”中的“风”解释得最为透彻。他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代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此境界,苏东坡有之矣。近世刘熙载《艺概·诗概》中云:“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有云:“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段话固来自庄子“齐物论”,庄子宇宙本体论的核心就是“齐物论”,在苏东坡看来,“变”与“不变”是齐一的;“消”与“长”是齐一的;“物”与“我”是齐一的。苏东坡之学非止于“儒”“道”,亦深谙乎“佛”,写大悲哀往往以大解脱为其终点,正如我所总结佛学之六字箴言:看破、放下、自在。辛稼轩之豪,犹执于象者;而苏东坡之旷,则观于象外,得之环中者矣。古今诗人中,与庄子心灵最是相通者,苏东坡堪称首选。他可以坐忘,可以撄宁,可以从人类的倒悬之苦中自我解脱。他在历尽谪宦、放逐的一切人生苦难之后,一定想起庄子的“齐物论”,生死何足论,他的归去,岂是从琼岛回到金陵?他回归到无极之门、回归到无何有之乡,他的心灵正是庄子所说的“天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刘勰《文心雕龙》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言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也,这是庄子环中说的典型文论,又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言与大化同脉搏也;“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言心灵与自然同体也。endprint
其实谈老庄、谈佛与谈儒亦无绝对之界限。孔子之孙孔伋(子思)首创“天人合一”之说,至一千九百年后王阳明的“心外无天”,这期间中国之士人,弃绝实证和天人二分,走向感悟“天人一体”的伟大思维之途。这是一座不仅为过去亦且为未来,人类所必须越过的思想桥梁。
刘勰于《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中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所希望于诗人的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诗人之禀才各异,若扬雄辍翰梦惊,祢衡当食草奏,相如含笔腐毫,贾岛“两句三年得”,虽迟速异分,而其与天同契则一也,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刘勰担心的是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这和作画为同一道理。“精”缘于对主、客体至深至切的认识;“变”缘于对事物的化育生发,曾不能以一瞬的根本把握,“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这“妙”,是自然恰到好处的存在状态,这“数”是自然掷向人间的一颗色子,爱因斯坦讲,“上帝不随便掷色子”,人类的本分是逐步地接近这“妙”和“数”。诗人苟能略通此理,事过半矣。
理解庄子如刘勰之深入,古今一人而已。虽然,刘勰毕竟亦是深受儒家浸染之人,他不忘“文章述志为本”,不忘“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这又给一些“美学家”一个很好的教训,在中国的学问中,“儒”“佛”“道”是可以时时打通关节的,正不可执一以求,死于章句。
乐府与诗韵之从来
先民于劳动、婚娶、宴饮之时,每以口号相愉乐。或二字、三字、四字,或押韵或妄知所为用,亦不欲留传千古,其中或有佳者,逐渐远播,传至今日,实千之一、万之一耳。初无规式,是先民无约束之酿制,流传最早的一首两言诗,引出一段古代孝子的故事,越王勾践,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因,因忧父母为兽所食,乃作弹以护之,百兽震恐而逃,父母得享永年。且作歌以述志,二言诗也:“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意思是:“让我断取修竹,让我削刻为弓弩箭矢。嗖的一声,将利箭射出,百发百中,驱走了虎豹熊罴。”这首诗出自勇士之口,略无修饰,天真淳朴,至“飞土”二字出,则神矢发矣,至“逐宍”二字出,则弩发兽倒,这是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首二言诗,距今二千五百年矣,《文心雕龙》谓为二言之始。兹后三言以出,谓“苍耀稷,生感迹”。四言者《诗经·大雅》有:“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又《牧誓》引“古人有言,牝鸡无晨”。以上两则见于《诗经》和《书经》,可见民间谣谚已入古代之典籍,此为四言之始。《春秋元命包》则载殷末谣谚:“代殷者姬昌。”此可为五言之始。王士祯《古诗选》谓《击壤歌》为七言之始:“帝力于我何有哉?”意为:帝王所施之政,给了我什么?细审《诗经》,四、六、八、九言皆有,然先人初不以此为诗之固定体式,兹后因语言中主、谓、宾、形、副之性质渐渐完备,则所最宜者为五、七言,因之古体诗(如古诗十九首)和近体诗(主要指唐后之五、七言绝、律)皆多用五、七言,而乐府诗则较随意,不为近体规律所束缚,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固为乐府无疑,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八言、九言参差用之,可谓竭尽诗人用字之变化矣。
先民既有诗之流布矣,则歌以咏之,凡可被于乐者,皆为统治者所注意,因彼时宫中之宴饮、歌舞、出行,往往择而用之,乃设“乐府令”以关注之,此秦至西汉惠帝时均已有矣。至汉武帝,“乐府”乃成专门之机构,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兹后,人们渐以“乐府”称作诗体之一种,扩而大之,凡魏、晋以降至唐代可入乐的诗歌和后代仿效乐府古诗之作品,统称为“乐府”,再扩而大之,宋、元之后的词,散曲和戏剧词曲,也称“乐府”。
后人以前人所作“乐府”为题者甚多,试举一例:崔豹《古今注》述“公无渡河”故事,谓:“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泪堕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这不过是一个疯子投河而其妻从而溺亡的故事,然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十六字,质白之中有平民的深情,普天下最感人的乃是一“真”字,“箜篌引”有之矣。复披之以乐,遂使后之诗人一一援引,曹植曾和之,然与《箜篌引》原来故事,杳不相关。又如《子夜四时歌》,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后人遂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这是另一种反其原意而用之的方法。其它如以原乐府中一句为题,或用题意而改题名,不一而足,兹不赘。
诗人为诗,往往有怀古之情性、趣味在,实非必须如此,或以为此是诗中之一格,则不免迂阔甚矣。唐代有“新乐府”者,如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不复依傍古人之题、意、句。“新”仅在此,并非于诗格、诗體有何创新耳。
至于诗韵,先是南朝沈约有平、上、去、入四声之说,然后依四声而循韵母分类,汇为韵书,供科举考试之用。金代始用平水韵(平水,实山西临汾别名),宋刘渊所编总一百零七韵,而金王文郁《平水新刊礼部韵略》总一百零六韵,少一韵之原因是将上声“迥”“拯”二韵及去声“径”“证”二韵合并为一部。王文郁本阴平、阳平各十五韵,上声廿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为元、明、清以来押韵之依据,沿用至今。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上声之“迥”“拯”二字不并,然此书不传。韵书之音读,今人操普通话者往往对入声字深感头疼,缘普通话中无入声。苟有一字焉,本为入声,而在普通话中为上声或去声,则于作诗无碍,而倘为入声,在普通话中偏偏入了阴平和阳平,人们就会于平仄上犯错误。如“白”,入声字,而普通话为阳平;“笃”,入声字,而同入普通话之阳平,所以北京人运用四声,困难在此。而山西人最得益于平水韵,于用入声时,绝对无误,山东、江淮、湖广之人亦可用家乡话以辨入声。endprint
诗韵之重要与诗从乐府走向近体有关,尤其至唐代,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以兴,法度森然,文化之发展往往如此,艺术至极境,乃是在苛酷的艺术规律中得到的自由,如杜工部之《秋兴八首》,音韵之合辙几乎可为不朽之典范,而诗味之深秀更为千古之杰构。对于初涉诗道、以为束缚者,而斫轮老手则以为自在之境。诗之格律非徒为设障也,乃有音节回环之美、声韵呼应之美在焉。
近体诗格律简析
近体诗之格律,一般指唐后之五、七绝、律、排律于音、韵上的法则。从初唐诗人运用之熟练,知六朝、隋代已具雏型,今试举两例:
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此两例乃五律之典型,两位作者均列“初唐四杰”。骆宾王起句平仄为:“平仄平平仄”,末字不押韵;王勃起句为:“平仄仄平平”,末字押韵,故可知无论五律或七律之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五绝如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押仄声韵,首句不入韵。骆宾王之五律中“无人信高洁”,第四字本应为仄声,误为平声;而王维此五绝中“弹琴复长啸”,第四字本应为仄声,误为平声。高手作诗,往往破除戒律,正如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祖父约翰·米希尔对少年克里斯朵夫讲,“对于大师是百无禁忌的”,因为克里斯朵夫发现了古典大师乐曲中于对位、和声之小儿科错误。北宋苏东坡写格律诗和词更是漠视平仄规律,致遭南宋李清照之讽刺。余曾祖父范伯子,自称“苏家(指四川眉山苏东坡)发源吾家收”,于平仄声亦视之甚淡。不过既言至此,必需提醒欲为诗者,不当以平仄之错讹而掩其诗学之陋,初学为格律诗,竟冒充大师、天才。当然,读者之所以见谅大师者,非无由也,如杜甫之《秋兴八首》中:“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其中“西望瑶池降王母”,第六字本应为“仄”声,而杜公用阳平“王”字,晚清钱谦益谅之,因此处必用“王母”二字也,以杜甫之精审,绝不会于此犯错误,“王母”二字和“瑶池”的联系是不可改的。由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平仄宜按格律,然平仄亦可破格律,但须具备两条件:其一,不得不耳;其二,的确是大师手笔,不原谅也得原谅。幸初学者先老老实实地按格律办事,及至声名显赫之时,再作出人意外之句不迟。
中国诗歌语言来自天地大美,来源于宇宙本体之根本规律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对称支配自然。”无际无涯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所构成的宇宙对称律,可能是百亿年来自然形成的最宏阔伟大的现象,在这现象背后是不可言说的、人类无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合目的性”不是上帝,而是十八世纪末德国大哲康德所提出的。“合目的性”使对称成为万物存在的方式,受其绝对支配。失去对称便失去平衡,物无以立、人无以生、天地无以存,“宇宙凭着六声部音乐”(开普勒语)运转,宇宙的和声和对位,是大音希声的音乐之构成要素;而大象无形则是宇宙大不可方的状貌。
从动物单音节的呼喊啼叫,到人类语言的巧密精微,各族群声调趣舍异途。至今人类有6000种语言,最小的族群人数仅千人之谱,而最大的族群当然是中华民族。有趣的是其他族群的语言多是表音字语言,唯独中国人操着表意字语言,既有意矣,则不自觉地使其意走向宇宙的“合目的性”。中国人最早在世界上提出宇宙万有的阴阳二元说,二元不仅对称,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杨振宁先生重视“对称中有不对称,不对称中有对称”的中国古典前哲学(前哲学指《老子》之前的《周易》),这种不对称性(或对称破缺)的思想传统使西方的大科学家大为惊讶,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普利高津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
以上所述正是为了说明中国诗歌语言之所从来,它来自天地之大美,来源于宇宙本体之根本规律。不完全对称,是太极图最奇妙的思维胜果。人类发明过无数的图象,以状万类之存在,然而恐怕没有可见太极图之项背者。最妙不可言的是,中国人凭借智慧,使语言在这图象的笼罩下走上一条卓绝的美妙境域。其对称之基础有四点:一是一字、一音、多音、四声构成骈俪的可能性;二是单字的词性因所处语境之不同,可以转换,以使对称的规律和不完全对称灵活运用;三是由于对称性的选择,使汉语的排列组合具有了使用者的个性。四是由于上述三点,使中国语言文字成为了诗性的语言文字,似乎中国必然成为一个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振宁先生曾用苏东坡的回文诗来说明中国对称和对称破缺的哲学,今天我近取诸身,用我父亲——精于诗道而又恃守谦虚的范子愚先生的四首悼念我慈爱的母亲的回文诗,来说明我上述的论点。我的母亲缪镜心是厦门大学著名哲学家缪篆(子才)先生的女儿,一生辛劳,但她精神上最大的安慰是我父亲对她的挚爱。母亲死后,父亲刻“独鹤”一印钤于诗稿,除去怀念母亲,不复有其他的诗作,诗心已死,独于母亲,能唤起父亲的诗情。
读东坡回文《菩萨蛮词》殊觉妙义,爰作效颦之举,题为悼亡:“镜同心照孤魂净,净魂孤照心同镜。天外世谁怜,怜谁世外天。我闻如是可,可是如闻我。悲我益卿思,思卿益我悲。 水流东去人何似,似何人去东流水。挥泪望云归,归云望泪挥。仰空悲月朗,朗月悲空仰。卿有镜为心,心为镜有卿。 晚窗新月窥人倦,倦人窥月新窗晚。云黑乱斜曛,曛斜乱黑云。问天穷更闷,闷更穷天问。卿诚我心诚,诚心我诚卿。 枕衾凉意秋来恁,恁来秋意凉衾枕。人世几回亲,亲回几世人。读书翻止哭,哭止翻书读。明镜照伶仃,仃伶照镜明。”
这远离了文字的游戏,而是感情深挚、动人心弦的诗句,每读父亲诗集至此,我都会潸然泪下。
每两句是前句中有后句,后句中有前句,对称而又有对称破缺,父亲的这四首诗达到前人所未见之深度哀伤。而中国语言文字的骈俪之美,可谓达到极致。这其中词性的转换,历历在目,“读书翻止哭”,翻,副词;而“哭止翻书读”,翻,动词,上句讲读书反能止哭,下句讲哭之既止,翻书自慰。意蕴对称中又有所不同,没有任何国家的文字可以做到这一点。
学习骈俪的方便法门,是以联语或诗钟起步,凡精于近体诗者,无不以此为看家本领。古代诗人相聚,往往以作联语、诗钟、嵌字联为乐,今略举数例:诗钟练人,最是艰难而有趣,以两件全然不同之事物为对,是炼字炼句的最佳法门。以下为诗钟两则:
(一)湘夫人 竹
愁予北渚,植彼南山。(范曾)
(二)楚辞 王维
吟于江汉,集在辋川。(范曾)
嵌字联两则:
(一)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古人)
(二)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古人)
以唐人诗句集联,且上联第二字为“女”,下联第二字为“花”。第一副对属甚工,有骈文面貌、诗词韵味矣,而独缺散文风骨;第二副对属亦甚工,而骈文面貌、诗词韵味、散文风骨兼之矣,此乃上乘之作。
骈俪几乎成为中国文字语言优秀的遗传基因,它是哲学的——阴阳二元;它是本然自在的——对称与对称破缺;它是诗意的——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它渗透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之中,成为全世界任何民族不可阶升而上的语言巅峰,我为海峡两岸全中国人而自豪,因为我们祖祖辈辈以此种语言为凝聚力,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瑰宝。
(作者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①范曾:《〈尔雅〉说略》,《文史哲》,2013年第2期。
責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