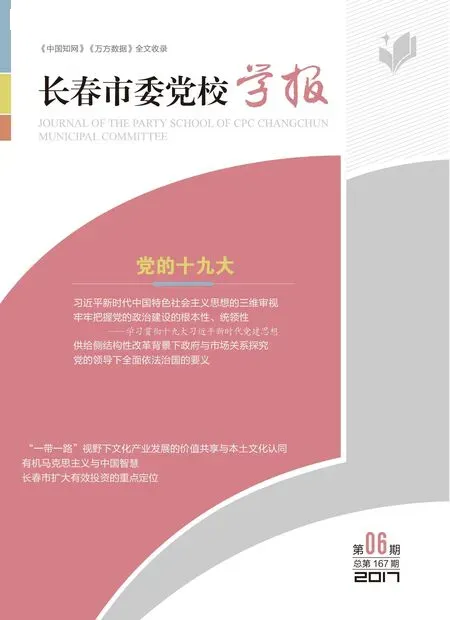从文献和考古遗存看东夏王朝兴衰始末
文/林硕
从文献和考古遗存看东夏王朝兴衰始末
文/林硕
作为女真族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第二个王朝,东夏历史长期湮没不彰。究其原因在于东夏的立国背景、征服者的禁毁政策,以及孤悬绝域的地理环境。通过梳理散见于《金史》《元史》和《高丽史》等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可以勾勒出东夏君主蒲鲜万奴离金叛蒙,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同时,上述文献可与吉林城子山山城等遗址发现的考古遗存相互印证,揭示出蒲鲜万奴薨逝后,东夏继续以蒙古藩属的身份活跃在东北亚舞台,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左右。
东夏;蒲鲜万奴;高丽
一、被湮没的王朝——历代史书不载东夏史事的原因
提起女真族(满族)建立的王朝,在大家的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爱新觉罗家族建立的清朝,其次便是同南宋长期对峙的金朝。其实,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还存在过另一个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亦可称之为“女真第二王朝”。然而,对于这个八百年前曾经在东北亚地区叱咤一时的国家,宋、金、明、清(各代)对它的记载竟都付诸阙如。
历代典籍均不见东夏史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时代背景。东夏立国在公元十三世纪初,正值东北地区战伐不断之时:蒙古族、契丹族纷纷起兵反抗女真族的统治,留守东北的女真军阀们则忙于扩充地盘,各方在白山黑水之间上演了一幕毫不逊于中原战场的群雄逐鹿。战乱频仍使东夏统治者戎马倥偬,未逞文治,纂修国史、典章尚未提上日程。其次,蒙古征服东夏后,对其采取文化禁毁政策,捣毁了大量的宫殿、庙宇,许多城池被夷为平地,使后人难以找寻当时的文明遗迹。第三,孤悬绝域的地理环境。蒙古人占领贺兰山下的西夏王朝后,也实施过文化灭绝政策,但我们仍能从宋人的各种记述中了解西夏史事。然而,东夏政权被蒙古势力阻隔在大陆的东北方,与宋、金均不接壤。偏居边陲的环境使宋朝史官、知识分子无法触碰到任何关于东夏的信息,更无从记录。上述原因造成后世对东夏的了解近乎空白。待到元、明两朝编修《金史》《元史》之时,甚至未给东夏开国之君蒲鲜万奴单辟立传,只在其他列传中零星提及其事,对东夏建国后的活动更是语焉不详。近代以来,吉林各地陆续发现了几处东夏时期的遗址、文物,政府也组织对东夏陪都南京所在的城子山山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利用周边民族所撰写的史籍证诸本国史事。东夏南部与高丽接壤,彼此交流与撞击亦较为频繁,因此在朝鲜王朝学者郑麟趾所著《高丽史》中,保存了大量东夏史实,可资借鉴。
二、文献中的东夏史事拾零
●契丹的反叛与出镇辽东
蒲鲜万奴,复姓蒲鲜,名唤万奴。由于《金史》《宋史》《元史》均没有为这位东夏开国之君树碑立传,导致后世对其生卒年和成长经历均付阙如。然而,通过分析“蒲鲜”这个姓氏,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测其系出名门。据《金史·百官志》记载:“蒲鲜”就属于白号之姓,封广平郡(今河北南部邯郸附近)。因女真人崇尚白色,故贵族姓氏在金朝被称为“白号”,地位凌驾于“黑号”之上。由是可知,蒲鲜万奴乃贵族出身,后来更因固守辽东抗拒蒙古-东辽①联军有功,还被赐予国姓“完颜”。因此,在《东平王世家》《元史》等典籍中称他为“完颜万奴”。[1](P2938)
1212年(金崇庆元年),契丹族的耶律留哥在隆安(今吉林农安)竖起恢复故国的大纛,聚众十余万,联合蒙古成吉思汗,动摇了女真族在东北的统治。面对起义,金主完颜永济任用蒲鲜万奴为咸平路招讨使前往剿灭,铩羽而归。1213年(金至宁元年),蒲鲜万奴受奉为辽东宣抚使,统领沈洲、广宁等路,②再次征讨耶律留哥,却接连败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咸平(今辽宁开原),退往辽阳。蒲鲜万奴虽然身处敌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但尚能通过辽东走廊与中都(今北京)方面保持联系。在《金史·奥屯襄传》中,可以查找到这一时期金宣宗给蒲鲜万奴等东北留守将领的谕旨:“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2](P2207)在诏书中鼓励他们同心同德,经武备边。但仅仅时隔半年,金宣宗竟宣布放弃中都南迁,渡过黄河退保汴京(今河南开封)。如此一来,辽东与中央政府的陆路联系被彻底隔断,蒲鲜万奴再难从朝廷取得任何支援。
●独立建国,尝试统一东北女真各部
面对不断进逼的蒙古-东辽联军,蒲鲜万奴在固守辽阳的同时,决定主动出击,统一东北。此时,包括上京会宁府在内的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在金朝留守官员手中。他们各自为政,或投降蒙古,亦或结堡自守。倘若蒲鲜万奴能进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的“龙兴之地”会宁府,既可以号召女真族共御外侮,又可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是故,在“贞佑南迁”后不久,蒲鲜万奴便发起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役。据史料记载:蒲鲜军队相继攻占了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澄)等地,东北残存的猛安、谋克③纷纷前往依附。然而,他在攻取婆速路(今辽宁西部丹东周边)时失利,两次皆负于婆速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之手。这让蒲鲜万奴威信扫地,之前归附的唵吉、斡都等十一个猛安纷纷叛附纥石烈桓端。[3](P2278)祸不单行,耶律留哥也趁辽阳守备空虚,一举攻占了蒲鲜万奴的大本营。失去巢穴的蒲鲜宣抚使行将沦为丧家之犬。为振奋士气,他在1215年(金贞祐三年)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史称“东真”),改元“天泰”。[4](P314)然而,仓促称王的蒲鲜万奴尚未回过神来,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便统领铁骑飞渡辽河,以东辽军队为向导,次第收服辽东各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势,蒲鲜天王采取求和策略。一方面,向成吉思汗递上了降书顺表,称臣归附,并遣世子蒲鲜帖哥为质。另一方面,自己率部沿鸭绿江退往海岛之中(今朝鲜铁山半岛以南的椴岛、椵岛以及身弥岛附近),休养生息。
●改号“东夏”,叛离蒙古
由于成吉思汗以入主中原为首要目标,很快便调木华黎回师攻金。蛰伏已久的蒲鲜万奴闻讯,迅速统御主力离岛,犹如蛟龙出海般席卷东北各地,更与完颜太平里应外合攻取了在女真人眼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上京会宁府;[5](P2666)甚至连高丽都畏惧其强盛的势头,助粮八千石。[6](P2281)公元1217年(金兴定六年,东真天泰三年),眼见东北大局尽在掌握的蒲鲜天王宣布脱离蒙古,将国号由“大真”改为“大夏”(史称“东夏”)。新政权以开元为首都,又分置南、北两京作为陪都。独立伊始,蒲鲜万奴对蒙古尚属恭敬:一方面,积极追随宗主国出征,有时甚至还派王子出阵助战;[7](P16)另一方面,蒙古在1219年(东夏天泰五年,高丽高宗六年)9月、1221年(东夏天泰七年,高丽高宗八年)9月、12月三次遣使高丽,也都有东夏使臣陪同,[7](P17、20、21)蒙夏关系进入蜜月期。但是,在木华黎和成吉思汗相继去世后,蒲鲜万奴逐渐显露出成为东北亚霸主的野心。不但轻慢蒙古使者,而且私下谩骂蒙古“贪暴不仁”,[7](P25)更有甚者在与高丽的文书往来中颐指气使,俨然以霸主自居。1233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东夏天泰十九年),窝阔台汗对蒲鲜万奴的狂妄行径忍无可忍,召集诸王合议讨伐:[8](P32)任命长子贵由为统帅,东平王塔思为副,一同出征;而塔思正是让蒲鲜万奴闻风丧胆的木华黎之孙。
闻知蒙古大军经高丽自南向北掩杀而来,蒲鲜万奴安排世子蒲鲜帖哥留守都城开元,自己前往南京——城子山山城迎击。蒙古副统帅塔思麾下大将查剌面对坚城,并不强攻。他先遣人佯攻东北角,诱导东夏军前往增援;继而率领勇士从西南侧发起冲锋,横槊立于城头,[9](P3603)大军乘势鱼贯而入。关于蒲鲜天王最后的归宿,史书上仅有“生擒万奴”四个字。[10](P1400)陪都陷落后,留守开元的蒲鲜帖哥出城请降。窝阔台汗对他较为宽大:册封王爵镇守东夏,内政事宜自行裁夺,只需缴纳赋税和派兵协同作战即可。
三、域外史籍与考古遗存中的东夏史事勾陈
●《高丽史》中的“后蒲鲜万奴时代”
进入“后蒲鲜万奴时代”的东夏再也不曾试图挑战蒙古的权威。作为第二任君主,蒲鲜帖哥汲取了父亲的教训,唯大汗之命是从。在窝阔台汗发动第三次高丽讨伐战之时,东夏军队应召出兵并担任前部,异常英勇。为表彰几代东夏君主的忠心,蒙古一直允许该国保持相对独立。然而,作为蒙古在东北亚最重要的两大附属国,东夏和高丽之间却牴牾不断。查阅朝鲜王朝郑麟趾所著《高丽史》可知:后蒲鲜万奴时代,东夏经常入侵高丽,战事频仍。比如1247年(高丽高宗三十四年)三月,东夏的一位猛安来函称有五十余名东夏人越境逃入高丽,要求遣返。高丽方面认为此乃无理挑衅,修书回应:“自贵国至我疆,山长路险,空旷无人,往来道绝。贵国妄称推究逃人或称山猎,越境横行。其于帝旨各安土著之意何如?自今无故越境一皆禁断!”[11](P39)简而言之,高丽抬出蒙古大汗做挡箭牌搪塞东夏:天朝上国让我们各守其土,管理好自己的百姓。贵国经常借口追捕逃人、猎物越界骚扰,应断然停止挑衅。事实上,东夏确实经常出兵劫掠高丽的牛马、人口。从规模上看,每次入侵的东夏兵多则二千、三千之众,少则百余骑。从频率上看,高丽拒绝遣返逃人之后的六年间,东夏分别在1249年(高丽高宗三十六年)9月、1250年(高丽高宗三十七年)2月、1252年(高丽高宗三十九年)5月和1253年(高丽高宗四十年)2月有组织四次的袭扰高丽。[11](P41)除陆军外,1258年(高丽高宗四十五年)12月,东夏还曾经出动水师进攻高丽高城县的松岛,烧杀焚船。[12](P38)后蒲鲜万奴时代的东夏国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高丽高宗四十五年之后,东夏对高丽的侵扰戛然而止,史籍长期没有出现相关记载。这说明在此期间东夏王朝内部发生了变动,无力发动对外战争。《高丽史》中最后一次出现“东夏”之名是在第三十卷的《高宗世家》:“(高丽忠烈王十三年)九月庚子,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来谒公主。”[13](P10)时间大致相当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据此可以断定:东夏政权至少存在到13世纪80年代。高丽史书能提供的关于东夏的相关信息至此结束,欲进一步勾陈史事,就需要借助20世纪以来发现的东夏考古遗存。
●城子山山城遗址考古发现与东夏史事勾陈
目前已确定的比较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位于今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以东10公里处的城子山山城遗址。一般认为该遗址即东夏陪都南京城所在地,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蒲鲜万奴据守的最后堡垒。城子山山城遗址本是唐代割据东北的渤海政权所兴建。蒲鲜万奴攻占此城后,将其打造为防御蒙古的桥头堡。由于城子山山势西高东低,故山城遗址也呈现出这一地理特点:城内设有东门、西门、北门和东南门四门。西门高居山上,门外还构筑了防御工事。环城东、南两侧分别有海兰江、布尔哈通河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正因如此,蒲鲜万奴才寄希望凭籍这座依山傍水的坚城阻挡蒙古铁蹄。城内现存百姓居住区和东夏陪都宫殿区两类遗址,零星散布着辽、金时期的铜钱、瓷片、瓦砾等遗存。宫殿遗址前砌有台阶,凡九层,颇有气势;可以想见当日东夏都城开元的宫室规模必定比陪都更胜一筹,足见其国力之强盛。
早在上世纪初,就有附近村民在城子山发现东夏时期的各类陶片、瓦当、铜钱、铜镜等文物,其中最具价值者当属1954年发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图一)。此印呈方型,铜质,边长6公分。印文为九叠篆书,阳文“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左侧有“南京行部造”字样。印背柱钮上刻有“天泰三年六月一日”,钮顶部还刻有一个“上”字。此印的发现为研究东夏初期的政权组织结构提供了珍贵史料。如前所述,蒲鲜万奴在天泰三年(1217年)将国号由“大真”改为“大夏”。“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的发现证明东夏立国之初就采取“三京制”的政权结构,以南、北两京拱卫都城开元。同时,印信左侧还刻有“南京行部造”五个字。所谓“行部”者,又称“行六部”,[14](P241)乃是延续金代旧制,在地方上设置行六部以代替中央实施统治,是朝廷控制力减弱的体现。铜印左侧的“南京行部造”证明:此时的蒲鲜万奴政权尚未确立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仍旧沿用金末设立“行部”的做法。

图一 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南京行部造)拓片[14]

图二 勾当公事之印(大同七年七月礼部造)拓片[14]

图三 《宁安县志》所载天泰十八年印拓片[15](P19)
除此之外,1975年在城子山山城遗址还发现了一件对东夏史事勾陈至关重要的文物——“勾当公事之印”(图二)。铜印呈方型,边长5.7公分,印纽呈柱状。印文为九折篆书“勾当公事之印”,左侧刻“礼部造”,右侧刻有“大同七年七月”。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大同”年号的君主有梁武帝、辽太宗两位。然而,梁朝偏安江左,辽太宗的大同年号实际仅仅使用了八个月,绝不会出现“大同七年”字样。故笔者认为:大同年号无疑属于某位东夏君主,但这个人显然不是蒲鲜万奴。首先,查阅《金史》《元史》以及《高丽史》,均无蒲鲜万奴改元大同的相关记录。其次,延吉以北的宁安县在1919年曾经出土过一枚刻有“天泰十八年”款识的“不匋古阿邻谋克之印”(图三),足以证明蒲鲜万奴在位19年并未改元,始终使用“天泰”年号。是故,“勾当公事之印”印信上所刻的“大同”,应该是“后蒲鲜万奴时代”的某位东夏君主所使用的年号。换言之,东夏君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保有自己的年号。直至忽必烈汗统治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16](P254-255)享受半独立状态的东夏王朝才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塔思传》,中华书局,1973.
[2] 《金史》卷一百三《奥屯襄传》,中华书局,2005.
[3] 《金史》卷一百三《紇石烈桓端传》.
[4 ] 《金史》卷十四《宣宗本纪》.
[5]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梁持胜传》.
[6] 《金史》卷一百三《完颜阿里不孙传》.
[7]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二《高宗世家》,明万历四十一年抄本.
[8] 《元史》卷一百五十二《石抹查剌传》.
[9]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
[10]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
[11]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十四《高宗世家》.
[12]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
[13] 《金史》卷十《章宗本纪》.
[14] 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3).
[15] 《宁安县志》卷三《古迹 金石》,1924年印本.
[16] 《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
注释
①1213(金至宁元年)三月,耶律留哥称王,改元元统,建都广宁(今辽宁北镇),史称东辽。
②“路”,北宋时期设立的国家一级行政单位,被此后的金、元两代承袭沿用。
③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采取的兼具行政和军事职能的制度,与清代“八旗制度”类似。猛安即千户长,谋克为百。
K246.4
10.13784/j.cnki.22-1299/d.2017.06.011
林硕,国家博物馆馆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和对外交流史。
责任编辑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