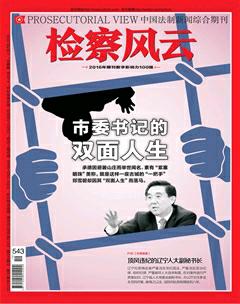暴徒先生
郑金玉
前一阵子看澳洲的报纸,看到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前财长,可能当官时得罪了人,离职后在餐厅遭到三个年轻人攻击。三人把他堵在卫生间里,其中一人按着他的脑袋向墙上猛撞。有意思的是,他是这样描述打他的人:“这时一个Gentleman(先生) 冲了进来,开始打我的头……”在描述案情时,他一直用极其正式的“先生”一词,来称呼对他施暴者。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应当咬牙切齿地说:有一个“家伙”,或有一个“暴徒”。
我于是注意到一个法律文化的细小差别。
在许多国家,对刑事被告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法庭成员对他仍然以“先生”相称。而我们是绝不会称这些坏蛋为先生的。我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们起诉书、判决,或者报道,都喜欢用“窜”这一个词。犯罪分子一定是“窜”到犯罪地点的。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敌人,我们对其一定要用贬义。
在这样的习惯之下,很多现象会让我们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号称“红色男爵”的德军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八十多架英军飞机,用我们的话来说:双手沾满了英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当他被英军击落时,英军却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放排枪向这位“英勇的战士”致敬。
我們如果有人这样做,可能会被追问:立场哪里去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唾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几个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对那位称打人者为“先生”的前财长,对厚葬敌方飞行员的英军,隐约有一些称许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这一隐隐的称许之意?
我们因此会发现:在仇恨与文明之间,后者往往拥有更强大的道德的力量。而这一道德力量,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法庭对一个“人渣”仍然以“先生”相称时,这不仅仅是尊重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这同样关系到仇恨可能弄脏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从而破坏了文明,最终危害社会。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不能容忍对敌人的尊重,而更崇尚“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对仇恨的考虑,甚于对文明的考量。西西里黑手党有一个规矩:凡出背叛组织者,全家杀光。但是,如果这个人自杀了,家人就可以豁免。
一味强调“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就容易走向极端,甚至造成恐怖。我们崇尚“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但不幸的是,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种境界。习惯对敌人这样以后,对同志一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无情”一旦变成习惯,对谁都会一样了。我们有些机关,对待人民群众,同样也是“门难进,脸难看”,就是一例。在这样的文化下,有些人连亲属也做不到“春天般温暖”。辽南农村曾有一案,姐夫与舅哥打牌,为了五角钱,姐夫一刀捅死了舅哥。
其实,面对敌人仍要保持文明,这不是他国的特权,本来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太平天国李秀成东征,清军猛将张国梁战死于桥下,李秀成感其忠勇,也厚葬了对手。但不知从何时起,面对仇恨与冲突时,我们开始缺乏一种从容不迫,一种温文尔雅,而更多是一种暴戾之气。
儿童读《狼和小羊》的故事,没有孩子会说:“一条恶狼如何如何。”其实,人类的本性,还是知道:尊重敌人,其实是维持自己的文明。我们长大了以后,还是莫忘这一本性为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