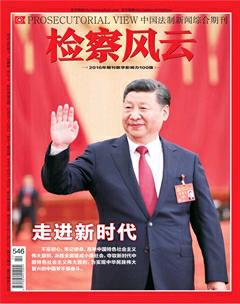看不见的心魔
宋颖
《看不见的客人》是西班牙导演奥里奥尔·保罗执导的口碑悬疑片,该影片上映不久便在多个网站拿下评分第一,其热度不可小觑。
该影片虽然只有短短的110分钟,但整体结构异常缜密,在细节方面的刻画相当精准,对于观众的心理拿捏极其到位,环环相扣的情节之下,观众丝毫不会因为倒叙、插叙、假设的多种置换而感到疲乏,相反大都伴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酣畅淋漓、欲罢不能,这正如导演推介所讲“看这部影片就像坐上了一趟高速列车”。
推理小说与刑侦的差别在于,推理小说设定好条件,带读者们进入到一个黑屋,然后在这种设定条件中推论并寻找多种可能,而刑侦则需要拓宽侦查人员的思路,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通过合法的手段、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的结论。两者冲突之下,法律人往往会提出自己逾越剧情框架的质疑,但又很享受这种逻辑推理的反转快感。
正像刑侦实践常提的一句话:“一句谎言,需要上百句谎言去遮掩”,剧情中男主角不断在欺骗,但在女律师的揭谎之下又不得不扯出其他谎言去圆上一个谎,种种谎言之下人性的幽暗展露无遗。但更为精妙的在于女律师本身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謊言,她用技高一筹的遮掩手段,利用审讯中常用的设谎导谎战术,让男主角不知不觉上当,交代出了沉尸地点。
但真正的刑侦实践并非如此:一方面,将车沉入湖底并不是销毁证据的绝佳手段,车中汽油的油花也好,车内尸体的腐化也罢,都将随着时间流逝给外界留下更多的线索;另一方面,行为与痕迹之间是相互印证的关系,只有超越当前勘察技术难以发现的状况,绝没有彻底消灭痕迹的可能,这不管是沉尸路上的血渍、车痕,宾馆留下的脚印、指纹抑或是其他。
虽然男死者的母亲通过假扮律师,通过精妙设计的对答窃取了男主角的语音资料,随着片尾音乐的响起更感觉到了朴素公平正义的实现,但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说,这并非完美无缺。一者,男死者母亲主体身份问题让她没有讯问的资格,这种对话难有法定的供述意义;二者,其以脱罪为名的对话,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和探讨之上,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男主角谋杀并不容易;三者,音频资料相对而言没有其他书证、物证的稳定性、唯一性,况且因为窃听程序不合法很可能被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当然,西班牙是陪审制,死者母亲通过获取陪审团的集体同情也并非绝无可能。
结合我国的法律责任角度来说,男主角与情妇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本来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加之事故起因是一头鹿意外窜了出来,而且车祸中所撞死者开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时发短信,这些都可以减少男主角的民事责任,通过保险理赔再加上自己一些额外赔偿到位取得家属谅解,再给家属一些抚恤金要求代为保密,尊重双方隐私,那么这件事完全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当男主角与其情妇选择驾车逃逸、沉车灭迹,则毫无疑问触犯了刑法,双双涉嫌交通肇事罪,相对比前面的结果而言可谓天壤之别。进而言之,若男主角最后所言男死者沉车时尚未死亡属实的话,男主角不施予抢救反而将车辆推入湖中的行为则涉嫌故意杀人罪。那么,将一场民事纠纷活生生变成刑事案件,最后还要再搭上其情妇的一条人命,谎言一个接一个,掩饰行为也一次又一次,真可谓一步错步步错。
侥幸、遮掩、回避、贪婪,这些其实都是人生而有之的心魔,它正如那个看不见的客人一样随时造访我们的心田,驱动着我们意图为所欲为,暗示着我们绝不会被发现,恐吓着我们要想尽办法去遮掩、逃避。倘若任由心魔驱使的话,我们无疑会一错再错,最终坠入地狱的深渊而悔恨终身。
解铃还须系铃人,看不见的心魔只能通过看得见的法律来拯救。两害相权取其轻,理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客观分析自己目前的境地,选择合法而最恰当的方式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这才是拯救自己、拯救他人的最好方式,也是真正能帮助人们从心魔手中彻底反转的唯一途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