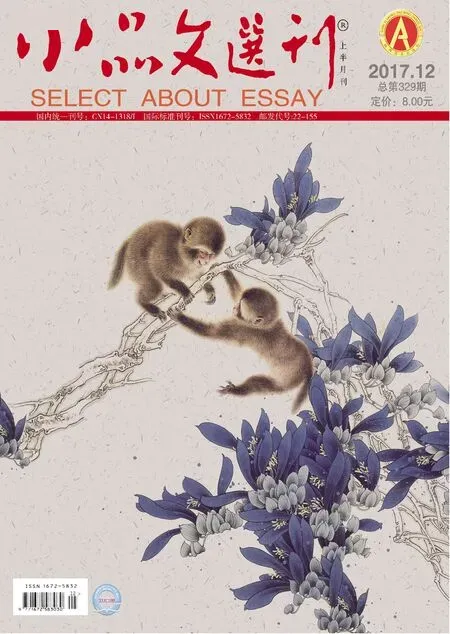会思想的芦苇
□赵丽宏
会思想的芦苇
□赵丽宏

最近回到我曾经“插队落户”的故乡,一下船,就看到了在江堤上迎风摇曳的芦苇。久违了,朋友!
芦苇,曾经被人认为是荒凉的象征。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随处可见的植物,却代表着美丽自由的生命,它们伴随我度过了艰辛的岁月。
从前,芦苇是崇明岛上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芦苇的一身都有经济价值。埋在地下的嫩芦根可解渴充饥,也可入药。芦叶可以包粽子,芦叶和糯米合成的气味,就是粽子的清香。芦花能扎成芦花扫帚,这样的扫帚,城里人至今还在用。用途最广的,是芦苇秆,农民用灵巧的手,将它们编织成苇帘、苇席、芦篚、箩筐、簸箕,盖房子的时候,芦苇可以编苇墙,织屋顶。很多乡民曾经以编织芦苇为生,生生不息的芦苇使故乡人多了一条活路。我在崇明“插队”时,曾经和农民一起研究利用地下的沼气来做饭。打沼气灶,也用得上芦苇。我们先在地上挖洞,再将芦苇集束成捆,一段一段接起来,扎成长十数米的芦把,慢慢地插入洞中,深藏地下的沼气,会沿着芦把的空隙升上地面,积蓄于土灶中,只要划一根火柴,就能在灶口燃起一簇蓝色的火苗,为贫困的生活增添些许温馨。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件无比奇妙的事情。
在艰苦的“插队”生涯中,芦苇给我的抚慰旁人难以想象。我是一个迷恋自然的人,而芦苇,正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妙礼物。在被人类精心耕作的田野中,几乎很少有野生的植物连片成块,只有芦苇例外。没有人播种栽培,它们自生自长,繁衍生息,哪里有泥土,有流水,它们就在哪里传播绿色,描绘生命的坚韧和多姿多彩。
春天和夏天,它们像一群绿衣人,伫立在河畔江边,我喜欢看它们在风中摇动的姿态,喜欢听它们应和江涛的簌簌絮语。和农民一起挑着担子从它们中间走过时,青青的芦叶掸我衣,拂我脸,那是自然对人的亲近。最难忘的是它们开花的景象,酷暑过去,金秋来临,风一天凉似一天,这时,江边的芦苇纷纷开花了,那是一大片皎洁的银色,在风中,芦苇摇动着它们银色的脑袋,在江堤两边发出深沉的喧哗,远远看去,犹如起伏的浪涛,也像浮动的积雪。使我难忘的是夕照中的景象,在绚烂的晚霞里,银色的芦花变成了金红色的一片,仿佛随风蔓延的火苗,在大地和江海的交界地带熊熊燃烧。冬天,没有被收割的芦苇身枯叶焦,在风雪中显得颓败,使大地平添几分萧瑟之气。然而我知道,芦苇还活着,它们不会死,在冰封的土下,有冻不僵的芦根,有割不断的芦笋。只要春风一吹,它们就以粉红的嫩芽,以翠绿的新叶为人类报告春天的消息。冬天的尾巴还在大地上扫动,芦笋却倔强地顶破被严霜覆盖的土地,在凛冽寒风中骄傲地伸展开它们那柔嫩的肢体,宣告冬天的失败,也宣告生命又一次战胜自然强加于它们的严酷。
我曾经在日记中写诗,诗中以芦苇自比。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比喻使我感到亲切。以芦苇比人,喻示人的渺小和脆弱,其实,可以作另义理解,人性中的忍耐和坚毅,恰恰如芦苇。在我的诗中,芦苇是有思想的,它们面对荒滩,面对流水,面对南来北往的候鸟,舒展开思想之翼,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我当年在乡下所有的悲欢和憧憬,都通过芦苇倾吐了出来。
我曾经担心,随着崇明岛的发展和进步,岛上的芦苇会渐渐消失。然而我的担心大概是多余的,只要泥土和流水还在,只要滩涂上的芦根还在,谁也无法使这些绿色的生命绝迹。我的故乡,也将因为有芦苇的存在而显得生机勃发,永葆它的天生丽质。
这次去崇明,我专门到堤岸上去看了芦苇。芦苇还和当年一样,在秋风中摇晃着银色的花朵。那天黄昏,我凝视着落霞渐渐映红那一大片芦花,它们在天地之间波浪起伏,像涌动的火光,重又点燃我青春的梦想……
选自《赵丽宏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