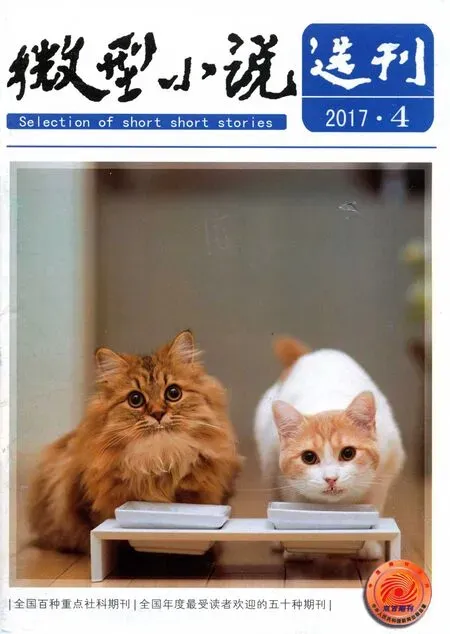一辈子的对手
□安 宁
一辈子的对手
□安 宁
1
我和他一直没有共同语言,我总怀疑自己是他捡来的。但事实上,我的确是他的亲生儿子:有着和他一样棱角分明的脸,一样淡漠冰冷的神情,甚至连眉毛的走势都和他一样倔强而执拗。每次我们一起出门,即便是一前一后地走,也会有人在我们背后小声议论:“这绝对是一对父子,你看他们昂头走路的姿势,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样的结论常常让我难过,他是一个我多么想要摆脱掉的人啊!他有着尖酸刻薄的言语,从来不懂得温柔,见了我永远像见了阶级敌人一样。母亲每次从远方来,看着我对她买的大堆礼物不屑一顾的样子,总会叹气说:“你怎么和他一样,总让人伤心呢?”我想这就是宿命,我极力想要逃掉的却愈加清晰、鲜明地烙进我的生命里。
在我14岁以前,我和他也有过快乐的时光。那时候,他和母亲还没有离婚,他在一家单位做工程师,业绩不错,倍受领导的赏识。那时的他不怎么和母亲吵架,但因为我的顽劣,他像吃饭一样频繁地对我恶语相向。他看见我拿回去的满是“×”的试卷,会立马愤愤然地撕掉;我在学校里惹祸,他会当着老师的面狠狠地给我一拳。尽管我常常被他打得眼冒金星,但依然英雄般地站着纹丝不动。母亲每次帮我们收拾满屋的狼藉时总会笑着说:“天底下还有像你们这样相像的父子吗?你们简直就是在跟另一个自己争吵。可是,人跟自己过不去是多么累的一件事啊!”但我和他并不觉得累,反而从中品出无限的乐趣来。
我喜欢看他企图将我的嚣张气焰打垮,装得像皮球一样精神饱满却颓然跌进沙发里的模样。那一刻,我感觉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并且得意地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他应该也是一样吧。当我因为怕冷,不得不将他扔过来的热水袋乖乖地拥进怀里时,他脸上的笑意是生动鲜明的。
2
我14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机器事故将他的双臂齐刷刷地卷去后,一切都变了。他的脾气变得史无前例地坏,他和母亲的关系也因此恶化,直至以离婚告终。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走,我看着窝在角落里头发蓬乱、神情凶恶的他,听他朝我大吼:“别在这里晃来晃去,让我心烦,都给我走!”我突然很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不要转学,我要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我选择跟他在一起。我没有想以后的生活会怎样艰难,在那一刻,我只知道这个曾经像狮子一样对我咆哮的人以后再也没有能力让我挨他的拳头和巴掌了。
乡下的爷爷奶奶来照顾我们。为了继续生存,他的嘴自此不只用来骂我,还学会了衔着笔艰难地绘图。一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只是无法得到提升,只能做一名普通的工程人员,但这份薪水足以养活这个家,他昔日的自尊也因此得以保全。他照例可以对我大吼大叫,施展一个父亲的威风和尊严。而他也只剩吼叫了,他那曾引以为傲的振臂一呼的英勇已荡然无存。
我依然是一个粗心的少年,知道他有爷爷奶奶照顾,便从来没有想过他要怎样解决那些在我看来易如反掌的吃饭、穿衣、如厕之类的琐碎事情。
因为作息时间不一致,我很少和他一起吃饭。每天放学后,他总是在我风卷残云般地吃完饭后才下班回来。早晨,我抓起书包冲出家门时,他的房间里才有习惯性的咳嗽声响起。后来,偶然的一次,我返回家向他要钱,一头撞进他的卧室,见他正光着脊背,努力地将脑袋钻进挂在墙上的套头衫里。那一刻,他像极了一条笨拙的虫子,他将头从里面探出来,而后长长地舒一口气,宛如做了一件劳苦功高的大事。当他看见我愣在门口时,他的裤子还松松垮垮地搭在“半山腰”上,头发好像鸡窝一样蓬乱。
我们彼此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先吼道:“谁让你没敲门就进来的?快给我出去!”我倚在门框上,昂着头没有吱声,然后走上前,细心地帮他扎好腰带,而后从他钱包里掏出一张20元的纸币,这才漫不经心地走出去。轻轻关上门的时候,我的背后一片静寂。但我知道,他的眼睛里写满了挫败和哀伤,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好强的人啊!
3
我似乎一下子长大成熟了。
我开始在他吃饭时,记得将吸管给他放好;在他吃得满脸米粒时,将毛巾洗好递给他;看他要去上厕所,走过去将马桶盖打开;见爷爷帮他洗完头发后,将吹风机拿过来插上电,等他坐定了给他吹头……我这样“殷勤”,他显然不适应。我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假装从容和自然,而且沉默又迅速,不给他任何反驳的机会,任他的一堆言语憋在心里像桃子一样烂掉。
我并没有逾越爷爷奶奶的职责,帮他穿衣服或是擦脸梳头,他也刻意回避我进一步的“殷勤”。这样的敏感和尊严,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不准我靠近半步。曾经争吵不休的我们很突然地陷入一种可能一触即发的沉默当中。
后来有一次,奶奶住院,爷爷去陪护,临走时嘱咐我别忘记早起给他穿衣服。那天晚上,我上了闹钟后很幸福地睡去,可还是起晚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时,他已经在客厅里,衣服上全是褶皱。我突然朝他大吼:“为什么不脱衣服就睡?”吼完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忘记在临睡前帮他脱呢?我无比羞愧地转过身去,拿起梳子给他梳头,他顺从地坐下来。我又将毛巾浸湿,笨拙地给他擦脸,刮掉新长出来的胡子。
我们之间的空气依然是冷寂而又沉闷的,直到我已经下楼,他突然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朝我喊:“记得放学后买午饭回来吃。”我抬头看他一眼,随即快步走开。我不能让他看见我的眼泪,就像他曾经那样千方百计地躲避我,不让我窥见他的脆弱一样。
我原来是这样依恋他,用伪装的冷漠爱着他。而他也是一样吧,因为我们是那样相像。我们谁都不曾低下头说出一个“爱”字,可岁月还是让我们相伴着走到今天,走到我终于承认他再也离不开我,我也不能将这个老去的对手舍弃。
(原载《学生天地·初中版》2016年第10期 江西潘光贤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