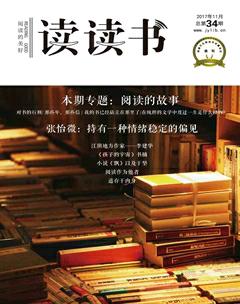乡音的胜利
李建华
我总感到锡剧里有一种百代的牵挂,在依偎着重柳绿杨的江南,似乎就掩映在明清的晚月里,组成江南民俗的一本特殊记录本。
听温软的吴语,使外地人到江南,就像走进雨夜听细细的雨声,而与京戏迥然相异的锡剧,就是对江南鸟音诠释。锡剧站立穷人家门口,心痕上也有一点翻身农民感,它楚楚可怜的韵致,更多时候还连着耳熟的唱春调。
王彬彬的一声唱,总是旁无杂音感时带出来,就像在为我竭力作申斥。那种乡音,在我听来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了,我一生没能走出故地,一生耳邊回旋的是锡剧,听锡剧,多半我就有接受细雨的那种滋润感;梅兰珍更像个江南文士旁聘来的一位红袖添香,她的清润嗓音,就是“沾衣不湿”的一场杏花雨,糯糯软软,又让我另有享受细雨的一种爱抚感。
听锡剧,就无需沏一杯上好的清茶了,因为它比清茶更入脑入心,它接近天然的音色,若用孟浩然、王昌龄的诗句来作比,怕也只能做个擦边形容了,沐浴在这种优雅的音色里,久了,我在背人处,往往也要音域窄窄地来上一嗓。在我看来,锡剧就好比杜拉斯的《印度之歌》,里面一样装着江南的秘密。
锡剧是江南的摇篮曲,是江南的玄妙。它是我们扰乱心绪的调整,是江南人最不费唇舌媒介,它是我拥抱过的一段充实。走进锡剧,我等于走进亚里克斯·哈里的《根》,江南是我的根。锡剧在江南,不是一个逗留些时日的过客,它是找对的门路,它是故人的重逢,是江南人的叙旧、唠叨,是二人又找回了的昔日乐趣。所以,才有一批批江南土著人为它心驰神往,为它如痴如醉。
锡剧,在审美上,甚至比我们听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交响乐更令人心肺涤荡,酣畅淋漓,尽管它更多的时候设定在一段苦楚,一段苦尽甘来的故事上。可它作成了江南人的贴身音乐,作成了我精神漂泊的最后归宿处。此刻,我在那一段丝竹声里,就走进《红楼梦》的山阴道上,也来一次潇湘妃子的“不悼人,却悼花”。我在接受免费的享受的时候。也陷进一点哀婉。
然而,锡剧毕竟是让人抖擞精神的东西,就像赏美景,我们就能赏到一种力量。江南为什么能给人有憧憬,就是因为江南美。不是吗,你透过圆圆的桥孔,藏得不仅有一弯弦月,还有点红的枫叶,还有染黄的银杏。江南的那一处风景里,不伴有黄鹂枝头鸣翠柳,江南的即景里,又几时少过喜鹊登梅声啾啾的绮丽。
这多河、多桥、多柳、多芦、多竹、多径、多雨、多雾、多园林、多丽人的江南,就是锡剧的衣食。它是江南民俗安置在本土上的一个浓酽的色块。锡剧,让江南融入一个它该有的常态,那个带点寂寞的孤独,且又宁静和充实的世界。
江南的吴歌浅唱,当然还有越剧、绍剧,还有评弹和昆曲,它们一如过往船只的欸乃之音,一如书场中行云流水般的弦索声,一如茶壶里氤氲的水气,共同湿润着这里的山水草木。
锡剧,就像慵懒的阳光洒落在江南本土上,时常在构成我的一段怀旧,构成我的一段时时可以拿来复审的档案。
走进锡剧,我才能不被讲普通话口音的人当做异乡人,我才能感觉一双脚是踩在我从前的血地上,是八字算命中说的,那个不能离开的血地。我能够醒悟,自己没误闯出苏锡常,我说一句:“吃刀子!”还不会有人找我算账。
那把阿炳的二胡,那把周少梅的二胡,那把刘天华的二胡,那把闵惠芬的二胡,那把演奏过《珍珠塔》、《拔兰花》、《红花曲》等等的二胡,在一个音节上作美美的消磨,千回百转,寸断柔肠。它是那样的铿锵有力。
在江南锡剧的强势面前,流行歌曲只能算一次逞强。锡剧不曾断线,只要有吴语,就会有传承。我又听到了慢按的云板,慢打的颤板,悠扬的丝管,又见到了大陆调、老簧调,又见到了票友们在民间抬起水袖演《西厢记》里一折: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锡剧不是我们江南人总也做不尽的一个甜梦吗?
锡剧,让我没了倦意。我支耳听,微风里竞也裹夹着这糯软的一声唱,年老的人总爱用个收音机作播放。在我听来,此曲虽淡却隽永,此味虽土却撩人。我置身在戴望舒的《雨巷》里,锡剧就绕着墨意浓浓的回廊砖栏,绕过着粉墙黛瓦曲桥花窗,竟把湖边退潮后裸露出蹼脚的鸭子,也驯化成了一个不错的锡剧票友,同样是鸭子,其“嘎嘎”声就少了北方鸭子的粗粝和阳刚。还有那牧童的老水牛,那“哞哞”的孤寂叫声,仿佛也浸染上了梅派风味和彬彬腔调,那个甜腻劲,都好像在作秀。
这吴侬软语的地方戏,就是这样感染你、同化你,让你造势张扬的话语听起来也不冲撞,因为它使你处于热电效应的血液获得冷却,处于膨胀状态下的心律获得宁静。
一幕哀怨和畅快,老牌而简约的《双推磨》,唱了一代又一代,而一代又一代又把街头巷尾流行的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爱的奉献涛声依旧明天是个好日子2002年的第一场雪老鼠爱大米睫毛歪歪菊花台青花瓷都给击败了。
这是乡音的胜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