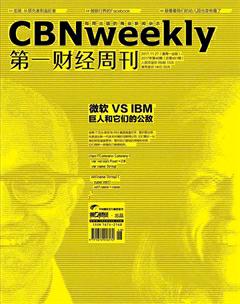眼看着我们的幼儿园也变有趣了
黄语晴
世界上第一个“幼儿园”的创办者、19世纪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内在本能”。因此,他主张,游戏和手工作业应是幼儿时期最主要的活动,而知识的传授只是附加的部分,穿插其中。
福禄贝尔的学前教育理念启发了包括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巴克明斯特·富勒在内的众多20世纪早期建筑师。如今,一些中国建筑师开始拾起福禄贝尔的理念,想要通过有趣的、充满互动性的空间设计方式来介入幼儿教育—在此之前,中国的幼儿园空间设计大多缺乏“激发儿童兴趣”的理念,与其他的学校空间没有太多区别。

“小孩在幼儿时期,他要完成三件事—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每一个幼儿园的设计都应该解决这3个问题。”山水秀建筑事务所建筑师祝晓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家事务所设计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幼儿园位于上海西北部的安亭。这是一个由不同的蜂窝型单元拼接起来的建筑,蜂窝构造在建筑内部形成了很多六边形的庭院、露台;同时园内采用了“月洞”、栅栏这类半通透隔断,整体建筑风格源自江南庭院。
由空间引导儿童的自发探索是建筑师的首要目的。与长方形的封闭教室、用实墙隔断的封闭走廊相比,儿童在这样的空间里能看到更丰富的层次—月洞和栅栏在视觉上塑造了更多“若隐若现”的半开放空间,吸引他们去游走探索。

连接这些半开放空间的,是六边形的室外走廊—儿童在这个空间里按着六边形的方式走路,这意味他每走一小段就会遇到岔口,就得拐个弯。沿着走廊,他既可以围着庭院绕圈,也可以在相互拼接的六边形路径中不断改变方向,观察左右两边的事物。“这会比走一个长长的走廊要有趣得多。”祝晓峰认为这种曲折的行走路径更贴合小孩发现世界时的“漫游感”,在无形中激发和引导小孩去观察和漫游,“长长的走廊当然非常有效率,但是不应该让一个儿童在小时候就去思考效率是什么。”
“曲径通幽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而且潜意识中其实是在培养他的方向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幼儿园园长汤英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开始,这一蜿蜒曲折、迷宫般的路径曾让不少家长和小孩迷路,但随后,这种设计方式成为了儿童探索空间的乐趣。

在此之前,中国大部分的公立幼儿园给人们留下的是千篇一律的印象:长方形的教室、讲究效率的直线走廊、封闭的教室。这样的设计在祝晓峰看来是枯燥的“指令性设计”,他认为,现代建筑已经被数字化了,如今的幼儿园设计规范里充满了各种数字:比如每天至少要有3小时日照,规定了每个教室的大小、高度以保证空气新鲜度等。“但规范里已经没有这种文化性的内涵。我们是希望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在孩子小的时候,在他们心里播下一点地域性的文化种子。”祝晓峰说。
“理想的教育空间应该是开放的、没有边界、平等的;而不是强大有风格的、显示权威和强调管理的空间。”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马岩松说。
如果你看过全球知名的幼儿园建筑设计范本之一—手冢夫妇设计的富士幼儿园,那就是一个开放性幼儿园的极端展现。鸟巢式的一层椭圆形建筑中几乎不设任何阻隔,连小朋友的教室都是依赖于家具来分区;而儿童随时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挪动家具改变空间,与隔壁班级聚在一起活动。二楼开放的椭圆形天台则可以让所有小孩跨越自己的班级边界,绕圈奔跑。这种开放环境能够增加儿童与他人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并让儿童适应开放性环境中随时可能遇到的变 化。
除此之外,空间还应为儿童提供安全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由于从母体脱离不久,与身体有紧密关系的小空间往往让小孩觉得安全,太过开阔的空间反而会对其造成心理压力。

今年9月,马岩松在日本爱知县冈崎市设计了一个名为“四叶草之家”的私人幼儿园,由旧居民房改造而来,崭新的、不规则的建筑外壳下还保留着过去居民房的部分木结构。建筑师通过包裹式的新外壳和空间内的老木头来实现幼儿园园长所希望提供的“家的记忆与感觉”。此外,为了给儿童营造安全感,建筑师还利用建筑外壳与内部木结构的空隙,在二楼制造了一个只有小孩才能钻进去的角落,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窗口保证采光,窗口正对着一片稻田。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建筑师朱竞翔曾在甘肃会宁为乡村学前教育做过“童趣园”,这个轻质建筑物在地面、墙上都设置了一些凹凸,小孩能够爬上爬下地躲到一个“窟窿”里。
在创造安全感之外,这种凹凸空间里也自然形成了人的互动。绝大部分设计过幼儿园的建筑师都把玩耍作为幼儿启蒙教育中的一部分,他们会想办法在空间里制造些乐趣。
“你有时看不到我,有时我能被你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有的时候咱俩又能互相看到,”朱竞翔解释道,“那这个时候就好玩了,哪怕不说话都可以制造很多的交流。小孩他不是通过词语来表达,他是通过行动来表达。”
在童趣园里,建筑本身附带的灵活组件提供了很多互动乐趣,而童趣园最初的设计目的,也是让学龄前小孩有一个安全的运动玩耍空间,同时引入一些志愿者教师,带动乡村缺失的学龄前启蒙教育。“学龄前小孩处于长肌肉、长身体的阶段,他实际上是靠运动来学习。”朱竞翔说。
同样,在迪卡幼儿园设计中心目前正在施工的“棒棒糖理想幼儿园”里,建筑师规划了大量的室外娱乐空间,包括了戏水区、沙石区、养殖区、种植区、攀爬区、木屋区、涂鸦区等。而由于场地西北侧高差较大,他们又以梯田为灵感做了一片有高差的活动场地。“其实还是寓教于乐的一个概念。”迪卡幼儿园设计中心创始人王俊宝说。要把这些丰富的设施统一在有限的室外场地也是一门学问,他认为必须做出动静区别和节奏性。
相比早已关注起幼儿园设计的日本,中国的幼儿园设计受到关注是近两年的事。与中国更倾向于丰富的、游乐园般的幼儿园设计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幼儿园相对朴素、自然的室外环境。
这可能与日本小孩的性格有关,“从全球的儿童对比上来看,日本的孩子会显得稍微偏安静一些。”日比野拓在给《第一财经周刊》的书面回复中写道。但他也并不赞成游乐场式的设计,“我们觉得幼儿园还是应该再朴素一些,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提供给他们,必须留一些让他们自己创造的机会。”
日比野拓是日比野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是日本颇为知名的幼儿园设计品牌,曾经设计过400多所幼儿园。日比野公司设计的很多幼儿园里,常有一些内凹空间,它们可能是窗台、闲坐的场所,也可能作为涂鸦 区。
幼儿园需不需要五颜六色?这是说到当下中国幼儿园建筑时,被频繁讨论的一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颜色也能激发小孩的感知与想象。“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幼儿园,但我们一直坚持的是,幼儿园真正的色彩应该是孩子们给幼儿园带来的颜色。”日比野拓说。
祝晓峰也有相似的观点:建筑要有一个素的基底,而之后小朋友和老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家具、贴纸,带着颜色加入这个建筑。“能激发小朋友的东西不只有颜色—空间层次、路径、身体感都是设计师能够用的方式,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有了,颜色就不是一个非要用的元素了。”祝晓峰说道。

迪卡幼儿园设计中心的不少幼儿园设计仍是丰富多彩的。“颜色是有游戏规则的。”王俊宝认为使用颜色的关键是要处理好色彩关系,让色彩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空间才会让人觉得舒适。如果整个幼儿园内的色彩组合混乱,加上装饰过多,儿童的注意力就会明显分散,“你会发现小孩子整天毛毛躁躁的,不冷静。”王俊宝说。
不管怎样,受访的建筑师都深信,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空间教育,它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幼儿园的建筑是比教育更有效的一种引导方式。”日比野拓写道。
那些可以调动儿童好奇心的建造细节—比如光影变化、不合常规的窗户设计和装饰设计等等,需要身临其境和每天的日常使用才能感受到。
“小孩子会对这个空间有很大的敏锐度。他可以通过光线的变化,而不是景象的变化,察觉到时间。”朱竞翔说。在他所设计的童趣园里,一高一低的屋顶可以将南向的天然光反射进屋内,加上屋子4面的门、窗,可以达到5面透光的效果,这就使得不同时段里,光线能从不同的方向照进屋内。
“为什么你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一模一样,没有想象力?”王俊宝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幼儿园建筑的设计。他在设计棒棒糖理想幼儿园时,设计了一些有高有低、形状不规则的窗户。“你可以用这些不同的设计,告诉小孩窗户不是只有1.5米×1.5米这一种形态;其次窗户除了在墙上,还可以在顶上。”他说。而在另一个纸飞机幼儿园项目上,他在建筑表面塑造了一些行走的动物雕塑,“哪天孩子长大,他可能就设计了一种鞋,穿梭于大楼上。”他说道,“飞机不也是这么诞生的嘛。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想象力。”
“这种影响很难外显,但它们带来的感觉确实不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幼儿园园长汤英杰也注意到了这种光影变化对小孩的启发性。在天气好时,阳光穿过建筑的月洞、栅栏,在走廊上和小孩的身上留下投影。她计划根据建筑内的光影变化设置课程,引导小孩去观察,而这是一般的封闭式建筑很难带来的启发。
目前汤英杰计划把幼儿园里蜿蜒的六边形走廊设置成小孩的自行车车道,设置一些交通规则,“它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但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也提倡孩子需要具备冒险精神。我们就遵从建筑原有的这些元素,给予一些变化,探究一些新的玩法。”她还希望基于建筑的蜂巢形状、光影变化开发一系列探索课。
而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很可能来自家长。祝晓峰在设计过程中曾遇过设计意见的分歧,家长认为六边形走廊应该加上玻璃、包裹在室内,成为室内走道,因为“这样小孩冬天在走廊上跑不容易感 冒”。
“确实可能有的人会因为这个感冒,但开放能够让人离开教室,去另外一个地方,感受气温的变化,我们觉得那也是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和日本幼儿园对比来看,中国家长总体来说是过度保护的。”祝晓峰说。后来,园方也支持试用室外走廊设计,并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许多日本幼儿园常被作为学习的范本,但王俊宝认为日本幼儿园的开放性目前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当下阶段的教育现状—绝大部分家长和幼儿园管理者都还很难接受一个像富士幼儿园一样完全开放、鼓励冒险的幼儿园设计。而在中国,大部分精致设计也更多地集中于私立幼儿园,由投资者或商业地产商牵头,几乎还未触及到公立教育体系。甚至曾有其他建筑师透露,幼儿园的建筑用地面积大多会在教育局的标准上“打折”,让位于商业住宅开发。
“国内的教育,现在更多的是加工厂的角色,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像是工厂里的流水线。流水线上的不同个性的人只是被管理。这个建筑如果是适合管理的建筑,那就是功能型建筑,有一定的模式,可以复制粘贴。”马岩松如此描述国内幼儿园普遍的设计现状,“但是日本的幼儿园,大多都倚靠着周边环境去创造以孩子的精神为中心的环境,这使得建筑更有特点—更朴实,有家一样的感觉。”
建筑对于教育的影响力也还未被广泛认知。如果把目光转向乡村,在贫穷地区,学前教育几乎是缺席的。而朱竞翔大约占地50平方米的“童趣园”对NGO来说,就是一种改进乡村学前教育的经济解决方案—成本低、易拆装,悬浮的基底使其适应农村各类地质条件。之后,朱竞翔还与NGO商量在童趣园内安装遥感系统,通过检测室内活动来了解建筑的使用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情况也许会变好。王俊宝看到80后、90后的家长对于幼儿园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新一代人的审美、观念的开放也将推动幼儿园设计的更新。日比野设计公司在中国的9个城市接下了幼儿园项目,而北京项目已经接近完工。“我通过跟一些业主沟通后发现,他们对幼儿园的认知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现在日本的幼儿园受到全球关注,可能十年后,中国幼儿园会变成全球最好的。”日比野拓在一次采访中说。
但受访建筑师也都承认,拥有一个好建筑仅仅只是开始。他们在空间里留下的启发性设计,还需要教育者的引导,才能对幼儿教育产生更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