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章五篇
小米
雨润无声
北方之苦夏,不比南方的湿热。
四年前我在广州逗留一周多,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南方。期间,天气有阴有晴,却无凉热变化,是持久而又一贯的闷热,除了心急火燎汗如雨下,再无其它。我那时想,南方之热,恰如把人搁在笼屉里蒸,皮肤黏黏糯糯,衣衫吸附于身,仿佛我不是我,已化身为蛇,且还多了一层将蜕未蜕的皮囊,挥之不去,除之不尽,让人心慌意乱,坐立不安。就算正在下雨,就算下了一场透雨,那种被围困或深陷的感觉仍不能消除。南方的热,即使空气也有了粘稠感,凝滞感,呼吸起来也感到艰难。
北方却不同。北方的热,是干热或燥热,只消一场大雨就可驱散尽净,就算还要热起来,哪也是几天后的事,至少眼下不会。在家乡,下一场透雨,好歹也能爽快几天,于身于心,都是一种调节。也是因为如此,在家乡,每逢盛夏,我常常会有盼雨的念头,由盼雨进而时常看看天色,已是夏季一种惯性的心理和行为。
身处南方的人,大约不会这样。
身在南方,即使盼来一场大雨,也是白搭。
这么一想就觉得,还是北方比较好。
在北方,热是暂时的折磨,不是恒久的牢狱。生活在北方,天气再怎么不好,心里总归是有个盼头的,生活在南方,夏天就是遥遥无期的苦役。
进入盛夏有一些日子了。天热了一些日子了。已有十多天未曾下雨了。
北方酷暑,是一步一步,步步相逼。抬頭望去,蓝天似大布,骄阳如飞轮,从很早晒到很晚,太阳才会恋恋不舍,退出天空。即使太阳落下,空中仍无半片云彩,地上只见万物蒙尘。若在上午时分,低头俯身,向地表看去,就可看到若干蒸汽,如一堵砌在地上的透明幕墙,如丝如缕,氤氤氲氲,挥挥洒洒,绵延不绝。水分就这么被阳光日复一日地吸走了,升天而去了。此情此景让人觉得,地表的草木土石也在熊熊燃烧,释放热能,除了没有通红的颜色,已与火焰无异。不热才是怪事。
连续数日,阴云久久酝酿,酷暑日渐式微,及至昨日,雨如银针,次第纷纷,不雷不电,不装腔作势,不疾不徐,不让人担心。唯见云锁山头,雾接仙境,柔雨绵绵,遮天蔽日。就在不经意间,已然消去了经久的酷热,从打开的窗户里,吹来习习凉风,顿生寒意,似乎少穿了该穿的衣服。
我不由得抬头,从窗口望了出去,只见一角雨幕取代了天空,耳中传来雨的合唱,一时突然激烈起来,这都是雨刚刚引发我关注的缘故。雨淅沥沥沥,刷拉拉拉,叮咚砰嗵——那是溪流般的檐水,耐心敲打邻家铝合金雨篷发出来的声音。
正在走神之际,妻子移步而来,走到身边,拿了一件薄衣,也不说话,只将衣服举在面前,要我穿在身上,以御寒气。我连忙摆手拒绝。我宁愿少穿,却也不想此时此刻,再加衣衫:热烘烘的气氛已经烘托得太久太久了,多体验一会儿凉爽带来的快意有什么不好呢?妻子无奈离去之后,我索性扔下写了半截的文章,离开电脑,走出书房,途经客厅,路过厨房,来到阳台檐下,举目远望。片刻之后,顿觉大爽,精神倍增,身心均已舒畅之极。比起苦巴巴地熬文章来,果然舒畅多多,快意多多。
有了雨,万物就有了润泽,人类亦有了福祉。天顺民意,就会热了几天之后,降下一场透雨。今年的天气,就是这样。
生命中要是常有这样的及时雨,又该如何欢心?
仔细想来,却也不是没有,而且不止一次。比如刚刚给我拿过衣服的爱妻。已有多少时日,我不曾体会到她的关心?她的片言只语,平常行为,时时处处,恰似雨润万物,悄然无声。要不是用心揣摩,用爱体会,必定难觉个中滋味。
念及此,心中已无怨忿,反而常常庆幸,常常感恩,家庭世事,每每太平。
我从阳台回来,妻已在厨房独自默默做晚饭。我悄悄走到她身边,不作声,只用一双糙手,将她额上的乱发,轻柔捋顺。
让蛾子飞
夏天,大小蛾子,忽然之间,不时在屋里乱飞。我跟妻子都挺纳闷儿:平时窗户关得好好的,进城当了城里人,不管在家不在家,门总会锁得紧紧的,蛾子怎么飞进来?蛾子不比蚊虫,蚊虫吸人血,令人烦;也不比苍蝇之流:苍蝇跟人争食就不提了,它能吃多少?塞牙缝的也能撑死它!问题是苍蝇偏要在追逐食物之余,追逐腐臭,天知道它是不是品完腐臭又来分享美食的?所以,苍蝇比蚊虫还让人生厌。
某日,妻先若有所思,后又恍然大悟,继而惊呼一声:“是不是面生了蛾子?”妻说的面,当然是面粉。我想一想,觉得有理。我家杂粮多,不仅有小麦面,还有玉米面、荞面、黄豆面、洋芋面,别家没有的,我家也有。这跟我是乡下人不无关系。回一次乡下或乡下亲戚进了城,多半拿些乡下出产的杂粮送我,不收不行,我爱吃这些。这些杂粮搁在家里,因为总是吃不完吃不尽,有一些面,就忘记了,放得久了,面粉也会坏掉。面粉坏掉的主要特征就是生蛾子。
我和妻立即动手,翻箱倒柜,果然很快找出几个装面的塑料袋来,装着面的塑料袋,袋口依旧扎得紧紧的,找到它们时,它们全都变了样子,无一不是遍体鳞伤,孔眼密布。想来,蛾已经过从一颗虫卵进化成面蛆的过程,它们已从面蛆进化成了蛾。在完成生理的蜕变之后,又从透明塑料袋里,再一次破茧而出,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化蛹为蛾。蛾子今天能在我家里飞,已比蝴蝶遭受了更高一层的精神蜕变,求生的强烈欲望让它们未曾活活憋死在透明的塑料袋里面。
妻一一打开塑料面袋,果然,无数蛾子在面粉里挣扎,正在蠢蠢欲动!
那些走出面袋的蛾子,在屋里乱飞,撞向墙壁、撞向玻璃、撞向防盗门。精疲力竭之后,仍然不死心,在墙壁玻璃防盗门上停歇,在桌子沙发电视机上观望。休整过后,蛾子又在屋里乱飞,想要重新振作,继续努力,觅得一条生路,却是仍然飞不出去。它们面临的是更为透明的玻璃、更为坚硬的水泥墙壁、更为牢固的铁制防盗门,在铜墙铁壁和庞然大物面前,翅膀太过轻微、牙齿太过渺小、头骨太过松软,就算折戟沉沙,头破血流,就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也属枉然。endprint
屋外就是如花的春天,似乎只有一墙之隔,可跟它们,仍有天涯之远。
蛾子不比蝴蝶,翩翩起舞,姿态万千,惹人艳羡,招人爱怜。蛾子一身素装,一脸素颜,仿佛乡下农妇,不涂脂抹粉,不妖娆勾魂,它们朴朴素素,普普通通,从不喧宾夺主,只以本色示人。
岳父退休之后,一门心思面壁信佛。这倒也罢了,他却不时就要他的女儿也跟着他,拜在佛门之下。妻是他的长女,常常顺着泰山大人,却因我的阻止,最终未能登堂入室,遁入佛门。但妻为了两头讨好,故意在我不在的时候,投其所好,不时就念一遍《地藏经》之类的。杀生的事,比如拍死一只蜘蛛蚊子之类的,妻本来胆小,起初还会狠下心来,背着岳父做做,后来就连这些也不做了。不仅自己不做,她还不让我做。
我本粗鄙之人,荤素不论,良莠不分,更不如妻那么善良,有一颗菩萨心肠。我讨厌次第起飞的蛾子,搞得屋子里飞虫纵横、此起彼伏。我找出苍蝇拍,拍起拍落之后,蛾子要么骨肉分离,要么横尸于地,几乎每击必中。仔细想想,蛾子为了突围,已是数日心力交瘁,要能躲开我的凶手,倒成了奇迹。
我的灭绝行为并未持续多久就遭到了妻的严厉制止。呵斥完我这个“不懂事”的老小子,妻立即开门开窗,用毛巾驱赶它们。她要它们到自由世界里,尽情去飞,尽兴去活。她还让我东施效颦,学习她的行为。
不知是蛾子发了闷了,或在跟我斗气,无论我们怎么驱赶,蛾子反而不出去了,它们在我们的追逐下,从客厅飞到厨房,又从厨房飞到客厅,似乎看不见窗户,也看不见门。它们跟我们夫妻,居然玩起了游戏!
打死它们,轻而易举。灭一个,就少一只。这是我最初的想法和行为。但我跟蛾斗完了气,颓然坐下,平心静气之后,却又有了新的想法:我是一条命,一只蛾子,不也是一条命吗?它们只是偶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又有什么理由和资格,主宰它们的生死?
我这么想,只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跟佛法无关。
索性不管它们了。休整过后,我与妻,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
门窗仍然洞开。
后来我就忘了跟蛾子之间产生的不快,后来寻找蛾子,亦是遍寻不见。
它们当然飞走了,飞到属于它们的大千世界里去了。不知它们是什么时候飞走的。不知它们是一起飞走的,还是陆陆续续,各自飞走的。我能够明白的是,蛾子已在属于它们的花花世界里,勤奋地活着,自由地飞着。
这也就够了。
落 发
发如岁月,不想落也落,拦不住的。
仔细想想,头发是什么时候开始飘落的?竟然不知。只是心里明白,这样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且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并已持续了一些年头了。
每次洗头,总能看见乌黑的头发,长长短短,如丝如缕,或在脸盆边沿附着,或在水中扭着,沉浮不定。脸盆光滑如镜,寸草不生,刚刚附着又被搅动的洗头水冲走了,于是再附着,再漂走,如此反反复复,周而复始。本该终生依附于脑袋的头发,却要百般努力,挣脱头皮,死心塌地地,前去依附一只盛了水的脸盆。不知脸盆有何好处,让头发如此痴迷,莫非它还能给它滋养不成?
那洗脸盆,因了水的缘故,如不搅动,一时倒也可以依附得妥妥贴贴,难以抠除。等到水干,头发就只能自行脱落、离去,飘入风尘之中,再也难觅踪影。头发这才明白,吸附于脸盆,实则极不明智,恰如自欺欺人,可惜悔之晚矣。所谓生在福中不知福者,头发应是典型代表。试想,植之于头皮,有脑袋给它那么多营养和思想的补给,生活无忧无虑,无需他顾,头发只管蓬勃生长就是,这是何等快意的一生,应该身心愉悦才对,头发却不知好歹,不愿修剪,不服管束,偏要設法脱离生存的母体,去自谋生路。头发哪里想到,脱离母体那时,便是它的死期!
凡是自行脱离的,无一不是青壮年头发。每次洗头,看见它们乌黑透亮,在水中漂漂荡荡,真是挥洒自如,如鱼得水。可惜的是,它已成了无根之物,却不自知,不免为之扼腕。
转念一想,走便走吧,去就去吧,留得了头发的身,留不住头发的心。强扭的瓜不甜,强留的青丝只会变成白发。光头的不一定的老翁,白了头的,多半都是!因为我毕竟对头发的离去,还不死心,我只好接着安慰自己:不是我这贫瘠的脑袋不想留住头发,是头发厌倦了这颗无冠无冕的脑袋,弃之如敝履。
少了一根头发,就少一丝牵挂,少了一缕头发,就少了一大把的牵挂。要是头发全没了,索性梳头、洗头、修剪、发型、甚至仪容,都可免掉。我想,只要大脑不死,思想还在,失去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本来就是逐步放弃的过程,想把什么都抓住,那是不可能的事。头发的飘落,无关痛痒,无关生死,更无关宏旨,又何必在乎?只要心在怀里揣着,爱在心里藏着,那些表面文章,那些装点之物,比如头发、比如美容、比如饰物,所有这些无关生死的东西,索性不要也罢。
我每每为洗头所累、所恼。
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不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至少不能让人对我掩鼻。
头要不洗,还是不成。
于是心想,头发不是不想在我脑袋上呆下去了吗?哪好,就请落得快些再快些,早早落完,早早省事,早早省心。如此,既可成全头发之愿,让它再寻沃土,再创新生,于我也可再无半遮半掩的嫌疑,舒耳明目,以正视听。待到不远的将来,我只需举着锃光瓦亮的脑袋一枚,不躲不藏,似乎盛满智慧,还能装成贤人,不仅洒脱,还可赚来一二分尊重。
如此快意之事,惟愿早日降临。
两棵榕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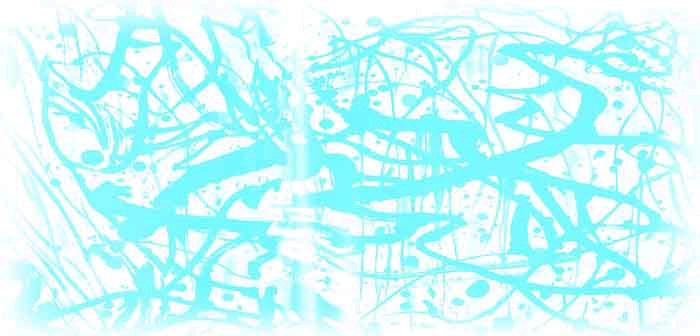
县政府大院,办公楼下,门洞两侧,几年前,栽了两棵榕树,一棵稍早,一棵略迟,一左一右。榕树初来时就有三层楼那么高了,树身粗得也是两人才可合抱。据说每一棵树都花了数十万元,我担心这南方树种,来了北方,季节气候都不适应,还是“中年”移栽,极易水土不服,恐怕难以成活。后来听人说,榕树是极易移栽成活的树种,我也就打消了疑虑,再无杞人之忧。endprint
隔日上班,看见几个工人在树周围搭架子,又隔一日,树已在“打吊针”——据说是给树输入营养液之类的。我当时虽已年近不惑,但因孤陋寡闻,却也是头一回见此光景,不由啧啧称奇。想不到人类享用也就百十来年的“打吊针”,树亦有福,居然也可享用一回,我要是榕树,得此优待,真是死了也值。
夏天了,两棵榕树终于,活过来了。也许晓得自己“睡过头”了,迟到了,于是很快急速成长起来,半月之后,已然次第婆娑,绿树成荫。
接下来的几年,两棵榕树几乎年年“打吊针”。
它们终未死掉,实属万幸。
好像是前年吧,树已不用“打吊针”就可活过来了。
但有一点不同:别的本地树,都是春天萌发,榕树兄弟,却是夏季换叶。它们的叶子替换得也比较独特,老叶子落了不足三五天,新枝新叶就已蓬勃,完全掩盖了苍老的树枝。榕树换季就跟人换了一件衣服一般,非常迅速。榕树不想长久地“裸体示人”,才会这么快吗?
榕树兄弟换衣,也是前后各不同。每一年,总是左边那棵先行换衣服,等左边那棵完全换完了,右边这棵才会接着换。左边这棵是先移栽的,右边那棵是稍后移栽的。莫非榕树弟弟在礼让着榕树哥哥?
我是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我已习惯了树木的春天萌发,夏季成荫,秋天落叶,冬天裸身。这二棵榕树,却是夏天落叶,夏天萌发,其它季节蓬蓬勃勃,绿意葱茏。
榕树乃南方树种,我却是北方土著。我对榕树知之甚少,对其习性,更难说清。
也许是榕树远离家乡,到了遥远的北国,生物钟全都乱了套了?
两棵榕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全然不顾北方气候,风土人情,真是好没道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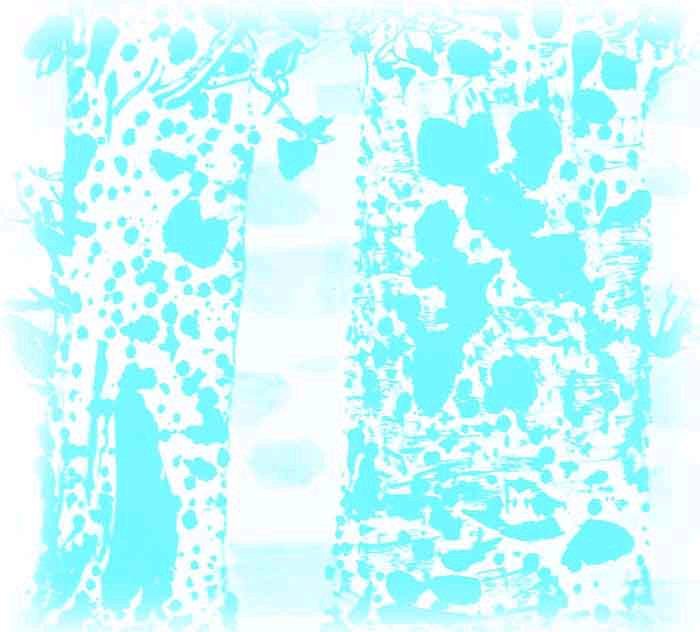
养鸡肥鼠
我不呆不傻,当然不愿养鼠。鼠又不是鸡,可以杀了吃肉,可以养鸡生蛋,再吃鸡蛋。但我进城之后养过多年鸡。鸡也不是我愿意养,喜欢养,才会养。乡下的亲戚要进城来,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带给我,到我家做一回客吧,他们自己先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只好将养在圈里的鸡,逮一只给我。来我家的不是亲戚就是长辈,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进一趟城,实属不易,人家都已大老远地把鸡拿来了,我还能让他再带回乡下去不成?何况,在乡亲们心中,送一只鸡给你,是最高的礼遇。我不能不识抬举。
鸡,我还得留下。
留下鸡是简单的事。客人酒足饭饱,回乡下去了。但鸡没走。鸡就这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大难题。怎么办?也不能人鸡共居一室。鸡要吃要喝,还会拉屎,我明白得很,这万万不行。
拥有第一只鸡时,我刚刚搬入新家,住在四楼。那时县城的楼房,四楼已属顶层。我既然进了城,又要买房,怎么也得买个顶层的房子住住。从前进城都是以乡下人的身份,在城里的大街上走,看城里人住那么高的楼房,仰视仍不能见到全貌,看得我脖子好酸!我那时就想,要是有朝一日,我也成了城里人,非得住最高那一层楼房不可!不为别的,只为脖子舒畅些,不再仰视——不仅不仰视,还可居高临下,俯视城中万物,岂不更好?
我也不是喜欢吃鸡的人,更不会杀鸡。我害怕杀鸡,不想杀鸡,不愿杀鸡。一只活蹦乱跳的鸡,转眼之间,就在一阵惨叫声中,死在我的屠刀毒手之下,想想都觉残忍,亲力亲为,更是难以接受,难以下手。我只有养着鸡。
我选择四楼顶层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买房时没有楼层差价,顶层住户自家头顶那一小块楼顶,可由顶楼住户,自行使用。搬进新居不久,各家各户就纷纷圈地,先把属于自家的那一块“领空”围出来,之后不久,我又在妻的再三催逼下,用水泥、沙子和砖头,在楼顶砌了间简易房子,房子砌好以后,就在里面搁一些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杂物。现在好了,鸡没地方呆,正好可以安排在楼顶,暂住一夜。
鸡成为我的家庭成员的第二天,我又在楼顶简易房斜对面不远,用木板铁钉,给鸡钉了一个棚子、一个食槽,总算把第一只到我家的鸡,安顿了下来。
亲戚们进城或我回乡下,除了送鸡给我,也送一些大米、白面、杂粮,尤其那些杂粮,总是还没吃完,就又送来。人家诚心诚意给我,不是用得着我,而是看得起我,却之实在不恭。我只得陪着笑脸,做感恩状,一一接受。这些粮食,一部分让我们一家三口吃了,一部分发霉变质了,一部分生了虫,不能再吃。我是乡下人出身,小时候种过地,饿过肚子,晓得粮食的艰难与金贵,即使坏了的粮食,我仍不忍扔掉。喂给鸡吃,却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更后来,吃不了的粮食,尽管没有坏,没有生虫子,因为一时半会吃不完,我也拿去喂鸡。
我养的鸡,因为总是不杀,就只增不减,逐渐发展到了六七八只。尽管如此,区区几只鸡,能够“消化”多少粮食呢?何况还有无法处理的剩菜剩饭,尽皆给了鸡吃。后来我喂鸡,鸡已不再是最初的欢欣鼓舞、趋之若鹜,而是对我的喂食行为,视若无睹、不屑一顾。它们当然得吃一些。但它们吃不了的,剩在食槽里的,就越来越多了。
更后来,在食槽或鸡棚里,我常常发现上窜下跳的老鼠。我想,鸡反正吃不了那么多,让鼠辈顺手牵羊,得些便宜,不使食物白白腐朽,也不算我暴殄天物。再后来,鼠辈就在楼顶简易屋子的杂物里,也不请示请示我,就与鸡为邻,自行安顿了下来。我想,鸡鼠之声相闻,也是一种生活气息嘛,虽然让人不快,却也无伤大雅。我于是默许了鼠辈的存在。
需要声明的是,我恨老鼠,更讨厌鼠辈。我赶过老鼠、抓过老鼠,甚至做贼一般,拿鼠药对付过它。无奈赶之不走,抓之不着,药之不尽,何况鼠辈的繁殖力,还又快又强。我终究势单力薄,就算穷尽一人之力,也是难以如愿,难成正果。不默许,不听之任之,我又为之奈何?
初衷为养鸡,结果却是,在养鸡的同时,我也养下了成群的鼠。后来想想,人生在世,養鸡肥鼠,也是常有之事,就不那么生气了。鸡未养好,鼠却肥硕。好歹鸡还活着,不养不成,肥了鼠辈,当作“意外收获”,看在鸡的面子上,也只能不跟鼠辈一争高下,一般见识。
可憎的是,到了后来,鼠辈居然在我家楼顶,大腹便便,从容信步,随地拉撒,一片狼藉。养鸡属于自觉自愿,一日三餐,添食续水也就罢了,让人难以容忍的是,我还得替鼠辈擦屁股扫厕所,着实让人忿忿不平。更可恶的是,尔等鼠辈,丝毫不将我这衣食父母,搁在心头,放在眼里,仿佛我天生就该养育它,就该伺候它!这些死皮赖脸的无耻之徒,不是白眼狼还能是什么!
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为此生气,就算气得我肚子大,鼠辈仍然不在乎我,更不计较我的态度,不生我的气,不仅不生气,它们还在我家楼顶养育子女,安居乐业,活得滋润着呢!反倒是我,为了鼠辈的衣食,还得忙忙乎乎,何苦来哉!
求爷爷告奶奶,我终于陆陆续续,把鸡送了出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养鸡还不成吗?请神容易送神难。鸡已多年不养了,鼠患却是至今未消除。楼顶本可种菜养花,添些绿色,补些氧气,陶冶性情,愉悦身心。我一直如此。更主要的是,我不施农药,不上化肥,既锻炼了身体,又有了绿色食品的补给,是一举多得的事。 endprint
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