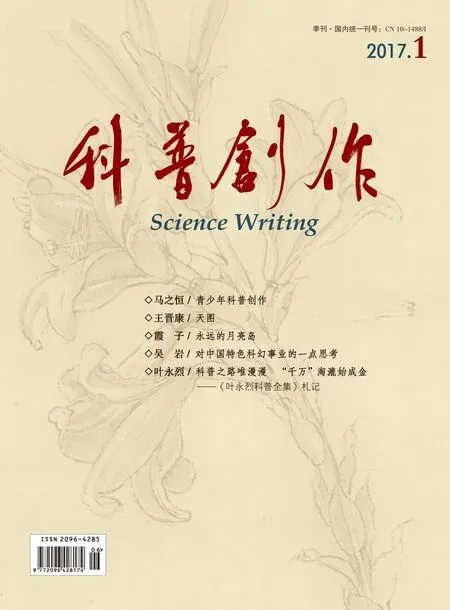鲁迅的博物学情怀
金 涛
题记
按《辞海》解释:博物,旧时总称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这句引自《汉书》的典故,虽不能说明博物学的科学内涵,但至少提示我们,在自然科学各学科分工还不太精细的时期,博物学是一个研究大自然的范畴较广的学科。20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为了认识自然界,揭开大千世界的秘密,博物学很是风行,不仅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经典之作。那个时期的博物学,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保持原始状态的自然界,它调动了人们亲近大自然的美好情怀,至今仍是令人神往。
今天,博物学又在中国以及别的国家、地区悄然兴起,令人欣喜。因此,回顾鲁迅先生的博物学情怀,多少也折射出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每一次的探索都低声诉说着他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一提起鲁迅的大名,相信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想到那位精瘦的寸髮怒竖、目光如炬、个头不高、身穿一袭棉袍的大先生,在荒野彷徨、向沉沉黑夜呐喊的孤独身影。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他,多少年来,中国的好几代人是读他的文章长大的,也无形地受到他的思想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影响。鲁迅是杰出的作家、思想的前驱者,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不过,这只是多数人对鲁迅的印象,至少我认为这不能代表鲁迅的全部。
如果我说,鲁迅深入到地下矿井,观察岩层结构,曾经描绘出中国最早的矿产分布图;他密切关注科学探险,心系北极遥远的冰雪世界和北极熊,又对在中国西部沙漠戈壁跋涉的驼队和不畏劳苦的科学家充满敬意,期望他们把探险经历和重大发现告知国人;他十分喜欢奇异的植物,常和年轻朋友一起,背着标本夹,翻山越岭,采集植物的枝叶、花和果实,然后制作植物标本……
这些,你会相信是鲁迅吗?不错,这也是鲁迅。他是一个博物学家,视野开阔,兴趣广泛,对自然科学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
一、鲁迅与《地质学原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谈到自己的人生转折:1898年春“到N进K学堂”(即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9年,又改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了整整四年,一直到1902年4月赴日留学。他在这里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课程,接触了达尔文进化论,加上第三年在江苏句容县青龙山煤矿的地质考察,从理论到实践,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
从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私塾转入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式学堂,对于清末许多年轻学子而言,无疑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鲁迅同样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不仅“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而且开始用思考的眼光,观察神奇的自然界,开始了他的博物学探索。
矿路学堂所用的教材,一本是讲矿物学的,名为《金石识别》,作者是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代那,中译本出版于1871年。另外一本是讲地质学的,名为《地学浅说》,译自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共38卷。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在地质学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关于地球的形成,一种观点是灾变论,即地球形成过程中遭受了许多巨大的灾难性事件,这种观点往往导入《圣经》里的大洪水,使严肃的科学探索与宗教掺杂在一起。另一种是渐进论,认为地球的变迁是一贯的、缓慢的,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作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质学教授的莱伊尔,是渐进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地质学原理》于1830—1833年分3卷出版,在他生前出了12版,直到20世纪,书中的许多观点仍然受到地质学界的重视。达尔文当年乘“猎犬号”环球航行携带的不多的书中,一本即是《地质学原理》。
达尔文曾经精辟地指出,《地质学原理》“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整个思想状况”。
鲁迅系统地学习了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由于课本《地学浅说》的刻本不易得到,鲁迅精细地照样抄写了一部,印象更加深刻。他还采集了不少矿石标本,放在木匣子里观察。
另一本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的书,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该书取自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前二章,并在按语和序中加上自己的见解,于1895年译成,1898年正式出版。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自称是达尔文进化学说最忠实的“斗犬”,他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宣扬了达尔文关于地球生物演化过程的新思路,而严复在《天演论》中提炼出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掀起层层波澜。
正是由于受到莱伊尔和达尔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影响,鲁迅的博物学情怀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对大自然的好奇,也不仅仅是对某些科学知识的兴趣,而是蕴涵着对自然界不断发展变化的深层思考:地球永远处在演化中,地层在变,岩石在变,动物植物也同样在变,那岩层中的生物化石即是死去的古老生命。生物变化的原因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以此类推,人类社会不也要变吗?哪个王朝不也是由兴而衰,最终走向灭亡?没有铁打的江山,世上没有活一万岁的皇帝!
这些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新思想,由朦胧变得清晰,进而支配了鲁迅的一生。
二、鲁迅与科学探险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成为清朝的一名公费留学生。他在东京弘文书院学日语,同时阅读各种报刊,像海绵一样汲取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最新信息。
这期间,有两个重大的科学事件引起他的关注。一个是北极探险取得的新进展,1893年6月24日挪威探险家南森与同伴向北极点挺进,花了近2年时间,于1895年4月7日到达北纬86度14分,离北极点仅235千米,这是当时人类距北极点最近的距离。另外一个重大科学发现,是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发射性极强的新元素镭。1903年,居里夫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耳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些重大的科学事件使鲁迅激动不已。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报刊,详细地了解有关科学知识,奋笔疾书,短时间内完成了一篇作品,题为《说鈤》(镭的旧译名),发表在1903年10月东京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全面介绍镭的发现和放射科学的论文,距居里夫妇发现镭仅五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仅半年。另外,1903年可说是鲁迅创作的“爆发期”。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8期),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东京进化书社),以及同一作家的另一部科学小说《地底旅行》第一、二回刊登在《浙江潮》10期,全书由南京启新书局于1906年3月出版。
1904年,鲁迅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说明他对北极探险的关注。1934年5月15日,晚年的鲁迅致信杨霁云,还念念不忘年轻时的这部译作,也许他又回想起当年对北极探险的痴迷和向往:“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拿去出版过。”根据信的语气,“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北极探险记》应是一部科学小说。不过,这本译著至今下落不明。因原稿遗失,原作及该书内容至今仍是一个有待发掘的课题。
不过,热爱大自然、对科学探险怀有浓厚兴趣的鲁迅,即便后期困守在孤岛般的上海,仍然以好奇的眼光尽可能地获取最新的信息。他在1929年6月10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夜同贤桢、三弟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北极探险记》影片。”又在1936年4月15日致颜黎民信中写道,“附记: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借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这也恰恰是一个博物学家的情怀吧。
鲁迅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科学考察的密切关注彰显了他的远大目光。
1927—1935年,由中国科学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全称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我国西北地区开展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这是20世纪20、30年代我国最重要的科考活动,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是第一次以我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当时双方签订的19条协议,一改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科学家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任意发掘、考察,并将大量文物和动植物标本掠至国外的屈辱历史,成为这之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的典范,意义重大。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共计38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取得了不寻常的成绩,填补了许多学科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虽然无缘参与考察活动,但是鲁迅的两位朋友却是这次科学考察的关键人物。
一位是刘半农(1891—1934年),又名刘复,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他是当时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推举的常务理事,西北科学考察团名义上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的,双方签订的19条协议,倾注了刘半农的心血。
另一位就是负有全面责任的中方团长徐炳昶。徐炳昶(1888—1976年),字旭生,著名史学家,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7年,徐炳昶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他知识渊博、为人正直,赢得全团中外队员的钦佩。徐炳昶与鲁迅早就相识。鲁迅的《华盖集》收有《通讯》一文,即是鲁迅与徐炳昶往来的四封信,鲁迅致徐炳昶的信是1925年3月12日、29日,徐炳昶致鲁迅信则是同年同月的16日和31日。1927年,徐炳昶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与赫定率团出征,以及此前中国学术界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这些频频见诸报端的消息,鲁迅肯定十分关注。
从《徐旭生西游日记》的序言可知,考察团从西北回来后,《东方杂志》编辑立即找到徐炳昶,转达了鲁迅先生的约稿要求。徐炳昶在序言中写道:“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序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于这次中外合作科学考察的高度重视。
他热切地希望徐炳昶“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把考察中的见闻、科考的发现、取得的成果迅速地告诉国人,这无疑是一次最生动、有影响的科学传播。
《徐旭生西游日记》(1930年出版,全三册)的序言,虽然总结了这次科考的许多情况,但是仅见于书中,其影响力恐怕远比鲁迅期待的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面要小得多。
三、鲁迅与植物学
鲁迅一生对博物学的热爱,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花花草草的钟爱,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许多博物学者的共同爱好。《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散文中,鲁迅对童年的乐园充满诗意的回忆;他还痴迷《花镜》《广群芳谱》《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等图书;他带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到西湖附近的山丘湖畔采集标本,和三弟周建人一起到绍兴的会稽山采集标本……所有这些,生动地勾画出一个热爱大自然、对植物世界充满好奇的鲁迅的身影。如今,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室还保存着鲁迅亲手制作的植物标本;旧居的四合院内,鲁迅亲手种植的丁香依然郁郁葱葱,这些无不是鲁迅博物学情怀的体现。
1926年7—8月,鲁迅在齐寿山协助下,翻译了荷兰作家望·蔼覃(1860—1932年)的长篇童话《小约翰》,为此写了《〈小约翰〉引言》和《动植物译名小记》。这两篇文章不仅讲述了翻译《小约翰》的由来,更重要的是,鉴于中国古代文献动植物名称与实物对照的模糊,尤其是植物、动物的中外译名如何统一、规范,提出了很殷切的希望。鲁迅列举了翻译《小约翰》时遇到的树木、昆虫、花草、禽鸟等外文名称以及考证准确的中文译名的经过:“我想,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则别的且不说,单是译书就便当得远了。”
1930年10月,鲁迅译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文章连载于《自然界》同年10月、11月第5卷第9、10期和次年1月、2月的第6卷第1、2期。以后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书名为《药用植物及其他》,该书出版9个月后(至1937年3月)已印了三版。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鲁迅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自然保护这一概念的先行者,并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自1912年起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鲁迅曾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载于1913年2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文中特别强调自然保护(名曰“保存事业”):“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对中国而言,这是很超前的自然保护的构想,并且将自然保护纳入美育教育的范畴。与此同时,该意见书还强调文物保护:凡著名的建筑,如伽蓝宫殿“所当保存,无令毁坏”“其他若史上著名之地,或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等,亦当令地方议定,施以爱护,或加修饰,为国人观瞻游步之所。”此外,还提到碑碣、壁画及造像的保护,指出:“近时假破除迷信为名,任意毁坏,当考核作手,指定保存。”这些已具备自然保护与文物保护法的雏形。
据鲁迅1912年6月14日的日记:“与梅光羲、胡玉缙赴天坛及先农坛,考察其地能否改建公园。”可见鲁迅曾参与将旧日帝王坛庙变为人民共享的公园之事。先农坛于1915年被辟为先农公园,1918年改为城南公园。社稷坛于1914年被辟为中央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天坛则在1918年被辟为公园。北京近代公园的出现,成为现代城市一道美丽的景观,是与鲁迅等前辈的努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