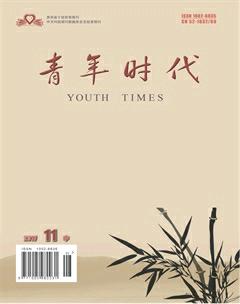卡约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
严浩
摘 要:卡约文化因在青海湟源县李家乡卡约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可证实卡约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以卡约文化青铜器为视角来探讨卡约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并兼论卡约文化在区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纽带作用。
关键词:卡约文化;青铜器;文化交流
卡约文化,是青海高原颇具地域特点的一支青铜文化,集中分布于湟水流域和黄河上游段,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发现遗存多达1877处,经过发掘墓葬达两千余座,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延续时间较长。青海地处中原文化圈、北方草原文化圈、欧亚草原文化圈的交汇区,卡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尤其出土青铜器从器形、纹饰等方面均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深刻体现了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也凸显了卡约文化在邻近考古学文化中所起的纽带作用。
一、卡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卡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间断的受到周边不同考古学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吸收并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根据目前的实物资料,可以肯定卡约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在西宁鲍家寨发现的铜鬲,是目前卡约文化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青铜容器[1],侈口、束颈,鼓腹分档,圆锥形实足,半环形立耳,分档处饰双线“人”字形纹。与商代二里岗上层郑州白家庄的同类器的纹饰、形制很是接近[2],在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M185出土了一件铜簪,这个簪顶端有镂的铃,相同的铜簪出土于殷墟妇好墓[3]。这是中原文化势力扩张到河湟地区的有力证明。
青銅戈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延续的时间较长,历经商、西周、春秋,至战国晚期渐趋衰落。上孙家寨的铜戈为直内戈[4],戈身呈三角形,无胡,援有脊,无阑,有两穿。内呈长方形,且有一穿孔。这种戈最早见于安阳殷墟三家庄一号墓,与河南殷商[5]、陕西城固[6]、洋县[7]发现的商代同类器物非常接近。
青铜矛始见于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兵器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商、西周出土青铜矛的地点约50处,总计逾千件[8]。卡约文化青铜矛出现于中晚期,大通黄家寨墓地[9]、湟源大华中庄[10]和花鼻梁墓地[11]发现的铜矛叶呈柳叶形,中间起脊,骹短于叶,骹口为圆形,矛身两侧多无穿孔。这些刃部为柳叶形有銎的矛,以銎下方无钮为特征,这种形制与西周时期铜矛类似,大华中庄M195出土的一件青铜矛,一侧有钮,在中原出土的商代柳叶形矛,基本上两侧都有钮[12],这对于探讨矛的来源相当重要。
青铜斧作为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物之一,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卡约文化M1025出土1件青铜斧[13]。銎背有一尖状凸起,高0.5厘米,銎两端有凸棱环绕,斧身有三条直凸棱,棱中部偏上有一圆孔,身两侧合范线明显,刃部较平直。通长9.2、銎长5.4、身高6.1、刃宽3.1、厚0.4厘米。这件青铜斧与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出土的青铜斧[14]在形制极为相似。
青铜钺也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直内青铜钺最早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15]。青铜钺作为仪仗及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 1980年循化县阿哈特拉山M12中出土一件七孔铜钺,扁长28厘米,宽6.3厘米,厚0.4厘米,直内,钺体上一排七个直径约1厘米的的圆孔,上部均匀的布有四个长方形的扁孔穿。钺刃部弧形狭长,两端上卷,系范制,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应非实用器,可能是用做仪仗[16]。钺在商代主要用于军事活动,弓矢与钺并赐方能征讨,弓矢用于作战,钺用于治军。体现在墓葬中,这与青铜钺的随葬情况恰可相合。即各等级贵族墓,皆有随葬铜钺的情况,军权与军功是决定随葬铜钺数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而非贵族等级。而在周代,铜钺主要用于行刑或诛杀的场合。施刑者和受刑者非王即诸侯,双方等级一致。虽然钺在各时期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做礼器使用,是权利的象征。对于卡约文化所出土的青铜钺,在造型上有学者认为其造型风格对关中地区的青铜钺造型构成了影响[17]。
除此之外,在卡约文化潘家梁M117出土一件青铜钺,刃部呈半圆形,有7个圆孔,饰隆起线,銎剖面为椭圆形,有三个方形镂孔,镂孔的上下饰粟粒纹。青铜钺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在受到境外管銎斧的影响后,在北方地区流行两者结合的管銎钺[18]。显而易见卡约文化出土的这件管銎钺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样,我们也在中原地区发现了管銎钺的存在[19]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原文化与卡约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往来。
二、卡约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
卡约文化属于西北青铜文化圈,所以在其遗存中出土的权杖、戈、刀等青铜器,与欧亚草原地区所出同类器有着密切的联系。卡约文化青铜器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其文化因素的影响。
李水城最早关注到了中国西北地区权杖头的意义,并进行了讨论[20]。据李水城的研究,北非的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法老们已经普遍使用手握权杖,宣誓自己绝对的宗教权威和对自己王朝的控制力量。近东的两河流域是世界重要的文明起源中心,早期的国王更是以权杖体现王权的威严。权杖无疑是西亚早期文明的特质,是神权和世俗权力的标示物。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由近东开始向四周传播,北向中亚草原传播,在向东向中国的甘青地区传播。
卡约文化中所出的权杖主要见于大华中庄墓地[21]和黄家寨墓地[22],另有一 件征集品,为巴燕峡[23]征集品。共四件杖首,其中四件杖首都为鸠首装饰,在大华中庄M87出土的一件较为特殊,銎为圆筒形,上为鸠首,圆眼,眼下一周联珠,长嘴,嘴端承托一狗,鸠首承托一母牛,牛下一小牛。卡约文化出土的这四件权杖首与欧亚地区出土的传统权杖首存在造型装饰上的区别,然而在器物的功能使用上笔者认为是作为礼器使用,青铜文化因素的传播是一个与当地文化不断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变化、创新而成为当地考古学文化重要组合因素的过程[24]。因此对于卡约文化中权杖首的装饰就不言而喻了,应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果。endprint
卡约文化青铜矛主要出土于湟水流域的大华中庄墓地[25]、黄家寨墓地[26]、花鼻梁墓地[27],这些遗址都属卡约文化晚期。在大华中庄墓地中出土了两种矛,一种是三棱型,细长矛身,另一种是柳叶型,中脊。这两种矛都有銎。花鼻梁墓地出土的矛和大华中庄墓地出土的后者类似,刃部为柳叶型,中脊,有銎。黄家寨墓地的矛只有刃部,刀部中脊,推测为柳叶型。这些刃部为柳叶型的矛,以銎下方无钮为特征。与此相类似的矛在欧亚北部的塞麻—特尔比诺文化中也有发现。相关学者认为大华中庄M14的矛可能是从塞麻—特尔比诺的矛发展而来的[28]。
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早期青铜文化以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西部为中心开始向四周传播。这支青铜文化至少在商代首先进入吐鲁番盆地,近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早期青铜器,如柄部呈凹槽状的环首刀、管銎斧等[29]。环首刀是刀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有学者将分其为三类,分别为环首翘尖刀、三凸状环首刀以及环首刀[30]。卡约文化中所出的环首刀主要发现于潘家梁墓地[31]。和大华中庄墓地[32]。其中在潘家梁墓地M221出土的一件环首刀较有特点,在该件环首刀的刀柄部饰有方格纹。大约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天山北路墓地都出土有环首刀,成为早期青铜文化中常见的器物。早期环首刀主要分布于与欧亚草原交界的中国北方最北地区,中原地区环首刀最早见于二里头三区,2号墓属二里头第三期,年代约公元前1610—前1555[33]。湟水流域潘家梁二期M221出土了一件柄部带有方格纹的环首刀,是卡约文化目前出土最早的一件环首刀[35]。进入卡约文化时期,从早期的湟中潘家梁到晚期的湟源大华中庄墓地都发现有环首刀,虽然出土器物不多,但一直贯穿于整个发展阶段。中原地区环首刀的年代基本上要晚于西北地区,该环首刀可能与西北青铜文化圈的影响关系最大。
互助高寨东村遗址[36]、大通良教[37]、同仁扎毛宗安寺[38]、潘家梁墓地[39]、发现有管銎式戈、凿、斧、钺。管銎式青铜器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代表器物。由于地域間的文化往来,四坝文化、天山北路墓地中均有管銎式青铜器的出土,管銎式青铜器是晚商到西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另一种重要器类,并形成若干地域风格。然而管銎式青铜器并未在西北地区有长足的发展,反而随着该文化不断向东扩散,被北方系青铜文化吸收并得到迅速发展,形成典型的地方风格。考古材料表明,四坝文化与卡约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所以管銎式青铜器很有可能是经由四坝文化传入卡约文化。也可能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直接传入北方长城一带,形成北方系管銎式青铜器后,经晋北、陕北渐次到达卡约文化。近年来,在山西石楼[40]、永和[41]、隰县[42],陕西延长[43]、淳化[44]出土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说明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三、卡约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
卡约文化青铜器与北方系青铜器的交集主要表现在管銎式青铜器(前文已做论述,此不赘述)和青铜器纹饰上。动物纹饰及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及我国北方地带常见的一种器物装饰,这里主要讨论卡约文化青铜纹饰与北方系青铜器纹饰的联系。
在卡约文化中,大部分青铜器制作较简单,装饰手法单一,但也有部分器物制作精美,如以鸟,鹰,羊、蛇等动物纹饰装饰的青铜器。极具地域色彩。这些动物纹造型生动逼真,写实性强,装饰手法多样,多以圆雕动物头像或动物立像装饰柄首。湟水流域中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饰有动物纹或以动物造型装饰,如鸠首牛犬权杖[45]、鸟形铜铃杖首[46]、三角援管銎戈[47]、奔兽纹亚腰形牌饰[48]、飞禽形牌饰[49]、蛇纹铜镯[50]、双马铜钺[51]等都极具特色。在湟水流域中又以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动物纹青铜器居多,其中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飞禽形牌饰平面形状呈亚腰形,器物顶端有一环形钮,牌饰腰部以下以直线纹为装饰,整体的造型犹如翅膀上翘的鹰。牌饰的一面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三只动物的轮廓,居中出为虎纹,右上角是一头牛,左上角有一个形体较小的似鹿的动物。其他在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青铜器纹饰多以蛇纹为主。
传统观点认为动物纹起源于欧亚草原。帕尔青格教授根据塞伊玛-图比诺现象中发现饰有圆雕动物形象的青铜刀剑,认为早期动物纹源于塞伊玛-图比诺和克拉苏克,其年代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52]。通过对这两支文化的观察比较,并未发现动物纹的文化因素,说明卡约文化的动物纹可能与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关联不大。乌恩通过对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阿尔泰、米奴辛斯克、蒙古等考古材料的对比研究认为,在公元前7世纪,夏家店上层文化内涵较上述地区丰富,兵器、马具、野兽纹艺术并非来源于前斯基泰或早期斯基泰文化,而是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53]。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深入研究,许多的中外学者逐渐支持动物纹多地起源论[54]。
与卡约文化年代大致相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其青铜器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动物纹[55]。分为圆雕、浅浮雕及透雕三种工艺,两者之间共同点显而易见,但它们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卡约文化圆雕动物纹多为全身立像式,见有鸟、羊、马等动物,不见动物头像;浅浮雕动物纹饰于铜铃、手镯及牌饰,不见饰于器物柄部,主要是蛇、羊、虎等;透雕动物纹极不发达,多与圆雕相结合,少见身体扭曲或兽搏图题材的动物纹牌饰[56]。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圆雕动物饰于剑、戈、鬲、罐、牌饰等器物,多为全身立像,还有少量动物头像,浅浮雕动物纹多上于圆雕动物纹,饰于器物柄部或牌饰,多呈行列式,动物有马、虎、鹿、狗、蛇;透雕动物纹,多为牌饰,比较发达,用完整的动物纹形象予以表现,有羊、狼、鸟、兔、蛇等。动物纹在西北地区各支青铜文化中并没有被充分展示,卡约文化的动物纹到中晚期才开始出现,说明非本土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动物纹是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卡约文化的一些动物纹可能是受到了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
四、小结
由于卡约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青铜器方面主要受到了来自欧亚草原青铜器、北方系青铜、中原文化青铜器的影响,因此卡约文化青铜器中反映出了多种文化因素。处于强势的中原青铜礼器系统对卡约文化的青铜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使之发生改变,如中原地区的铜鬲、铜戈、铜矛、铜钺传入该文化区域。来自欧亚草原的属西北青铜文化的青铜器也反向影响了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卡约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青铜器存在较多的共性,说明它们之间较为密切的联系;区别则体现着文化的时代性及地域性发展变化的特点。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中的权杖、管銎斧、环首刀等文化因素经新疆、河西走廊、长城地带直接或间接对卡约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卡约文化虽然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因素,但也秉承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因袭相承了西北地区早期青铜制品的风格,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制品,个别青铜器形制较复杂,代表了当时冶铜业的最高水平。某些青铜器,除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外,还被人们赋予特殊的寓义,用以表达人们内心复杂的思想情感,尤以杖首最具特色。由此也凸显出了卡约文化的纽带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卡约文化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也为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卡约文化所属的区域正是在当时发挥着文化传播的纽带作用,从而使得欧亚草原地区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青铜制作工艺得以通过该路径传入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卡约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为中原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交流架起一座桥梁。卡约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正是由于处于各个文化圈的交界处且又发展着自身文化特色,因此也呈现出多元融合但又独树一帜的文化特点。由于出土资料及笔者学识水平有限,本文尚有诸多不足。不当之处还望前辈们批评指正。endprint
参考文献:
[1]马兰:《青海文物精品图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页,图八: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青海省博物馆:《河湟藏珍历史文物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图10-2。
[5]郭鹏:《殷墟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辑。
[6]唐金裕:《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青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7]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三五、图一一九。
[8]李健民,《西周时期的青铜矛》,《考古》1997年第3期。
[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青海大通县黄家寨墓地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3期。
[10]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第11-34页。
[11]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迹》,《考古》1986年第10期。
[12]杨新平、陈旭:《试论商代青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13]刘宝山:《青海的青通斧和青铜钺》,《文物季刊》,1997年第3期,第60—63,69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第509—517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一件青铜钺》,《考古》2002年第11期,第31-34页。
[16]同[13]。
[17]刘静:《先秦时期的青铜钺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第52-79页。
[18]杨建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边疆考古研究》2005年第7辑,第136-150页。
[19]沈融:《一组外流中国青铜兵器评述》,《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58-60,26页。
[20]李水城:《文明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21]同[10]。
[22]同[9]。
[2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存》,《考古》1986年第10期,第882-886页。
[24]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第51-57页。
[25]同[10]。
[26]同[9]。
[27]同[11]。
[28]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第73-88页。
[2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30]杨建华:《欧亚草原的东部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的孕育过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
[31]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集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32]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33]白云翔:《中国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34]同[29]。
[3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平安、互助县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36]陳荣、刘小强:《大通县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青海文物》1990年第9期。
[37]高东陆:《同仁县扎毛宗安寺出土的几件文物》,《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5年第9期。
[38]同[30]。
[39]马兰:《青海文物精品图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68、62、63、66页。
[40]山西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41]杨绍禹:《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第5期。
[42]隰县小西天文管所:《山西隰县出庞村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91年第7期。
[43]姬乃军:《陕西延长出土一批晚商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44]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45]同[10]。
[46]同[23]。
[47]刘小强、陈荣:《大通县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青海文物》1990年第5期,第83页。
[48]刘宝山:《青海史前的铜泡饰、铜片饰和连珠饰》,《青海文物》1999年第13期,图三:3。
[49]刘宝山:《青海史前的铜泡饰、铜片饰和连珠饰》,《青海文物》1999年第13期。图五:6。
[50]刘宝山:《青海青铜时代的铜管和铜环》,《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图二:8。
[51]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文物》1992年第2期,图版八:1。
[5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中国冶金史论文集》2006年第四期,第24页。
[53]邵会秋:《早期斯基泰文化与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探讨》,《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54]乌恩:《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地位》,《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第1期。
[55]乌恩:《我国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45-61页。
[56]乔虹:《卡约文化金属制品及其文虎意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4-77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