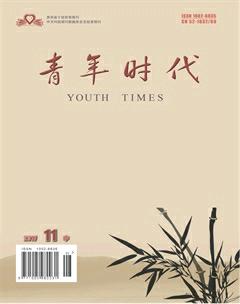王弢国际政治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和张力
王建瑞
摘 要:王弢破除了唯我独尊的传统天下观念,相信世界文明通过融合贯通终会实现天下大同。这种理想主义源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和“三世说”,也与王弢长期接受的基督教育有关。纵观王弢的国际政治思想,不难发现其中的复杂、充满张力,这是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也是他那一代先知先觉者共同的特点。
关键词:王弢;理想主义;思想来源
王弢屬于较早认识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在他的国际政治思想中,始终有一种“世界主义”的信念。其他思想家少有的长期海外经历,使王弢认识到中国和中华文明只是世界众多国家和文明之一,但他仍相信世界文明本质上是相同的,,最终实现天下大同。
一、 王弢国际政治思想中的理想主义
(一)文明多元——中华天下观的解构
古代中国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观,宋代文人石介曾在《中国论》中写道:“居天下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一方面,这种世界观是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结果,认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以“中国”为同心圆依次递减,判断其他民族进步程度的标准就是他们被华夏文明的改造程度;另一方面,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是文化,而不是近代国家的领土、人口、政权等要素,这种国家观念与近代不平等条约中大量损害主权的条款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的华夷观念是永恒的、静止的、绝对的,是一种根据距离远近的、同心圆的文化自大主义。王弢重新定义了“华”、“夷”这组概念。在《华夷辨》中,王弢首先反对根据地理位置即与中华距离的远近来评判其他文明的做法,“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以此为标准,华夷的分别不是绝对的,不再固定地专指某些民族,而要看他们文明程度。“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这体现了王弢正眼看世界后反观近代中国后产生的深深危机感,在《华夷辨》的结尾,王弢反问,“岂可沾沾自大,厚积薄人哉?”[1]
王弢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他破除了华夏文明唯我独尊的天下观,他承认世界上不同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今天下教亦多术矣”,儒家文化只是其中一种,并且发现中西的区别在于中国是“我中国以政统教”和“泰西诸国皆以教统政”[2]。王弢的对世界文化多元性的承认体现了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文明平等的观念。
(二)由器及道——文明融合与天下大同
王弢突破了传统中国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承认了文化平等和多元,在认识世界之后对未来世界作出展望时,贯穿王弢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文明交流整合之后的天下大同。
王弢的出发点是:“天下之道,一而而已”,因此虽然世界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但他们的“道”都是一样的,因此,“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这种观点了体现了王弢对“普世”的初步探索,即认为人的最终追求是一样的,“道”也是一样的。在他建立的文明谱系中,耶稣教与儒家思想类似,而天主教与佛教类似,其他宗教都位于二者之间,这就把东西方的文明打通了。
由于山川阻隔,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不能相互交流,只能在各自范围内自生自灭。而当西方发明出轮船等先进交通工具之后,就为实现融合提供了条件。王弢认为实现“道由异而同”的路径是由器及道,先从器物层面的交往开始,“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与洋务派将“道”和“器”剥离的观点不同,王弢认为“器”可以“载道”,器物层面的交流必将最终引起文化的融合,“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3]文化融合的最终结果将是“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凡有血气者莫不相通”,“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
二、王弢理想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来源:大同理想和“三世说”
“大同”是古代中国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是历代中国士人的信念追求。对这种社会理想最完整的描述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天下为公、人得其所、各尽其力、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王弢将此作为人类奋斗的方向和前进的归宿,一个永恒的、终结历史的、不以地域为限的乌托邦。
“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向前演进。《公羊传》评价“三世”的分别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天下远近而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由此可见,人类最终的归宿是天下归一,普天万物无差别地和谐相处。
大同社会和三世说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世界主义的理想和关怀,其基础是以自我为中心、内外分明的同心圆式的天下观,在这一理想的实现路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中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近代以来,传统的天下观开始解体。王弢较早地接触到了西学并曾赴欧洲游学,他的世界观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看到了世界的多元并有了平等的意识。因此,与大同理想和三世说不同的是,王弢世界主义理想的基础变成了他的“天下一道论”,即“天下之道,一二而矣,夫岂有二哉?”。世界各地虽然在物质、制度的“器”上千差万别,但各种宗教信仰的“道”内在都是相通的,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而已,“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始于器物交流的交流碰撞最终会实现人类文明的统一。
王弢的父亲是当地的私塾先生,他幼年从父亲那里接受传统的经学教育,“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在《论道》一文的最后,他直接引用《中庸》描述自己设想的未来世界,可见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对王弢的影响之大。
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劵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endprint
三、 王弢的思想张力
王弢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幼年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当国门打开、睁眼看世界时见到另一番天地和学问,如同岩洞中的囚徒第一次看到洞外的世界。“新学”令他们好奇、激动,而传统的“旧学”又是那样地挥之不去;王弢相信“天下一道”并期盼世界大同,但他同样强烈地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世界,互相交织、混杂,构成王弢思想中的张力结构。
王弢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又一次文明转型的开端,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一百多年前的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王弢本人用“创局”形容这一时期。王弢属于站在这次“创局”最前端的先知先觉者之一,柯文将王弢与孙中山对比时,“由于王弢这一代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的中国,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孙中山更大。因为王弢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35,率先接触西方的他们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中西融合是这次“创局”的重要内容或路径依赖,中西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都体现这一代思想家的身上,然而,凭借一代人的努力和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人类史上融合两大文明这样宏大的历史工程。他们的工作更多是发问、尝试、启发,思想中充满了张力。
救亡图存和现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国的两大主题,构成了王弢思想中的又一对张力。王弢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这一历史角色要求王弢学习发轫于西方的近代政治、法律、经济思想,进而开启中国的近代化之路。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开启方式是被动的——列强用一次次入侵将中国拖入了近代。因此,生存的压力使得救亡图存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更何况士大夫自古有着担负天下兴亡的使命传统,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前赴后继、奋斗终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庚子国变之后的预备立宪,所有近代化的尝试都带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功利诉求和现实原因,救亡图存成了最急切也最有正当性、最易达成共识的目的。李泽厚用“救亡压倒启蒙”概括这一对张力及其结果,莫如说启蒙只是救亡的工具、为达到救亡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因此,虽然王弢相信天下一道并盼望着世界大同,也还是将其实现之日设在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未来。近代中国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形成了国家观念、主权意识,因此,王弢也是最早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之一,这在他所写的大量政论文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思想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和张力是几乎所有启蒙时代思想家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对于王弢这样一只脚还生活在近代前中国的一代人。他的思想从未有一次实践的机会,终生游离于体制之外,晚年狎妓饮酒、渐至颓唐,最终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寂寞地死去,似乎是完成角色使命后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
参考文献:
[1]王弢.华夷辨[M],李天纲编.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131.
[2]王弢.原道[M],李天纲编.弢园文新编,2012:1.
[3]王弢.六合将混为一[M],李天纲编.弢园文新编2012:8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