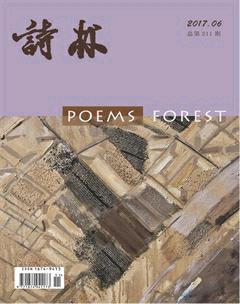《BUG中质数的甜度》阅读说明书(节选)
梦亦非
诗 行
人类既有的诗,都是一行一行的,组成一个文本。如果我们不这样建行呢?如果时间与历史不是线性发展,那么,线性诗歌的意义又何在?虽然我们并不会把诗歌视为历史的镜像,虽然诗歌的确总是成为历史的镜像,哪怕自以为是历史的镜像。在本诗中,我用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一行诗,第一部分主行;第二部分复行(主行上面的英文部分);第三部分弹幕(主行下面的话外音)。在主行之中,又使用了不同的字号,小字号可以被忽略,小字号也可以被加进来阅读。并不是每一行皆如此,有些诗行只有两部分,有些诗行有三部分,有些诗行有四个以上的部分。
这样一来,仅仅一行诗就构成了它自身的阻碍,构成多声部的复调,是最小单位的众声喧哗,有时构成对话,有时则不。这些部分的布置亦无规律可言,它们处于漂浮状态。一句诗即是一个语言事故的现场,即是最小型的不妥调、不和谐。
诗 节
我曾经写过漫长时间节的十六行体,因为我喜欢发明一种诗体并推到极致,这种十六行体是“三四三二四”的分节,每首五节,分别为三行、四行、三行、二行、四行。在《空:时间与神》《素养歌》《儿女英雄传》这些长诗文本中,便用的是十六行体。到了《BUG中质数的甜度》,则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文体建构,文体不再结晶,它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每部分有多少行,是不固定的,每几行组成一节也是不固定的,完全是一个随机的过程,需要的效果是语言的碎块在漂浮中互相碰撞,随机暂时性的联接,随时又互相游离而去。
如何阅读
《BUG中质数的甜度》理想的表现状态,应该是一个小程序,形成一个诗行的球体,漂浮的诗行形成一个小宇宙,你用手尖划动、拨动那个诗行之球,诗节随机地浮到你面前,但这太极端了,会让习惯传统诗歌阅读方式的读者受到伤害。
所以,最终的视频版的表现方式,是H5的方式,让诗行获得动态,在一个页面上,先出现主体,再出现复行,再现出弹幕;或者弹幕先出现,再出现复行,最后出现主体;或者一起出现;或者只出现主行而无弹幕……一个页面可能只出现一行诗,也可能出现一节诗,也可能出现一个部分,完全是随机的,诗行的颜色也会有所变化,所以这是文本的表演,是文本的奇观。
如果读者拿在手中的是印刷的纸本,那很不幸,这是此诗最无可奈何的呈现方式,也即是说,你拿到的只是此诗的“脚本”,但脚本也有脚本的阅读方式:
A,先读主行大字,再读连带小字在一起的主行,接着再读英文的复行,最后读弹幕。
B,先读英文的复行,再读主体,最后读弹幕。
C,如果阅读水平有限,只读弹幕,不读主行与复行。
D,如果不认识英文,可以只读主行与弹幕。
E,只读主行。
F,只读主行中的大字。
G,……
一首诗是许多首诗,一首诗即是一个糟糕的宇宙,或者一个无限可能的历史列车事故的现场。
异质语言
我曾在多年的写作中,为每首诗变换不同的语言风格,有《苍凉归途》的新历史主义式的理智,有《空:时间与神》的古奥,有《素颜歌》的清简,有《咏怀诗》的素朴。这些不同的语言风格,仍然是可以理解的传述意义的语言,而到了这本《BUG中质数的甜度》,语言方式发生了断裂、破坏,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变化或延续,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个人语言风格的时期。在这个文本中,语言不再遵循某处风格,它们表现为异质碰撞:快速,破碎,变音,连音,程序,公式。
快速的言说会驱逐意义,带来意味,但也容易因为语速与语境的摩擦力而带来情绪,而情绪是我所要消除的,所以,必须放弃完整的言说而采取破碎的言说;需要一些变音,变音读起来像错别字;需要一些连音,连音破坏了语言的流畅度,让语音挤压在一起。更多从声音的角度来考虑句法结构,第一考虑不是语言,而是语音,从所指漂移向能指。
我纳入一些非文学性的语言,使用了计算机程度代码的片断,使用数学公式。这已经超出传统诗歌的领域了,在《BUG中质数的甜度》中,亂码已是正常语态,程序与公式让语言变得更极端,迫使诗从文学内部打开通往科学世界的一丝裂缝,哪怕只是无用的微小的裂缝。我的观念是:文学迟早会变成一个程序,变成程序的脚本。
负抒情
负抒情不是传统抒情,不是冷抒情,甚至不是反抒情。传统型的抒情构成伟大的抒情诗传统,也构成伟大的史诗传统,但那是农业时代的辉煌,不属于拟像社会。冷抒情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范畴,而反抒情属于后现代文学范畴,当然,它们互相之间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叠。这些抒情方式都假设或实有一个抒情的客体对象,抒情发自一个言说的主体,只是抒情的态度与目的有所区别,但都属于“抒情的意识形态”。负抒情则不是这样,它并非源自某个主体,也不针对某个特定客体,它是语言自身在情绪、情感上的耗散,它不但不能增加抒情的增长,反而耗掉了情绪与情感,以及潜在的情绪与情感。但一个负抒情的文本并非冰冷的文本,相反,它是力量四射花团锦簇的奇观文本。这些都只是暂时的镜像,是残碎的语言泡沫,没有温度,没有触感,因为文学特有的温度与情绪已被抽空。
脚 本
如果把诗视之为脚本呢?视之为影像的脚本,以及视之为计算机程序的脚本呢?是不是对诗的侮辱?为什么诗就不能侮辱?诗必须得一定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诗就那么脆弱,对它的异化就是对它的侮辱?
《BUG中质数的甜度》事实上模仿并部分地实现了成为影像、程度的脚本,TXT文本只是它静态的脚本,它的性质应该是EXE程序,并且是程序运行的视觉、声音效果。如果我学过编程,如果我是程序员,可能我会用JAVA语言或PYTHON语言来写作这首诗,遗憾的是我仍然只是个文字冒险家,所以,它只好残存在普通语言的世界中。
也许未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应该作为脚本以及可执行程序而出现,它们是互动的过程,是用传统印刷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的文本。诗人是一个文字工作者,诗人更应该是一个程序员。也许,当AI很成熟很廉价的时候,诗人们可以不用学习编程,而只是像使用WORD软件一样使用AI软件来程序化写作,只要到这一步,离此诗中所言的魅影社会也就不远了。endprint
言说:混沌与有序
事实上我们无法使用混沌语言進行传统写作,试想将词语放在一个筐里摇晃使它们混乱,它们便只是一堆语言,不能传递出有效的信息。虽然混沌是宇宙的真相,是天地大道的真相,是太初之前,但显然混沌的语言无法成为信息载体。在传统的写作中,语言几乎都是有序的语言,因为语言是工具,是用来传递、交流信息的公用工具;因为语言是家园,人类居住在清晰的、可以理解的家园之中。所以,写作的语言一般都是有序语言。
但换一下观念,如果语言不被用来作为信息的载体,不被用来作为容器,语言只是材料,用来架构、填充一个“文本”,文本变成一个“艺术品”,那么,语言就可以是混沌的,因为它摆脱了传递信息的责任,卸掉了作为家园的义务,它回到符号自身。“奇观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作为“艺术品”而出现,所以它可以做到在一定的程度上使用混沌语言,这些诗节不表意,只呈现构图,不提供太多的所指,只在能指上做漂移游戏。
有序语言间杂混沌语言,构成了《BUG中质数的甜度》。
美:残损
《BUG中质数的甜度》文本美学关键词是:残损。
以残损为美。
人类的文明处于残损状态,人类的肉身亦处于残损状态,联接肉身与文明的大自然,更是残损的状态。魅影本身似乎即是残损本身。残损构成了当下到未来可见时间段之里的基本状态,所以此诗即以残损为美。诗赞颂的是残损,诗表现出的文本现场亦不是完整的、而是残损的。语言被残损化,技巧亦是建立于残损的基础上。一份残损的文本宣扬着残损之美。
审美是一首长诗必须考虑的,它的设定是仅次于价值系统建构的重要工作,甚至没有价值系统的贯注,但有强大闪耀的审美在照亮,一首长诗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长诗最基本的底线了,有了这条底线——独特的审美——长诗就可以成立。
美是人类共同的宗教,而审美是人类共同的朝圣之旅。
有限/无限
《BUG中质数的甜度》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有限与无限。方式是有限的,而材料是无限的;人类是有限的,而魅影是无限的;原本是有限的,而镜像是无限的;病毒是有限的,而传染是无限的。诗歌是无限游戏,公文是有限游戏。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在传统框架内写作的文本却是有限的,它们被传统的信条所限制,它们不越出传统框架,从形式到价值到审美到技法。写作的意义在于做无限游戏,在无限游戏中去探讨、表现、承载有限/无限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更愿意把诗歌视为数学的某种结晶或结晶的模仿。数学是无限游戏,好的诗歌应该是数学的变体。在现代主义之后,伟大的诗歌曾接近于宗教,但在现代主义之后,伟大诗歌更倾向于接近数学。
关键词
关键词亦是此诗中的象征物之一,关键词构成了世界的节点,人们从关键词去“抓住”世界,系统从关键词去“检索”信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让自己成为时间之流的一个关键词,让后人或旁人从它去捕获、理解当时语境或某个领域的发展史。
但关键词是一个幻觉,人类想象了关键词,设置了关键词,让自己成为关键词。关键词本身却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错觉以及言说的便利,在深度学习的AI时代,关键词这种初级的检索便利和重要性在下降;而到了更远一些的时间流程上,关键词可能不再是一个幻象,仅仅是技术史的淡略记忆。
但关键词在此诗中仍然被设为一个权宜的象征,从这些关键词中,如果说可以检索/抓住此诗的关键问题,不如说因此而失去此诗更重要的部分,当然,并没有哪一个部分比哪一个部分更重要或更有意义,所以关键词的象征也仅仅是一个假的象征。
关联时代
我一再重申我的想法: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到关联论。从互联网开始,关联论的时候到来,“我们都知道大势已去,但不知道未来已深入我们之中。”我近十年来所有的写作都是基于这种哲学史的认识,有意识地从关联论的角度进行文本思考、建构。
关联时代是没有人的,人早就在语言化的时代降格为物,到了关联时代,人彻底被抹去,成为暂时被分配交互任务的代码节点,而这些节点并不是非人不可,没有人技术也仍然发展,没有人的网络世界中,一切照常运行。
关联论的基本要点是:世界是被关联起来的偶发性的变化状态,没有主体,没有实体,一切取决于科技这个没有主体的幽灵。关联时代的“真实文本”正是奇观文本,变化而短暂,一次性而又可以无限复制。
现代主义之说与后现代主义之困
有趣,或并不仅仅有趣的是,后现代主义有文本,无理论,只有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但没有后现代方式的理论。可以用后现代方式写作出一份“作品”,但不能用后现代方式写作出一份“理论”。后现代主义破碎、无中心、混沌、解构,它如果构成一份“理论文本”,那只是一份“作品”而不是一份“理论文本”。在后现代的前缀之下,理论一旦写出,迅即成为“作品”。
因为理论是本质性的,它的本质是现代主义的话语方式,理论需要结构、意义、意义归集、意义结核,它是现代与前现代所发明、默认、忠诚的“魔咒”。它假设出对象是恒定的,对象有意义,意义可以被抽吸出来。清晰是理论的美学要求,交流是它的使命,它就是交流的工具与方式。因此,理论必须是非后现代主义的,必须是结构主义的。
必须使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阐述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就是理论的反讽,也是理论的胜利。
如果不借助于理论,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则可能失却“价值”,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甚至比现代主义的作品更借重语论的阐述,这就让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有作为“观念艺术”中的一种的嫌疑。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品不再在乎价值、理解、意义这些现代主义的要求,便可以无视理论的威胁,但迄今并没有做到。
所以,《BUG中质数的甜度副本》虽然不是一份现代主义文本,但它的阅读说明书,这份《路径》一文,只能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理论”的指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