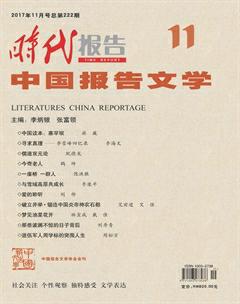百岁母亲沧桑路
崔韶全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得空回家,探望月余未见的母亲,筹划农历七月初八在家给母亲过一百周岁生日。
回到家,我径直来到床前,慢慢扶起她老人家,捋捋白里泛黑凌乱卷曲的头发,轻轻搓搓久睡麻木的脊背……
母亲长舒了一口气,挪挪身子,迎着光线,缓缓睁开沉重的、满是翳疾的眼睛问到:“你是谁?”
我贴近母亲的耳朵大声说:“我是全子(我的乳名)。”
“你说的我听不见!”
“我是全子……”尽管声高力竭,母亲依然说:“你说的,我听不见……”
“给我喝口酒!”
我立刻从床头柜上拿来母亲专用的不锈钢扁酒壶。
母亲慢慢拧开壶盖,不多不少喝了三口,这是她每次的定量。
母亲心满意足地又躺下了。身躯佝偻卷曲,骨瘦如柴。就是这个身高1.5米左右,裹着小脚,目不识丁,姓名鲜有人知的农村女人,历经百年沧桑,耗尽全身精力,滋养了全家上下六代,哺育了一百三十多口人。
我默默地站在母亲的身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百感交集,浮想联翩,思绪伴随着母亲的百年人生徐徐展开。
一生艰辛
母亲名叫王改区,农历1917年7月8日出生在神木县花石崖乡前申沟村。外爷外婆共生养了14个孩子,仅存活了5个,母亲是老大。母亲四五岁时开始缠足,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女孩子要过的人生难关。为母亲缠足的操刀者是外婆和大外婆(母亲的大娘)。一开始就把母亲的脚拇趾以外的四趾用力地屈于足底,然后用白棉布使劲裹紧,假以时日等脚型固定后,再穿上特制尖头“小鞋”,白天在外婆及家人的“监视”下,母亲拄着小拐棍慢慢行走,以活动血液;夜里大外婆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如此两三年。到了六七岁时,又把母亲的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其脚变形、变小。愚昧落后的年代把母爱扭曲成了摧残。俗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一回足,鬼门关上走一遭。母亲缠脚历经两三年,期间流血、化脓、生蛆无数次,不知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繁重的劳动加上生子、失子的反复折磨,外婆身体虚弱眼睛不好,身为大女儿的母亲就成了外婆最得力的家务活帮手。四五岁开始缠足,也就是四五岁开始照看弟弟妹妹。七八岁开始学做针线活,十岁左右就担负起了全家针线活的重任,织布匹、缝衣服、做鞋子。到十二三岁,母亲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上山砍柴挖野菜,下沟担水洗衣服,喂猪喂羊洗锅做饭,农活家务活样样精通,从早到晚手不停脚不闲。
1933年,16岁的母亲嫁到20里外的崔家沟村,与父亲成婚。母亲首先面对的是如何伺候好养父母。父亲20岁时过继到邻村崔家沟村当了养子。父亲养父母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在七天之内相继去世。遭此沉重打击,爷爷奶奶两个人双双害上了抽风昏厥病,每有不和或争执便发作,胡言乱语、口吐白沫、抽搐不止。每次遇爷爷奶奶犯病,还是小孩子的父亲母亲也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久而久之,母亲居然无师自通总结出一套施救的办法:宽衣解带、低脚高姿,针刺人中、手掐内关;苏醒后,喂汤喂水、好言相劝;不管有无过错,赔礼道歉、乞求原谅。母亲的这套方法是否科学且不论证,但是用在爷爷奶奶身上却是非常有效。
爷爷由于人生坎坷,情绪多变,脾气暴戾,加之传统的轻视女子的观念,对儿媳要求极其严苛,有时不近人情到近乎虐待,但母亲向来逆来顺受,不改孝顺衷肠。有一次耕地,爷爷扶犁,母亲拉牛。因拉犁牛未经耕地调驯,不听使唤,挣脱缰绳,狂奔而去。母亲随后直追,可三寸小脚,跌跌撞撞,哪里追得上。后来,经周围干活的人帮助才把牛撵了回来。爷爷歇斯底里,当着众人的面对母亲破口大骂,指责她没有把牛拉好。母亲忍受着摔跤的伤痛,忍受着无理的谩骂,脸上挂满泪珠,仍默默地牵着牛在犁沟里踉踉跄跄前行,一回又一回。
俗话说,养子难当。父母婚后,决心比一般的亲生子媳更加孝顺,长年给爷爷奶奶开小灶,每顿饭都是做两样,家里有点儿好吃的全留给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爱喝米酒(当地亦称黄酒或浑酒),每年秋收后,母亲就开始碾黍子米做準备。一年做两次,冬至前做一次,从冬至那天开始喝,一直够喝三个月。春分前再做一次,一直喝到夏至。遇到饥荒年或借或买也要做,如此几十年,直至爷爷奶奶去世为止。
母亲从17岁始到39岁的22年间(我出生前),分娩九次、流产两次。细细算来,母亲在这二十来年的日子里不是怀孕就是在哺乳不满周岁的孩子,根本没有休生养息恢复身体的时间。尤其是母亲的第一胎在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遭受国民党匪兵的禁闭拷打流产了,因胎盘迟迟不能自然脱落,实在无法,外婆用土办法剥离,致使大出血,昏睡几天几夜,差点丢了性命。这期间,母亲生养九个,流产两个,没有坐过一个囫囵月子,往往是头天生下孩子,第二三天就要下炕自己料理生活,否则连水都喝不上。母亲的难,外婆外爷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奈,只好指派比母亲小12岁的姨姨陪伴照看。算来,母亲生大哥时,姨姨也就六七岁。姨姨出嫁成家后,伺候月子的就是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了。去年,我的女儿也生了孩子,提前一个礼拜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优美舒适的环境,现代化的医疗设施,大夫护士精心管护,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堂哥堂嫂还有女婿全天候亲情陪护,女儿的孩子还没出生,月薪12000元的月嫂就早已雇好。触景生情,我既为女儿的幸福庆幸,又联想到母亲的恓惶,内心涌动无限的伤感。
生儿难,养育更难。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给母亲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也焕发出无穷的动力,母亲彻底进入到忘我状态。合作化前,家里连分带租,种六七十垧地(近一百五十亩)。母亲是父亲种地的得力帮手,春种时,点籽、抓粪、打土疙瘩;夏忙时,锄地、浇水、施肥;秋收时,收割、背背、打场。样样能干,手不停,身不闲,母亲完全顶得上一个男子汉、壮劳力。
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挑灯夜战。全家十几口人,加上外爷家的日常穿衣,舅舅姨姨结婚用衣全是手工缝制,冬换棉夏换单,光是衣服鞋袜一个人常年做都忙不过来。母亲一年四季的夜里总有针线活,不是织布就是缝衣做鞋。煤油灯下,一夜一夜地熬。哥哥姐姐们几觉醒来,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干活,懵懂幼稚的孩子们还以为母亲从来不瞌睡,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能在白天光鲜亮丽的走在人前,是母亲煤油灯下一夜一夜烟熏火燎熬出来的。endprint
煤油灯下干活,光线差加上烟熏,时间长了眼睛有了病,没时间也没钱治。拖延到有时间也有钱了,病也没法治了,现已双目失明。
生活的苦、劳作的累、不眠的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加上坐月子干活,过早地摧残了母亲的身体,一遇节气变化,浑身疼痛难忍。体质差,抵抗力减弱,肝胆湿热邪气缠身,耳鼓膜反复发炎,演变成顽固性化脓性中耳炎,迁延多年,直至失聪。
纳鞋咬针,牙齿松动,疼痛难忍。母亲四十多岁牙齿就掉光了,吃啥都是囫囵吞咽,口感荡然无存。致使常年肠胃疼痛。
养育难,成人更难。随着孩子们的一天天长大,儿女们念书识字是大事,儿成婚女出嫁更是农村人的头等大事。前三个哥哥结婚,爷爷奶奶、特别是父亲还都在世,问题也罢、困难也罢,有男人当家支撑。1965年,四哥结婚时,爷爷奶奶、父亲都已去世,为给父亲治病,家里已负债累累,几个成家的哥哥每家都分摊了不少的债务。亲戚邻里劝说母亲,给四儿结婚缓上几年再说,母亲坚持不改主意。她想:老子没了,四儿为了全家已当了农民做了牺牲,再不能亏待他。再说,等几年五儿也该成家了,一个困难变成两个困难,更是难上加难,必须在年内办。决心是软的但银钱是硬的,我们老家有一句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为了筹措四哥的结婚彩礼和花销,母亲到处求人借债,把能求的人都求遍了。无奈世道普遍贫穷,十元、八元解决不了大问题。母亲只好出下下策,把当时只有十岁的三女儿(我的三姐)定了娃娃亲。家里人常讲的故事是:四哥1965年结婚时和二姨家借了两条白羊毛毡,八十年代二姨家的老五结婚时才给清了账。苦涩的笑话后面,掩藏着母亲多少艰辛与苦难!
历尽艰难困苦的母亲今年一百周岁了,人们常常会问长寿的秘诀,我的母亲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没吃没喝没穿没时间害病。记得母亲大约五十多岁时背上长了一个疮,村里的土医生拿一把杀猪刀剜掉疮,撒了一点磺胺粉,棉花纱布一盖,胶布一贴,就算把手术做了,不过三天就上山劳动。还有一次,母亲的胳膊被狗咬了一口,剪了一把狗毛敷在伤处(土法,以毒攻毒),揉揉就算了事,该干啥干啥。母亲无论春夏秋冬总感寒凉的病,中药西药吃了无数,总是无效。1996年,家里给母亲过八十岁生日,亲朋好友争先敬酒,母亲非常高兴,虽第一次沾酒也还喝了不少。第二天,五哥问母亲昨天喝的难受不?母亲说:不难受,喝了酒,身上热乎乎的,冷也不怕了。五哥劝导母亲,那你就常喝点,咱有的是酒。母亲初期舍不得喝,一天三口两口。儿女、孙子外孙看母亲爱喝酒,就买酒孝顺母亲。酒多了,母亲身体一有不适就喝酒,三天两天一瓶,喝酒当喝水。现在,“给我喝口酒”已成为口头禅,别人喝酒图高兴,母亲喝酒为解疼痛。
母亲的艰辛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生存,母亲的病痛换取了全家人的健康安宁,母亲的付出换来一个家族的未来。
位卑识远
在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尽管岁无宁日、时艰世难,父母仍用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昼夜不息地劳作,坚守人生的美好向往,不仅养育孩子们长大成人,更期望孩子们能活出和父母不一样的人生。一次,母亲带着大哥、二哥去外爷家,外爷和大舅(王定民,母亲的堂哥。神木南乡较早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共同开导母亲,要供孩子们念书识字,否则长大了都是受苦汉。一语点中母亲的心病,天资聪慧的母亲早就想到孩子们不念书识字,未来就是走父母受苦的老路。可是,村里既无学校又无先生,自己家又没有经济实力,孩子们念书的事年复一年的耽搁。外爷和大舅的话促使母亲痛下决心解决孩子们念书的问题。
当年冬天,母亲就在家里腾挪地方,垒台制凳,请来教书先生,大哥、二哥开始“私塾”冬学。因为只是冬天授课,加上在自己家里因陋就简的凑合,头几年费用不高,还能勉强支撑。后来,随着年级升高,课程难度加大,先生不能胜任,需要出门到乡里正规点的学校上学。离家上学费用自然要大,家里的活也没人干了,怎么办?父母亲只好做了这样的统筹安排:大哥家里的冬书读完后,便跟着当乡长(土地革命时期)的爷爷到乡公所上学(在孙子们上学的问题上,爷爷十分支持),一边照顾爷爷(抽疯病),一边读书;二哥身体好,能受苦,在家读完冬书就辍学,逐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三哥接着读冬书。大哥跟上爷爷读完高小,去神木上中学;三哥读完冬书也该出门去花石崖上高小;这时二哥已经17岁,再不复学就无法再读。三个孩子都离家出门上学,家里是实在供养不起。于是二哥复学后直接就读高小五年级,并且和三哥轮流上学,你半年,他半年。等二哥需去神木上中学时,四哥、五哥也需出门上高小,家里根本無法供养五个孩子同时出门上学。当时,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家里的自有耕地相对减少,母亲瞅准这一机会,毅然做了个大胆决定:卖耕地牛。一天,母亲来到外爷家,与外爷商量:
“大,我想卖牛?!”
外爷一听,“啊,你不要命了?虽说合作化了,地不多了,也该有二十来垧,卖了牛,地怎么耕,是不是想把你们两口子往死里受呀?”。
母亲苦喃喃地说:孩儿念书……
外爷对我们家的情况心知肚明,听到母亲的半截话沉思不语。
良久,外爷对母亲说:“女子,我知道了,回和你公公们商量去吧”。外爷的“知道”两个字说的轻松,做的却厚重如山!自母亲结婚生子,外爷一家的帮助就未曾停歇。舅舅帮种地,姨姨看孩子,外爷做生意给补贴……
母亲回到家里,伙同父亲和爷爷奶奶商量。爷爷说:养儿为孙,望长久远。卖了牛种地肯定难,可眼前的难是一阵子,再怎么难,也不能难孩儿们一辈子。爷爷支持卖牛供孙子们读书。卖牛时,母亲、二哥抱着牛头放声大嚎……
牛卖掉了,父母代替了牛,我的几个哥哥都能出门上学了。只是亏待了三个姐姐。重男轻女是原因,没有女孩子念书的学校是原因,女孩子念书没有前途也是原因,家里实在不能承担所有的孩子上学更是主要原因。我的三个姐姐为家庭、为哥哥、弟弟做出了一辈子的牺牲。
随着家里人口的逐渐增多,吃饭、穿衣、上学支出越来越大,光靠陕北贫瘠的土地肯定无法维持。无路处寻路,生活逼迫父母想出了种地之外的生路。种地为主,兼营蒸酒漏粉、养猪养羊。秋收后,别人开始农闲休息,我的父母却开始更为辛苦的劳动,起五更,睡半夜用粮食蒸酒,用绿豆做粉条。蒸酒剩余的酒糟、做粉的豆渣喂猪羊。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农产品深加工、循环经济。靠智慧,靠勤劳,靠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一家人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也为几个儿子上学读书提供了物质支撑。我们弟兄后来的发展证明父母当初的远见卓识。大哥1955年神木师范毕业分配在府谷县庙沟门任教;二哥1960年神木中学毕业并留校工作;三哥1962年花石崖中学毕业分配在花石崖公社农村任教;五哥神木中学肄业(因文革中断学业)后,参加社教并分配在榆林县大河塔公社任青年书记;我自己1982年榆林师范毕业分配在贺家川小学任教,六个儿子五个参加了工作。只有四哥因父亲患病去世,被迫中断学业,回家劳动,苦了自己,帮了全家。endprint
坚强不屈
我爷爷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共产党解放区的一个乡长。1934年的一天,国民党匪兵来家抓我爷爷,爷爷事先得信逃脱,家中只剩下母亲和奶奶。国民党匪兵进院前,怀有六个月身孕的母亲,急中生智,把奶奶藏进家中唯一能藏一个人身的土坯粮仓,结果她自己没来得及躲避,被抓走了,在邻村关了五天禁闭。匪兵严刑拷打逼母亲说出爷爷的去向,母亲始终没有开口。保护了身为共产党的公公,自己却因为严刑拷打、忧惧交加,导致流产,差点丢掉性命。
我是1962年3月出生,生下后,村里的人问父亲生了个啥,父亲说:生的个小子,赶得上吃我的献供。言下之意年过五十才生的这个小儿子,吃自己死时的祭品没问题,自己是靠不上这个儿子了。父亲的话一语成谶。当年秋天,父亲的身体急剧消瘦,吞咽十分困难,下地干活毫无力气。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不敢想象这座全家人的靠山倒了该怎么办?1963年正月,母亲倾家所有加上七借八凑的两千多元钱,派大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领着父亲到黄河对面的山西省兴县县医院治病。父亲踩着冰凌过了黄河,五个月后,躺在小船里度过激流滚滚的黄河回家。父亲患的是食道癌,住院做手术花光了两千多元,暂时挽救下了生命。1964年5月,父亲与世长辞,留下九个子女,六个未成家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两岁,还有治病欠下的一屁股债。父亲去世的时间,正是春耕大忙的季节,母亲头天掩埋了父亲,第二天就上山种地。看看身边嗷嗷待哺的儿女,母亲顾不上悲伤,没有擦眼泪的时间。
文革期间,母亲的五个儿子先后受到冲击,二、三、五哥被开除公职;大哥虽然保留公职,一家人却被遣返回原籍务农;四哥当村干部也未能逃脱,经常遭受批斗;家庭成分也要从贫农改成富农。走出去的又都回来了,平静的家庭横祸平添。作为农村妇女的母亲,如何能理解社会大变大革的反复无常,但是,母亲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正是这颗心引领着儿女们战胜困难走出困境。
四哥在接受批斗时,造反派把父亲在山西兴县看病买回的唯一的竹皮暖壶摔碎。母亲坚决要求打碎暖壶的人赔偿,说:“我儿子犯错了,我们家的暖壶也犯错了?!”她据理力争,不依不饶,打砸的人自知理亏,不得不赔了一个新的。
担任榆林县大河塔公社青年书记的五哥,被清洗回家,情绪低落。1968年征兵,正值中苏交恶,边境形势紧张,战云密布,敢于应征者甚少。五哥有意应征,母亲坚决支持,觉得这是五哥重振士气找到新的出路的契机。但有人诬陷我们家是“富农”,当时富农成分是过不了政审关的。母亲翻箱倒柜找出家庭成分是贫农的证明,过了政审关。五哥当兵走的那天,有人居然高声诅咒:“XX,你当了兵就不是富农了?你当了兵也是挨枪子儿的!”。母亲不甘示弱大声说:“我们五生(五哥小名)挨枪子也是为了共产党,死了也是解放军!”噎得那个叫嚣的人没有再说第二句话。五哥蒙冤回家,光荣参军并转业工作,是母亲用痛苦和勇气换回的尊严与荣耀!
农历1978年7月19日,母亲的长子、我的大哥崔乐生(乳名乐子),由花石崖公社赴瑶镇公社履职的途中,坐拖拉机遭遇肇事不幸罹难。第二天上午,母亲听到贺家川公社放大站在喇叭上通知,要崔家沟村的人去陈家坪梁上抬人。懵懂不知的母亲还问正在院里石磨上磨麦子的人:“咱村谁出事了,要抬人?”来坐娘家的三姐再无法隐忍,抱着母亲嚎啕大哭:“我大哥在花石崖跌坏了!”惊天霹雳打蒙了母亲,根本不相信前一晌还回家看她,告诉她要到神木北部的一个公社当书记的儿子,和自己商量了一夜家事,打算为这个弟弟帮办这事,为那个妹妹帮办那事的儿子,走时频频回首和自己告别,谆谆嘱咐自己保重身体的儿子,说没就没了?看见自己的女儿伤心欲绝哭成泪人,看见周围的邻里也低头掉泪,她明白了这不是梦中,明白了自己的骨肉儿子没有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山河呜咽,百草含悲,人间苦痛,千言难说,万语难状。
悲痛欲绝的母亲拍掉身上的尘土,擦干泪水,指挥哥哥姐姐们料理了大哥的后事,一个月后,她就挪动着颤巍巍的身躯,劳作在乡间贫瘠的土地上……自从父亲去世,身为长子的大哥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母亲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苍天夺走儿子,如同用尖刀剜走母亲的心!可是想想还有八个儿女,还有大儿子留下的三个孙子,最小的只有三岁,需要她率领着走艰难的人生路。母亲挣扎着爬出痛苦的深渊,下地秋收,上场打谷。
从1978年大哥去世到2003年这25年间,我们家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不再愁温饱,生活一天比一天好。1979年,二哥平反,恢复原职,回神木中学工作。三哥在神木县贺家川兽医站工作。五哥1982年转业,分配在神木县公安局工作。随着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几家哥嫂们的户口都转为城市户,家随之搬回县城。1984年,我从乡镇小学调到神木县检察院,母亲也随我从老家搬到县城居住。分散的家,集中在了县城,母亲又成为了我们的中心。从1986年开始,全家在县城自己动手修窑盖房。母亲租住的房成了来帮助修窑盖房的“民工”据点,母亲成了伙夫。从1986年开始到1989年间,我们弟兄几个共修建18间(孔)房子和窑洞,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母親也搬进了五哥的新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舒心如意。本以为母亲从此会享尽天伦之乐,可是,世事难料,从2003年3月至2011年7月八年间,母亲三次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莫大悲怆。
农历2003年3月,二哥不幸因病突然去世。母亲虽已86岁高龄,但一点都不糊涂。家人害怕母亲承受不了二哥去世的打击,统一口径,说二哥因腿病(因幼年繁重劳动导致脉管炎,母亲知道)长期在西安儿子家居住,方便看病。从此以后的日子里,只要二哥家的孩子来看望她,只要是有家人说去过西安,她必定会问及二哥。当初几年,她信以为真,后来起了疑心,时常出神发愣,自言自语,呢呢喃喃:“我不信拖子(二哥小名)这么铁石心肠,再怎么有病,这都好几年也不来看我了?”每每这个时候,家人都忍不住转过身去抹眼泪。
实际上,母亲心里早清楚了,她不刨根问底,是自己骗自己,不愿意捅破最后的一丝企盼。这一蒙就是八年。直至2011年五哥去世,家人商议不能再隐瞒。当母亲知道二哥也去世的事后,眼含泪花,淡然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给我说,让我的心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放不下?!endprint
农历2007年7月三哥从医院病危回到家去逝。三哥家与母亲相邻居住。给三哥穿好葬衣后,母亲坚持要最后看一看。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立在棺前,仔仔细细端详了一遍自己的儿子,用长满老年斑的粗糙小手,浑身上下抚摸了一遍,凄凄楚楚地说:“我知道你从小有病,就怕你埋不了我,你还是不埋我就走了,孩儿,你受了一辈子罪,走了也好。”在场的儿孙听见这话,无不凄恻泪下。
妈妈,你要忍受多少人生的磨难,才能将内心的至伤至痛表达得这么风轻云淡……
农历2011年6月五哥病逝。五哥是我们家的中坚栋梁,也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大哥罹难,家业待兴,文革蒙冤待肃。二哥三哥常年在乡下工作,力不从心。五哥舍弃部队的美好前程,毅然转业,协助二哥三哥奔走呼号,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农转非,批地盖房、迁徙进城,招工招生无不渗透着三个哥哥的心血。五哥事母至孝,晨昏定省。现撒手人寰,母亲凄声苦语:“五子,我为什么不能替你死”?母亲的天问是何等的哀伤!愿以己死换儿生是何等的凄怆祈求!
母亲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耄耋之年连失三子。但她没有倒下,没有气绝身亡。有泪不轻弹,有苦不常言。母亲不是麻木,不是糊涂,是历尽沧桑苦难的豁达、淡定。母亲超凡脱俗的定力与境界,更让我们面对百岁的老母亲,真真切切的产生高山仰止顶礼膜拜的冲动!
大爱无疆
母亲少年婚嫁,自己又生养这么多孩子,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娘家的困难。我三姐(排行第八)身后,母亲流产了一个孩子。正好我表姐(舅舅家的孩子)没奶吃。母亲便把我九个月大的表姐抱养过来,直至表姐7岁时,母亲高龄生我后,实在支撑不下去,才把表姐送回舅舅家。母亲上年纪后,时常回忆她的童年及抚养我们时的艰难,经常提及外爷一家对我们的帮助。母亲话中有话,大舅、三姨去世早,我表哥、表姐们孩子多,就业成为难题。我们把母亲的话深记心间,千方百计满足母亲的要求。我小舅一生未育,抱养的儿子十分优秀,小舅举家到神木供养表弟上学,数年居住我侄儿的房子。母亲常对我侄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老舅没钱,你不会和他要赁钱吧?!”。我表弟考上南开大学,母亲慷慨解囊,我们也随即跟进。现在有些糊涂的母亲,还经常呼唤远在天津与我表弟居住的小舅名字,亲情没有因时空而阻隔。
母亲管教子女十分严格,常说惯子如杀子。子女有错必受惩处。我是母亲45岁时生的,刚两岁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母亲格外疼爱,到6岁才断奶,11岁要到外村陈家坪念书才和母亲分睡。哥哥嫂嫂姐姐们对我也宠爱有加,我从小没有挨过饿受过冻。顽皮、不听话、不学好,是被溺爱孩子的通病,我也不例外。小时候最喜欢跟着来村里乞讨的乞丐学说打哄。有一次,我又听到乞丐说喜的快板声,着急去学,就将母亲吩咐推磨的营生草草了事。回到家还嬉皮笑脸的给母亲学说“送喜神,接贵神,前后跟着个活财神,我给你家来送神,打发个吧(要求施舍)”!母亲扬手就是几个耳光,厉声训斥:“你个不成事的鬼,你老子死的早,你学讨吃不学好?”现在想来母亲拼死拼活就是为了儿女不能沦为社会底层,不懂事的我却以做乞丐为乐,戳在了母亲的痛处。母亲的重责醍醐灌顶,我从此暗下决心:要奋发有为,走正路,做好人。
母亲有孙子、外孙25个,父亲去世后,哥哥们就不让母亲参加农业社劳动,主要任务是看孙子,种自留地。经母亲照看的孙子外孙有十几个。无论是对儿女还是对孙子,母亲人前夸奖,人后管教。经常挂在口头的话是:“人的名头,树的荫凉”,“但掏好心,不坏前程”,“吃亏吃不死人”,“钱有白黑,不该拿的不要拿,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不能乱拿”,“明里出去,暗里回来,做好人做好事自然会有好报”。母亲的至理名言是我们家的品格基因,更是我们家每一个人的精神法度。
数十年来,母亲一直是家里家外最有威信的人。她有一种不露声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家大人多是非也多,谁来诉说她都倾听。等诉说的人道完心中的不平,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实在逼得不行,也多说大的,少说小的;只说自己的儿女、孙子不对,不说儿媳、女婿、孙媳的不对。几个儿子去世后,她对儿媳妇们疼爱有加。经常给小的儿女说,这个你嫂苦,那个你嫂累,你们要照顾。大嫂进城后,生活艰苦,经常起早贪黑背着人捡破烂,她发现后就对五哥说:“你要管你大嫂,不要让起早贪黑捡破烂,有个三长两短,你哥留下的孩子怎么办?”五哥出面劝说,大嫂有所改善。嫂子们对母亲也非常尊敬,为自己,替丈夫,尽责尽孝。
与人为善,和睦邻里是母亲的处世理念。她常说,有千年的邻家,没有千年的父母。前村后舍,邻里邻家,谁家有困难,只要找上门来她都给予帮助。谁家生孩子,她是老有经验的接生婆,谁家娶儿嫁妇她是裁剪衣服鞋样的巧手,谁家和谁家有矛盾,她是处理问题的能手。
改革开放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村里人家家户户收获的粮食无处存放。母亲突发奇想:糊纸瓮。把家里的旧书旧本、废报废纸、烟盒烟标、烂衣烂裳,能用的全部收集起来。找来大大小小的瓷盆瓦瓮做模型,混面打成浆糊,把收集来的纸张粘贴在模具表面,晒干后脱落成型。把高粱箭杆一劈为二,水上泡软,去掉杆芯留下杆皮,缝箍在纸瓮缘口。一个存放粮食的廉价器皿就此形成。母亲的发明创造解决了当时村民们的存粮难题,一个时期村里村外糊纸瓮蔚然成风。去年我回村一趟,看到母亲的杰作还在有人仿效。
母亲做饭厨艺较好,饭菜又香又干净。村里来的下乡干部都愿意来我家吃饭,母亲的家俨然成了村里的接待站,母亲乐此不疲。母亲有个质朴的思维:我的孩子和来的人一样,都是吃公家饭的,下乡做事是为了老百姓。况且,来的干部不一定和我的孩子相识,我不能给我的孩子丢人。
母亲一生艰苦朴素。1980年之后母亲已儿孙满堂,衣食无忧,但她始终没有改变简单的生活作风,仍然是:粗茶淡饭饱即休,被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衣食住平平常常,名与位已有就好),不贪不妒老即休。母亲一生自强自立。1997年之后,儿女纷纷要求抚养居住,但她始终不答应,坚持自住、自理。直到2009年,92岁的母亲才逐渐有选择、有季节性的和儿女们分别居住一段时间。居住期间,给啥吃啥,从不挑剔,从不搬弄是非。家里的人都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伺候的老人。
母亲记忆力惊人,面对满堂儿孙百十号人,她不光能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还能准确说出他(她)们的生辰日月。为此,孙辈们常和她开玩笑说,都是因为她嘴馋,记住生日是为了吃好的。其实一个个生日,意味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晚辈健康平安是母亲最大的心愿。母亲开朗豁达,无论有多少儿女孙甥,母亲都愿意绕膝承欢,不厌其烦。有时,孙辈们和她开玩笑:“娘娘,什么时间吃你的糕呀(陕北习俗,人去世出殡要吃一顿糕)?”“你们狗儿的,等不上啦?娘娘还要好好活著!”
1987年我从榆林地委党校中青班毕业后,因为学历上了一个台阶,老想折腾到榆林、西安工作,母亲不同意,说“我扑狼扑虎跟着你,你走那么远,我怎么办,你的家怎么办?”那时的我,怎能懂得母亲的心。1991年,我有个机会可以调到华能精煤神府公司(大柳塔)工作,这次和母亲商量,母亲欣然同意,认为在一个县里好照应。2001年春节前夕,我所负责的神华集团社会保险工作要全部集中在北京办公,意味着我要到北京工作了。春节我回家和母亲过年,告诉母亲我要到北京工作,家也要随着搬到北京。看的出,母亲一个春节既高兴,又忧伤。高兴的是:她的从小失去父亲的儿子,从崔家沟村混到了有“皇帝”住着的北京首都;忧伤的是,她的老生儿,离她越来越远。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父母和儿女注定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母亲上升不到这样的哲学高度,她只希望所有的儿女亲人围绕在她的身边。
母亲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是大爱无疆的一生。母亲的品德,是普天下母亲共有的品德,更是我们民族共同的集体人格。但我的母亲,她的经历更为传奇,她的能耐更为独特。她受尽磨难,却能处变不惊;她身小力怯,却能屡撑危局;她一字不识,却能贯通事理;她久居僻壤,却能兼爱亲朋。她铸就的定力、格局、智慧、品德牵引和滋润着我们整个家族的门风和运势。现在全家五代同堂,122口人和睦共处,家业兴旺,贤才济济,平安幸福。这一切,皆是百岁母亲这一尊瑰宝的恩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