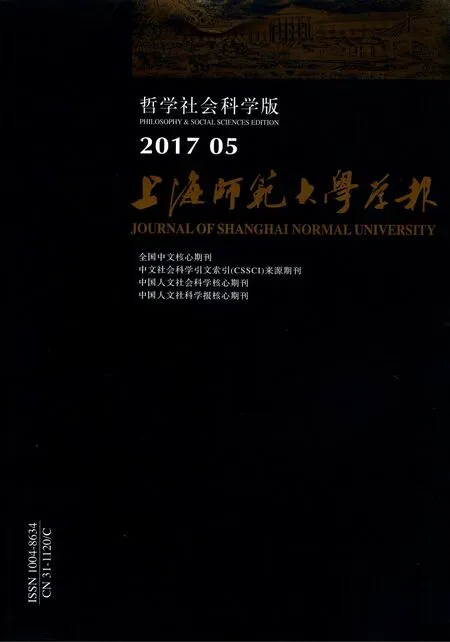弱嵌入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现实选择
黄兆信
(温州医科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弱嵌入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现实选择
黄兆信
(温州医科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模式,通过运作社会资本成功进行城市创业,从而推进城市融入进程,进入发展论预设下的“发展—经济”模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具有弱嵌入性,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社会管理模式下,通过创业等经济行为,能动地嵌入已有的社会结构中,挖掘关系网络、动员价值资源,渐进城市融入的轨道。
弱嵌入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城市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从 “生存—经济”模式到“发展—经济”模式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是将代际概念、阶层概念与职业分层概念融于一体的定义,是融合结构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复合型称谓。当前国内学者对这一群体展开了多元化的解剖,尤其在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上,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方面呈现出“半城市化”状态,[1]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一直待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初期农民工的行为逻辑和意义带有浓厚的“生存—经济”的烙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其行为的需求、动机和目标与初期农民工相比,分化的裂痕逐渐明晰,生存论预设下的初级的解释模式渐渐失去强效的解释力度。但不可否认,无论初期的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的需求始终处在第一位,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社会、政治的需求是有益的延展和补充。因而,在发展论预设下,在保障经济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是他们所选择行为的逻辑和意义。
社会结构学认为,职业是衡量一个社会人的重要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人们试图通过正向的职业流动(job mobility)来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2]虽然职业流动的正向或负向并没有恒定的标准,但对照老一代农民工从事以单纯的生存型职业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包含的发展性、权益保护等诉求更高。[3]在知识储备、能力素质、人力资本等各方面相对较低的前提下,创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正向职业流动的一个最佳选择。根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愿意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27%。在“发展—经济”的叙事模式下,新的经济身份即争取“城市创业者”的新标签和揭去“农民工”的旧标签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拓展的新的意义空间。
美国学者柯尔(Cole)在1965年把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在欧美,创业者(entrepreneur)被定义为组织、管理一个生意或企业并承担其风险的人。香港创业学院院长张世平认为,创业者是一种主导劳动方式的领导人,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业现象,是一种需要具有使命、荣誉、责任能力的人,是一种组织、运用服务、技术、器物作业的人,是一种具有思考、推理、判断的人,是一种能使人追随并在追随的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是一种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依此定义,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界定为具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在城市中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力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进行创业活动的人。
毋庸置疑,资本在创业过程中至关重要,尤其对脱离了地缘、血缘等多种优势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创业资本的获取是创业成功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经济”行为逻辑决定了通过创业获取经济价值并不是最终目的,融入城市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可选择的现实情况下,倾向于运作利于城市融合的创业型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公用品,社会的不平等可能存在于社会资本当中,尤其是在流动的过程和转换标签的过程中,权衡社会资本的成本和利益,是归纳选择各种形式的创业型社会资本清单的基础。
根据亚历詹德罗·波茨的观点,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嵌入社会网络中能够被利用产生效益的那部分资源,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规制的形式,即是社会资本。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弱嵌入性”概念,在指出社会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制约的同时,也看到经济活动并不是社会关系的奴隶,嵌入者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对社会结构有建构的作用。波茨进行理论迁移,提出嵌入者可以是理性,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人;被嵌入者则可以是社会的经济文化结构。这使得“弱嵌入性”的观点能适用于许多社会现象。已有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刻板地将其归为弱势群体,并将其弱势的原因大致归结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管理的落后等,并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二元结构的解构、先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实现。[4]这将是漫长的过程。在实际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已经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通过创业等经济方式,集结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主动嵌入社会结构中,能动地融入城市生活里。因而,本文依据弱嵌入性理论分析模式,分析在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城市创业的过程中,嵌入者是新生代农民工,被嵌入者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变革的大背景下,正在变革和调整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以及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就业制度等。被嵌入者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新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为规范等新的社会属性,而在嵌入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城市创业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抗拒社会变革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适应新的生活的过程。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嵌入,给被嵌入者带来了相应的影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基于此,从“弱嵌入性”这一中层理论视角、从个体与结构互动的层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过程及行为,是遵循新生代农民工应对社会结构变革所产生的行为变更而来的。建立于社会融合根基之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为了回避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性而造成了社会融入经济能力较低、公共政策公平性缺陷剥夺其平等参与机会、公共服务供给额能力和均等化不足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滞后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融合环境等问题,他们作为嵌入者,如何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下进行创业,如何引导创业行为符合他们“发展—经济”模式,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分析策略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佣他人的老板、占有少量资本且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采用抽样调查的定量分析法,并结合个案访谈进行调查。在城市的选择上,考虑到调查数据的代表性,课题组不仅选择了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南京等大城市,还选择了青岛、福州等东部其他经济发达城市;另外,也派出调查组奔赴中部的武汉、合肥、南昌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同时,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课题组选择所处城市温州作为重点调查区域。在具体调查地点的选择上,考虑到农民工创业一般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餐饮、维修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服务业以及农产品、家具、服装、鞋帽等加工业,课题组在收集数据时将城市中的小商品市场、农产品市场、餐饮集中区域以及市郊规模较小的工业集中区作为问卷发放的重点,采用城市—街道—社区的模式,分层抽样收集数据。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与其他创业者进行比较,调查人员仅对调查对象是否是创业者进行确认,而并未刻意排除其他类型创业者填写问卷。因此,在回收的832份有效问卷中,有312份为城市居民创业者所填,其余520份为农民工创业者所填。在520份农民工创业者填写的问卷中,6份填写者出生于1960年前;39份填写者出生于1960-1970年间;118份填写者出生于1970-1980年间;310份填写者出生于1980-1990年间;47份填写者出生于1990年后。我们将1980年后出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标准,那么实际回收有效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问卷共357份。结合问卷调查,调查人员在杭州、温州、宁波等地共深度访谈41位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观察他们的常态生活,作为定量分析的补充。
根据实地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企业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自雇型的家庭作坊;二是雇工型的微型或小型企业;三是中大型企业。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中51.3%为小本经营的自雇型家庭作坊;26.6%为微型企业;13.9%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7.6%为大型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内源性需要为基础,所经的“商”大多指商业(狭义商业,以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极少涉及工业等。根据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基本特征如下:
1.创业主体的关键词:80后,男性,未婚,高学历
调查发现,86.8%的被调查对象为“80后”,而男女比例约为3∶2,未婚者达到60.2%;39.8%的为已婚,其中,已婚并生育的占27.8%,已婚未生育的占12.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城市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多为未婚的青壮年,和中国目前从事其他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婚育状况较为一致。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创业者,学历水平明显增高,其学历特征依次为高中或中专(22.4%)、大专(29.1%)、初中(23.8%)、本科及以上(23%)、小学及以下(1.7%)。
2.创业内容的关键词:商业,自雇型作坊,资金不足,竞争激烈,特色不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普遍采用“夫妻店”形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创业的职业类型也出现多样化,无证的游商游贩仍然是一部分创业者在初创阶段采取的方式。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类型依次为个体工商户(42.6%)、私营企业主(27.5%)、企业普通股东(5.3%)、包工头(3.4%)、企业控股股东(1.7%)、无证小摊贩(17%)、职业投资者(2.5%)。访谈中发现,选择无证小摊贩的大多为游商游贩,在经营的内容上多为小吃零食类和餐饮业,属于小成本生意,经营成本投入为5万元左右的占76.9%。但由于小成本生意投入少,带来的不稳定性也大。从外出创业到被调查的这段时期,有过1~3次经营内容和地点变动的达到47.2%,有3~6次变动的达到16.1%,6次以上变更的有11.9%。在实地采访中XJ村的刘某在生意稳定之前先后转战过株洲、周口、西安、兰州、银川、福州等地。根据调查结果,39.1%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认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其次是经验和创业方向。38.2%的创业者认为他们所在领域竞争者很多,竞争激烈;34.3%的创业者认为竞争比较激烈;16.8%的创业者认为竞争者虽多但其有自身特色;8.3%的创业者认为其特色明显,竞争少;仅有2.4%的认为其具有独特性,几乎没有竞争者。
3.创业者收入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内部收入差异大
在调查的样本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的存款为10万以内的占55.9%,10万~30万的为24.3%,50万以上的约占11%。在各收入水平的人数分布上相对均匀,各收入层级人数相差不大,家庭收入为2000元以下的占9.7%,2000~4000元的为31.7%,4000~6000元的为25.4%,6000~8000元的为15.4%,8000元以上的为17.8%。 相应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群体的月消费在2000元以下的占32.9%,2000~4000元的占42.8%,4000元以上约占25%,意即群体内各类人的收入水平有差异,贫富差距两极化不明显。
4.创业欲望强烈,具有执着的创业理想
调查显示,样本中创业1次的占63.6%,2次的占24.8%,3次及以上的占11.7%。即便清楚自主创业存在风险,没有打工来得“保险”(方言:有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仍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25岁的labe(应受访者要求,采用英文名)是ZG镇人,他从19岁起开始跟着亲戚学做糕点小吃,开一家自己的小店一直是他的愿望。2003年初labe在温州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店,主要制作里脊肉批发,之后他遇到很多困难,也搬过几个地方,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泄气,他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在加工、分类、运输、零售、管理等环节实现一体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开一家食品厂”。
三、嵌入者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现状解读
1.主动的关系嵌入与被阻滞的进程
脱离了乡土,暂时或间歇地切断了血缘、地缘关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的创业地需要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在创业过程中,强关系网络逐渐疏离,业缘关系、与社区、管理服务组织结成的关系以及由娱乐活动构成的关系成为新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不仅能教给新生代农民工各种技能,还能促进他们在新环境下的进一步社会化。当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着美好的愿景,投入新的关系嵌入过程时发现,阻滞的力量要强于他们的预期。
(1)与城市居民的关系距离难以跨越。新生代农民工属于低禀赋的流动人口,他们创业地点首选为城市中的社区,而社区是中国特色的“身份型”社会的缩影,因而,尽快实现自身的身份融入,主动地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是他们获取更多利益的基础。[5]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主动投入关系网络建设之后,这些进城经商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和当地的居民有过多的来往,在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方面也尽量避免发生问题。在问卷调查中,有39人表示在外经商期间受到过当地居民的排斥。50多岁的彭为省在外做糕点小吃多年,老彭表示:“人出门在外,能忍就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2)与城市管理者矛盾突出。农民外出经商相对务工来说,与城市生活接触度更高,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也更为突出。相较于城镇人口,尤其是下岗失业人员,新生代农民工经常会遭受“创业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事个体经营,办营业执照不容易;二是从事个体经营,常常被驱赶、罚款,有的受管理人员的欺骗、讹诈;三是没有城市户口和抵押品,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四是要办多种证卡,被额外收取种种费用。
2.被动的制度嵌入与“打折”的社会管理
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专门的以及相关的政策,学术界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这些政策都普遍指向务工农民,也就是“被雇佣者”。在外出经商的农民工方面,相关政策却很少涉及。
由于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多身兼老板与雇工两种角色。在当前出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中主要涉及的三方主体为:当地政府、用人单位、农民工本人。由于缺少“用人单位”环节,缺少用人单位这一统一的平台和第三方支持,政策中所涉及的用人单位的责任与投入对经商的农民工而言毫无意义。而在失业、生育保险和最低工资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身份”限制和体制缺位,也无法享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福利和待遇。
(1)医疗保险。在调查中得知,被调查的外出经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早在2003年就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5年底为止,全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亿,全民医保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存在社会满意度低、保障水平低、宣传不到位、程序过于繁琐等不足。除此之外,外出经商农民工也因为常年在外做生意,很少有在家报销医药费的机会。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医疗保险还不能达成业务的互通,这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来说相当不便。
(2)养老保险。相对于较早施行的新医保,新农保对一些外出经商的农民工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问卷显示,只有353人参加了新农保,45人准备参加,还有325人不清楚什么是新农保。在问到希望通过什么方式养老时,选择“参加养老保险”一项的人最多,达393人;226人选择“银行存款”;207人选择“养儿防老”;144人选择“买商业保险”。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外出经商农民工是有参加保险意愿的,却因为一些制度和宣传的原因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参保率不高,这些因素都亟待改进。
(3)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事实上,除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可以自行缴纳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是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于2010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参加这三项保险的主体都是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如该法的第五章关于失业保险的条文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另有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失业前本人及其所在用人单位已经按照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这些规定都将独立自主经营的外出经商农民工拒之门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职业的不稳定性高,很容易因各种原因导致经营失败,甚至失业。一旦遇上较大波折,其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
(4)小额信贷。问卷分析显示,有76.9%的农民工经营的启动资金都少于5万元,从事资金门槛低、经营规模小的小本经营。而在启动资金的来源方面,429人凭借“此前的积蓄”,282人选择向亲戚朋友借,仅有67人选择向银行借贷。
通过在XJ村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在这个2000多人的自然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外出经商,主要是做糕点生意。他们的集资方式一般是自己攒钱、向亲朋好友借钱或合资经营,很少有人会向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十分清楚如何贷款,村民普遍反映贷款手续繁杂,即便找到几个担保人也不一定能贷到。而一些村民提到的需要几个担保人的户口联保的说法,则是指过去老式的农户联保贷款,由5~10户联保,一般都是由兄弟、叔侄等担保。这种做法其实没有什么约束效力,一旦发生风险,担保人往往不认账,而且这种担保没有什么财产保证,所以经过农信社和村委会的审核评定后,这类贷款申请很多都被拒绝。
被誉为“富民工程”的小额农贷政策,始终未能破解广大农民“缺乏担保抵押就贷不到款”的传统观念。一些农信社在对小额农贷重大意义的认识上有偏差,加上各个方面综合管理的薄弱,导致小额农贷回收率偏低,难以持续;有的没有发掘有效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思路,没有向村民推广行之有效的业务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
3.完全被动的生活政治嵌入与权利的缺失
关于社会政治的类别划分,吉登斯的观点独树一帜,他将政治分为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以及如何重建社会团结,如何对生态问题做出反应等。[6]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的关注显然只是对生活政治的关注,生活政治的嵌入直接影响了他们创业的便利以及所能获取的利润。但在生活政治嵌入的环境下,他们的状态是完全被动的。
(1)选举权利自动放弃或难以实现。选举权利关系深远。调查发现,高达78%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并未意识到选举权利的重要性,在他们眼光所及之处,是新当选的村委会是否能给村民实惠,是否能免去他们在外经商所必须回乡办理某些事宜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特意为一次选举而回乡必然误工,还要自行承担往返费用,于他们而言,自动放弃或请他人代选是比较明智的方法。而在他们暂居的社区内,约47%的农民工希望获取选举权利,这将直接与他们的创业利益相关,而这一想法目前只能存在于设想之中,难以实现。
(2)教育培训政策难覆盖。农民外出经商与外出务工在技术要求上存在差别。受雇于工厂企业只需要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而作为自主经营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除了掌握相关产品制作技能或相关知识以外,更需要掌握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关于“当地外出经商农民经营的技术和经验的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168人在打工时学得经营的技术经验,446人为亲戚朋友的传授,上过培训班学习的仅有36人,还有202人表示没有经验技术。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个人素质与技术技能的提升不仅仅对其自身的发展有帮助,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的经营工作,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素质与技能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就餐饮行业而言,除了传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食品的制作技能之外,更应该重视他们食品安全卫生知识方面的教育。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进行全面的职业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3)信息与资源支持的政策性缺失。外出经商农民工有着相对较高的个人能力,而且他们也有着很强的创业积极性,但是被调查者仍反映外出经商会遇到重重困难,主要表现为:市场信息闭塞,不了解当地政府政策,办证难,收费繁杂等。
通过调查得知,外出经商农民工获取市场信息的途径非常原始、单一。297人都是自己盲目地实地尝试;232人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某地做得很好才跟去;在被调查的100人中,仅有5个人是从媒体或者政府那里获得市场信息的。XJ村村委会妇女主任祝亚英在谈及本村村民的外出经商现象时说:“主要是一个传一个,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都这样传过来的。”
在夏岭村采访labe时我们也了解到,他就是因为不清楚当地政府的规划,而在步行街开了家小吃店,正当生意红火时被城管查封了,损失惨重。他在采访结束时说,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信息,做到很好的宣传沟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一旦找到门面(经营地点)了,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办证问题: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暂住证……在被问及遇到的困难时,33%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者反映办证难(包括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21%反映收费繁杂(如地方城市的管理费用、国家税费等),19%反映与城管的矛盾突出。受访者彭志辉表示,由于是外地人,或多或少存在被区别对待的情况。
4.能动的文化嵌入与不断地调适
文化能够培育稳定的、具有情感性的嵌入关系。泽利泽认为,市场深深地嵌入于各种文化和结构设置之中。市场和产品本身即是一种尽然了基于共识之上的意义的文化事务,是这些意义的符号或表达。[7]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了解所在地的文化是创业成功的关键。然而,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身上,则表现为逐渐形成乡土文化“内卷化”与接纳城市文化“去内卷化”的对抗力。
(1)对城市创业文化的向往和模仿。大量研究表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充满向往,相较于他们的上一辈更善于模仿。尤其在经商过程中,能主动接纳城市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抓住商机,留住顾客,创造利润。[8]在H城JG区BY街道社区内开蔬菜水果超市的小张,来自四川,与妻子一起创业,外请了四五位服务员和工人一起运营。在工作服的问题上,小张犹豫了很久,他认为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服装能提升超市的整体形象,可是咨询过朋友、实地考察过几家大型的超市后发现,需要设计统一的标识、设置统一的颜色和样式,最好能有自己的品牌口号。最终他觉得太过复杂,便给每位员工买了一件白色衬衫,“虽然不是那么好,但感觉上干净利索一点”。与城市居民尤其是一线城市居民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经历过创业文化的耳濡目染,他们的知识储备和禀赋差异导致他们愿意主动追求城市创业文化,但是缺少掌握实质内容的方法,只能随着经商行为的不断深入,进一步调适心态以适应创业文化的需求。
(2)乡土文化“内卷化”。根据调查,61%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在日常饮食中惯用家乡饮食,如在温州经商的河南人,日常主食仍以馒头为主。尤其逢年过节,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必然会遵循家乡的习俗,进行祭祀或者庆祝。尤其在经商所在地,他们会结成以地缘为主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乡土文化“内卷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他们的语言中,“我们老家那儿”成为习惯用语。一方面,由于远离了家乡,乡土文化缺少环境的培育和发展,逐渐丢失;另一方面,根植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内心深处的乡土文化是他们的家园和港湾,一旦在融入城市文化过程中遇到障碍或阻滞,他们会求助乡土文化的治愈功能。
四、被嵌入者赋予新生代农民工的规范与行动制约
1.制度的不完善、不公平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城市创业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9]因而,个人所属群体或所在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被该群体所控制的特定的社会资源。这也是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体现。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连带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相对封闭网络,虽然很多城市推进了户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民工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0]二元体制直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取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进行创业。
除此之外,公共财政体制难以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向本地户籍人口有限分配,对农民工的服务意识不足。另外,社会管理体制落后,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管理存在问题,有的地方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想要融入城市而产生的问题。
2.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制约其城市创业的进程
首先,在城市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已脱离户籍所在地,但在城市中仅取得暂住证等,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调查显示,75.7%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参加所在企业或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56.2%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与到家乡的村委会选举,69.1%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加入工会等相关组织或其他非官方组织。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所在地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机会。
其次,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初期并没有因地点变化和职业变化而弱化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但在创业起步后,亲缘关系在社会资本中的显著地位慢慢失去。但新的关系网络因为体制、经济方面的原因并未建立起来,基于业缘和友缘的社会交往很少。
3.社会舆论、负面标签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
当前,城市舆论对农民工群体存在负面的宣传炒作现象,给农民工贴上了“不文明”“没文化”“老土”“不遵守社会规则”“缺乏技能”“爱占小便宜”“不诚信”等负面标签,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遭遇不公平的对待,甚至遭受人格上的侮辱。这对其创业成功的信心不仅未给予帮扶,反而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五、弱嵌入性:嵌入者与被嵌入者互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嵌入者,城市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作为被嵌入者,自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创业之时,便开始了嵌入的过程。嵌入互动的结果是立体多元并在,显性与隐性并存。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创业活动中,弱嵌入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主动的关系嵌入和能动的文化嵌入,被动的制度嵌入和生活政治嵌入。四种嵌入类型的主动与被动的程度并不相同,如图1所示:

图1 四种嵌入类型的主动与被动程度
针对这种弱嵌入性,要进一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进程,使其成为推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可操作化途径之一。有效的资源动员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成功的关键,需从嵌入者和被嵌入者两方面进行考量,全方位、立体化地规避可能产生完全被动嵌入的模式,尽可能地创造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能够主动调适、创造的嵌入环境。
1.嵌入者:进一步发挥能动性和策略性
从创业的阶段来看,创业初始,大多数农民工是借助亲缘关系起步的。建立起简单的工坊或者店铺后,以亲缘关系为起点的关系网络无力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转向情感支撑。在创业初期到中期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试图寻找并建立新的关系网络,挖掘新的社会资本,但他们被拒绝在城市的社会资本网络之外,强嵌入性的关系与他们绝缘;而众所周知,社会资本是讲求付出与回报的,要充分嵌入城市,必须付出与期望获得的社会资本相当或更多的资金、情感。并且,高额的支付未必能得到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出现两种分化:一种是转向“弱嵌入性”,有余地、有自主性地进行嵌入,这是嵌入者对被嵌入者能动的适应。另一种是封闭在原来的社会网络之内,或者游离在城市社会网络和农村社会网络之间,形成一个狭小的网络圈。后者本文不进行阐述,对于“弱嵌入性”的现实选择,依据帕特南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的解析,新生代农民工所能挖掘的社会资本类型主要有如下三种:[11]
(1)关系网络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分为先赋性和后致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先赋资本主要通过亲缘和地缘产生,在创业过程中最先被消耗。在经营活动中需要工具性动员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即人际关系网络,结成组织共同体,并遵循关系网络背后积淀的社会规范。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情即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即使需要支付高额的代价,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必须开拓如“饭局网”“拜年网”等关系资源,随着其资源动员能力的增强,操作高难度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会变得越来越轻松和简单。
(2)信任型社会资本。本文将信任型社会资本分为政府和相关职能机构先天形成的权威信任资本和自组织与个体之间所形成的信任资本两种。在创业到一定时期后,通过街道社区、工商、税务、行业协会等建立起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逐渐增多。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创业,所受到的特殊福利待遇要低于城市居民,但目前大多数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相对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要积极发掘组织型社会资本,一是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二是积极呼吁为自身创业发展谋求更多优惠政策,三是吃透、领会相关政策规定所带给自身的真切利益,而不要盲目不知。
(3)规范型资源。一种是指由传统人情所带来的基本规范。对城市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要了解并遵循城市、农村所带来的规范差别,树立起令城市消费者刮目相看的良好形象,令创业之路平坦顺利。另一种是指基于现代市场规范的资源。随着创业进程的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会逐渐增强,基于法律、契约、市场交换法则之上的资源是新生代农民工推动其创业规模扩大的必备资源,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能迅速揭去“农民工”标签而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经之路。
2.被嵌入者:多元化、差异化地赋予优质创业资源
追溯流动群体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时,许多学者和研究都将根源指向户籍制度的限制。[12]而关于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最新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的改变只对高素质的流动人口有利,对低禀赋流动人口无效,甚至将产生负向作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而言,的确产生了诸多问题和阻碍,但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无时不存在。韦伯认为,制度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制度形成了结构惰性,还因为制度开始对人们具有意义。因而一味强行改变或颠覆原有制度、逻辑和体系,并不一定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基于此,本文所指向的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机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适,以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嵌入。
(1)建立生态的创业资源动员社会化机制。城市创业的扶助体系已初具雏形,并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如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建立相应的资源动员机制,解决这一小部分弱势群体的创业难题,是被嵌入者应尽之职责。生态化的概念,是强调政府组织不应当强行介入或摊派任务,以免揠苗助长。首先,政府组织应当重视这一群体,遵循创业过程的自然规律,助力具备良好基础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项目成长、成熟,让不具备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自然退出市场。其次,政府组织需要整合包括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是指社区和社区之间、社区与所在地的工商税务城管等职能部门之间、社区与所在地管辖的企业及商铺之间的资源,尽可能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项目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纵向资源是指社区与上级政府组织之间、社区与所辖居民之间的资源,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项目评比、扶助等活动,让新的地缘关系孕育产生并进一步成熟。再次,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府组织应建立有效的联系。一是通过联系以全面掌握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情况,跟踪服务,尽量将家乡所在地的地缘、血缘资源与创业所在地的业缘资源都紧密结合起来,当遇到难题时为他们出谋划策。二是两地联手推进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地区拓宽创业门路,将职业技能开发作为关键,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三是两地联手推动城市创业和回乡创业的回转帮扶机制,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将在农村有优质资源的创业项目在城市进行推广,而将适宜在农村运作的城市创业项目带回农村创业。
(2)形成弹性适宜的创业管理逻辑。一是积极推进信贷扶持政策,大力推进小额信贷工作, 积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家庭信贷计划的可能性,尽量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资金困难的创业难题。二是推进科技教育扶持政策,要把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作为重要环节来抓。三是积极开展参与式帮扶, 采用点对点对口帮扶的政策,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形成帮扶工作的合力,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参与经济开发。
(3)打造富有包容性的创业话语体系。一是要有效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进取心,引导舆论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案例进行宣传报道,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成功或失败的现象要摒弃自卑的心态,建立起一种公平客观的态度。其次,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无歧视的舆论环境,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引导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帮助他们去除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规范的行为举止,建立起新城市人的身份标签。再次,建立省级创业扶持专项资金、创新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推行“整发直贷”模式,落实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贴心政策,加大扶持农民工创业的力度。
[1] 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2]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3] 江立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5] 杨轶清.浙商的自然社会来源及其生成机制[J].浙江社会科学,2008,(5).
[6]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Zelizer, V. Beyond the polemics on the market: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J].Social Forum,1988,3(4).
[8] 秦昕,张翠莲,等.从农村的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J].管理世界,2011,(10).
[9] 胡荣,黄晨颖. 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10] 王玉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J].江淮论坛,2015,(2).
[11]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裂,赖海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2] 魏万青.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2).
(责任编辑:知 鱼)
WeakEmbedment:RealisticChoiceofNew-GenerationMigrantWorkers’CityEntrepreneurship
HUANG Zhaoxin
(School of Innovation amp; Entrepreneurship,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Survival is the first thing for migrant workers to fit into city life, and their living is supported by “survival-economy”, while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et up their enterprises through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get integrated into city life , and their living is supported by “development-economy”.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life by setting up their enterprises is a kind of weak embedment.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current social management model,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more active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fitting into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 by means of social network and value resources to become part of the city.
weak embedment,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city entrepreneurship
D422.6
A
1004-8634(2017)05-0005-(09)
10.13852/J.CNKI.JSHNU.2017.05.001
2015-12-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VIA150002)
黄兆信,浙江平阳人,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新生代创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