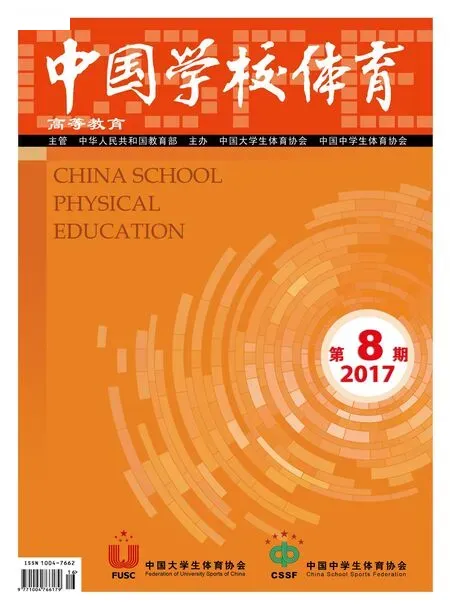刑法规制“假球”问题的罪名选择新探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切入点
姜 瀛
(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辽宁 大连 116023)
刑法规制“假球”问题的罪名选择新探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切入点
姜 瀛
(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辽宁 大连 116023)
采用文献资料法与法律解释学方法对刑法规制“假球”问题的路径展开新思考。从文献研究来看,学界就“假球”的刑法规制问题形成了“立法论”与“解释论”的立场纷争,二者争议的焦点在于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可以适用于“假球”行径的罪名。前者持否定态度,而后者持肯定态度。从实质解释角度来看,竞技体育赛事是一种非物质产品,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假球”应当被解释为是提供假冒的非物质产品的行为,属于我国《刑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以假充真”行为。因此,通过妥当地解释《刑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产品的外延,就可以达到规制“假球”行径的目的,而无需在立法(修法)上“增设新罪名”。关键词:假球;罪名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解释
自1994年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足球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假球黑哨”的质疑声。而在2011年,我国司法机关开展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赌扫黑”行动,随着司法裁判文书的生效,相关犯罪人被定罪量刑并付诸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反赌扫黑”过程中,涉及“假球”案件的相关犯罪人多是被以《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假球”行径的法律定性问题而言,裁判文书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学者将之概括为“重反腐、轻打假”的错位[1]。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社会科学I辑),以“假球”为篇名进行检索,截至2017年7月1日共获取文献28篇;排除其中属于事件介绍或新闻报道性的文献之外,笔者筛选出9篇直接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时间分布为2006年至2016年。从上述文献资料来看,学界关于“假球”刑法规制问题的理论研讨一直没有停止,但难以形成一致看法。鉴于此,本文希望对学界观点作进一步梳理,并指出其局限性,最终论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制“假球”行径可行。
1 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评述——“立法论”与“解释论”的立场纷争
正如上文所指出,由于2011年所展开“反赌扫黑”行动以及后续的刑事司法审判并没有直接对“假球”行径的法律定性问题作出回应,学界此前对于“假球”如何定性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相关文献梳理如下。
有观点认为:“目前并无‘假球’可以适用的罪名,应适时进行刑事立法,不过应设置较高的入罪标准,降低其适用范围”[2]。有观点认为:“对于假球、赌球等行为,有必要依据法律经济学原理调整刑法的制度设计。在犯罪问题上增加操纵体育比赛罪;在法律后果问题上扩充刑罚类型”[3]。有观点指出:“操纵体育比赛具有侵害法益的独特性和严重性,不能为刑法已有规制手段所保护,亟需通过立法方式单独创设的行为类型予以刑法规制。从刑法规范视野出发,选择操纵体育比赛罪比诈骗罪、赌博罪对体育法益的保护更为合理”[4]。有观点指出:“操纵比赛现象在我国当下的职业足球赛场上愈演愈烈,而现有法制却对此种行为的惩治于法无据,有必要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5]。也有学者在借鉴域外立法后指出:“美国《模范刑法典》明确设立了操纵公开竞赛罪以供各州参考。我国宜借鉴美国联邦规制操纵体育比赛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非法操纵公开竞赛罪,以此打击与操纵比赛相关的各类犯罪行为”[6]。
与上述系列观点不同的是,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已经存在可以适用于“假球”行径的相关罪名。有观点指出:“参赛者未向组织者提供真实的比赛,获得“债务免除”利益,假球应定性为诈骗罪。因假球而受贿的,则触犯诈骗与受贿两罪名”[7]。有观点指出:“‘假球’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当前行业规范、部门法律却不足以有效地控制或消除,刑法有必要介入。相关参与人员的行为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犯罪、诈骗罪等”[8]。有观点指出:“假球黑哨的主客观表现及刑法中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求比较,适用刑法解决假球黑哨问题最适宜的罪名是诈骗罪”[9]。在上述认为“假球”行径应构成诈骗罪观点之外,还有观点指出:“在评价假球时不能只关注获取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应关注行为对公共财产安全法益的危害。假球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特征,而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0]。
总体来看,关于“假球”行径的刑法定性,学界存在明显分歧。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不同立场。持“立法论”立场的学者们都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中现有罪名无法直接适用于“假球”行径,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在刑法中“增设新罪名”的立法(修法)方式来规制“假球”行径。从罪名的表述来看,多数观点认为应当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
与“立法论”立场不同,持“解释论”立场的学者们强调,通过正当地解释《刑法》中的相关罪名及其构成要件,便可以发现适用于“假球”行径的罪名,也即认为无须通过刑法修改来增加新的罪名。至于具体的罪名选择,多数观点主张可适用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对“假球”行径加以规制。此外,还有个别学者认为“假球”行径可适用我国《刑法》第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对“立法论”立场的简要回应
由于足坛“反赌扫黑”司法实践中也是采取了间接路径——将因收受贿赂而踢“假球”的行径纳入到《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中。或许,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刑法》中没有罪名可以直接适用于“假球”行径,进而印证了“立法论”立场者的观点。
对于这种“立法论”立场中可能存在的看法,笔者作出以下回应。司法实践中的罪名选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选择以《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假球”行径追究刑事责任存在多种可能性。首先,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的过程中,可能认为“假球”行径涉及多个罪名,各罪名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公诉机关选择了处罚较重的罪名进行指控;其次,或许由于证据上的原因,公诉机关仅选择了证据链条更为完整、更为有利于定罪的罪名进行指控;最后,也可能是由于刑事政策上以避免打击面过大的考虑,重点打击对象是收受贿赂的“假球”行径,而对于未收受贿赂的“假球”则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司法政策。总之,仅仅以司法裁判最终所判决的罪名,尚不能表明我国刑法中的现有罪名无法直接适用于“假球”行径。
当然,由于本文针对“假球”行径采取了“解释论”立场,也即主张我国《刑法》中存在可适用于“假球”行径的相关罪名,后文详细论证的过程便是对“立法论”观点的直接回应。在此,笔者不再对持“立法论”立场的学者及其相关观点作更多评价。
3 对与“假球”行径相关的罪名之解读与评析
“假球”是指在职业足球比赛中基于特定目的并采取操纵比赛的方式以达到预定的比赛结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假球”行径可能涉及的罪名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赌博罪”“诈骗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上述罪名在适用于“假球”行径的过程中要么需要满足特定的限定条件,要么是存在理论偏差,因此都难以成为刑法规制假球罪的正当选择。以下分别加以分析。
3.1 “假球”行径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需要以收受他人财物为条件 我国《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上述刑法条文中可以看到,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需要满足3个基本条件:1)利用职务便利,2)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为他人谋取利益。该罪名在适用“假球”行径时不仅要求球员利用其参与特定足球赛事的机会踢“假球”,而且还需满足“收受他人财物”这一基本条件。
实践中,存在2种情形会导致《刑法》第163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难以适用于“假球”行径。1)球员在没有收受贿赂的情况下踢“假球”,如参与赌球投注了自己参加的比赛,希望控制比赛结果;或者是为了做掉主教练而故意踢假球;也可能是单纯出于感情(如为了帮助对方保级)而踢“假球”。2)在证据上难以证实的,也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球员踢“假球”是因为收受了他人财物。在上述情况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都无法直接适用于“假球”行径。
3.2 “假球”行径不符合“赌博罪”的行为要件 与“假球”行径存在一定关联性的另一罪名是“赌博罪”。我国《刑法》第303条“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可以看到,赌博罪属于目的犯,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在具备这一目的的前提下,赌博罪分为2种基本样态:1)聚众赌博,2)以赌博为业。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构成“聚众赌博”:1)是组织3人以上赌博,且在抽头渔利或是赌资数额、参赌人数上达到特定的数额标准;2)是组织我国公民10人以上赴境外赌博,从中收取回扣、介绍费的。显然,球员踢“假球”的行径是一种竞技体育活动,比赛结果虽与赌球投注的输赢相关,但球赛本身并不是赌博行为。因此,球员因参与赌球而踢“假球”不属于“聚众赌博”。此外,学理上来看,“以赌博为业”要件所强调的以赌博作为常业的“常习犯”特征。赌博所得成为行为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且行为人赌博已成习性,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赌博[11]。事实上,考虑到球员因参与赌球而踢“假球”不可能成为习性,亦不能在长时间内反复实施,因此,球员因参与赌球而踢“假球”不属于“以赌博为业”。
3.3 “假球”行径适用“诈骗罪”存在理论瑕疵 对于“假球”行径而言,多数学者认为可适用诈骗罪对其加以规制。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直观来看,球员踢“假球”的行径代表了“参赛者未向组织者提供真实的比赛”,因而可能被认为属于一种欺诈行为。然而,这种“参赛者未向组织者提供真实的比赛”的情况与我国《刑法》中“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仍然存在差异。
在学理上以及司法实践中,成立诈骗罪需要经过如下“线路图”:1)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2)致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3)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产→4)行为人取得财产→5)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失[12]。直观来看,将“参赛者未向组织者提供真实比赛”之“假球”行径解释为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并无不妥之处。但成立诈骗罪,需要行为人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致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产给行为人。而在球员的“假球”行径后,通常不会发生致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的效果,这不符合诈骗罪典型的构成要件。此外,球员的“假球”行径并非是以非法占有球票收入为目的的。就主观层面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而言,“假球”行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最后,对打“假球”的行为,由于观众买票在前,而球员踢假球在后,一般不符合诈骗罪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致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的实践逻辑特征。综上,球员的“假球”行径不符合诈骗罪的定罪“线路图”,因而不宜定性为诈骗罪。
3.4 “假球”行径不同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 少数观点认为“假球”行径可构成我国《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罪名的立法构造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及投放危险物质罪相并列构成选择罪名,其要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性。易言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实际上应达到“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等同的危险程度,只是由于立法上无法穷尽所有的危险行为,立法者才用“其他危险方法”作为补充规定来防止法律的漏洞。但在解释“其他危险方法”以及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司法机关必须参照“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来衡量相关行为是否已经到达了刑法所要规制的危险程度[13]。显然,“假球”行径也是竞技体育赛事,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具有明显危险性的活动,更无法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等同的危险程度,因而不能将“假球”行径解释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
4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产品”的解释空间之拓展
虽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赌博罪”“诈骗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于假球行径都存在局限性或理论瑕疵,但我国《刑法》中并非没有合适的罪名可适用于“假球”行径。通过刑法解释上的进一步论证,我们便可明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理应成为刑法规制“假球”行径的路径选择。
4.1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法律规范分析 我国
《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此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而从法益定位上来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经济犯罪,其所保护的法益为消费者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事实上,从法律衔接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对接的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7条的规定,也即“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我国《刑法》中的延伸,这种延伸的必要性源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制裁手段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具有局限性。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最后手段,刑事制裁手段在先天上就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机制,刑法以其最为严厉的刑罚措施来威慑那些已经侵害或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人[14]。
4.2 “产品”的内涵及其法律解释之扩张 依照语义解释,产品即“生产出来的物品”[15]。而按照经济领域的说法,产品是向市场提供的,引起获取、消费或使用,以满足欲望或需要的任何东西[16]。而从价值观念上来看,产品是组织制造出来的任何向市场所作出的供给,以提供给消费者(购买者)的直接利益或效用[17]。总体来看,产品可以被概括为能够供给市场,被人们使用和消费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东西,包括有形的物品、服务、虚拟财产或特定的非物质性对象以及它们的组合。
当然,法律语境下的产品不能完全等同于语义上、经济学中或者是价值观念上的产品。从产品范围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法律上对产品的最初定位仅仅限于物质产品。但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上限于物质产品的消费观念开始淡化,一些非物质性的、观念性的产品类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听音乐会、演唱会,观看体育赛事等,已经成为基本的消费方式。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单纯的物质产品已经无法包容产品的外延,在传统的物质产品之外便出现了非物质化的产品类型[18]。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基于约束经营者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与实践需要,产品的法律解释空间一直处于扩大之中。显然,作为竞技体育存在的职业足球赛事是以非物质产品形式存在的,其应当被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4.3 “假球”行径应被解释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以假充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职业足球赛事是以非物质产品形式存在的。而“假球”行径系生产者所提供的伪劣产品,其应被定性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以假充真”。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对刑法语境下的“产品”所作出的解释需要依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对“产品”的定位。目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多种形式的非物质产品都已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职业足球赛事属于典型的非物质产品,其已被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19]。因此,与“假球”行径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对象。考虑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刑法领域内的延伸,刑法所规制的产品类型也必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协调、相衔接。可以说,依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对“产品”范围的新定位,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产品”的解释范围也应当包括竞技足球赛事这一非物质产品。
从实质解释的角度来看,“假球”已经不具备竞技体育赛事本身的“性能”。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虽然“使用性能”更加侧重于物质产品,但作为一种非物质产品,竞技体育赛事也具有其特定的性能。竞技体育赛事能够为球迷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这种愉悦和满足既是源自球员精湛的技术、精妙的配合、激烈的对抗、团队的精神,更在于竞技体育赛事结果的“不确定性”[20]。此不确定性乃竞技体育赛事基本的“性能”。竞技体育赛事的结果虽受到双方综合实力的影响,但临场发挥的差异以及竞赛中的不确定因素(伤病、红黄牌)都可能带来以弱胜强的冷门或难以预料的结果。然而,“假球”行径乃是对比赛过程的人为操纵,将本应“不确定”的比赛结果“相对确定化”;缺乏了“不确定性”也就失去了竞技体育赛事的“性能”。
4.4 司法实践中的注意要点 在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假球”行径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下问题还需要严格把握。
1)关于涉案数额的计算。我国《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规定的入罪门槛是“销售金额5万元”;如“销售金额”未能达到5万元,则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只能作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入罪门槛所规定的金额为“销售金额”,而不是获利额度或非法所得额,销售金额应当以“假球”场次实际出售球票所获收入来确定。
2)关于犯罪主体范围的把握。实践中,“假球”既可能是由俱乐部组织实施,也可能由一个球员或数个球员等个体来实施。对于仅有一个球员个体直接实施“假球”的情况,可以将其作为犯罪人来处理即可;对于数名球员参与实施假球的情况,需要考虑实施“假球”行径过程中的犯意提起以及各位球员在“假球”比赛中的实际作用,综合判断来区分主从犯。对于俱乐部组织实施“假球”的情况,应当认定俱乐部领导、主管人员或领队、教练等在实施假球过程中具有支配地位,对于踢假球的球员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避免刑法的打击面过大。
3)关于量刑问题。考虑到假球行径本身不具有暴力性,若球员系初次实施“假球”,且比赛是不属于事关争冠、保级、升级或其他资格的,可以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上考虑轻缓化处罚;对于可能判处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符合缓刑的刑期条件),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5 结 语
总体而言,对于如何从刑法上规制“假球”行径,学界形成了“立法论”与“解释论”的立场纷争。前者强调通过“增设新罪名”的立法(修法)方式来规制“假球”行径,而后者强调通过妥当地解释《刑法》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可规制“假球”行径。笔者赞同“解释论”的基本立场,认为妥当地解释《刑法》便可达到规制“假球”行径的目的。但对于所选择的罪名,笔者持不同看法。竞技体育赛事是一种非物质产品形式,而“假球”行径应当被解释为是提供假冒的非物质产品的行为,系我国《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以假充真”行为。因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适用于“假球”行径具有该当性,应当成为刑法规制“假球”行径的可行选择。
[1] 潘星丞,陈芹.假球行为的刑法定性[J].体育学刊,2014(4):37-41.
[2] 郭玉川.论“假球”的罪名适用及立法完善[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9-102.
[3] 王利宾.操纵体育比赛的刑法规制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3(1):8-11.
[4] 王庆国,贾健.论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刑法规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6):547-552.
[5] 王栋.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的初探[J].体育世界(学术版 ),2011(11):60-61.
[6] 吕伟.美国规制操纵体育比赛犯罪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1):44-49.
[7] 潘星丞,陈芹.假球行为的刑法定性[J].体育学刊,2014(4):37-41.
[8] 吴先雄.“假球”问题及相关参与人员刑法定性[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3):25-29.
[9] 王阡.假球黑哨适用刑法浅探[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1): 82-83.
[10] 井厚亮.论“假球”对公共财产安全法益的侵害及其该当性[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6):527-530.
[11]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46.
[12] 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10.
[13] 陈兴良.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3(3):2-13.
[14] 姜瀛.论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对刑法机制的冲击及解决路径[J].行政与法,2014(3):100-105.
[15] 莫衡.当代汉语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94.
[16] 吴健安.市场营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6.
[17] [美]唐纳德·R.莱曼,拉塞尔·S.温纳.产品管理(第4版)[M].汪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
[18] 王博.足球赛事产品消费中的法律关系研究[J].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2014,1(8):16-20.
[19] 王博.消费模式变革型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146.
[20] 王博.论球迷消费权益的法律保护[J].体育文化导刊,2013(7):8-11.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hoice of Charge in the Match- fi xing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Point of the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Fake or Substandard Products Crime
JIANG Ying
(Faculty of Law,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Liaoning China)
With the approach of literature reviews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starts a new thinking on the path of regulating the match- fi xing by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rmed the dispute of "legislative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f the match-fixing.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is whether there exists a criminal offens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he match-fixing in criminal law. The former held a negative attitude, while the latter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From a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point of view, sports match is an immaterial product form, which is the object in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er law; the match- fi xing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provision of counterfeit nonmaterial products, belonging to China's "Criminal Law"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fake or substandard products takes the act of faking fact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regulating the match- fi xing can be achieved by properly explaining the extension of products in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unterfeit products," without "creating new crime" in the legislation (revision).
match-fixing; choice of charge;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fake or substandard products crim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G80-051
A
1004 - 7662(2017)08- 0015- 06
2017-07-15
姜瀛,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刑法、体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