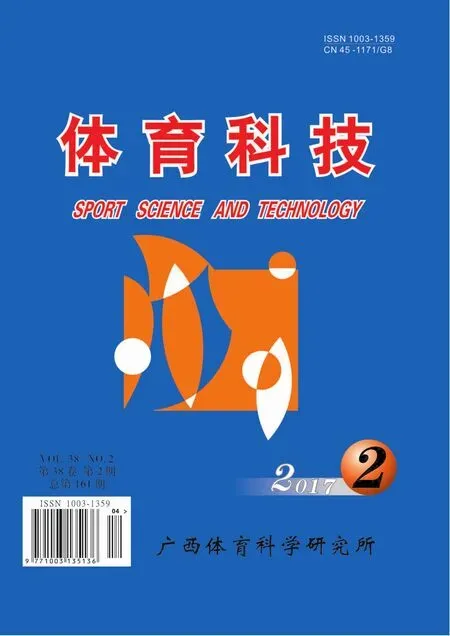论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叙事取向*
刘文沃 万讯而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 肇庆 526020)
论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叙事取向*
刘文沃 万讯而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 肇庆 526020)
叙事学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启发意义。叙事学的技术强调研究者担当旁观及引导的角色,让被采访者表达体育行为的过程及意义。在研究中,应该放下专家标签,把传统体育作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以他者的视角去重新阐释体育文化。
体育人类学;叙事;研究方法;田野工作
随着体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建构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人类学代表性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也逐渐为体育界所接受。田野工作作为质性研究的代表方法之一,越来越被体育学研究者所采用。然而也存在一些乱象:国内一些研究者对田野工作的理解不深,或研究态度不严谨,随便到调研点走一走、拍拍照即当成是田野工作,把田野工作与政治性的调研混为一谈,导致调查没有深度、田野资料单薄、调查资料没有说服力。因此,如何做好田野,成为体育人类学发展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田野工作又称为参与观察研究法,强调的是一种在“参与当地人生活”的基础上体验人们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那些在特定岁时节日随意往来的调查,并不能算作严谨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特别强调一个“离自己远去”的过程。“离自己远去”有两层含义,分别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上,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往往是一个生产周期甚至更长)内离开自己所生活的熟悉的社会文化体系,到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社会开展调查研究,深入研究当地人的生活。当然,有些研究者即便做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离自己远去”,其田野报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想象的异邦”,究其原因是研究者本身没有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对当地人的生活和内心境界理解不深。[1]针对此现状,笔者倡导在田野工作中使用叙事技术,以期更好达至研究目标。
1 叙事技术及其意义
叙事技术来源于叙事学研究,最早应用于心理学领域,强调引导当事人从主流的观点中解放出来,正视自己否定或忽视的经验,重新去探索自我。澳大利亚心理学家麦克·怀特最早在 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故事、知识、权利-叙事治疗的力量》,是叙事学的最早著作之一。[2]叙事技术作为一种后现代思想,在解构和阐释当事人文化与思想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作为研究技术,叙事学强调通过引导当事人叙说故事,让被采访对象谈论自己的过去,解构体育行为,重点对于体育行为本身及行为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用新的视角去诠释体育行为,发现体育行为对被采访人及其所在社会建构的意义。
叙事学的技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田野研究尤为重要。目前国内的田野方法中,注重体质测量、结构式访谈、实地观察,但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获得外化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更深层次的意义,即当地人的生活及社会根基与这些知识之间关系,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获得。叙事技术在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应用,首先应该强调体质测量、结构式访谈等传统的田野方法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强调文化、制度、个人感受对于体育行为的影响,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待体育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研究人员通过叙事者的故事,捕捉当事人的生活史和内心世界,使研究者真正地做到在心灵上“离自己远去”,发现一个他文化的细节及其意义。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是促进知识世界的构建,展现多元的人类文化。而在很多时候研究者掌握着话语权并带着其价值观念,在研究和展示文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夹杂了研究者主观想法,“写文化”有时候变成了个人的独角戏。研究者运用叙事技术去聆听他者故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达成人类学“发现未知自我”研究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放下文化的偏见,研究者实际上是书写文化的笔墨,而写文化的话语权在于当事人,以当地人的世界观和思想来展示“地方性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体质测量、问卷调查等传统的体育人类学田野方法不重要,而是说叙事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传统田野方法深入不足的缺陷。
2 叙事技术的观点
如何在研究中运用好叙事技术,促进研究目标的达成呢?以下列举一些叙事技术的观点:
2.1 撕下专家标签
去专家化是叙事学的重要观点。去专家化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专业技术,而是强调在人类学研究的语境下,我们更强调研究者走进田野的能力。虽然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并建构起高度专业化专家形象的自我概念,但田野工作更多地需要研究者具有生活世界的历练,走进被采访人的心里。每一个被采访者的人生道路都是唯一且独特的,这种唯一性无法用结构化的研究方法真正读懂。以龙舟运动为例,各民族各族群对于龙舟运动都有自己的解释:龙舟运动有怎么样的历史,如何影响族人间的往来,都有千百种说法。再到每一个参与龙舟运动的个体,他为何要参加?感受如何?龙舟运动对其本身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是千差万别。研究者不能从自己高度专家化的自我出发,来想当然地推断他者的想法,这是不合理甚至错误的投射。相对于研究者数个月甚至是只有数天的田野经历,被采访者当地的生活时间要长得多,体验也丰富得多。一些仪式、运动、游戏反复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呈现,对于如何组织、如何开展、如何体验、如何反思这些活动,当地人或多或少地有所理解,这些地方性知识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其自我建构当中。因此,作为研究者,放下专家化的自我,聆听当地人关于体育行为的故事及内心体验,一来利于抓住与研究目标相关的蛛丝马迹,二来充分发挥了被采访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充分展示内心构建的体育世界。
去专家化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做到悬置判断,即把研究者专家化的自我搁置一边,对于被采访者所诉说的民俗、故事采取“未知”的态度,既不判断其对与错、有用与无用,而让被采访者充分在其世界观里建构仪式的知识体系,研究者要做到的是在此知识体系里面发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世界乃至不一样的自我。研究者在被采访者叙事之时,应该是一个对仪式和活动“未知”的听众,因此聆听的技巧相当重要。研究者要专注于体育行为、仪式、活动本身,在谈话的过程中紧紧跟随被采访者的故事,避免先入为主和定势思维特别是潜意识里“专家学者的自我”的影响。所以,笔者建议在谈话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做到几点来维持“未知”的态度:
2.1.1 避免对故事进行先入为主的假设。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往往会做大量的文献研究,以掌握当地的基本资料及体育活动的基本概况。这些资料是我们重要的参照体系,但并不唯一真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完善世界的知识体系,发现未知的人类文化及其意义。“未知”的态度恰恰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态度相吻合。因此,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者应该避免被固有的文本知识和经验所禁锢,更不应该在前人文本基础上进行预设,以影响田野过程中的判断。
2.1.2 接纳当地人。这似乎是所有田野工作中都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实际研究中依然有一些研究人员难以做到。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私人日记也显示出对当地人厌恶和排斥的情绪。这是因为每一个研究者在社会化过程中都建构起一个自我,我们根据自我的标准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对的什么错的,特别是在专家化的自我面前,一些研究者容易对当地人作出价值判断,既破坏了田野的氛围,又为达成田野的目标设置了障碍。田野当中,研究者应该表现出对异文化的兴趣及当地人的关注,避免站在专家的角度来套用观念并对当地文化作出价值判断。
2.1.3 在研究中合理发问。叙事技术强调引导当地人对活动的细节进行思考,并在恰当之处发问。比如在苗族独木龙舟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当地人对仪式的细节、活动的组织、民间的传说进行分析和归因,并在谈话中呈现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进行提问,澄清调查中的疑点[3]。
2.2 传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叙事学的哲学根源是后现代主义,其中受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较大。不同于单纯的生理与心理自然属性视角,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每个社会个体是由制度、历史与文化等诸因素共同建构结果。同样,传统与现代、优与劣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都是被环境和文化所建构的。基于此观点,传统体育只是作为适应特定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并无好坏之分。像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族群中广泛存在的镖牛,一度被认为是血腥的、残忍的身体活动,这些负向的标签,其背后的逻辑根基是不同文化体系差异。
认识一个群体的传统,更应该立足于该群体的历史和特殊性,特别是创造历史的人。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的缩影,对人的解读是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福柯认为,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非被发现出来的[7]。不同的学科“发现人”的方法不尽相同。体育史学更多的关注对体育运动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而体育人类学则更多关注基层人物,两个学科,一个关注大人物一个关注小人物,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通过对“小人物”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家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小人物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正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协同、冲突、交流,使得民间文化得以生存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更是如此,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是存在于乡野之间、在小人物的记忆、行为和生活之中,这些故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需要体育人类学工作者用脚去丈量,以致还原体育文化建构过程。我们在田野当中看到很多的传统的体育(或身体活动)可能确实出人意料,这些习俗和仪式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不道德或野蛮的,然而从社会适应的视角来看,却是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而不道德或野蛮等标签,也是基于不同环境与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建构起来的。
用主流的观点去审视传统体育,往往带有刻板的缺陷,因为主流的观点往往告诉研究者什么是有效和无效的身体活动、什么是有益和无益的身体活动,以致我们总是按照有无价值的二元标准去评价传统项目,忽视了当地人的观点。或者退一步说,文明作为副产品[4],很多情况下其价值都是内隐或未明的。正如目前对很多传统项目开发所遭遇的困境,用主流的技术对传统项目“升级改造”之后,使得这些项目面目全非,脱离了文化根基的传统项目在现代社会难以为继。因此,叙事技术帮助我们带着谦卑的态度去倾听他者的身体与叙事,体验我们不曾经历过的生命形式,帮助我们了解在传统文化建构与个体身体活动之间相互作用。
2.3 尊重他者的异质文化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我们发现社会大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但这种开放和接纳并非全面的,而是呈现出越是外化的差异越容易为他者察觉和接收,比如身高、体重、肤色等,相反地,心理特质、价值观等内在的差异,人们往往表现出较低的觉察能力和接纳程度。内化的特质差异也是造成一些研究人员在田野过程中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比如,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哈尼族传统节日扎扎节的时候就面临剧烈的文化震惊。一般认为扎扎节是一项祭祀下凡巡视天神的节日或农事节日。但在一些地方,扎扎节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形式,即节日期间伴以大量具有性意味的舞蹈和身体活动。这样的形式使得一些研究者心生疑问:这似乎与心中古朴醇厚的民俗并不搭边。事实上,这完全符合当地人的逻辑:年轻人通过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化妆及身体活动表演,显着“人”的存在和力量,以及对美的追求、生命的歌颂[5]。
人与人的天然差异包含外在差异和内在差异。但是绝大部分的差异是非批判性的、可兼容的。作为研究者,在观察当地人身体活动的过程中,要本着开放的态度去接纳这些非批判性的异质化。田野是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片田野是彩色的,我们需要用包容的眼光去审视它。所谓处处是田野,时时在田野,总有一些事一些人出乎研究者的意料,给其带来心理的冲击,只要我们用包容的心来审视他者的目光,终究能够融入这片田野。
2.4 用他者的眼光重新阐释体育文化叙事学的目标是让研究者在聆听他者的故事之后,跳出研究者文化体系重新诠释他者身体故事。该目标背后的逻辑依据是他者的行为存在着另一种逻辑的合理,即基于其生活环境、地方传统的合理。当然,这个重新诠释的过程是依靠研究者和叙事者协同完成,在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支持、提问和帮助下,让被访谈者叙说他参与体育行为、身体活动的故事,自由地表达他的想法。研究者在搜集各类信息之后,理解和对身体故事的换位思考、提升,以文本或其他的形式呈现叙事者的身体活动经历及其体验。
重新诠释体育文化的技巧,主要强调三点:第一是引导被访谈者针对其体育行为或参与体育运动的经历展开正反两面的讨论,引导被访谈者讨论没有此类活动及有此类活动之后生活体验的差异,以发现被访谈者在此过程态度和生活状态的改变;第二是对事件的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引导被访谈者去叙说身体活动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细节,包括参与者所穿服饰、所用器具、唱词、身体动作的细节及其意义,用参与事实作为文本呈现的依据,克服研究者对事件的不合理认知和归因;第三是提出创新性的问题,引导被访谈者多方面思考体育行为。与此同时,通过提出创新性的问题,引导叙事者调整叙事状态,把其注意力从过往过度关注的方面中抽离出来,关注其参与体育活动或身体活动之时的整体环境或过往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或意义,并反思这些因素对自身体育行为、想法的影响,呈现出该体育行为完整的文化意义。
3 小结
叙事技术与传统田野工作的访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获取当地人故事、分析其生活史及体育行为的意义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针对目前田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倡导使用叙事技术去参与研究,以期获得更贴近“当地人观点”的知识。叙事学方法的应用最终还是为了促进体育研究的发展,也响应了体育学科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从整体与实际出发的研究走向[6];在强调人文关怀的同时,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更好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1]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杨晓霖.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叙事革命:后现代“生命文化”视角[J].医学与哲学,2011(9):64-65.
[3]胡小明.体育人类学方法论[J].体育科学,2013(11):3-16.
[4]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11.
[5]岚峰.哈尼族“苦扎扎”节的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研究,1995(1):53-54+48.
[6]倪依克,胡小明.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J].体育科学,2014(12):3-7.
On the Statement Dir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 for Sport Anthropology
LIU Wenwo, etal.
(Zhaoqing Medical College, Zhaoqing 526020, Guangdong, China)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编号:2371SS16108。
刘文沃(1985-),广东新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