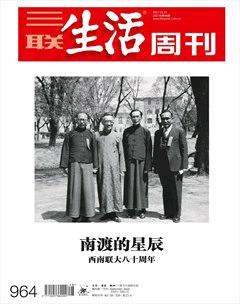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
钟和晏
卡巴科夫夫妇一再强调,他们的作品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人的状况,对乌托邦的欲望以及实现的不可能性。
当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在55岁离开苏联移居西方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绘画这一媒介本身。他觉得一幅画不足以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氛围,开始建造占据整个房间的“整体装置”(Total Installation)。虽然达利和杜尚经常被认为是装置艺术媒介的开创者,但是在卡巴科夫的手中,整个房间成为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沉浸式艺术品,让他们相信正身处某个不同的世界,某个不同的时刻。
他1985年的整体装置《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的人》就是这样的例子,目前正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与其他五个“整体装置”一起展出。作品重建了一个大概3米见方的小房间,里面极其凌乱:地板上的碎石瓦砾和一双破旧的男鞋,一张没有床垫的单人钢丝床靠着墙壁,黄色条纹被子胡乱地摊在床上。墙上有一幅画,描绘了“东方一号”宇宙飞船从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塔上空飞进太空的庄严时刻。其实观众想要进入这个房间是不可能的,匆匆钉在一起的墙板挡在面前,只能从墙上狭窄的缝隙看到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卡巴科夫装置艺术作品《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的人》,1985年
除了这幅画,乐观的、精神蓬勃的苏维埃宣传海报贴满房间的三面墙壁,一种红色的基调弥漫其中。正中央有一个奇怪的弹簧和皮带装置从屋顶悬挂下来,像是凑合做出来的飞行弹射器,下面一块木板搁在两把椅子上。弹射器上方的天花板上开着一个大洞,让人意识到这间卧室的主人已经被发射进入太空,他已经消失了。
这件作品的诞生来自伊利亚·卡巴科夫居住过的莫斯科集体公寓,一座四层楼房的顶层。他这样叙述他的邻居、建筑工人尼古拉耶夫的故事:“两年前,他在我们的集体公寓里被分配了一间房间,他的房间在我右边。我不太认识他,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工作,他总是独自生活,也不太情愿让别人进入他的房间。他生活非常糟糕,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睡在没有床单的折叠床上。他用海报而不是壁纸贴满墙壁,他说这样会便宜些。”
“有次我去拜访他,他的房间里到处是散乱的图纸,其中一些粘在墙上。我以为它们是用在他的建筑工地的。拐角处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我们的街道和公寓的模型,我问他为什么有一条金属带附在模型上,并从公寓屋顶向上指引着。他突然说,这就是他未来飞行的轨迹……”
可以说《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寓生活的寓言,作为发射的必要条件,主人公为自己设定出逃离这种生活的技术解决方案,不是到任何地方,而是直接通向天堂。就如伊利亚·卡巴科夫自己的阐释:“这是对逃避、恐惧和飞翔的普遍性隐喻,一个人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但是可以让救赎成为可能,把自己从孤独中拯救出来。”
卡巴科夫夫妇的许多作品都涉及类似希望的概念,希望寻找更好的东西。他们一再强调,他们的作品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人的状况,对乌托邦的欲望以及实现的不可能性。可以说,每个社会都在努力达成乌托邦,苏联只是迄今为止最显著的例子之一,试图从公寓房间飞进太空是徒然的尝试,对乌托邦的寻找也许也是如此。
卡巴科夫夫妇是他们这一代中最著名的俄罗斯艺术家之一,也是被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作品的第一批在世艺术家。从10月中旬开始,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与莫斯科国立冬宫博物馆、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等合作,为伊利亚和艾米莉娅·卡巴科夫夫妇举办第一个在英国的大型展览“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展览总共展出了大约100件作品,包括绘画、素描、模型和装置等,来探讨这对开创性的夫妇在国际观念艺术中的地位。
伊利亚和艾米莉娅·卡巴科夫分别于1933年和1945年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Dnipropetrovsk),他们是远房表亲。1973年艾米莉娅迁往以色列,随后又去纽约定居。1987年伊利亚也搬到了西方,先是奥地利,后来也到了纽约。两人从1989年开始共同创作,1992年结婚。从那时起,他们一起合作了大约700幅画作和200多件装置。

卡巴科夫夫妇在他们的画室中(摄于2013年)
在苏联的时候,伊利亚·卡巴科夫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是1965年“艺术家联盟”的成员,作为一名儿童图书插画家和官方艺术家,在他的官方工作室里制作他的“私人”作品,向居住在斯雷腾斯基(Sretensky)大道上的艺术家朋友作展示。
移居纽约之后,卡巴科夫夫妇的整体装置仍然借鉴了苏联的视觉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叙事传统,涉及被操纵的空間、讲故事的想法以及乌托邦、梦想、恐惧等普遍主题。他们的做法像是一种炼金术:把悲伤、内疚和愤怒等情感变成虚构的情节和叙述,通过艺术来表达心灵的嬗变,比一般的西方观念作品更具隐喻性。
展览的标题“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来自伊利亚·卡巴科夫对俄罗斯抽象艺术家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研究,文章发表在《A-YA》杂志1983年的某一期上。卡巴科夫在隐喻式的写作中想象马列维奇是学校校长,选择前往夏令营的学生,只有少数最好的人将被带入,只有马列维奇知道是谁。
艺术家及其作品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它们如何被未来的新观众、新艺术评论家、新收藏家和新策展人接受和理解?这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是让他的作品在今天被理解和接受,还是希望它们能够生活在明天,其中的区别又是什么?
展出的总共六个“整体装置”中,1990年创作的《迷宫/我母亲的专辑》属于伊利亚·卡巴科夫最具自传性的个人化作品。装置的基础是一条迷宫般回转的昏暗走廊,裸露的灯泡从天花板悬挂下来。走廊和天花板的上半部分呈灰色,下半部分覆盖着红褐色的涂料。一些明信片、照片和文字挂在没有玻璃的镜框中,挂在走廊墙壁上,外观看起来都一样。照片是伊利亚的叔叔、一位专业摄影师拍摄的,拍的是亚述海边小城市贝尔丹斯克的风景,公园、花园或绿叶林荫大道等。每张照片下面一段文字,叙述了伊利亚母亲的生活故事。
他的母亲贝莎·索罗杜克哈娜(Bertha Solodukhina)是犹太人,出生于1902年,1987年去世。她的一生跨越了苏联自1917年革命一直到解体前的社会变革动荡时期,从俄罗斯革命、内战、1921至1922年的饥荒,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性和重建政策。
她一直作为女佣来谋生,努力抚养儿子长大,忍受着反犹太人虐待、无家可归和不稳定工作等种种不幸境遇,只是为了生存下来而苦苦挣扎。在她去世前几年,伊利亚说服她写下了自己的生活回忆录。
在《迷宫》装置中,单调的布置、走廊的状态、微弱的光线、一个沉闷省会城市的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在以无言的形式表达出严峻的现实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的苦难和绝望的气氛已经包含在其中,被昏暗走廊的浓厚氛围加强着。
伊利亚·卡巴科夫曾经说过:“当我回头看我过去的生活,一个最基本的图像就是大量的走廊:笔直的、悠长的、短小的、狭窄的、转折的等等。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的光线都很差,总是没有窗户,两边是关闭或者半开的门。我敲门,门打开了,我问了一些问题——‘好的,等一下。门又关上了。我站在走廊里等待,不能离开。这种一动不动的状态不会结束,好像永远会继续,好像时间已经停止了,我生活中的所有走廊都与这种无尽的折磨时刻有关。”
这是他萦绕于怀、不断重复的生活回忆:年少时在学校里,他站在走廊等待学术委员会对他“恶作剧行为”的惩罚决定。成为画家之后,他在出版社等待主管人分配工作。在贝尔丹斯克城市执行委员会的走廊上,他等待与主席会面,让他们允许他母亲进入合作社……当然也有“好的、快乐的”走廊,比如艺术学院宿舍里的宽阔走廊,还有集体公寓里温暖美好的走廊。
在《迷宫》装置中,重要的是观众通过走廊的过程。他进入迷宫中,只身留在那里,他的移动速度取决于他是否愿意阅读画框中的文字。走廊形成两个螺旋形:一个从入口处开始朝向中心移动,另一個从中心向外展开,迷宫中心处是一个面积只有1平方米的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里安装了一台磁带录音机,伊利亚·卡巴科夫正以低沉的嗓音演唱着俄罗斯的浪漫歌曲。观众刚开始进入迷宫时听不到什么声音,随着向中心移动,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观众也许会期望看到唱歌的人,但他看到只是一个小房间,那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除了垃圾和忧郁的歌声之外,迷宫的中心什么也没有。